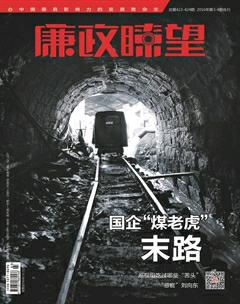鸭绿江对岸
琅琊王生
一 条鸭绿江,将长白山脉一分为二。鸭绿江西边是中国,东边是朝鲜。吉林省临江市与朝鲜中江郡隔江相望。
辗转国内许多城市多年后,不免对临江这座边境小城十几年的生活又心向往之。那十几年间,目睹并经历了生活在这条界河两畔的人们发生的许多事情,任何时候回味起来,都别有一番滋味。
一
几十年前,鸭绿江两岸的人们每天清早都会听到慷慨激昂的广播。不同的是,鸭绿江西岸的大喇叭传出来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中文声声穿云裂石;而东岸的广播讲的却是“金日成思密达”,朝语阵阵惊天动地。
几十年后,已经听不见大喇叭声音的临江市业已发展成为居住着十余万人口的旅游城市。而隔江相望的中江郡依然沐浴在它每日如约而至的广播,维持着它几十年前的色彩。
临江居民都说自己已经习惯了每天清晨被异国的广播唤醒,那是他们最熟悉的“铿锵有力的起床号”。一样的嗓音,一样的语调,一样的那么不容置疑。每天上午9点,“铿锵有力的起床号”便成了“催促上班的号角”。临江居民笑称“只需听广播,从来不对表”。
每年隆冬,是临江最带劲儿的季节。大雪纷飞数日,山舞银蛇。厚厚的积雪将沟沟壑壑填得平整。这时候是孩子们最能撒野的时候。但是“欣赏长白雪景,或是在鸭绿江上滑冰,必须在太阳下到猫儿山之前收拾回家”。这是长辈们对“玩疯了”的孩子们的忠告。因此,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只要太阳一开始跟临江市躲猫猫,大家就不约而同地跑回家里。
二
鉴于60年前“鲜血凝成的友谊”,鸭绿江有远比黑龙江等河流更为特殊的待遇,中朝两国国界不以河流主航道划分,而是只要互相不登岸就算不越界。
少年时代的男孩,最为顽皮,总是一心想到鸭绿江对岸去看看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
从临江市往鸭绿江上游回溯几十公里,平均三四十米的开阔江面逐渐收缩为十余米的峡谷,在几个急转弯的地方甚至只有三四米。生性淘气的中学男生最爱冒险。每年暑假,他们总是不约而同来到那个急转弯,换好一身行装,后退十几步,一路助跑之后,飞身起跃到峡谷对面。匍匐在蒿草间,行走在青纱帐,“半日出国游”就此开始。
朝鲜的女人们挺勤快,每天总有三三两两的女人怀抱军绿色的盆子,来到江边浆洗着军绿色和藏蓝色的衣物。她们身后,总是跟着一群咿咿呀呀的孩子,从五一到十一的漫长时间里,那些孩子从来不穿衣服。
西岸穿得花花绿绿的孩子有时悄悄嘟囔:“他们都不穿衣服,多自在,我也不想穿。”多半时候,看着毫无色彩的同龄人,西岸的孩子又不免心生恻隐,于是带上自己不穿的旧衣物和妈妈多余的洗衣粉,央求河边的游船开到河对岸,嘴里讲着含混不清的朝语,手里比划着稚嫩的手势,把船上的东西一股脑的丢给那些孩子和他们的妈妈。
到了深秋,一天凉似一天。第一场雪降下来之后,鸭绿江西岸的农田里,饱满的水稻被压折了腰,玉米棒子挂满干瘪的秆子;而对岸的水稻却直直地指向天空、玉米杆子在寒风里瑟瑟发抖。
“都是同一个育种基地出来的种子,一样的化肥,咱们的粮食吃不完,他们就得挨饿。”临江市四道沟镇的农人每年秋收时候都不免“恨铁不成钢”地叹气,“春天野草长得比庄稼还茂盛,怎么能指望秋天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