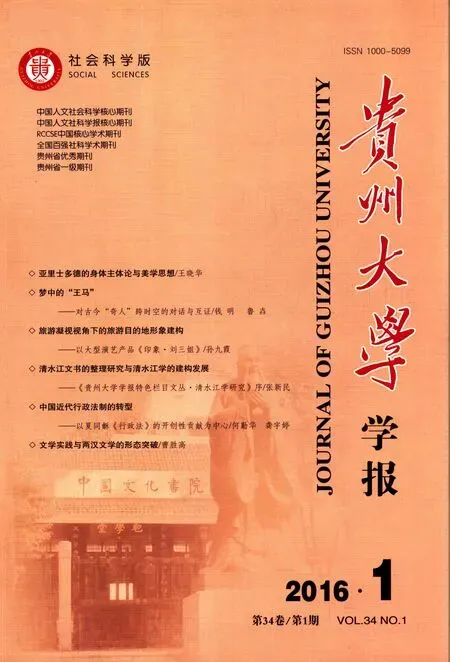化如“灰烟”了无痕——贾宝玉死亡符号探析
张劲松
(贵州大学 科技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化如“灰烟”了无痕
——贾宝玉死亡符号探析
张劲松
(贵州大学 科技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红楼梦》中贾宝玉一直在叙述着他独特的死亡观念。这种话语由一组独特而诗意的死亡符号——“化灰化烟”的不断叙述构成。它充满着一种激情的想象和灵性的痴意。这种死亡符号体现了贾宝玉独特的死亡心态,既来源于他的特殊性情,更是对大观园这片理想世界的净土乐园的固守;同时也象征了作者试图摆脱死亡的焦虑,在暗夜缝隙中呼吸新的空气。
关键词:《红楼梦》;贾宝玉;死亡符号;理想世界;净土;
一、贾宝玉的死亡叙述
维特根斯坦尝云:“死不是生命的事件,人是没有体验过死的。”[1]96死是人无法体验的滋味,不过,人们还是可以谈论和叙述死亡,通过死亡观念的能指符号获得某种安住。贾宝玉有一种迥异他人的生命意识,特别是其关于死亡“化灰化烟”的叙述。在这个钟鸣鼎食的大家庭中,这种话语透着浓浓的激情和灵性的超脱。如果说“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那么,宝玉恬淡而充满想象性的死亡叙述符号则构成他对彼岸世界的一种独特观照。[2]1鲁迅尝云:“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3]243可谓中肯。然宝玉所“领会”者何?其话语表现者亦有显示乎?鲁迅之意暗示了宝玉的独醒,那么“化灰化烟”的死亡叙述符号正好是此种领会和人性苏醒的凸显。
宝玉自我生命显现其实是很特殊的。表面上天天沉醉儿女柔乡中,诗酒宴会,无忧无虑,可他居然早对死亡有一种伤感却喜悦的期待,这在传统中国是很少见的。因为儒家一直否定对任何不可知的彼岸的渴望。在死亡的叙述中,宝玉最倾心于“化灰化烟”的符号想象。他最早说到死后的情景就是“化灰烟”。小说第十九回袭人欲“箴规”宝玉,提出要他今后改正的几件事。宝玉就忙笑道说:
你说,哪几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亲姐姐,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哪里去就去了。[4]271
这是小说中宝玉第一次描述他死亡的象征符号“灰烟”。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希望在姐妹们未散之前化去。一直到第一百回他听说探春要远嫁,他依然绝望地说:“这日子过不得了!我姊妹们都一个一个的散了……为什么散的这么早呢?等我化了灰的时候再散也不迟。”[4]1409可见这个心思一直未变;二是描述“化”的过程,即在与身边女儿们相守之后,先化为“飞灰”,因“灰”尚有迹,故再化为“轻烟”,随风散去,无影无踪。这是宝玉对于死亡的“疯话”般的诗意叙述和想象。飞灰和轻烟似乎消解了死亡的恐惧,而产生出对死的欢喜。在整部小说中,宝玉几乎丝毫不避讳关于这种死的话谶,而且常常说得激情满怀,诗意无限,但也暗暗让人心惊。第二十二回宝玉又一次谈到“灰烟”的死亡符号:湘云因黛玉事气恼,宝玉急了说:“我倒是为你,反为出不是来了。我要有外心,立刻就化成灰,叫万人践踹!”[4]305为表白心迹乃以死去“化灰”为证。由此亦可推测,以“灰烟”化去的死亡观念大概是经常徘徊在宝玉脑海中的,否则他不会常常脱口而出。因此,有人说“宝玉是带着死亡意识去存在的人”[5]。
第三十六回他在对袭人批评历来的“文死谏,武死战”后,突然给自己描绘了一幅自己死后得到众女儿泪葬的画面:
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 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4]493
世间女儿爱哭,故由“千红一窟”的泪水之河让他的尸首漂起来,送到幽僻之地,再“随风化了”。宝玉还是惦记着泪葬后的化去,他似乎急切盼望着这个“死的得时”的“泪葬”的到来,因为他能得到女儿们的泪,因为这些泪,他感觉没有虚度此生。这“化灰化烟”含蕴了多少人世的惘然和伤感呢?宝玉对于如此浪漫的“泪葬”恋恋不舍,此回中他听到龄官和贾蔷的话而痴起来,又对袭人等叹道:
“我昨晚上的话竟错了,怪道老爷说我是‘管窥蠡测’。昨夜说你们的眼泪单葬我,这就错了。我竟不能全得了。从此后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罢了。”袭人昨夜不过是些玩话,已经忘了,不想宝玉今又提起来,便笑道:“你可真真有些疯了。”宝玉默默不对,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伤“不知将来葬我洒泪者为谁?”[4]495-496
宝玉虽悟得“人生情缘各有分定”,但内心还是盼望死后有泪葬的知音(洒泪者)。如果说宝玉对袭人和湘云说的“化灰化烟”以及“泪葬”还较温情和浪漫,如一个性情中人的幻梦,那么,他在第五十七回对紫鹃的叙述则说得很沉痛。值紫鹃情辞试宝玉后,他对黛玉定亲之事很敏感,又将“灰烟”死亡叙述想象到极致:
一面说,一面咬牙切齿的,又说道:“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还可凝聚,人还看见,须得一阵大乱风吹得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一面说,一面又滚下泪来。[4]806
在这里,宝玉又一次详细描绘了他死亡的过程:死——灰——烟——散。死亡的叙述呈现了递进式的逻辑推进,从有形的灰烟终至无影无踪消失于人间。这种死后极致的自我符号显现了宝玉心灵的绝望。也许是他预感到和黛玉的悲剧结局,故死亡的叙述已经不是欢欣而是透着绝望,灰散烟吹,自我彻底消失。“我立刻死了”看似轻生其实是留恋,但当紫鹃表示只是担心林姑娘时,沉痛立即又变得喜悦:
宝玉笑道:“原来是你愁这个,所以你是傻子。从此后再别愁了。我只告诉你一句趸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4]806
这里的特异处和前几次颇不同:先前他的“化烟化灰”所指不过是自己,现在却谈到黛玉和其他女儿“一起化灰化烟”。这就是宝玉“化灰化烟”死亡叙述符号能指的最终所指之意:既是宝玉对爱情忠贞的象喻,同时也让死亡在嬉笑间成为一种趣味的玩话。他对林黛玉就说得很直接了,因为他的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以黛玉之生为前提的。
宝玉“化灰化烟”的死亡符号叙述在全书中出现多次,其所蕴含的意味非常值得探讨。既然“心智的生命以符号为基础”[6]239,这种特殊的死亡符号叙述自然与宝玉的死亡心态和想象密切相联系。因此,关注宝玉特殊的死亡表述固然重要,但深度挖掘内中因缘,即此种死亡符号出现的复杂原因和个体自我对死亡的独特领悟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二、“化灰化烟”的死亡愉悦
胡兰成曾说中国人对于死亡的态度是“豁达而激情”的[7]80。宝玉倾心于“化灰化烟”的死亡叙述,既和他的符号自我——其独特性情有很大的关系,也和《红楼梦》的理想世界的构思密切相关。两者组成宝玉独特的死亡愉悦的独特心态。
宝玉的死亡符号首先是他个体性情的反映。他出身不凡,是“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的贵公子。既生而不凡,故行为话语皆脱俗超拔尘世。这是他的禀赋和天分,更是其符号自我的先天文化之气。如《西江月》词之明贬实褒的“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实狂。行为偏僻性乖张”等。宝玉心灵符号自我的形成是很独特的:他从小被史老太君宠爱,生活在锦衣玉食之中。长于贵族红楼,养于妇人之手,又长期游戏于少女堆中,遂成就了他灵气与痴性的凝聚。因为他从小就和身边的脂粉丫鬟相处,对女儿钟爱体贴,得“怡红公子”之号。他喜欢“调脂弄粉”,常和丫鬟们一起“淘漉胭脂膏子”,因此染上“吃人嘴上的胭脂”的嗜好。(第十九回)宝玉还有一个“爱红”的毛病,书中未详叙,大概喜欢穿女儿红装吧。他看得太多了,叙述世间女子的变化也最透彻;
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4]833
宝玉死亡叙述的对象绝不仅是自己,也针对身边的女子。女子如水之灵气透净陶冶了他的气质,故只有面对女儿们,他才有一种期待死亡的喜悦和灵性表达。 宝玉虽托身这样的“诗礼簪英”的大家,生活悠裕,然却属于体质柔弱之人,这种体质的人一般都有一颗至情至性的温柔心灵,第六十四回便这样叙述宝玉夏日饮茶习惯:
说着,芳官早托了一杯凉水内新湃的茶来。因宝玉素昔秉赋柔脆,虽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将茶连壶浸在盆内,不时更换,取其凉意而已。[4]909
书中写到他“禀赋柔脆”的地方还很多,如第十三回秦可卿死了,他便“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声,直奔出一口血来”[4]176。这样柔弱的身体,心灵必然是极其敏感细微的。他是贾府中男人唯一有“兜花葬水”举动的。他的“无事忙”就是对女儿们的体贴入微与“做小俯低”的细心伺候。宝玉长期生活在女儿堆中,但并未成为冷子兴所说的“色鬼”,却成为闺阁中的良友、脂粉堆中的知音,这就是第二回雨村所说的“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4]30。小说中曾谈到他的“意淫”,则是其情痴的象征,而其化灰烟的死亡符号未尝不是这种情痴般爱欲的升华活动。西哲蔼理士云:
在性心理学范围,所谓升华包括两点,一是生理上的性冲动力,或狭义的“欲”,是可以转变成比较高尚的精神活动的一些动力,二是欲力既经转变,就不再成为一个急迫的生理上的要求。这样一番转变,虽非不可能,却是不容易的,也不是亟切可以期望成功的,并且也许不是人人可能,而只有少数神经组织比常人为细腻的人才真正可能。[8]506
宝玉恰好就属于“少数神经组织比常人为细腻”这一类人物。贾府中除了宝玉,没有第二个人有真正生命意识的思考,更勿论对死亡有如此超脱的表述。他读书奇特,虽然也读《四书》这样的正经书,但却专好奇书杂笔。小说中尝借宝钗之口谓其“杂学旁收”。这些“杂”塑造着他独特的痴情性灵。大观园题诗,他的诗就比那些头巾气的清客们好多了。他又特别喜欢佛道之书,尤其浪漫的《庄子》,常常细读玩味。《庄子》至乐篇中庄周对待死亡“鼓盆而歌”的喜悦态度对他肯定产生了暗示*余英时说他“最喜欢的古人是阮籍,最喜欢的古籍是《庄子》”。见《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红楼梦的两个世界》,189页。。而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的生命哲学与宝玉化“灰烟”而无迹的想法确有相通之处[9]271。庄子是春秋时代最有灵性的文人,《养生主》篇以“适来适去”的“安时处顺”态度看待死亡,而宝玉亦将死亡视为愉悦的解脱,他是“无成于毁,似悲实喜”[10]。
其次,“化灰化烟”的死亡叙述符号还蕴含了对大观园这个理想的干净园地的留恋和追求,即达到与女儿们的“共生共死”[11]123。按照余英时的说法,《红楼梦》写了两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一个是肮脏的现实世界,一个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净土。大观园的女儿世界正是这个理想的代表。宝玉满怀激情地展开死的想象叙述,正是这种理想的涅槃:
这样的死,不但不是理想世界的幻灭,而且恰恰是理想世界的永恒化。因为只有如此,才真正彻底的干净,再无被现实世界污染的危险。第二十二回黛玉为宝玉的禅偈续上两句:“无立足境,是方干净。”作者的深意是值得我们细心体会的。[12]80
“干净”是这个理想世界的象征符号,对于宝玉的死亡叙述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塑造。第二回宝玉曾说过:“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4]28学者们长期一直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但如果站在理想的净土乐园这个角度看,就很容易明了。大观园的女儿世界是干净的,闺阁之外的“男人世界”是“浊臭”的,甚至那些“文死谏,武死战”的也不过是“浊气”之涌而已。因此,寻找一方干净世界,留恋此净土乃是宝玉的自觉意识,与女儿们一同干净地死去或自己干干净净地化去。《红楼梦》中宝黛二人一体“遥遥知意”,而黛玉《葬花词》中名句“质本洁来还洁去”,正好指引我们进一步认识宝玉死亡心态的路标。第二十三回宝玉遇见黛玉葬花,黛玉云:
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来,撂在那水里。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呢。”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遭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它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4]325
“随土化了,岂不干净”乃是黛玉宁愿葬花而不愿花随流水遭污的重要原因,正所谓“一杯净土掩风流”。“随土化了”不也是化为烟灰吗?宝玉也怕将落化践踏了,故“抖在池内”。但黛玉则欲更彻底地使其干净。在《红楼梦》中只有黛玉说了与宝玉相似的“化了”的话,这并非偶然的。甚至宝玉的死亡想象或许也是受到了黛玉的暗示,也未可知,两人确是前世的知音。葬花虽是明代唐寅的发明,但黛玉的想法却是“土化”不留痕迹,这就超越了前人。宝玉的死亡心态也同样如此。所以他很欣赏《寄生草》词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干净。黛玉续其禅偈有“无立足境,是方干净”之语可谓“化灰烟”的最好注解。其实宝玉亦非完全没有死亡的焦虑,第二十八回他听到黛玉唱《葬花吟》就“恸倒山坡之上”。但他不是恐惧死亡本身,而是忧心大观园女儿们的“斯处、斯园、斯花、斯柳”也必然要随着无法逃避的死亡的逼近而消失。因此,他的性情“只愿常聚”,同生共死,不愿一刻分离。若不能如此,则宁愿死在姐妹们的前面,让她们泪葬了他,而他则化灰烟而去,永久保留那份理想和纯真的气息,正如胡兰成所云:“有的只是满满的浩然之气,像贾宝玉对眼前诸人都是难舍难分,只愿相守到他死了,化为飞灰,然后可不管了,化为飞灰尚有痕迹,要化为一股气,吹得无影无踪。”[13]120这恰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真意。宝玉前世乃一石头,被空空道人携入红尘,本是人世间的过客,故不留行迹于浮尘中。他的无影无踪的死亡标记就是一种诗意栖居后的灵性想象。因为“历史的消息有灵气”,它决定了宝玉对于死亡符号的叙述和选择。他最后的出家其实也基本完成了这个宿愿,他终于隐肉身于人间了。
虽然宝玉有这种化灰化烟的不留行迹的死亡预想,然而他似还不能彻底忘情人间,如他还说死后给黛玉驮一辈子碑。生命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宝玉才有了去得干净的“化灰化烟”的死亡符号。它使生命成为艺术,这是宝玉死亡符号的内涵,他希望永远守住这份灵性的生命和纯净的乐土。皮尔斯所说的“没有生命就没有符号”对于宝玉的人生是再恰当不过了[6]270。宝玉“化灰化烟”的浪漫激情象征了他对于死的豁达的自觉及对传统的死亡文化表述的某种突破,它的文化价值何在?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三、“化灰化烟”的符号意义
“《红楼梦》写贾府人家就是一个人世的风景,但已是宋儒以后的拘滞的家庭了。”[7]74“化灰化烟”的死亡叙述对于宝玉而言,是对这种“拘滞”的摆脱,“直视骄阳”,从而寻找生命的灵性意义。尽管中土的死亡文化中这种“化灰烟”的意识并非曹雪芹首创,但依然使小说闪烁着文化的光芒。
首先,宝玉化“灰烟”而去,符号所指对着伦理家庭传统的背离,意味着他“拒绝生产,选择断子绝孙,‘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11]128。这在传统社会可谓罪不可恕。《红楼梦》中,贾母这个享福人象征着中国世俗所艳羡的子孙满堂,宴会游玩,福禄寿全;贾敬的修道则表现着中国道家希图肉体长生不老,从容享受食色之乐的不死的理想;贾政逼宝玉获取功名,则代表儒家士大夫阶层对于获取功名利禄的人生最高理想的希冀。但宝玉的化灰烟则使得这福(多子多孙)、禄(功名富贵)、寿(长寿)的三大幸福都消失了。同时,“化灰化烟”的死亡准备与中国人千方百计包裹和保留死者躯体的习俗相背。对此,李劼分析得最好:
因为渴望身体的永恒,列祖列宗的价值共在和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便构成中国人的血缘宗教和伦理道德。既然身体的永恒和血缘的绵远是不死的象征,那么延年益寿和生儿育女就不啻是伦理的规范,而且还是心理的自觉。[11]120
中国文化一方面重生避死,但又宣扬忠臣的愚忠和烈女的烈死。而宝玉的死亡准备对这个也抛弃了,第三十六回他就批判了那种“浊气一涌”只顾“邀名”,“图汗马之劳”的“文死谏,武死战”,谓之“皆非正死”。[4]492“人谁不死?只要死得好。”在宝玉心中,所谓“好”的死就是能够和如水般的女儿们相处一世,服侍她们,然后干干净净地“还洁”化灰烟而去。以此而言,宝玉的死亡话语是冲决罗网的了。小说最后,他果然悬崖撒手,隐身红尘。如果说“文化是一种惯例”[14]141,那么宝玉的死亡叙述就是对这种惯例的打破了。
其次,不断的“化灰烟”的言说与想象也标记着对传统死亡价值取向的重新界定,即死亡是生命的必然过程,人是向死而生。表面上无忧无虑的大观园的女儿国,终究不能掩埋一个痛苦的真相:宴席无论多么豪华,都会散去,如一个丫鬟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宝玉死亡的“灰烟”让人感到希望的如灰如烟,显示出文化的“焦虑感”。但小说的价值取向恰好在于宝玉以“化灰烟”的愉悦又超越了此种“焦虑”。中土历史上的文人只有屈原是主动自杀的,但那是在异常痛苦煎熬后做出的选择,而其自杀,乃因“美政”不能施行,毫无愉悦的激情。中国历代临终绝笔诗文中,多数较为悲凉,即使对死亡很旷达的陶渊明,其《拟挽歌》《自悼文》等也还透着“人生实难,死如之何”的哀痛。惟有宋代和尚的偈子倒充满了类似宝玉的激情,如被诬处死的临邛僧:
为无赖士人胁持,诬以不轨,僧下狱乃口占云:“宿业因缘人不知,如今啐啄与同时。今生欢喜偿他了,来世分明不欠伊。梦幻色身从败坏,闲田虚树已生枝。休休休也归家去,石女怀胎产一儿。”[15]1414
“今生欢喜偿他了,来世分明不欠伊”与宝玉在与女儿们缘尽后干净化去的心态确实很类似,而且还包含有一种“一切时处”的安住心态。“艺术的目的便是为人的死亡做准备,耕犁他的性灵,使其有能力去恶向善。”[16]41宝玉谈论着他的死亡准备,剥开了伦理社会对于死亡的层层“遮蔽”,《红楼梦》才有了灵性荡漾的大观园。中国文化总体上是一种喜悦的“乐感文化”,宝玉化“灰烟”与“泪葬”的叙述其实也很符合传统的思维:“中国人这对于死的达观而激情,一种大的无可奈何,十分的现实而有万古的惘然,最有诗情的,而皆造型在丧礼里。”[6]80而宝玉的丧礼就是女儿们泪水流成的“泪葬”,青春而艳丽,绝不悲哀;纯洁和缠绵,毫无俗气,可谓死亡叙述的绝唱。尤其重要的是宝玉通过“化灰烟”这个独特的死亡符号再三叙述,最终实现了类似黛玉的“还洁去”,成就了“本真”的自我,而“本真的人,不再歪曲自己的定命,他将做出一种高贵的顺从的姿态,甚至是出于意志的自觉选择,人由此获得了去‘死的自由’,这就是说,他获得了面对死亡的自由”。宝玉真正是向死而生了。[17]53
再次,中国文化一直讳谈死亡,死亡叙述一直没有真正进入思维和文学领域。除庄子外,先秦诸子敢于谈“死”者很少。孔圣一句“未知生,焉知死”(先进篇)就理性地回避了人间的最终真相。而《红楼梦》却通过宝玉的死亡言说,重续了传统文化河流中的死亡符号。这是明清小说中主人公大谈死亡的第一部。此前的《金瓶梅》《水浒传》《姑妄言》等都未能如此。诸家只有庄子喜论生死,并以生为赘死而乐。如其《至乐》中髑髅所言之“南面王之乐”。庄周“无生,无形”之谈与宝玉的飘渺叙述很相似,但毕竟无化灰化烟之谈,且后之道家追求肉体的修炼成仙,恰与化灰烟相反。“灰烟”即空,此种死亡意识似更受到佛家的启发,盖佛徒本以“身心皆为幻垢”为本。[18]81死后火葬,本就有“诸幻尽灭”之象。尤其《圆觉经》所言之“得无所离,即除诸幻。譬如火两木相因,火出木尽,灰飞烟灭”。[18]70“诸相犹如虚空”等[17]140。“灰飞烟灭”则诸幻皆离,宝玉希望不留痕迹,也就是不留人世的幻象之意,达到佛家之“生死涅槃,犹如昨梦”境界[18]。这恰是整部小说的解脱之道。小说第一回空空道人的“因空见色”就是用《心经》“色既是空,空即是色”的“五蕴皆空”之说[19]213。“空”是整部《红楼梦》“大旨谈情”背后的符号所指。第五回宝玉游太虚幻境至迷津,警幻就曾告诉他“中无舟楫可通,只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撑篙,不受金银之谢,但遇有缘者渡之”[4]91。此处的“木掌舵”和“灰侍者”,既是《圆觉经》“木尽灰飞”之喻,亦如《庄子》“形如槁木,死如死灰”之比。“灰烟”即是“空”之喻。宝玉的死亡叙述既是对肉体的抛弃,同时也是对尘世的绝不留念。但化灰化烟的叙述对佛教亦有所发扬:佛经以“解脱”为根,“火葬”是烧去三世之业,但毕竟未将死亡作为生命的滋味来咀嚼,且此种体验由对女儿们之情而种下,此乃宝玉所独有。且佛教徒尚追求金身、舍利子这些“有形”的痕迹,而宝玉的死只是逝如灰烟了无痕,这是超越佛家的。可谓“非儒非道非释非耶稣基督,端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今中外独一无二”![20]71《西江月》称其“似傻似狂”,其实他的“疯话”均是正话,伤痛之极语。而其愈是富有想象性,则愈蕴悲凉。化灰化烟不留痕迹于世间,固然豁达,然其内囊却是绝大的悲哀。也许只有鲁迅的“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的话能够作为宝玉死亡疯语的最好解释。宝玉知道他只不过是这个浊世的过客罢了。
鲁迅所谓《红楼梦》出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21]128,勿论此话正确否,然贾宝玉关于死亡的叙述却是打破了传统的。几乎没有哪部作品像《红楼梦》般以主人公的身份缠绵执着于叙述死亡。中国文化哲学一直缺乏正视死亡的勇气和气魄,但《红楼梦》跳过了藩篱,它通过贾宝玉的死亡叙述,在传统文化中注入了新的生命。这部小说诞生于所谓乾隆盛世,但那并非一个健康的社会,腐朽之气已经在紫禁城的夕阳中飘荡,尽管宝玉不知出路在哪,但“对死亡的熟思也就是对自由的熟思。谁学会了死亡,谁就不再有被奴役的心灵,就能无视一切束缚和强制”[22]95。宝玉灵性自我依然了悟。第七十一回,贾府颓运已至,尤氏等说宝玉“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姊妹们玩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还是这样,一点后事也不虑”,没想到宝玉却马上想到死亡的解脱:
宝玉笑道:“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李纨等都笑道:“这可又是胡说。就算你是个没出息的,终老在这里,难道她姊妹们都不出门的?”尤氏笑道:“怨不得人都说他是假长了一个胎子,究竟是个又傻又呆的。”宝玉笑道:“人事莫定,知道谁死谁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遂心一辈子了。”[4]1014
注意,这里宝玉谈死亡都是“笑”着叙述的。宝玉并非无忧无虑,但他的“挂碍”居然就是喜悦地迎接死亡的来临,而且突然的死亡是可以让他“遂心一辈子”的安然。“一个人必须不断地想到死”,生活才能有序、从容[23]97。当然,宝玉化“灰烟”的死亡叙述,并非是对生命哲学的穷尽,毕竟“人们知道生命问题的解答在于这个问题的消灭”[1] 97。所以“死亡”的叙述永远在路上,“灰烟”化去固然不留痕,但并不会真正地消失,依然跳动在追寻人生意义的人们心中,比那些有形之物器还要永久,永久!
参考文献:
[1]〔德〕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M].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2]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全集出版社,民国三十年.
[4]〔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5]文一茗.红楼梦叙述中的符号自我.[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121.
[6]〔美〕迪利.符号学基础[M].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7]胡兰成.中国礼乐风景[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
[8]〔英〕霭理士.性心理学[M].潘光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诸子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86.
[10]胡兰成.禅是一枝花.[M].西安:长安出版社,2013:15.
[11]李劼.论红楼梦: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M].上海:知识出版社,1995.
[12]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13]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
[14]〔德〕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笔记[M].许志强,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15]〔宋〕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第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6]〔德〕塔可夫斯基.陈丽贵,雕刻时光[M].李泳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7]〔美〕辛格.我们的迷惘·卷下(一)[M].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8]圆觉经·卷上(二)[M].佛陀多罗,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9]心经[M].玄奘,译.南京:金陵刻经处,2007.
[20]王蒙.红楼启示录·卷上(二)[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
[21]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C]//鲁迅论文学与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2]〔法〕蒙田.蒙田随笔全集·上[M].潘丽珍,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
[23]段德智.西方死亡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钟昭会)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6)01-0166-07
作者简介:张劲松(1970—),男,四川三台人,博士,副教授,贵州省《红楼梦》研究学会理事,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特约研究员,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历史。
收稿日期:2015-09-15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6.0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