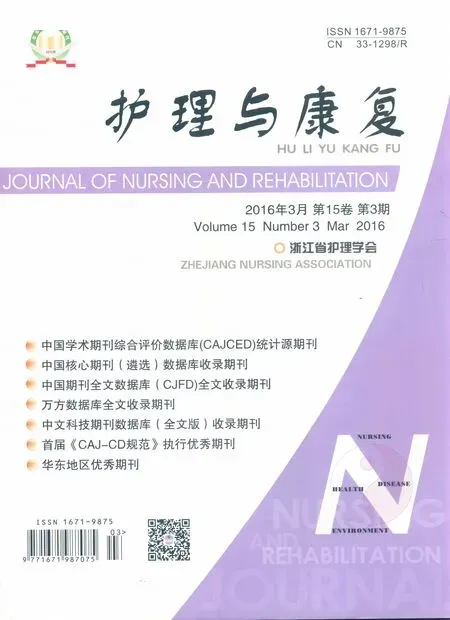医院安全文化的研究进展
·综述·
医院安全文化的研究进展
陈晓宇,黄丽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杭州310006)
关键词:医院;安全文化;研究;进展
doi:10.3969/j.issn.1671-9875.2016.03.009
医疗卫生保健行业存在较高风险,尤其在缺乏系统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安全文化时更为突出[1],医院安全文化[2]建设是预防负性事件、防范医疗差错事故和保证医疗护理质量的基础性工作。及时评估医院安全文化现状,了解不足和隐患对降低医疗风险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医院安全文化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本文结合文献将国内外医院安全文化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医院安全文化的概述
医院安全文化概念由Singer等学者于2003年首先提出,是医院文化的一个分支,同属于组织文化,可以理解为是将希波格拉底的格言“无损于患者为先(first do no harm)”整合到组织的每一个单元,注入到每一个操作规范当中,是将“安全”提升到最优先地位的一种行为[1]。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各大医疗机构对医院安全文化的研究趋向深入,逐渐形成共识:医院安全文化的建立是改善患者安全的潜在战略,通过改变组织文化来提升安全质量意义重大、效果斐然;医院安全文化的建立有赖于评估工具的选择,不仅提供了理解安全文化的方法,本身更是促进安全的一种措施,安全评估可以随时进行,及时发现隐患,不断干预预防,实现组织安全水平持续提升;医院安全文化的建设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可能仅通过某个层面、某个团体或某项措施来完成,是一个系统性文化建设,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完成。
2医院安全文化现状
2.1常用评估工具目前,已经公开发表的用于患者安全文化评估的问卷有9个:患者安全的组织途径(SLOAPS),医疗保健组织的患者安全变化(PSCHO),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患者安全文化调查问卷(VHAPSCQ),关于患者安全文化的医院调查(HSOPSC),安全文化调查(CSS),安全态度调查问卷(SAQ),安全氛围调查(SCS),用药安全自我评估(MSSA),医院输血服务安全文化调查(HTSSCS)[3]。9个问卷均采用5分制的Likert Scales(李克特量表),其中,7个是针对个体进行调查(PSCHO、VHAPSCQ、HSOPSC、CSS、SAQ、SCS、HTSSCS),2个需要团队一起完成(SLOAPS和MSSA)。SLOAPS、MSSA致力于患者安全所采取行为的程度评估,而其他7个主要测量受试者对患者安全不同方面的态度,调查内容条目广泛(从19个到194个不等)。在美国,HSOPSC、SAQ使用最广泛,PSCHO和VHAPSCQ使用也较频繁[4]。Sorra等[5]收集了美国331家医院2 267个部门50 513份报告,论证了测量工具HSOPSC的信度和效度,证明其可作为评估医院安全文化水平的测量工具。在我国,台湾地区以Dr Bryan Sexton医院患者SAQ为蓝本,完成适合台湾地区医院使用的患者安全文化评量工具。大陆地区,2009年陈方蕾等[6]对医院的护理人员进行有关患者安全文化评价的调查,并引入了SAQ,其后郭霞[7]、许璧瑜[8]分别在翻译SAQ和HSOPSC英文版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增删,制作出中文版的评估问卷。
2.2不同国家医院安全文化现状评估的结果
2.2.1土耳其一项针对土耳其中心城市科尼亚12家初级卫生保健中心180名员工的调查显示:HSOPSC的各个维度中,正面评分最高的是“部门内部团队合作”(76%)及“安全的总体感知”(59%),评分最低的是“事件报告的频次”(12%)及“对错误非惩罚性的回应”(18%)。87%医生、92%护士和91%其他医疗人员报告错误的频次不高,说明对错误没有进行及时报告和回应。与之前对美国58所规模类似的医院所做同样调研得出的基准数据比较[9],这次土耳其主要医疗服务区域的患者安全文化得分较低,42个维度里有34项都低于基准数据,如“事件报告频次”“对错误非惩罚性的回应”“管理者对患者安全文化的支持”等,认为患者安全文化是“好”或“完美”的人数比例也远低于基准数据(42%、76%),事件报告频次更是远远低于基准数据[10]。
2.2.2荷兰Wagner等[11]通过使用HSOPSC对荷兰45家医院3 779例患者进行安全文化评估。在“部门内部团队合作”这项得分较高,有较大改善空间的维度是“转床和交接环节”;此外,对医院内不同群体人员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医生、护士、药剂师、检验室人员等关于安全文化的概念理解存在差异,因此,促进安全文化还应针对不同目标群体的态度和观点。
2.2.3中国Nie等[12]通过使用HSOPSC,对15个城市32家医院1 160名医务人员(其中医生301人、护士722人、其他岗位人员137人)进行调查评估,结果显示,有3个维度的正面评分都低于60%,分别是“患者安全总体感觉”(55%),“对错误的反馈和沟通”(50%)及“人员配备”(45%)。“人员配备”正面评分低,说明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工作负荷大,现有的人员配备并不足够应付患者安全,特别是在一些综合医院,患者和医护人员的比例更大。
2.2.4沙特阿拉伯Alahmadi[13]通过对沙特阿拉伯Riyadh市13家综合医院223名医务人员关于患者安全文化现状评估的调查发现,对总体评分,60%的受访者勾选了“好”或“非常好”,33%选了“可接受的”,7%选了“不合格”或“差”;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管理者忽视了一再发生的安全问题,63%受访者表示“不会为完成更多工作而牺牲患者安全”,70%受访者认为“系统能很好地预防错误的发生”,33%受访者认为“更多严重的错误没有发生是因为巧合”,43%受访者指出“在本部门存在患者安全问题”,大多数医院的强项在于“组织性的学习/持续改善”“部门内部团队合作”“对错误的沟通和反馈”,大多数医院需要改善的维度有“事件报告”“对错误的非惩罚性回应”“人员配备”和“部门间的团队合作”。研究同时表明尽管普遍的观点认为管理行为要将患者安全列为第一优先,但管理行为通常只有在严重事件发生后才被驱动。这点和其他研究证明的大多数改善患者安全的尝试都是应对性而非前瞻性的观点不谋而合。
2.2.5美国Robida[14]对170名来自加利福尼亚和圣弗朗西斯科的四年级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显示,“公开交流”“对错误的非惩罚性回应”和“医生间的交接”3项内容评分最低,另外,56%医学生报告“看到有损于患者行为时不能够大声说出来”,55%报告“当发现事情看起来不对时他们不敢发问”,48%报告“实习期间因犯错而被责备”;对“为患者提供安全照护受到最大影响的文化来自”这一问题,60%医学生报告来自供应商,23%报告来自临床服务,仅13%来自医学中心,4%来自医学院校。
2.2.6阿富汗Durani等[15]通过对527名初级医生(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实习医生)关于患者安全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对患者安全文化自我评价高,但74%被调查者不知道“高可靠性组织”的概念,60%不知道“不安全行为/潜在情况”的概念。高度统一的观点是“即使经验丰富的医生也会犯错”,但高年级实习医生、外科实习医生等仍认为“犯错误是无能的体现”,初级实习医生认为“和患者安全相比,领导们更专注于实现业绩目标”。
3影响医院安全文化建设的因素
3.1制度因素调查显示,对错误的反应是医疗组织安全文化建设的决定性因素,构建安全文化首先要去除3个破坏性元素:指责、恐惧和对错误的沉默[13]。因此,从指责文化中解放出来,实行“无惩罚的错误报告制度”是消除医务人员对错误的恐惧,增加报告意愿,增进对报告文化的认同感的前提条件。错误报告不该被看成是事件的终结,而应是一种从错误中学习成长的方式,是减少伤害、改善患者安全的第一步。以“无惩罚”为基础的制度体系才有可能引导正确的应对错误的反应。
3.2环境因素多项资料显示,医务人员参与安全文化建设程度和工作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医疗信息的透明度、文化建设的情况报告、人际关系工作氛围以及身边其他从业人员的态度等因素。美国Perez博士等[16]通过回顾性研究发现,较高的医疗信息透明度不仅有助于医生间的交流,也有助于医患共同努力促进患者安全;中国台湾对9家三级医院1 109名护士进行问卷调查时发现,护士对医院报告文化的感知影响其参与安全行为的程度,而护士作为一线从业人员,参与患者安全行为的程度与患者安全紧密相关[17]。澳大利亚对131名儿科护士关于“用药管理规范遵守情况”的问卷调查显示:导致护士不遵守规范的主要原因是护士感知的他人行为和病房文化[18]。荷兰通过邮件的方式对323名在职护士长进行问卷后发现,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促进护士长的工作表现,其中,护士长和护士行政管理人员的人际关系最可能影响其工作参与度,而护士长和医生的人际关系最可能影响其工作中的主动行为[19]。所以,对医院而言,必须设法建设良好的报告文化,提高医疗信息透明度,构建和谐团队,尽可能控制影响元素,从而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有利于医务人员参与安全行为的工作环境。
3.3管理因素管理层的态度对医院安全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领导力是保证患者安全措施有效到位的关键。斯洛文尼亚通过使用HSOPSC对976名临床和非临床工作人员进行关于医院患者安全文化的心理评估[14]及Feng等[23]对248名护士的调查,均佐证了此观点,因此,管理层要对安全文化建设引起足够重视,管理者需要为患者安全做出明确承诺并以身作则确保患者的安全。
3.4资源和设备医院硬件设施在建设活动中往往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规模较大的医院往往对安全文化具有更积极的看法,因为这些医院拥有更好的人员配备、设备仪器,工作人员也能得到更好地培训,很多有助于改善患者安全的措施也会在这些医院进行试点,甚至,这些大医院在实施质量改进措施时也包含了认证标准的制定[18]。但不管医院规模如何,各个国家地区、各级各类医院对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重要性的认识已趋统一,保证员工数量是一个需要率先解决的问题。随着网络时代的全面来临,共享体系的建立变得势在必行,中国台湾北部对一个重要的医疗中心919名护士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社会资源资本和知识共享对患者安全存在影响,共享知识体系不足容易导致不良事件发生,社会资本包括社会交往、信任和共同愿景,应成为知识共享的先决条件[21]。
4结语
综述国内外文献发现“医院安全文化”已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重视,欧美等发达国家更是从国家甚至国际层面系统展开评估活动,在我国,虽然也开展了对医院安全文化的相关研究,但从已发表的文献资料看,研究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且关注的主要为大城市的综合医院,研究也多在护士层面展开,对基层医院几乎没有资料报道,对医院其他群体特别是行政管理人员资料采集也不足。随着安全问题关注度持续升温,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医院安全文化的研究,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Hudson P.Applying the lessons of high risk industries to healthcare[J].Qual Saf Health Care,2003,12(S1):7-12.
[2] Singer SJ,Gaba DM,Geppert JJ,et al.The culture of safety:results of an organization-wide survey in 15 California hospitals[J].Qual Saf Health Care,2003,12(2):112-118.
[3] Colla JB,Bracken AC,Kinney LM,et al.Measuring patient safety climate:A review of surveys[J].Qual Saf Health Care,2005,14(5):364-366.
[4] Jackson J,Sarac C,Flin R.Hospital safety climate surveys:measurement issues[J].Curr Opin Crit Care,2010,16(6):632-638.
[5] Sorra JS,Dyer N.Multilevel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AHRQ hospital survey on patient safety culture[J].BMC Health Serv Res,2010(10):199.
[6] 陈芳蕾,周立.患者安全文化测评问卷的构建[J].解放军护理杂志,2009,26(1):1-4.
[7] 郭霞.中文修订版安全态度调查问卷的初步研究[D].太原:山西医科大学,2009.
[8] 许璧瑜.医院安全文化评估量表研制及其应用[D].广州:中山大学,2009.
[9] Sorra J,Famolaro D,Dyer N,et al.Hospital Survey on Patient Safety Culture:2008 Comparative Database Report[EB/OL].[2015-06-08].https://psnet.ahrq.gov/resources/resour-ce/7104
[10] Bodur S,Filiz E.A survey on patient safety culture in primary healthcare services in Turkey[J].Int J Qual Health Care,2009,21(5):348-355.
[11] Wagner C,Smits M,Sorra J,et al.Assessing patient safety culture in hospitals across countries[J].Int J Qual Health Care,2013,25(3):213-221.
[12] Nie Y,Mao X,Cui H,et al.Hospital survey on patient safety culture in China [J].BMC Health Serv Res,2013(13):228.
[13] Alahmadi HA.Assessment of patient safety culture in Saudi Arabian hospitals[J].Qual Saf Health Care,2010,19(5):e17.
[14] Robida A.Hospital Survey on Patient Safety Culture in Slovenia:a psychometric evaluation[J].Int J Qual Health Care,2013,25(4):469-475.
[15] Durani P,Dias J,Singh HP,et al.Junior doctors and patient safety:evaluating knowledge,attitudes and perception of safety climate[J].BMJ Qual Saf,2013,22(1):65-71.
[16] Perez B,Knych SA,Weaver SJ,et al.Understanding the barriers to physician error reporting and disclosure:a systemic approach to a systemic problem[J].J Patient Saf,2014,10(1):45-51.
[17] Chiang HY,Lin SY,Hsiao YC,er al.Culture influence and predictors for behavioral involvement in patient safety among hospital nurses in Taiwan[J].J Nurs Care Qual,2012,27(4):359-367.
[18] Gill F,Corkish V,Robertson J,et al.An exploration of pediatric nurses’ compliance with a medication checking and administration protocol[J].J Spec Pediatr Nurs,2012,17(2):136-146.
[19] Warshawsky NE,Havens DS,Knafl G.The influenc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on nurse managers’work engagement and proactive work behavior[J].J Nurs Adm,2012,42(9):418-425.
[20] Feng XQ,Acord L,Cheng YJ,et a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agement safety commitment and patient safety culture[J].Int Nurs Rev,2011,58(2):249-254.
[21] Chang CW,Huang HC,Chiang CY,et al.Social capital and knowledge sharing:effects on patient safety[N].J Adv Nurs,2011,68(8):1793-1803.
中图分类号:R197.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75(2016)03-0229-04
通信作者:黄丽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收稿日期:2015-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