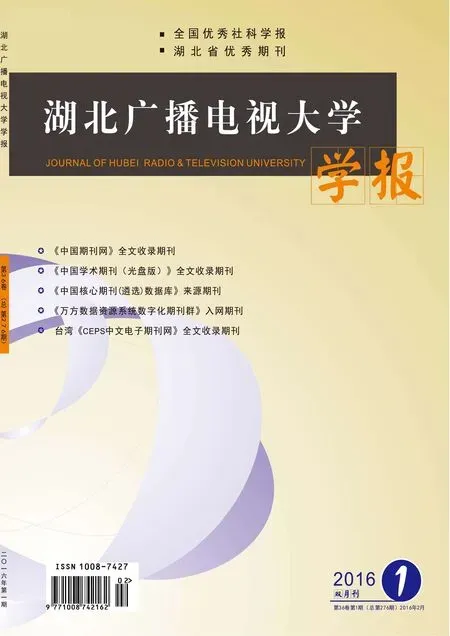论黄人《中国文学史》对明代戏曲的撰写
秦军荣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论黄人《中国文学史》对明代戏曲的撰写
秦军荣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湖北襄阳441053)
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为国人自撰文学史初期的重要著述。它将传统学术鄙弃的俗物——戏曲纳入文学史的书写范畴,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和较为细致的点评,为中国古代戏曲的现代经典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当是一部承上启下的文学史著作。
黄人;《中国文学史》;明代戏曲;撰写
尊崇诗文的中国传统学术中,戏曲基本被视作词俚俗、品卑下、不可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为儒硕鄙弃不复道。至近代,即便有梁启超等学者为提升戏曲小说的地位振臂高呼,然戏曲进入中国文学史的书写视域亦相当艰难,比如国人首部《中国文学史》的撰写者林传甲便认为戏曲最多可纳入风俗史。而同样作为中国文学史编写之草创期的撰著,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却体现出不同于时人的大气和勇气,将中国戏曲请进了中国文学的历史殿堂,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尤以明代戏曲着笔最多,在概述的基础上逐一评述明代传奇、杂剧的代表作品,新见迭出,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一
中国文学史的现代撰写,是由外国人发端的,俄国瓦西里所著《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年),被公认为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其他,还有日本末松谦澄的《支那古文学史略》(1882年)、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1897年)、笹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1898年初版,1904年经由上海中西书局翻译成汉语并印行)、英国翟思理的《中国文学史》(1901年)、德国顾路柏《中国文学史》(1902年)等等。其中,偶有涉及中国戏曲的简介,但因为文化的差异,总有雾中看花之嫌。
国人自编中国文学史始于1900年代。最初的文学史著述,为后世所知的有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年)、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约1905年)、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1906年)、来裕恂的《中国文学史稿》(约1909年)等。
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是为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历代文章源流”课程所编讲义,据编者自称是“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1]。但是两者无论是结构布局,还是作品论说,相似之处皆少。尤其是笹川氏《中国文学史》对戏曲的推崇与简述,遭到了林传甲的强烈批判:“日本笹川氏撰《中国文学史》,以中国曾经禁毁之淫书,悉数录之。不知杂剧、院本、传奇之作,不足比于古之《虞初》,若载之风俗史犹可。笹川载于《中国文学史》,彼亦自乱其例耳。况其胪列小说戏曲,滥及明之汤若士、近世之金圣叹,可见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2]故中国戏曲并未出现在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中。
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分“文字原始”、“经”、“史”、“子”、“集”五部分,近乎国学概论。“叙集第五”虽提到“曲”,但却认为“曲则其品益卑”,仅以一百来字概述元明清戏曲。
来裕恂的《中国文学史稿》虽认识到戏曲为元代之特色,但例举简单,所述不全。分别用一百多字交代元代与清代戏曲概貌,对于明代戏曲,则忽略不写。
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则不同。该著从文学“实为代表文明之要具,达审美之目的,而并以达求诚明善之目的者也”[3]2这一定义出发,不仅将戏曲与诗词并提,还较为详细地评述明代戏曲作品,为提升戏曲的文学史地位积砖添瓦:“独曲之一体,其内容则括历史、小说、词章、音乐,而尽有之,庄谐互见,雅俚相成,又多长篇巨制,极变化曲折,隐现离合之妙,非似寻常诗歌,寥寥易尽。自院本盛行,科白一体,亦文质相宣,各擅胜场,足以补曲文之不逮。”[3]48
二
传奇(明清长篇戏曲)乃是一种特别之文辞。黄人《中国文学史》认为,元曲“气粗而健,词俚而俊”,可谓“文界之异军苍头”![3]15而明清传奇则是“化合蒙兀之曲文、小说,而成一种特别之文辞。”[3]16“特别”之处主要有三:
其一,在文学界上,传奇俸格最下,而容积最富(与历史等),律令最严(与八股等),应用于社会之力量则又最大。原因在于:“凡朝政之得失,身世之悲愉,社会之浇醇衰盛,执简所不敢争,削青所不敢议,竿牍往复所不敢一齿及者,辄借儿女之私昵,仙释之诡诞,风云月露、关河戎马之起落万态,著为传奇,以抒写之。”[3]16黄人《中国文学史》中的这段论说文字含义丰富,它一方面道出了传奇乃是抒写朝政得失之叹与个人身世之悲等各种题材的最好工具,可以无所不写;另一方面则蕴含着传奇作为文学作品是虚构性与真实性的统一,故事可能是虚构的(大多取材于以前的文献资料或文学作品,如人物传记、唐人小说等),但传达的却是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体验与感受。且是用百姓喜闻乐见的以歌舞演故事的形式表达出来,即“传心情于弦管,穷态度于氍毹”,从而达到“使死的文学变为活的文学,无形的文学变为有形的文学”的效果,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即“应用于社会力量则又最大”。相形之下,“寻常文学,惟影响于文学界中。即通俗小说,亦必稍通文学者,始有影响”,[3]16阐述了长篇戏曲在社会功能上的优越性。
其二,明之传奇,化质为文,由疏入密,惟其异之(元曲),是以胜之(元曲)。对于元曲与明代传奇,学界有比较之论:“或谓元曲元气淋漓,尚含天籁,节短韵长,不烦敷佐。明之传奇,喜玩春华,杂陈宾白,不免多卖胭脂、横添枝叶之诮。”[3]16针对这种“崇此祧彼”的失当言论,黄人的《中国文学史》进行了有力地驳斥:“不知化质为文,由疏入密,惟其异之,是以胜之。……执此以议文学,则吾文学史所骈列者,皆狗尾蛇足矣!何独传奇哉?”[3]16体现出较为明显的进化文学史观。
其三,明代传奇,当“与八股文并峙于有明一代之文学界”。仍是针对学界的相关言论而发:“或又谓:实甫、则诚,已奏筚蓝之绩,传奇一体,明人实因而非创。”[3]16对此,黄人的《中国文学史》首先用打比方的方式进行辩驳:“五典断自唐虞,秦纪别于嬴政,草创自与大成有间。”[3]16然后正面回应:“况关、王旧本,已涂改于金采;而高氏生世,究未定为元明。又《伏虎绦》传奇,虽相传为元人作,亦无确据。而其所著之实质,仍为延长之杂剧,传奇体制,犹未完备焉。《西厢》、《琵琶》,既不能当先河之目,则云亭、稗畦,亦不能据积薪之势。”[3]16极为清晰地阐述了明之传奇在中国戏曲史上承上而启下的重要作用。“故传奇一体,当与八股文并峙于有明一代之文学界,无可议者”!
三
以概论、节选与评点相结合的方式介绍明代代表传奇作品与杂剧。在明代众多的戏曲家中,黄人最为推崇徐渭和汤显祖。于汤显祖及其《临川四梦》用笔最多,见解新颖,对我们理解作品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总体阐述“临川四梦”的主题与艺术特色。“至情”是我们解读“临川四梦”的关键词。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便是以阐发汤显祖的“至情”论为着眼点。
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主旨的程朱理学在明代前期气势非常。至明代中期,虽现衰颓之象,但其影响却已深入士大夫的骨髓之中:表面夸谈性理而实则醉心功名富贵,即“矫饰”,形成独特的儒林景观。而受陆王心学激进派——泰州学派影响的汤显祖,却深刻地认识到理学的虚伪性,形成了“情至说”的哲学思想,并将之作为精神主旨贯穿在自己的戏曲创作中,着实不易。作为观者或读者,只有顺着“情至”这条思想脉络,才可能对“临川四梦”做出较为合理的阐释,恰如蒋心余氏为之诠曰:“人而无情,虽盗贼禽兽之不若。”黄人《中国文学史》则曰:“即以思想论,亦足与《庄》、《骚》、《太玄》、《参同》、《首楞严》方驾。”[3]311将“临川四梦”与《庄》、《骚》并称,地位不可谓不高!然而,“世之持买椟之见者,徒赏其节目之奇,词藻之丽,而鼠目寸光者,则诃为绮语,诅以泥犁,尤为可笑。”[3]311道出了经典作品不为常人所解的惯常现象。
至于“临川四梦”之艺术特色方面,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亦使用比喻手法对其用典之贴切、关目科白之美妙、词料丰富等语言特征予以赞美:“运古入戏,化腐为新,为填曲者别开一新天地。至关目、科白,皆七襄云锦之妙,观止矣!《四梦》词料如天宫龙藏,拾其铢缕,即可敌陶猗,又如君房仙药,蛇鼠食其余,亦得飞升。”[3]311
其次,对“临川四梦”进行比较分析。第一,“四梦”的主题既有差异性又相互勾连:“玉茗四梦,鬼(《离魂记》),侠(《紫钗记》),仙(《邯郸记》),释(《南柯记》),分配富贵功名,渲染儿女闲情,而提挈以梦,人生目的尽于是矣。”[3]312概括精妙。第二,“四梦”的艺术方法和风格因为题材来源与主题的不同而迥异:“《离魂》最脍炙人口,然事由虚构,遣词命意,皆可自由。其余《三梦》,则皆据唐人小说为蓝本。其中层累曲折,不能以意为之,剪裁点缀,煞费苦心。《紫钗》之梦怨,离合悲欢,尚属传奇本色。《那郸》之梦逸,而科名封拜,本与儿女团圞相附属,亦易逞曲子,师长技。独《南柯》之梦,则入于幻,从蟒蚁社会杀青,虽同一儿女悲欢,宦途升降,而必言皆物,语不离宗,庶与寻常有间。”[3]312对此,黄人《中国文学史》发出了由衷赞叹:“使钝根人为之,虽绞尽脑汁,终不能得一字也。而此君乃因难见巧,随手拈来,头头是道。”[3]312第三,关于“四梦”主人公问题。黄人《中国文学史》认为,“四梦”之鬼、侠、仙、释的宗旨,决定其主人公有客观与主观之分。客观主人公即表面主人公,比如杜女(《牡丹亭》之杜丽娘)、霍郡主(《紫钗记》之霍小玉)、卢生(《邯郸记》之人物)、淳于酒徒(《南柯记》之淳于棼),四人俱为“梦中之人”。主观主人公为《牡丹亭》之冥判、《紫钗记》之黄衫客、《邯郸记》之吕洞宾、《南柯记》之契元禅师,四者皆是“梦外之人”。“盖前四人为场中之傀儡,而后四人则提掇线索者也。”“玉茗之天才,所以超出于寻常传奇家百倍者,正以寻常传奇家但知有客观的主人,而不知有主观的主人,非徒以词藻胜之也。”[3]312
再者,对“临川四梦”逐一进行介绍,包括简要评点和戏文节选。以《牡丹亭》为例。先对关于《牡丹亭》“为讥太仓昙阳子而作”一说进行驳斥;又以一小段文字简括《牡丹亭》的本旨:“书(《牡丹亭》)之本旨,谓一梦而亡,则较但问名而殉一从者,其情尤挚。”[3]311再有,惊叹学界“以男女秘戏及生殖器句比字附释《离魂》者”[3]311,竟然能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既显示了《牡丹亭》的神奇,亦透出曲无达诂的批评理论思想。最后,便是节选大量的《牡丹亭》戏文,略加评点,对于《冥判》一折的评语是:“判官,若士自况也。试以若士历史比例之。”[3]311亦可自圆其说。
后世,有人对比阅读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与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1926年大东书局出版),发现两者在明代戏曲的书写方面高度一致,这固然是一个值得考辨的学术问题。是黄人写就、吴梅抄袭,或是吴梅帮助黄人编撰文学史时融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等等,该问题的讨论与本文关联度不大,本文只关注黄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呈现出的书写状态。为了谨慎起见,文中并没有使用“黄人认为”等字眼,而是以“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指称。不过,起码有一点,我们可以达成共识,即《中国文学史》关于明代戏曲的书写是得到了主编者黄人之认可的。
事实证明,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确实比其前辈乃至同辈的同类撰述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尤其是,它以积极的态度将传统学术鄙弃的俗物——戏曲纳入文学史的书写范畴,为中国古代戏曲的现代经典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因此,“他的《中国文学史》是一部承上启下的作品,在我国文学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4]然而,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止于明代,故未能书写清代戏曲亦是一大缺憾。
[1]林传甲.中国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2]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2.
[3]黄人.中国文学史[M].杨旭辉点校,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2.
[4]黄霖.中国文学史学史上的里程碑——略论黄人的《中国文学史》[J].复旦大学学报,1990(6):78-84.
(责任编辑:张锐)
[Abstract]Huang Ren's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works that composes the early stage of the Chinese own literature history.Drama,which is considered as a vulgar in traditional academic circles,is absorbed into the category of literature history by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and is given remarkable and detailed comments.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modern canonization of the Chinese ancient drama,therefore,it is regarded as a transitional works in the literature history.
[Key words]Huang Ren;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drama in Ming Dynasty;composition
On Huang Ren's Composition of Ming-Dynasty Drama i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Qin Jun-rong
(Literature College,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Xiangyang,Hubei 441053)
I209
A
1008—7427(2016)01—0049—03
2015—12—12
湖北文理学院博士启动经费资助项目“文学史书写与元代戏曲的经典化”的阶段性成果。
秦军荣(1973—),女,湖北宜城人,博士,湖北文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