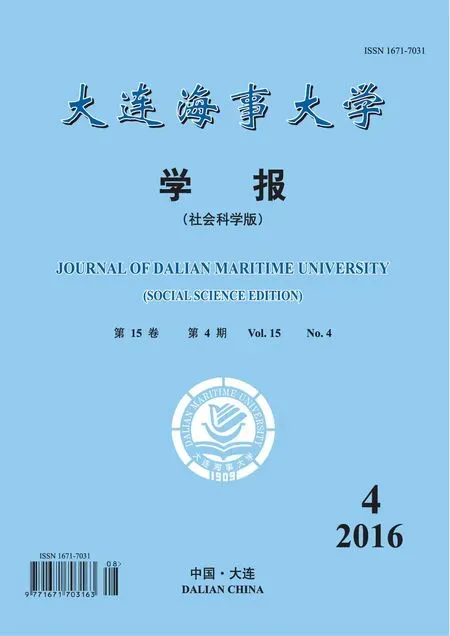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理念举要
——对中华原创经典蕴含的传国心法与治国理念的现代经济学解读
钟永圣
(东北财经大学学科建设处,辽宁大连 116025)
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理念举要
——对中华原创经典蕴含的传国心法与治国理念的现代经济学解读
钟永圣
(东北财经大学学科建设处,辽宁大连116025)
在中华文化语境中,“经济”的本义就是“政治的”,是“治国平天下”的代名词。古人所谈的经济,是体悟天地自然之道的圣贤君子,在“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和追求下,发起利益大众千秋万代的无上事业,绝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处心积虑的竞争取财行为。在《易经》《尚书》《诗经》《道德经》《论语》《黄帝内经》和《管子》诸种经典中,蕴含着一以贯之的中华传统政治经济学理念和方略。建立在天人合一世界观与德本财末价值观基础上的中华传统政治经济学,以贯通伦理、生理和物理的文化表达方式,揭明财富的来源、风险的实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道德核心因素等现代经济学悬而未决的基本议题。重新整理、学习和运用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是实现中国经济走出独一无二的复兴道路的理论前提和教育基础。
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传承;天人合一;德本财末
一、导论:对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态度
“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在中华文化中本来就存在着。中华文化的圆觉贯通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跨学科性质,也决定了它不被习惯了分科表述的现代社会所认知。从其本质文化精神上说,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早就“圆满地存在”,并不需要创建;但从现代社会所熟悉或者所要求的学术规范上说,它确实需要梳理、总结和翻译。
当前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至少面临三个理论来源,并且要相应地采取三种应对措施:
一是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它是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精神的政治经济学问传承,语言表达与陈述方式都具备完全的“中国特色”和“自主知识产权”,是中华文明在治理天下社会和富国安民方面的智慧结晶与经验总结,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由于它还不被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一百多年的大众所认知和熟悉,所以必须对它进行时代总结和现代表达。
二是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它也是时代的产物,生发于中华文化传统之外的西方文化传统中,曾经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历史进程,所以必须对它进行客观评价与合理吸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面包含两种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以亚当·斯密为开创者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了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为深刻认识资本对人类社会的组织与行为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严密的理论分析。
三是近年西方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它是西方文化思想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更新和扬弃,虽然有纠正“旧政治经济学”的可贵诉求和精专探索,但是明显存在着体系不够严密、方法过于工具化和理论解释力不足等缺憾,还有待于历史事实的检验,所以必须对它进行审慎借鉴和清醒观察。
对于时下的中国而言,除了时隔三十年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重要性之外,最重要、最紧迫的经济学任务,就是对中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挖掘和整理。
从学理上说,“学究天人之际”的中国古代圣贤已经把“经济”研究透了;从实践上说,“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明君圣主也已经把“经济”实践过了,理论总结与案例记载全都彪炳史册,只要能够“与时偕行”地变通施行,就可以在二三十年间实现天下大治、繁荣昌盛;但是从当代应用上说,西学东渐二百年,人们已经习惯了西方分科式的学术范式和表达方式,已经不屑于看、其实也常常看不懂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言表述,甚至连想承认它存在的人都可能存在着至少十年的经典阅读鸿沟。如果人们不精读自己的先祖如护眼命般保存下来的经典,不吸取前人用生命试验出来的经验和教训,拒绝抓取“以百年之身获得千年智慧”的机会,是不是一种学理上的自负?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于具有千年以上传承的学问,绝不应该置若罔闻。
二、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精神略说
“伊周经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商代贤相伊尹和周朝周公那样的作为,才堪称中华文化语境中的“经济”。但是,伊尹和周公治理国家的方略不是自己创造的,是传承的结果。根据《尚书》记载,武王向商代贵族箕子请教治国的根本大法,箕子将商代贵族的文化传承和盘托出,成为周朝治理天下的根本依据,也是后来历代盛世时期领导人治理家国天下政经措施的精神原旨。这一传承的核心精神,用现代的词语来表述,就是“中华传统政治经济学纲要”。
商代的治国方略来自夏朝,夏朝的治国方略传承自大禹。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显示,夏商之际,制度变化不大,真正发生明显变化的是周朝。而根据《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和《论语·尧曰》等信史或者经典的记载,大禹的传承来自虞舜,虞舜的传承来自唐尧。尧是轩辕黄帝的第五代孙,显然尧的传承来自黄帝。黄帝依然有传承,由于黄帝在文治武功方面具有划时代的功勋,我们尊黄帝为“中华人文始祖”。但是很明确,黄帝时已经有了“传统文化”,比如当时称为“归藏易”的《易经》,和传承自广成子的“道家心法”。统一的、多民族或者多部落的“国家”早已经形成。只不过,上古时代的“国家”指诸侯国,“天下”才是“统一”的目标范围。从尧传舜、舜传禹来看,中华文化中“天子”之间的传承不仅仅是“大位”的更替,真正核心的交接是“道统的延续”和“心法的传承”。在《论语·尧曰》中记载,尧在传位时告诉大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关键后面还有一句:舜亦以命禹。清晰地记载着传承的顺序和内容。而《尚书·大禹谟》记载大舜传给大禹的内容在文句上就更详细一些:“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箕子传给周武王的内容被记录为《洪范》,就不是一两句话的记载了,可以说是内容宏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高度成熟的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大纲。可是如果表面化理解《洪范》所载的“九畴”“五行”“八政”这些内容,是读不出这种活的文化精神的。必须透过这些似乎过了时的表述,体悟到文字背后的精神,才能把胡适批评过的“故纸堆”活化为当代可用的智慧。
尧传舜这一句“天之历数在尔躬”,表明这个传承是《易经·坤卦·文言》所载文化精神的体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这一精神被传承孔门心法的曾子表达为《大学》的“三纲八目”“内圣外王”。表明中华道统、儒家心法和贵为天下治理原则的“中华传统政治经济学”是“一以贯之”的,是“天人合一”的,是内外贯通的,直接揭示了天下安危、困穷大治在本源上其实系在“天子”(最高领导人)一人之身的品德、智慧、能力和时运,它也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物质决定时空”观念在人类世界的体现:一个人的“内心真实境界”决定着自己的人生境遇、家庭状况、事业发展和国家安危。
孔子“人在政兴”的表述,同样表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天人合一”观基础上的,不但“以人为本”,而且是以人的道德修养为本质、为核心、为关键、为决定因素。由此可以判断,在《易经·坤卦·文言》《尚书·尧典》和《大学》中所揭示的中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层级结构是:心性、伦理、道德层面的行为经济学,决定着以秩序、规则和法律为核心内容的制度经济学。
三、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文化实质
在地道的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中,现代的“国家”概念,在地理上是古代“天下”的范围。由于中华文化在1840年之后已经逐渐被尘封在历史典籍当中,中华文化语境在社会主流的表达中日渐式微,仅仅存在于少数隐性传承中。这样,中华文化的表达方式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等待着下一次“隆重登场”的历史机遇。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文化概念“清洗”“覆盖”或者“替代”了中华文化的本土表达,使得今天许多似乎已经是约定俗成或者司空见惯的“外来语”表达完全“鹊巢鸠占”地挤走了“土著语”表达。
以“经济学”为例。“学”在中国文化中,原来不是“专业”或者“领域”的局限概念,“经济”也不仅仅是“稀缺性引起的资源配置”的“小术”,而是“经邦济世”的“大道”。所以“经济”这种学问不是通过“记忆”“背诵”或者“理性思考”就能获得,而是必须经过历练、反求诸己并且亲身“体悟”才能获得。但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当时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受到极大的打击,对于固有文化几乎完全丧失信心,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下,开始向近邻日本学习。大约在1892年前后,一个叫神田孝平的日本人,把奉亚当·斯密为鼻祖的economics翻译成了汉字的“经济学”,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准确的翻译,会引起很大歧义,可是当时的留学生并不了解,以为日本的崛起不但是因为学习了西方的“科技”,而且学习了西方一种叫做“经济学”的学问,就以讹传讹地传播开来。有现代学者考证,英语词汇economics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大体上经历了“富国策”“理财学”“计学”和“经济学”四种翻译。到了1902年严复节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原富》,就使得“经济学”这三个字逐渐失去了它在华语中的地道本义,完全沦落为一个西文词汇在中文语境中的翻译词汇,从此一错一百多年。
“经济”在中华语境中本来就是现代语汇“政治经济”的含义,“经济学”在中华文化的本义中本来就是现代专业词汇“政治经济学”的意思,不但包含着统治阶级如何构建最高统治集团的治理结构、如何改进财政税收制度、如何筹措国防军队的费用,还包括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现代西方学术界,以马歇尔发表《经济学》为标志,试图把“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分离出来,单独发展“不带政治”的经济学,导致中文“经济学”的地道含义与西文economics的含义越来越混淆不清。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天人合一”观基础上。其实天人合一的含义就是人要按照自然规律来行事。自然规律是现代的表达,古代的说法就是“天道”,简称“天”或者“道”。那么,天人在何处合一?答案是:在遵道贵德处合一。如《黄帝内经》所言,“天之在我者,德也”,德行,是天在人身上的化身。一个人的起心动念、言行举止合乎德行,就是与天道相合,就会百福汇集、所愿吉祥;如果悖道缺德,就是人天分离,就会百祸汇集、所愿乖违,因为得不到天的护佑。按照《易经》的揭示,其实天的护佑就是自己德行的护佑,所以叫“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一个人如此,一家如此,一国如此,同一时代的“天下”也是如此。人生命运其实是一个人全部内在德行的物理显化,家运是一家成员内在德行的表现,国运来自于全体国民的内在德行,时运来自于时代内所有人的内在德行,看似纷繁复杂,其实十分清晰简洁。时来运转,其实是积功累德的结果。经济繁荣和经济萧条具有周期性和阶段性,也就是积德与败德决定的交替更迭。
对于家、国、天下来说,做主的那个人、组织、阶层、集团、政党,对其所在组织、阶层、集团、政党和国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即“一人担负天下安危”的道理。所以,尧传舜,不但传天子位,更重要的是传治理天下的心法。能够与天道、民众、百官精诚为一的领导人,就能够实现天下大治,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国泰民安。
大道至简。国家政治经济的道理,是大道理,但是十分简单。《论语》当中记载孔子所言,真实不虚。例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素书》上说,“夫人之所行,有道则吉,无道则凶,吉者百福所归,凶者百祸所攻,非其神圣,自然所钟”。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感,同类相依,同义相亲”,“此乃数之所得”。天、德、人三合一的君主、圣贤、志士,如果都能够“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则都会有“功成事遂”的结果。
四、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念
观念的教育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繁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礼记》中说,“自古先王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建设国家,首要的任务就是教学。教对了,垂拱而治,天下太平;教错了,“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例如,“约束条件下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论就很可能会直接导致学习者为了最大化自己的私利而无所不用其极。所以经济理念的正确与否,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甚至生死存亡。
经济的本义是用最圆满、最彻底、最无害的方式帮助天下人在明理合德的基础上过富足而有尊严的生活。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虽然“法本无法”,但是不能脱离它的基本原则,即发心要纯正,实现途径要遵守程序正义。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政治经济学,从来都是“伦理的经济学”,或者“道德的经济学”,也是“经济学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它的核心理念看起来并不复杂,却是深深地符合天人合一的要旨,践行起来又会觉得深不可测。
1.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要旨:主明则下安
“主明下安”出自《黄帝内经·灵兰秘典论》,这四个字扩展开来,可以说是全部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它体现着“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完全是中华文化的表达方式。按照《易经》开创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文化构建原则,《灵兰秘典论》中先是通过介绍人体十二种器官的功能,把人体的器官和现实世界里国家各个部门的功能联系起来,把人体运作的机制规律和治理国家的机制规律一理贯通起来,指出“以此养生则寿,以为天下则大昌”,人人可以体会,人人可以验证。20世纪哈耶克写《感觉的秩序》,本质上就是触摸到了这一文化原则,试图以人体中枢神经的运作机制解释经济组织的运作和效率。
《管子·心术》篇阐述的国家经济管理理论,同样是这个道理:“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如果心是“明”的,也就是做主的那个是“明”的,则天下大安。天下,对于人指“身体”,对于国家指“市场”。
2.贯通伦理与物理的基本价值观:德本财末
中国传统经济学十分彻底而清晰地揭示了财富的根源:财富是人的内在道德在物质方面的变现。曾子《大学》中有一段把天理、生理和物理贯通的经典表达:“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段话不但清晰地指明了财富是道德之根(本)产生的果实(末),还指明了财富聚散的道德决定性:不是正路赚来的钱(悖而入),也不会正常地消费支出(悖而出),往往面临水(洪水)、火(失火)、王(国库没收)、贼(被贼所盗)、亲(逆子败坏)五种耗费结果。
中国经典对于“本”非常重视。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观念中,人们只重视物理的“资本”,做生意也最怕“亏本”,却没有把人的真实行为和财运联系起来,导致了伦理道德行为和物理财富之间关系的脱节。其实,中国文化揭示,在伦理上亏了本(道德行为有亏),那么迟早也会在物理上亏本(赔钱)。举更具体的例子来说,在家庭五伦中缺德亏孝的经营者,迟早会在生意经营上亏本。伦理行为对财富运势的影响十分重要,而且表现也十分复杂,但是只要时间足够长,就会发现它是一条“公理”。所以《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论语·学而》中记载有子说,孝悌是为人之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既然道生一二三乃至万物,当然也就生发财富。
3.经济行为的伦理准则:利者,义之和也
在现代社会,一提起“经济”就意味着“谋利”,几乎是不可改变的观念,而且这个利几乎就是“收入减去成本”,没有指标考量“这个钱该不该赚”。但是,在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里,只有“符合天经地义”或者“符合各方利益”的财富,才是“利”。所以,在中国的经济传统里,原本就没有“原罪”的概念,因为财富从一开始就是“善财”,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就是“善财利生,普济天下”。简单地说,经营者有自己中国特色的“信仰”,秉持着“人在做,天在看”的信念,或者“头上三尺有神灵”的观念,不该赚的钱,穷死也不取,守着一份义气,诚信传家久。如北宋的苏东坡就在《赤壁赋》中表明立场:“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在中国是最悠久的传统,因为“利者,义之和也”的观念出自《易经·乾卦·文言》,《易经》卦象约有七千年以上的历史,其中的“文言”是文王所作,有三千一百年的历史。
在西方经济学中,“帕累托最优”这个概念类似“利者,义之和也”的理念,如果把能够分配到的资源定义为“利”,那么最和谐的状态就是没有改进余地的最理想状态。
在“利者,义之和也”的观念中,隐含地解释了经济风险的来源:小人行险而侥幸。如果结合“德本财末”的价值观,就更能揭示市场风险的根源。就如同《黄帝内经》里论述“淳德全道”不会得病一样,德不缺、义不亏的经营者也不会赔本。关键问题是,现代人对“德”字缺乏最起码的体悟,无法领会“外在的一切境遇,是内在德行外化的物理现象”这一道理,也就无法知道,市场风险的本质根源是德行有亏。
4.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原则:治道之要,与民休息,贵在不扰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西方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为了保证市场的运行,西方经济学提出“政府不干预”的学说,让“看不见的手”来指挥经济运行。但是几乎所有西方经济学者都忽略了一点,由于“看不见”,必然导致政府和市场的双重“盲目”,当“市场失灵”发生时,政府出不出场都是一次混乱的调整过程。以1929年美国大萧条为例,危机发生时,美国政府天真地相信“市场的自动调节作用”,坐视不管,导致美国经济从危机走向崩溃。随后的“罗斯福新政”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逻辑的必然,实际上美国经济进入“政治经济”阶段,政府强力干预、监管和控制。由此还能得出一个十分隐秘的判断:美国联邦政府从此不再相信“市场会自动配置好经济资源”的自由主义教条。
在中国传统经济学中,没有看不见的规则。看不见意味着蒙昧,肉眼看不见是功能问题,心眼看不见是智慧问题。即使对于在物质形态上没有形象可以抓取的“心性”,中国人也在智慧上要求明白,叫明心见性。孔夫子“入其国”即可“知其教”,用《道德经》的话来形容就是“有无相生,微妙玄通”。
中国文化是“中道文化”,是“恰好符合”的文化。国家不能没有治理,但是治理的标准是“为无为”,是按照事物本身的自然规律去因势利导,所以从实际效果上看,并不干扰事物本身的发展变化规律,这就是从西汉初年见于胶西盖公的表达:“治道之要,与民休息,贵在不扰”。政府保持着高度警觉,但是只要市场正常地自然运行,就不必“有为”。《道德经》中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它实际上仍然是尧舜禹时代“允执厥中”传国心法的另一种说法,本质上没有任何不同。
年代久远,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时代表达,也需要精准的系统性翻译,以显明文化的核心精神。
5.利他就是自利: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中国传统文化把世界看成一个浑然的整体,自他不二。在这样的文化观念下,必然产生“利者,义之和也”的价值判断。在这样的判断下,自他之间是和谐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竞争的。所以中国经济学是和气生财的经济学,不是对立竞争的经济学。《道德经》中揭示了经济行为上自他不二的秘密,“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己就会变得越富有;越是大利天下,自己拥有的就越多。越是能够生产提供精致、精良、精美的产品,就越是能够“占领市场”,获得稳定而高额的利润。
6.市场发展的动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西方经济学用竞争来解释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以为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份额,就没有生存机会。在中国文化中,即使“竞争”也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竞是奋发,争是惜时,所以竞争其实是有志之人的自我奋发、自我激励和自我升华,与他人无关。而且“和气生财”是中国传统经济学的公理,永远对顾客真诚,才能持久地生发财富。竞争往往破坏和气,即使一时赚得,也不长久。
《易经·乾卦·文言》中揭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经济不是谋利的伤害,而是互利的关爱。就如《道德经》所言,“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
五、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应用
中华的儒家传统、道家传承和国政治理方略同出一源,本来并无界限,也不分家。所以,汉文帝能够凭借“黄老之学”开创“文景之治”,宋代丞相赵普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关键在于“人”,关键在于“明”,关键在于“用”,关键在于“行”。《诗经·灵台》说:“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本文之所以对一门学问的“理念”举要,就是因为一句理念悟通,就可以改变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是明明白白的人,用是恰如其分的用,行是道法自然的行,由此可以稳健地生发一切事业,就能做到《素书》所说的“时至而行,得机而动”。
[1]邹进文,张家源.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4):116-121.
[2]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喻中.风与草:喻中读《尚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尚书今注今译[M].屈万里,注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9.
[6]管子今注今译[M].李勉,注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9.
[7]爱因斯坦.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浅说[M].杨润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尚书[M].周秉钧,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1.
[9]黄石公.素书[M].李慧,李彦舟,释评.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9.
[10]了然.在诗经中修行[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14.
[11]徐芹庭.细说黄帝内经[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12]老子道德经注[M].王弼,注;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
[13]周易今注今译[M].南怀瑾,徐芹庭,注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9.
[14]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15]李学勤.《史记五帝本纪》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016-07-26
钟永圣(1973-),男,博士
1671-7031(2016)04-0087-06
F092.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