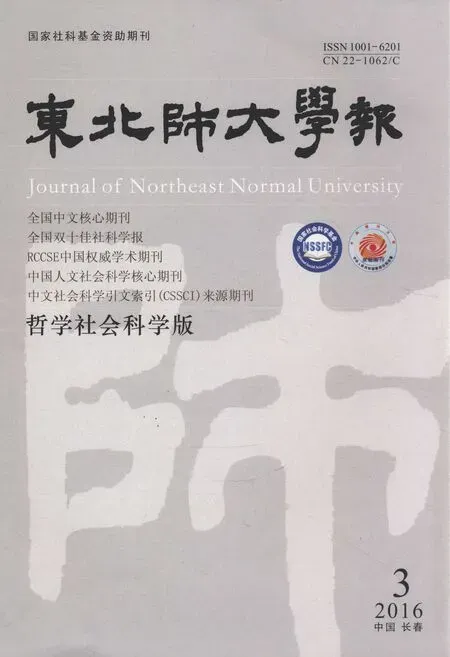基于新制度主义对我国社区照顾宁养患者的援助机制研究
张 朝 林
(长春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基于新制度主义对我国社区照顾宁养患者的援助机制研究
张 朝 林
(长春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作为制度存在的社区照顾与宁养服务,在理论层面具有契合的可能性,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出现了制度拒斥现象,其根源于物质性实践与象征性符号的分疏。因此,在建构社区照顾宁养患者援助机制时,需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从政府规制、学术规范、实践融入及教育传递等方面,让社区照顾癌症患者的过程中纳入宁养服务的象征性符号。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社区照顾;宁养服务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2013年全球新增癌症患者已超过1 400万人[1]。其中,我国新发癌症病例约350万,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 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数据来源于2013年1月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而70%的已确诊患者会在1年内死亡,单纯的疾病治疗与延长寿命已无法满足患者及家庭的需要,缓解疼痛、提高末期生命质量及维护善终尊严的宁养服务需求明显。在李嘉诚基金会的支持下,从2001年起我国内地掀起了宁养服务的浪潮,迄今已成立了31家宁养院,已有近30万癌症患者直接受惠。我国的宁养方式受到医疗水平及患者家庭的限制,完全区别于国外及香港地区的住院宁养的疗护方式,而采用医生跟进回访、患者家庭照料的居家宁养模式。这种模式依然是家庭而非社会责任,造成社区照顾部分功能缺失和宁养患者社会参与不足。实际上,宁养患者在治疗、化疗过程中照顾需求主要集中在“健康教育、康复护理、服务和预防保健性的护理技术服务”,这些服务“技术含量较高”、“个性化特征明显”,更需要社区照顾[2]。社区照顾与宁养服务在内容上交叉,在形式上相近,在方法上相同。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出发,推行社区照顾活动接受宁养患者并建立一种可持续的援助机制,不仅是社区照顾内容的丰富,宁养服务实践方式的创新,也拓展了社区照顾和宁养服务的理论空间。
一、制度性存在:社区照顾宁养患者的发展现状
社区照顾是一种偏向物质性实践的制度。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有许多福利性质的养老院、精神病院、孤儿院开展特殊群体的院舍照料服务,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使收容者“标签化”而加剧了心理伤害。因此,英国政府期望通过“反院舍化运动”改变机构照顾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与负面影响,推行受照顾者回归家庭与社区,由专业性社区工作者整合各类社区资源实施生活照料、物质支持、心理支持、整体关怀等服务活动。直到20世纪80年代,社区的功能逐渐凸显,欧美国家将发展社区照顾成了这些政府福利政策的导向之一,如1982年的“巴力克报告”、1989年“社会福利白皮书”,90年代初的《国家健康服务与社区照顾法令》等。我国内地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与社会体制的转型,传统的“企业办社会福利”或“政府包办社会福利”无法全面有效地满足社会需求,专业化、社会化的社区照顾得以引入并获得政府部门的广泛推行,如1993年民政部联合14部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1995年民政部颁布的《社区服务示范城区标准》、2000年民政部等国家部委出台的《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由此我国大部分城市社区都尝试性地开展了大量的老年人、失独家庭、残障人士的社区照顾服务,形成了“在社区建设中发展社区照顾”的独特经验,涌现出了一批如上海浦东罗山市民会馆、广州文昌地区慈善会等典型范例。综上所述,国内外社区照顾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由规制性制度(政府及相关部门出台政策法规推行)向规范性制度(专家学者论证支持)、认知性制度(物质实践探索、群众接受)的发展。政府组织试图将弱势困境人群的需求与问题转化为技术专家的物质实践,以消解社会大众维权要求的冲突性紧张。归根结底,社区照顾是政府组织消解社会矛盾的举措,是一种技术专家的物质性实践。
宁养服务是一种偏向文化符号系统的制度。宁养服务起源于早期基督教教徒的义工服务,1879年都柏林修女Mary A itkenhead及1905年伦敦另一名修女分别在修道院收容癌症末期患者,运用博爱精神照顾患者。而现代意义上的宁养服务始于1967年英国护士西西里·桑德丝将社会工作、现代医学与宗教灵性照顾相结合的“圣克里斯多弗安宁院”癌症末期病人服务。随后,世界各国相继兴办安宁缓和治疗机构开展宁养服务。20世纪70年代欧美及澳洲开展宁养服务,80年代日本、新加坡、香港地区率先发起并引领亚洲宁养服务的发展,90年代天津医学院成立了临终关怀研究中心、汕头大学成立了宁养院标志着我国内地宁养服务的启动与发展。截止到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成立了安宁院8 000余家,其中我国内地也开办了31家宁养院,每年约有数百万癌症患者受益。同时,宁养服务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体系化成就,有宁养服务发展现状、理念伦理、实务模型及与生命死亡、宗教信仰、做人尊严的关系研究,形成了大量有影响力的著作与文献。除了宁养院数量规模的扩张与理论研究的深入外,发达国家与地区都通过立法形式规范与支持宁养服务,如至1991年美国各州都通过了自然死及生预嘱(Living Will)法案,其中包括末期病人拒绝急救的权利及预立医疗指示的权利;我国台湾地区也于1989年5月23日立法通过了《安宁缓和医疗条例》[3]53。综上所述,宁养服务是一种制度性存在,由认知性制度(宗教信仰实践、世界各国认可)向规范性制度(专家学者研究),再到规制性制度(国家政府立法)的发展。归根结底,宁养服务是一种理念的践行,是一种文化符号的延续。
新制度主义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重要的制度秩序,都会根据各自的中心逻辑——物质性实践与符号结构系列——建构其组织原则,促进组织与个人的发展[4]271。当前所有的核心制度是由物质性实践与象征性符号系统共同构成的,只不过在制度的建构过程中会出现“符号产生实践(如宗教信仰)”,也会出现“实践形成符号(如政策措施)”等。上述的社区照顾与宁养服务都是制度性存在,都基于不可观察、概念化、超理性的意旨即“扶危济困”的符号系统而开展的实践活动,两者具有契合性的可能性。国外大多采用独立的宁养院服务模式为病患者提供最优质的宁养服务而并未与社区照顾服务相结合。依据我国的国情及医疗体制,病患者无法享受到现代意义上全面的医疗服务,在李嘉诚基金会支持下只能推行符合我国国情的居家服务模式,仅对居住在大城市的贫困晚期癌症患者开展低标准、广覆盖的宁养服务。而这种居家服务离不开社区支持与精神照顾,是社区照顾的重要形式之一,属于“在社区照顾”的地理范畴,但并不属于纯粹意义上的社区照顾宁养患者服务模型。
二、制度性拒斥:我国社区照顾宁养患者的物质性实践与文化符号的分疏
国外发达地区开设宁养院服务癌症患者,有其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如宗教盛行、医疗发达、资金充足、社会参与度高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容忽视,我国癌症患者每年新增数量约350万人,占全世界新增数量的1/4,现行医学水平与国情无法全面推行独立宁养院服务模式,如此大规模的癌症患者依靠建立独立的宁养院开展现代专业化的宁养服务显得不太现实。同时,现阶段所推行的居家服务覆盖面小、标准低,也无法真正回应患者需求。与社区照顾对象一样,宁养对象也是失能者,在治疗、化疗过程照顾需求主要集中在“健康教育、康复护理、服务和预防保健性的护理技术服务”,需要社区支持与照顾服务,推行社区照顾宁养患者制度势在必行。很显然,作为制度存在的社区照顾与宁养服务,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存在契合的可能性,在推行社区照顾宁养患者制度时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与分析这种可能性下的不可能因素。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社区照顾与宁养服务两者间存在许多的共性,在内容上交叉,在形式上相近,在方法上相同,只是在服务的对象上有分别,存在契合的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下,许多专家学者也纷纷论证并提出“社区照顾宁养患者制度构建”策略,如王杰军等提出“新世纪的肿瘤防治应充分立足于社区”、“强化社区医护照顾的制度,完善社区医护照顾的内容,制订《社区癌症患者诊治规范》将成为肿瘤治疗非常迫切的任务”[5]23;柴玉萍通过98例晚期癌症患者的调查,得出结论“社区服务中心是开展临终关怀较理想的机构”[6]111。但是,社区照顾宁养患者是一个跨学科多系统的繁杂工程,参与人员素质高低不齐,也缺乏完善的可操作性强的法规指导社区癌症患者医护照顾服务。
也就是说,当前理论上的可能性并未成就两者的有效契合,相反在实操层面却呈现出了社区照顾与宁养服务两层皮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恰恰说明了两种制度间的拒斥,表现为物质性实践与文化符号系统间的分疏。具体而言,分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现代意义上宁养服务是居家照顾宁养患者的试点与探索,未能产生社区照顾应有的文化意旨。当前在我国推行的现代化宁养服务主要是居家照顾宁养服务,而这种服务模式是将癌症患者从医院或机构照顾中脱离出来放在社区照顾,但只是地理概念的变化属于“在社区照顾”的范畴,仍采用社区外医院现有的医生、心理咨询师及项目所招募的社工与义工,并未动员与整合社区内部资源,是一种社区照顾的表面形式与假象,无法真正意义上实现社区照顾文化符号的建构,进而居家照顾实践与宁养服务象征符号被人为“二元化”;另一方面,我国本土社区照顾宁养患者的尝试,被简化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社区失能者(癌症患者)照顾,忽视了宁养服务象征符号的融入。有关社区服务癌症患者的实践在国内已非常常见,大多针对患者家庭经济困难提供物质帮助或不定期上门访视,有些完善的社区还会动员社区医生资源提供疼痛护理服务,但鲜见心理辅导和哀伤疏导,这与宁养服务内涵有本质差别,未能自觉地做到理性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忽视了“人道主义”、“尊重生命”等宁养服务符号的践行与融入。
在新制度主义看来,各种制度是一种符号系统,有着不可观察的、概念化的、超理性的意旨,也有着具体体现它们的可观察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总是同时具有工具性的和仪式性的内容。换句话说,制度既是工具理性的结果,也是价值理性的结果。上面社区照顾宁养患者两者结合的制度出现了拒斥,其根源在于实现了工具理性但未能有效地建构并实现价值理性。这是因为对于个人和组织而言存在多重逻辑,单一的制度(社区照顾或宁养服务)影响并型塑了个人的偏好和组织的利益,以及个人用以获得他们的利益或实现他们的偏好或利益的传统知识贮备和技艺[4]271。如果没有通过对象片体系进行建构,赋予社区照顾宁养患者活动以意义,则会使社区照顾与宁养服务间存在潜在的矛盾而出现制度间拒斥的现象。
三、制度性重构:社区照顾宁养患者象征符号因素的纳入
社区照顾与宁养服务无论在理论支持和实务开展都有着天然的联系,把宁养患者纳入社区照顾的范畴并建构一个基于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相互交融的、完善的、可持续的援助机制,既是对社区照顾领域的拓展,也是对宁养患者服务方式的创新。当前我国社区照顾宁养患者未能构建成完善的体系,在新制度主义看来是物质实践与象征符号的分疏,走向了功利主义或权利为导向的个人与组织行为活动。因此,迫切需要在社区照顾的物质实践过程中引入宁养服务的象征符号,再生产出特定的社区照顾宁养患者的文化符号,实现社区照顾与宁养服务的有效契合。
政府规制与学术规范共同生成与再生产社区照顾宁养患者象征符号。要进行成功的制度重构,不仅有赖于制度支持者所控制的资源,也有赖于权利的性质和提供、分配、控制资源的具体制度规则,这源于人们对规则的使用具有高度的背景敏感性[4]271。人们在物质实践过程中会将规则逐步内化并在后续的实践中形成象征符号。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自然死及生预嘱(Living Will)法案、台湾地区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由相关的部门出台《社区照顾宁养患者服务条例》。同时,我国医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工作等领域内的专家,认真疏理国外有关宁养服务的研究现状,总结提升现行社区照顾癌症患者的实践,探寻符合我国内地的宁养服务价值理念、伦理准则并形成象征文化符号,指导社区照顾宁养患者的实践。
组织和个人可以在物质实践过程中主张或融入象征性符号。象征性意义符号是一种价值规范系统,也是一种认知系统。在社区照顾宁养患者援助体系的建构中,在现有社区照顾模式的基础上组织和个人需要引入宁养服务的价值理念,即要在社区照顾的实践过程中秉持如下理念:要最大限度地解除晚期癌症病人的疼痛,控制病人躯体上的不适症状,缓解患者和家属精神、心理上的压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顺其自然地维持病人的生命,保证其生命的尊严[7]28。在引入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实践来构建适合我国传统观念及伦理价值的象征性符号。在实际的服务过程中,可以通过最为外显的文化现象“行为习惯”予以呈现,镇痛治疗上应秉持“行善”与“不伤害”理念,与病人及家属共同分析治疗利弊,在三阶梯治疗法基础上由病人决定用药量的“度”;护理上坚持“病人主体”,调动病人主动性对病人的身心健康实施整体护理及家庭护理指导;心理疏导上应在语言与行为上基于尊重生命理念表现出“真挚、亲切、温暖”,设法减轻或消除病人的心理障碍,以亲切、科学、可信的言语与行为帮助患者面对现实,直面人生,正视死亡[8]12-14。
通过教育宣传“生死”理念与服务技能,完成社区照顾宁养患者物质性实践与象征符号的有效传递。首先,借助大众媒体、科普读物、报纸杂志进行广泛的宣传,让人们认识到生与死的自然规律,引导社会大众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其次,在学校开设社区照顾宁养患者相关课程,我们可以在中小学阶段开设生死教育课程使公众认识到生死悲伤的事实与情感,在大学(医学院医学、社工类学科、心理咨询)培养宁养服务理念及传授服务技能;最后,在实践环节中,加强专业督导力量的建设,做好传帮带工作,使得刚刚接触社区照顾宁养患者服务的工作人员在理念及技能上得到提升。
社区照顾宁养患者援助机制是一项系统、繁杂的工程,涉及政府部门、社会力量、患者本人及家属等多个主体,通过一篇论文达到援助体系的建构不符合现实情况及科学逻辑。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社区照顾与宁养服务间的制度拒斥,提出在社区照顾中象征符号的纳入观点,提供一个全新视角供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借鉴,促进我国特色的宁养服务快速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陈松整理.世卫组织:全球癌症患者每年新增1 400多万[N].成都商报,[2013-12-18].http://q.115.com/t-172846-27194.html.
[2] 曾友燕.老年家庭护理需求与服务内容的研究[D].第二军医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2007.
[3] 钟进财.中国宁养服务发展之我见[J].医学与哲学,2003(8).
[4] 沃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吉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M].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 王杰军,邹建军,郑莹,卢伟.上海市社区癌症患者医护照顾的现状和展望[J].医学与哲学,2003(8).
[6] 柴玉萍,贾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晚期癌症病人的临终关怀护理 [J].中国临床研究,2012(18).
[7] 王京娥.宁养服务中的伦理探索[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0(3).
[8] 马振山,邵军.宁养服务与医学伦理[J].锦州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责任编辑:何宏俭]
A Research on the Aid Mechanism of Caring for Hospice Patients in our Country’s Community Based on New Institutionalism
ZHANG Chao-lin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As the institutional existence, community care and hospice service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matching in theory. However, their rejection of institution happens in reality. As a resu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governmental regulations, academic standards, combing practice and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id mechanism of caring for hospice patients in community, which makes the community add the symbolic sign of hospice service in the process of caring for cancer patients in community.
Key words:New Institutionalism; Community Care; Hospice Service
[收稿日期]2015-08-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84003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840020);教育部春晖计划基金项目(403-004084020)。
[作者简介]张朝林(1961-),男,安徽利辛人,长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6)03-0240-04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3.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