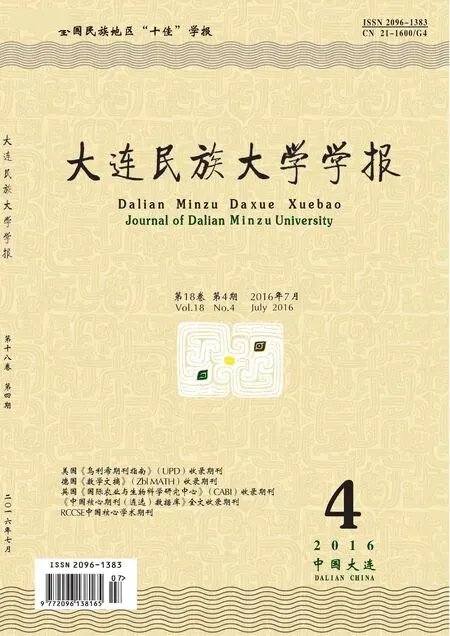科尔沁乡土小说中的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
白叶茹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科尔沁乡土小说中的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
白叶茹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科尔沁乡土小说的文化叙述表现为蒙文化与汉文化相融合生活方式的叙述。通过分析科尔沁乡土小说的具体作品,从生活习惯的改变、贸易活动的出现以及蒙汉语混合的叙述语言三方面来阐释科尔沁地区农牧业相混合的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特征。
关键词:科尔沁乡土文学;地域文化;民族文化
位于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的科尔沁草原,自古就是多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地方。匈奴、东胡、鲜卑、蒙古、满等十几个民族都曾在这片草原留下过自己的足迹。15世纪初科尔沁人在科尔沁草原立足以来,受到了满、藏、汉等民族的影响。其中,汉族对于科尔沁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到了近现代,科尔沁与汉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更加密切,科尔沁的语言、教育、本子故事、胡仁乌力格尔等都受了汉文化很大的影响。
科尔沁文化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后结合自身的特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不断进行着改革与发展,这成为科尔沁文化发展的内在原因。因此,科尔沁文化具有自我调节的积极性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独特的历史背景与地理条件使科尔沁草原成为蒙汉两种文化相互排斥、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场域。农业文化的到来打破了游牧生活的文化传统,汉文化的渗入使科尔沁人的生活习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日常语言、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等都有了改变。这些改变在科尔沁乡土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一、生活习惯的改变
位于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地区与内地相邻,从18世纪初期开始便有大量的农民相继定居科尔沁,开始了农耕生活。内地的农民在科尔沁开荒种田,传播农业文化,推动了科尔沁半农半牧的进程。与此同时汉族手工艺人的到来,影响了科尔沁蒙古族传统手工艺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木匠、铁匠等等,为科尔沁文化带来了新的血液。蒙汉族人民混居,蒙汉文化间的交流增多,使得科尔沁人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放下马鞭、套马杆,拿起了锄头、镰刀开始农耕生活;定居生活使他们搬出了蒙古包住进了泥瓦房。但是他们又没有放弃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于是就形成了科尔沁人马鞭锄头一起拿、红茶奶茶一起喝、炒米馒头一起吃的蒙汉结合的生活方式。巴德巴和阿拉坦高娃的小说寥寥几笔生动地勾勒出蒙文化与汉文化相融的生活图画。
牛羊群已洒满牧场贪婪地嚼吃着鲜嫩的牧草。晚起的犁把头鞭打着耕牛赶往耕地,其后紧跟着背种子袋的年轻媳妇。村头出现了几位背着锄头的男人,他们懒洋洋地朝着刚刚催芽的田头走去。
——阿拉坦高娃:《土地》[1]
蒙古米子是科尔沁地区主要种植的粮食品种,炒过以后就成为科尔沁人最喜欢吃的炒米。经过相关文献记载,不论是科尔沁人还是其他地区的蒙古人大多都以炒米为主要食物。炒制炒米需要控制火候时间等,需要较高的技艺。因此,炒米的过程成了科尔沁妇女展示手艺的机会。蒙古米子不仅可以做炒米,还可以酿酒,同时又对治愈骨折具有神奇疗效。蒙古米子已经成为了科尔沁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与此同时,农业文化带来了各种米和豆子使科尔沁地区开始种植五谷杂粮。麦子是一种可以适应科尔沁气候的农作物,科尔沁人从很早便开始种植麦子,清明前十几天便种上,夏至之前要收割。科尔沁人将麦子磨成白面做成各种各样的面食,如:面条、馒头、饺子、馅饼等等。科尔沁人喜欢吃奶油拌炒米,同时馒头面条也是他们主要的食物。
科尔沁人酷爱吃酱和咸菜,这些显然是从汉族人民那里传入的。因为就连蒙古语中的酱咸菜都是从汉语里的酱咸菜音译过来的。科尔沁人常说吃饭可以没有菜,但是一定不能没有酱和咸菜。做酱的黄豆自己种,经过炒和煮之后团成馒头一样的圆疙瘩,等发酵好以后放到酱缸里加上适量的水和盐,大概三个星期之后就可以端上饭桌上了。吃饭的时候从自家菜园子里拔几棵大葱,蘸着酱吃对科尔沁人来说是世上最好的美味。到了秋天,菜园子里的芥菜、萝卜、豆角、黄瓜、茄子大丰收,科尔沁人就会将收获的蔬菜腌成咸菜,以备过冬的时候吃。芥菜疙瘩可以做成美味的芥菜丝,茄子可以做成酸茄子,就连豆角黄瓜和萝卜加上盐和水,经过腌制都能成为美味的小菜。科尔沁人善于学习,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自己的智慧装点着美好的生活。
蒙古人一般喜欢吃牛羊肉,吃青草长大的牛羊是传统蒙古族主要使用的肉类来源。但是科尔沁人的半农半牧生活使他们想要吃到新鲜的牛羊肉成为了奢侈。科尔沁人从很早便开始习惯吃猪肉。科尔沁地区本来没有猪,随着内地农民的迁徙,他们把自己赖以生存的猪、鸡、鸭、鹅等家畜也带到了科尔沁。猪的体型不是很大却有很高的产肉量,而且可以用粮食来喂养,非常适合在科尔沁地区喂养。在科尔沁地区,每家每户都养上两三头猪,从秋天开始便用玉米养得胖胖的,到过年的时候杀了,够吃一年了。因此,猪成为科尔沁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必需品。
科尔沁人不习惯喝奶茶,但是酷爱喝红茶。如博·照日格图在小说《黑土地》中描写的“下雨天抽的烟和第二杯茶等用洞房花烛夜也不换”[2]。科尔沁人不爱喝奶茶爱喝红茶也是受到了汉族人民的影响。在过去,科尔沁人赶着牛车,不舍昼夜的赶到现在的郑家屯等汉族聚集地,去购买一年要喝的红茶。由此可以看出科尔沁人对于红茶的喜爱。
从上述科尔沁人民的生活习惯可以看出汉文化对于科尔沁人民生活的影响。汉族人民的到来为科尔沁人民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而科尔沁对此吸取精华并且结合自身而不断改进并发展。从而形成了既区别于汉族,也区别于其他地区蒙古族的独特生活方式。
二、贸易活动的出现
早在17世纪末,汉族手工艺人就来到了科尔沁地区,影响了蒙古族传统的手工艺,培养了一批蒙古族手工艺人。随着手工艺的发展,蒙汉间的贸易活动开始逐渐增多。
然而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蒙古族对于贸易活动是非常反感的。首先,蒙古族自古以来的生活方式是传统的自给自足式的生活方式,贸易活动对于蒙古人来说不是必要的。他们的衣食来源于自己饲养的牛羊马,无需过多的进行贸易活动。再加上蒙古族认为贸易活动是通过说谎来交易而达到贸易目的,所以奉诚信为做人首则的蒙古人对于贸易活动是不屑的。这一点可以从蒙古语中“贸易”一词的词根为“谎言”而可以看出。
从很早开始,“就有一些小商小贩经常到科尔沁地区,把茶和铁锹等当地人们喜欢的东西卖给他们,换来一些牛肉和毛皮等东西拿到城里卖。这样既保障着农村的需要又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发展。从内地来的这些商贩为了能够在陌生的地方有个落脚处,常常会接近那些慈祥的老阿爸老阿妈,并认他们做自己的干爸干妈。”[3]402《蒙古贞阿爸》中娜布其额吉的干儿子图古斯朝克图就是这样一个小商小贩。然而面对这种既有益于农村又有利于城市的行为,蒙古贞阿爸则嗤之以鼻。蒙古贞阿爸对于特古斯朝克图做买卖这一事情表明自己的态度,说:“作为蒙古人,你做什么买卖!都是坑人的,跟过去地主恶霸剥削人民有什么两样!”[3]413蒙古贞阿爸认为最懒惰、奸诈的人才做买卖。勤于劳作的人哪有时间往外跑去骗人。这样的认识在赛音巴雅尔的短篇小说《骑手帖木儿和摩托手特格喜》中也有所描写。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贸易更加深入到科尔沁人的生活。面对优胜劣汰的社会,科尔沁人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与自我反思,逐渐改变已有的观点,努力适应着新的形势。然而这个过程是充满矛盾,时进时退的曲折过程。有些人接受了新鲜事物,有些人依然墨守成规,甚至在一个家庭里都有不同的认识。在仁钦道尔吉的小说《弯曲的路》中,扎马巴拉虽然身处新社会但脑子里却满是旧思想。他对于自己家中的财产没有分配的观念,只知道“家里的牛马不能卖……卖了多可惜啊?不卖在家放着还能生仔呢”[4]。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妻子萨木嘎,整天忙碌于家庭作坊与市场之间,希望能够以此来贴补一些家用。这种鲜明的对比展示了新思想的进步与旧思想的落后。
接受新思想最快的是一些年轻人。特·宝音的小说《再见,深夜》中描写了年轻人“他”从播放电视机到深夜十二点之间的心中所想。主人公“他”脱离旧思想,自己搞了一个运输队,而且具有很强的经营能力,是一个新型农民。小说中描写了“他”一夜的心理活动,展示了“他”彻底脱离了旧有的观念,积极接受新事物,同时具备践行的能力,是一个科尔沁新青年。
贸易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成为越来越不可缺少的部分,越来越多的人们改变着自己的观点。因此,科尔沁乡土文学中有很多作品都涉及到这一题材,也有一些作品专门写这个题材,并且做了深入的剖析。如布和德力格尔的小说《娃娃亲》里,新时代的年轻人杜冷对年轻的女掌柜车丽木格产生好感,并辞去自己的“金饭碗”到车丽木格的特产公司谋求共同发展。杜冷认为“做买卖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不会做买卖的民族是不健全的民族。”[5]年轻一代的科尔沁人在接受新事物、新生活,对过去传统的认为贸易可耻的思想进行了彻底颠覆。小说最后,杜冷的娃娃亲对象杜丽金退还定情信物,默认了杜冷和车丽木格才是美满的一对,暗示了传统的迂腐思想终会走向末路,新的思想具有抵挡不住的生命力。
如果说科尔沁人最早对于贸易活动的接受是被动的,对于外来文化的渗入他们无力阻挡,那么到后来他们逐渐适应接受并结合自身得以发展则是一个自觉选择的过程。科尔沁乡土文学在展现这一过程的同时挖掘科尔沁人民的内心世界,指明了科尔沁的未来发展之路,具有很深的思想价值。其塑造的接受新事物从事贸易的新青年形象是对传统的突破,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三、蒙汉语混合的叙述语言
正如严家炎所说,乡土文学强调人物的形象性、语言的表达性,而语言对于人物的形象性与作品的表达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尔沁乡土文学的语言别有特色。随着大量汉族人定居科尔沁地区,与当地人民交流逐渐增多,共同的生活圈使得他们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语言都受到了影响。科尔沁人从刚开始的不懂汉语到能听懂,再到会说甚至到最后出现了“前村的人把蒙语都忘了”( 博·照日格图《迁徙鸟》)而不得不用汉语交流的情况。新语言的加入是一个痛苦的脱胎换骨的过程,是一个扬弃、挑选与吸纳的复杂过程,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洗刷最终形成了科尔沁地区独有的语言表达形式——科尔沁方言。虽然其他地区蒙古族同胞认为这种方言不是标准的蒙古语,但它确确实实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孕育了科尔沁乡土文学。当翻开历史,就可以理解科尔沁是在渗透多种外来文化的情况下还能保留自己民族语言是何等难能可贵。是复杂的历史与社会原因导致了科尔沁方言这种语言的变异,所以应该辩证地看待它。正如著名蒙古学家苏尤格教授在《科尔沁草原上盛开的红彤彤山丹花》中所说:“方言这个东西不是花园中长出的‘野草’,而是新开出的‘鲜花’。”[6]这句话充分肯定了科尔沁乡土文学表现语言的“异样性”。
科尔沁方言受汉语言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汉语言词汇,将有些汉语词汇去掉其声调,直接运用到日常生活中,从而形成蒙汉语相混合的状态。听科尔沁人相互交谈,即使是不懂蒙古语的人,也能听出一两个词语,能猜到个大概的意思。科尔沁乡土文学正是以这种方言写成,作品呈现出别样的光彩。这种独特的叙述语言不受书面语言束缚、使人感到强烈的真实感,让人感同身受并给人以亲切的感觉。因此具有鲜明的特色、浓郁的地域性与强烈的表达效果,这也是科尔沁乡土文学的特色之一。
科尔沁乡土文学的语言不刻意追求规范的书面语,而是将口语直接运用到作品中。一些特定的名词不是按照蒙古语中的标准表达形式,而是将日常生活中为了方便而用的汉语名称直接写到作品中。如:沙发、当家的、掌柜的、司令、电话、经理、庄稼等等。虽然蒙古语中这些词都有相应的表达方式,但是科尔沁人民习惯于汉语的表达方式,科尔沁作家便把这样的表达方式直接运用到作品里,从而形成鲜明的特色。
还有一种是蒙汉语混合的字和词。就是指同一个字或者词里面既有蒙古语还有汉语。科尔沁人民在接受汉语的同时发挥才智,与自己的蒙古语相结合造出了很多便于使用而又具有很强表达效果的新的字词。如:“沏茶”中的“沏”字,词根是“qi”,后加上表示时态的词缀形成一个新的字,可以表示“沏茶了、要沏茶”等意思;“庄稼汉”的“庄稼”是词根,加上表示人的词缀以后变成“庄稼人”这个新字。还有如“领导干部”一词中“领导”用的是蒙古语,“干部”则直接用汉语;“土坷垃”的“土”用蒙古语,“坷垃”用汉语。除了这些还有仓房、不含糊、饽饽、烧饼等词语在科尔沁乡土文学中屡见不鲜。
有时候为了突显一定的艺术效果,科尔沁乡土文学会把一些日常生活中不常用的汉语词汇直接用到作品中。《青青的群山》中有一个人物叫梅姐。“梅”是她的姓,因其是一个可以“呼风唤雨”的大人物,所以大家都尊称她为“梅姐”。“姐”这个词在蒙古语里面有自己的叫法,然而作品中没有运用标准的表达方式,而是直接用了汉语中“姐”的表达方式,也是为了突显其大姐大的形象。
关于科尔沁乡土文学的叙事语言有一些人持反面观点。他们认为科尔沁乡土文学的叙事语言蒙汉语相间,对于蒙古语的规范有不利影响。然而正如著名作家巴德巴在他的小说《回光返照》的序文中所说:“有些同志在看过我的小说之后总是批评我在小说中使用了过多怪异的方言。而对于我这个离开了自己家乡的语言就写不出一个字的人来说,如果需要对我的文字做注释的话,恐怕得从题目就开始了。”[7]这一段独白可以说代表了所有科尔沁作家的心声以及他们的艺术追求。家乡话是他们从小开始说的语言,这并不只是因为习惯,而更多的加注了感情色彩。习惯的家乡话使他们的写作轻松顺手,更加贴切地表达他们心中所想,更能表现出他们对于自己的语言、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科尔沁乡土文学没有华丽的语言,而是质朴的家乡话,与科尔沁草原上质朴农民的品质是一样的。
参考文献:
[1] 阿拉坦高娃[M].通辽:内蒙古少儿出版社,2005:61.
[2] 博·照日格图.黑土地[J].启明星,1999(3):82.
[3] 巴·格日乐图文学作品选:二[M].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6:402.
[4] 仁钦道尔吉.弯弯曲曲的路.哲理木文艺[J].1990(2):66.
[5] 布和德力格尔.老紫檀[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83.
[6] 苏尤格.科尔沁草原上盛开的鲜红色山丹花[N].内蒙古日报,1981-10-31.
[7] 玛克斯尔,巴德巴·巴图孟和短篇小说集[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265.
(责任编辑王莉)
RegionalandEthnicCulturesinKhorchinNativeNovels
BAIYe-ru
(SchoolofMongolianStudies,InnerMongoliaUniversity,HohhotInnerMongolia010021,China)
Abstract:Inthisarticle,theauthor,throughanalyzingsomeworksoftheKhorchinnativenovels,examinestheethnicandterritorialculturesoftheKhorchinfromthefollowingperspectives:thechangeoflifestyle,theemergenceoftradeandthemixeduseofMongolianandChineselanguage.
Keywords:Khorchinnativefiction;regionalculture;ethnicculture
收稿日期:2016-01-16;最后修回日期:2016-04-06
作者简介:白叶茹(1986-),女,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蒙古族现当代文学研究。
文章编号:2096-1383(2016)04-0380-04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志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