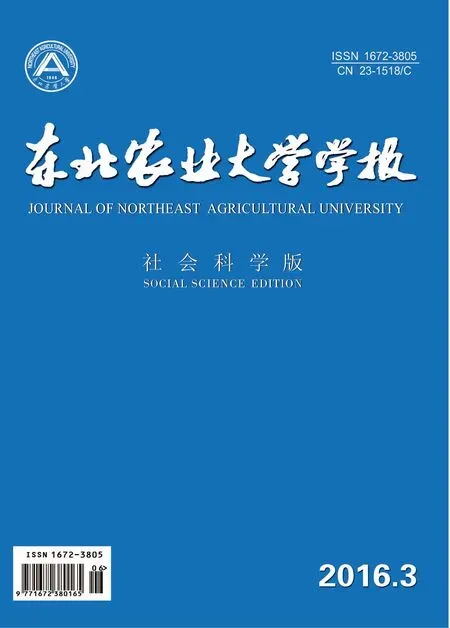大众文化中电视剧艺术的审美接受嬗变研究
董立娟
(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大众文化中电视剧艺术的审美接受嬗变研究
董立娟
(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视听艺术形式之一,深受观众喜爱。电视剧以较强故事性及复杂人物关系感染受众情绪,产生对剧中人物心理认同及对事件审美认同,从而获得愉悦审美体验。通过研究电视技术演进中,受众对电视剧艺术感知、认知与理性思辨的审美接受嬗变,提出电视剧创作者应树立精品创作意识及受众培养策略,使受众最终获得“净化心灵与精神启迪”的审美接受。
再现;表现;形而上;审美接受
从1958年我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开播至今,电视剧类型与数量不断增多,使受众精神愉悦的同时产生审美认同。“从创作角度而言,电视剧作为商业化语境中的产品,其创作不仅是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更是审美活动。”[1]随着电视剧关注度提高,其审美价值与受众审美接受成为学者关注与研究课题。电视剧审美接受研究分为以下层次:第一,以“某一类题材电视剧”为研究对象分析审美接受,如李城《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审美接受范式》、李姗姗《国内家族题材电视剧受众研究》等;第二,以“某部电视剧”为研究对象的审美接受研究,如杨洋《电视剧“武林外传”美学特征研究》,张卉《从接受美学看“奋斗热”与“金婚热”》等;第三,以“某一导演的系列电视剧”为研究对象分析,如骆雪松《李少红电视剧的审美探析》等。在电视剧发展历程中,随着社会时代背景改变及电视技术更新,电视剧艺术审美价值与受众审美接受不断变化,因此本文从理论角度研究我国电视技术演进中的电视剧艺术审美价值,从技术哲学角度讨论技术改变与受众心理需求关系,从艺术表现角度分析电视剧题材如何贴近当代受众心理,从美学角度切入受众对不同时代电视剧的审美接受,建立从“受众审美接受”到“创作者创作”互动研究框架,突破以往对某题材、某创作者及某部剧审美接受研究局限。在电视技术发展下研究电视剧艺术历史发展脉络,分析受众对于电视剧艺术审美体验的改变,从而促进电视剧创作者精品创作意识,树立电视剧创作正确价值导向,电视剧不仅应适应受众,更要培养不同时代受众社会鉴赏修养,避免产生浮躁与妄想的社会欣赏心态。
电视剧艺术审美体验对于电视剧创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目前,很多电视剧为获得高收视率,利用大尺度场景吸引受众关注。电视剧在创作过程中应将给予受众精神美感作为终极目标,不应取悦于娱乐化市场,成为完全娱乐化的商业产品。“若电视媒体只热衷于收视率带来的经济效益,放弃对艺术的审美化追求,会制造出一批缺乏深度、庸俗荒诞、哗众取宠的电视作品,进而使受众产生审美疲劳,甚至有损社会风气。”[2]凭借荒诞故事及夸张语言等刺激感官,形成低层次快感,无法给予受众灵魂愉悦,更无法谈及审美体验。“通过内在的感官的幻想力的形象世界也就活跃起来,也就是通过审美获得灵魂愉悦”,方为更高级的审美认知,电视剧艺术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客观社会关系、历史客观进程的反映,也是人的主观世界——思想、情感、意志、愿望的反映[3]。
现代社会中,电视剧创作观念发生较大转变,电视剧艺术不再是生活的再现艺术,也不仅是表意性语言符号,而是后现代语境下具有文化功能的社会角色。此变化来源于电视剧艺术赖以生存的电视艺术文化哲学与美学语境改变及电视剧艺术文化表现中内部张力给予受众的审美接受。
电视剧艺术中,受众心理接受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视听双重直观感受,其次是视听带来的丰富联想,最后则是艺术接受同时产生对自身生活的联系与想象,三层次相互作用与交融,在故事叙述声画中,受众通过视、听觉感知事件发展和人物情绪等表现出的内在节奏,并随之思考生活处境或回忆过去,从而获得精神满足。
不同年代电视剧审美认同与体验不同,从最初黑白影像电视剧对英雄人物的心理趋同,到二十世纪八九十时年代随着电视剧人物类型增多形成对人物类型的心理认同,最后到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因情感问题复杂性与社会性问题增多,受众沉浸感日益增强,易受到剧情感染,甚至融为一体,从而产生图像优于概念、感觉优于意义的感觉美学。与“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境界相同,屏幕内接受电视剧剧情安排与人物认同产生情绪感知,屏幕外通过个体人生经验产生认知迁移,从而获得精神满足。
一、黑白影像中的“再现”:受众“入乎其内”的情绪感知
随着文学、戏剧与电影艺术发展而形成的电视剧艺术,从开始即被打上现实生活烙印,早期电视剧艺术创作理论支点在于真实再现生活,因此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利用黑白影像播放的200余部电视剧均贴近现实生活,并反映人的情绪,如《女状元》《党救活了他》等。其中电视剧《党救活了他》将上海钢铁厂工人邱财康的真实事迹搬上屏幕,受众通过屏幕见证新时代英雄,为之感动并竞相学习。
从黑白影像屏幕上看到生活中鲜活人物原貌与事件,使受众感受到电视剧可准确再现与模仿客观世界,电视剧与现实间产生对应关系,契合电影理论家巴赞提出“再现论”语言观念,他认为“语言能够准确模仿与再现客观世界,同时现实与这种语言一定具有特定对应关系。”在众多艺术门类中,电视剧艺术活动影像最接近并能够准确复制生活场景,在电视剧中利用视听语言符号表达的故事类似于生活再现,因此“再现”被赋予“表征”“描绘”“复制”“模仿”等内涵。在7吋、9吋等黑白屏幕上,因观影环境与受众生活处境影响,只能产生“入乎其内”的情绪感知。
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曾言:“在高度分化并充满张力的范围内,哲学与各种科学之间存在不同水平上的亲和关系,其中,有些或多或少依赖于哲学思想,其余则多多少少可以接受这种思想的提升。”[4]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电视剧的“再现”非简单呈现生活,而是准确反映社会认知,因此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电视剧内容基本侧重于政治思想教育,大多反映现实生活,讴歌新时代,宣传新思想,赞颂新人物,既对历史、时代和社会做出贡献,又显示出全新艺术样式的生机。
在艺术表现形式较匮乏年代,电视是家庭奢侈品,受众对电视剧艺术内容的接受仅处于“入乎其内”状态。“入乎其内”即受众置身于剧情中,感受剧中人物情绪波动,获得感官满足。1975年电视剧《神圣的职责》,描述了六十年代投身祖国农村与偏远地区建设的青年生活,受众通过视觉获得感官愉悦,但局限于具有共同经历受众的情绪感知与还原,由于欣赏性限制与艺术性表现力较弱,多数受众难以接受。
二、彩色荧屏中的“表现”:受众“出乎其外”的认知迁移
随着电视技术发展,1978年电视剧《三家亲》通过彩色荧屏播出,以此为契机,我国电视剧发展进入新阶段,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1979年到1985年,全国电视机总量从485万台增长到5 000万台,电视剧创作数量也从央视播出的19部增长到全年制作量1 500集,受众人数达到全国总人数的50%,电视剧艺术创作风格及题材更加丰富。
1979年,上海电视台播放了以张志新烈士为原型的电视报道剧《永不凋谢的红花》,张志新平凡而伟大的形象扎根于受众心中。随后电视剧创作百花齐放,描写动乱后工厂改革的《乔厂长上任记》(1980),描写知青生活的《蹉跎岁月》(1982),轰动全国的知青返城故事《今夜有暴风雪》(1984),失足少年在工读学校的故事《寻找回来的世界》(1985)等,在彩色荧屏中大放光彩,引起受众观看热情。新时期刻画英雄形象的《冠军从这里起飞》(1985)、关于新农村生活的《冤家》(1986)、展示军警风貌的《便衣警察》(1987)、《篱笆·女人和狗》(1988)与《家·春·秋》(1988)、表现高中学生青春生活的《十六岁的花季》(1989)等,使受众在屏幕中获得精神愉悦。1983年《西游记》中幻化的场景,唐僧与孙悟空等师徒四人不畏艰辛的取经过程,即使是既不精细也不伶俐,且自作聪明的精细鬼和伶俐虫这样的小角色均生动呈现在受众面前,成为受众心中经典。12集的《便衣警察》通过屏幕塑造出有血有肉的警察形象,使受众了解警察也是普通人,也会被人误解,但他们对于工作的忠诚,保卫人民安全的责任感永远不变,正如主题曲“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这部剧激励受众坚持信念,永不言弃,从而产生精神满足与快感。“无论是联想还是净化,归根结底均为审美主体借助艺术作品,舒缓、疏导和宣泄过分强烈的情绪,恢复和保持心理平衡,从而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快感即美感。”[5]
彩色荧屏中的“表现”不同于生活“再现”,电视剧艺术审美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生活中真实色彩还原到彩色屏幕上,使受众感同身受,从情绪感知中逃离,伤感、快乐、愤怒、同情等情绪触动受众灵魂,甚至使其幻化成剧中人物,进入忘我的虚幻世界。电视剧艺术在反映社会生活时,已超越“再现”生活范畴,重在“表现”生活,因此不再是复制原本生活,是对社会生活的艺术升华,受众对电视剧审美认知也发生质的飞跃。
受众作为电视剧接受者不再被动接受,而是积极调动生活经验、认知水平欣赏电视剧,并通过联系与想象,完成认知迁移。“认知”使电视剧艺术具有鲜活生命力,受众“出乎其外”的认知迁移,是将感情体验、移情联想与电视剧剧情和人物相互交融且相互作用,形成跳出屏幕与故事外的主体情感意向表现。电视剧艺术“会在那些具有特定欣赏能力者身上激起一种‘探照究竟’的潜在创造力量”,而且“影视像一束探照灯,照射到一个全新方向,昭显世界中被无知、冷漠掩盖的角落,也将我们内心隐藏的情感召唤出来。”[6]
《渴望》(1990)、《编辑部的故事》(1991)、《北京人在纽约》(1992)、《过把瘾》(1994)等电视剧召唤受众内心情感并产生情感共鸣。90年代初收视率超过90%的我国第一部室内剧《渴望》,讲述善良普通工人刘慧芳的情感与磨难。宋大成默默守护的爱,王沪生与刘慧芳短暂的婚姻均使受众在观看电视剧时思考自身命运,引发对人性与情感的思考。受众不再是默然的旁观者,而是在电视剧使物质精神化的“表现”中思考、感悟、理解,从而与剧情形成通感。
在电视剧故事中,受众会充分调动生活经验与思想,将电视剧事件和角色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联系,在“通感”基础上产生“移情”效果,释放情感,延展到画框外,最终产生丰富联想。从屏幕故事中解放出来,是客体剧情与主体受众心理的联通反应。“影视作品为受众提供代偿性满足,使人类能够尽情倾泻情感、憧憬和迷醉,从而使心理从不平衡走向平衡,由不和谐变得和谐,身心进入愉悦状态。正如精神分析学观点:“艺术作为‘白日梦’,可以替代性地满足人的潜意识欲望。”[7]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围城》《和平年代》《刑警本色》《苍天在上》等剧热播,具有不同经历的受众等凭借生活体验与体会,产生不同思想认知,获得不同生活启示。
三、大众文化中的“体现”:受众“形而上”的理性思辨
二十一世纪后我国电视剧进入发展繁荣期,电视剧制作数量越来越多,题材、风格、样式越来越广,思想性越来越强,观赏性越来越高。电视剧艺术进入大众文化视野,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电视剧,在本原意义上,是一种特殊的客观存在的人类社会精神文化现象,是一种新兴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是艺术的一个品种。”[3]作为具有商品性、流动性、通俗性、娱乐性等大众文化特征的电视剧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特殊文化社会行为,在文化角色中起着重要文化构建与文化行为作用。
2001—2006年,军族题材电视剧引起受众关注,特别是反映改革后军队建设的《女子特警队》和《DA师》引起广泛思考,时代感较强的反腐连续剧《大雪无痕》考虑受众观看心理,艺术化处理严肃反腐题材,将深刻寓意与娱乐化情节融合,以道德伦理塑造清官形象。老字号品牌世家故事《大宅门》、平民生活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心理剧《冬至》、家庭剧《金婚》、青春剧《奋斗》、军事题材剧《亮剑》、谍战剧《潜伏》等,均获得较高收视率,这些电视剧以现实主义手法探讨七八十年代多子女的婚姻家庭故事,九十年代人的家庭伦理,二十一世纪初年青人创业与奋斗等。
英国学者汤普森认为文化是一种“结构化背景中的象征形式”“文化概念可以适当地用来一般性地指社会生活的象征性质,指社会互动交换象征形式体现的意义特征”[8]。任何一种文化内在精神气质均需要以“作品”形式表现出来,电视剧作品呈现出精神即为大众文化表现。大众文化中电视剧艺术成为受众生活必不可少的娱乐形式。电视剧创作者将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的故事通过电视媒介传播给受众,因此具有大众文化本质特征,是由群众创作,与生活实际相关,并对社会群体产生影响的文化现象,电视剧在大众文化中起导向作用。“体现”是受众观看电视剧后,个体或公众集体,经过审美接受后表现出对其社会生活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
“电视剧本身蕴含大量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思想文化艺术信息,蕴含丰富历史内容,这些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把握电视艺术现象的基本维度和重要线索。”[9]处在社会化进程中的受众,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对电视剧业余生活需要和欣赏需要越来越强。受众通过电视剧艺术作品认识客观世界,是受众的精神需要。
电视剧不再是一种以表意性语言符号再现生活艺术,而是具有社会实践功能的文化行为。受众从生活到电视剧,再从电视剧回归生活,形成“形而上”的精神反映。如2007年《奋斗》描述“80后”对事业、婚姻与生活的困惑,引起“80后”共鸣,激励“80后”群体为了事业、爱情与婚姻,走上“奋斗”之路。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认为法则无形,称为形而上;器用之物有形,称为形而下。电视剧凭借画面与声音有机结合,通过演员表演呈现出故事与剧情为形而下,受众通过人、物、景、光、色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段看到的及对电视剧的审美接受与体验是无形的,受众观影后内心情绪变化因个体生活经验、感情体验与丰富联想而产生的差异性变化,不同于早期机械地复制再现的情绪感知,也不同于表现生活后的认知迁移,而是个体审美差异性较大的“形而上”的理性思辨。电视剧艺术中对于剧情的感知,使受众情绪变化,通过认知迁移对主题产生深刻理解,在感知与认知基础上形成理性思辨,进而对电视剧艺术作品形成审美批判,形成受众更高级审美认知,即大众文化中电视剧艺术角色的最终体现。
受众对电视剧哲学领悟与理性批判是理性思辨层面重要内容,受众接受画面与声音中演员的表演等多重视听刺激后,与大脑感知的经历发生内容匹配,结合内心感受形成价值判断与理性思考,与电视剧剧情匹配获得精神导向,产生共鸣,最终形成理念认同。多次循环往复的刺激与作用中,受众经历具有重要参与作用,影响受众理性思辨。不同年龄段观众观看一部剧,但理解与精神反馈不同,如时下热播电视剧《欢乐颂》与《守婚如玉》。《守婚如玉》一定是四十多左右,兼顾事业与家庭的受众更能够感同身受的故事。《欢乐颂》则可引起“80、90后”的生活同感。由理想式《奋斗》到现实型的《欢乐颂》,十年间受众在内心感情激发、情绪生成和扩展的过程中,审美认知也发生变化。同样的“80后”二十几岁经历着理想式的《奋斗》带来的青春幻梦般拼搏,三十几岁经历着现实型的《欢乐颂》带来的生存问题思考,使受众体会出不同时代电视剧带来的艺术性深刻内涵和主题,进入对电视剧艺术表现出的精神主旨“形而上”的理性思辨,从而思考现实生活。
哲理即电视艺术作品中深沉、含蓄且不外露的思想。哲理性可提升电视艺术思想高度,引起受众对时代、社会、人生的追求与探求,使之浅移默化、心甘情愿地接受作品思想的启迪与教益[10]。这种哲理性通过画面中内容与声音氛围配合,产生欣赏主体即接受者的感知,并进入认知层面,主体主动参与,引起较强审美注意的审美态度变化,从而完成对电视剧艺术哲理性思考的审美认知。只有充分调动接受者审美注意,方可引发其对电视剧艺术哲理性的思考。韩国电视剧《太阳的后裔》让受众对军人与医生形象肃然起敬,剧中多次重复军人角色话语“军人必须服从命令。我是军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多次重复医生角色话语“我庄严宣誓把我的工作生涯奉献给人类,我会超越人种、宗教、国籍、社会地位,只对患者尽我的义务”“我是医生,生命是有尊严的。我认为没有任何价值或者理念可以凌驾于生命之上……”,使受众深刻理解军人与医生职责,甚至产生从军或从医想法。在受众理性思索基础上结合感性认识,加深对电视剧内涵的哲学领悟,满足受众精神愉悦,获得“形而上”的理性思辨。
四、结语
电视剧艺术审美认知在电视技术演进变化与艺术完善中发生嬗变,从黑白色调的物自体中受众充满感性认知,到彩色屏幕上多种生活方式呈现,使受众主体产生复杂理性思考,直至当前电视剧艺术本体思想内涵更接近于现代人生活场景与原貌,进入人类生活内部,以理性批判角度审视认知后现代社会语境下的电视剧艺术创作。
“象征性实践”电视剧话语生产,不仅建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还可以建构生活模式、处世观念、知识体系,甚至个人信仰。电视剧创作与社会文化建设紧密相连,是彰显时代精神与书写人类生活的重要手段[11]。创作者把握受众审美接受,满足受众审美需求,可使电视剧艺术永葆生机。但满足并非迎合,2015年电视剧生产总数为395部,集数为1.65万集,但质量堪忧,“雷剧、神剧、狗血剧”较多,缺乏来自于生活的原创精品,很难引起受众情感共鸣,更无法上升到受众高级审美认知层面。研究受众审美认知意义在于,创作来源于生活的电视剧艺术作品时,要体现时代精神与人文文化,而非仅迎合受众喜好。电视剧创作者开始将视线转移到受众身上,作为电视剧商品主要消费者,受众对电视剧事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12]。因此电视剧创作者在创作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考虑视像性下受众的审美需求。电视剧艺术作为大众文化艺术形式,受众群体广泛且复杂,必须最大限度满足受众精神需求。较接近生活的平民剧比玄幻剧和抗日神剧更易使受众接受。“现实题材平民剧是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再现,使其呈现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审美品格。对这种审美品格的追求,应当是所有现实题材平民剧创作者的终极目标。”[13]作为具有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电视剧艺术,必须结合受众接收方可完成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的传播过程。受众文化心理结构重构即电视剧唤醒受众游离情感,从而产生对现实生活的理性思索。
其次,注重培养受众审美期待,创作电视剧精品。受众审美期待可以培养,但不能一味迎合、批量生产,导致电视剧艺术“媚俗”化。电视剧创作者通过“审美化评价”方式,在电视剧作品中体现“价值意识”,通过移情作用,潜移默化影响受众[14]。随着电视技术发展,应培养受众对电视剧艺术更高级的审美认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受众对电视剧审美认知未引起创作者足够重视及学者广泛关注,电视技术进步下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审美差异研究尚属初步探讨阶段。
最后,加强电视剧艺术创新意识。创新意味着避免模仿,电视剧艺术是一种文化现象,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发展与改变,具有较强社会性与时代性。电视剧艺术创新意识是保证电视剧作品质量前提,关系到能否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更是电视剧艺术作品保持生命力的关键。
电视剧艺术以屏幕表现的艺术化手段,呈现出“心灵辩证法”的精神力量,使受众从个体生活到剧情,再从剧情到自我生活,经历从“入乎其内”情绪感知表层到“出乎其外”的认知迁移,最后进入“形而上”的理性思辨,产生理性积累,获得高层次审美认知、接受与体验,形成新的审美意象。创作者要充分考虑电视剧艺术社会角色,不应陷入“娱乐”中无法自拔,要让受众获得“净化心灵与精神启迪”的审美体验。
后现代语境下电视剧已非简单再现生活的艺术,而是打上具有文化功能符号的艺术文本。这种艺术符号与精神分析学等理论具有间互性,而这种文本更要从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维度研究。对于电视剧受众心理学研究应加大力度,电视剧如何吸引受众关注,满足其审美期待,创作精品,是后续研究重点,在“娱乐消解文化”困境下如何树立电视剧创作创新意识,面对当前电视剧生产类型多样化、数量高产化、内容娱乐化现状,如何实现自我突破,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1] 佟小娟.电视剧艺术创作的审美思考[J].青年记者,2016(3).
[2] 王玉玮.当前电视剧收视率与品质之间的错位及其思考[J].中国电视,2015(6).
[3] 曾庆瑞.中国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4] 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5] 凌继尧.美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周安华.现代影视批评艺术[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7] 钟友循,何宇宏.影视与影视鉴赏[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
[8] 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高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9] 曾庆瑞.电视剧原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10]高鑫.电视艺术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1]金丹元,周旭.类型·审美·资本·媒介:对2014年中国电视剧研究的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3).
[12]李丽.媒介娱乐化狂潮下军事题材电视剧创作探究[J].吕梁学院学报,2015(4).
[13]秦俊香,字宁宇.论近年来现实题材平民剧的审美品格[J].中国电视,2015(9).
[14]付李琢.电视剧艺术生产的价值取向研究的逻辑起点[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2).
J901
A
1672-3805(2016)03-0073-06
2016-05-16
董立娟(1973-),女,东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影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