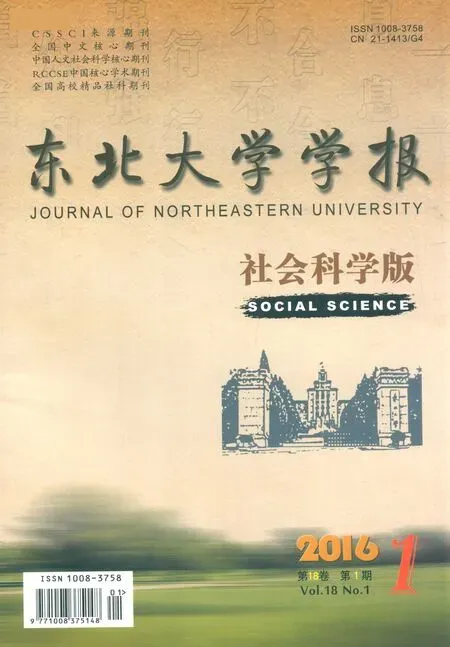“作者之死”的再审视
史 凤 晓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2)
“作者之死”的再审视
史 凤 晓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100872)
摘要:法国思想家罗兰·巴尔特在《作者之死》中宣判了作者的死刑,其思想影响深远,学界就支持还是反驳这个观点争议不断。但是若将《作者之死》与巴尔特其他的作品对比阅读来厘清这个观点涉及到的作者、语言、文本与读者这些核心概念,会发现它的产生、发展轨迹及其中的变化与反复。这与他的思想发展与变化,把玩文字的游戏创作风格有关,也有人类思想发展的必然性。“作者之死”的思想脉络包含着比学界对“作者是否死了”的争议更丰富的理论内涵。将“作者之死”放入他更大的思想框架中和宏观的历史背景下,有助于对此观点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形成更客观、更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作者; 文本; 语言; 读者; 罗兰·巴尔特; “作者之死”
——————————
1967年,法国思想家罗兰·巴尔特在美国一家先锋杂志《阿斯彭》(Aspen)上发表了论文《作者之死》。论文篇幅不长,只有大约2 500字,但影响深远,争议不断。在文章中,巴尔特按照自己的逻辑,自古至今追溯了作者的出现、发展与削弱。他援引马拉美、瓦莱里、普鲁斯特及超现实主义等的创作特点、创作观,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以及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步步为营,将“余威尚存”的现代作者驱逐出文本,把作者的死亡提高至对抗上帝、理性、科学和法律的革命之举,文末一句“读者的诞生要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1]1470宣判了作者的死刑。寥寥数页的文章在中西文学批评界及其他人文学科领域所引发的一场革命持续至今。
其影响和争议在4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可见。有些学者为其革命性和前瞻性感到兴奋。皮特·拉马克证明了巴尔特观点的合理性[2];安德鲁·贝内特认为巴尔特的《作者之死》让对于作者的讨论热烈起来,把作者问题带到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前沿[3]。有些学者为其极端性捶胸顿足,批判,哀叹,呼吁;否定作者的死亡,召唤作者的回归。肖恩·柏克从巴尔特援引的例证出发,一一动摇其准确性。他认为瓦莱里是一直赞同作者的权威,超现实主义虽然影响了几个作家,但没有在文学史上留下任何影响[4],他从巴尔特立论的根基上质疑、动摇了“作者之死”的合理性。哈罗德·布鲁姆指出“作者之死”“隐含恶意”[5]。国内学者多认为巴尔特观点极端,大都是论证“作者之死”的荒谬与危险。肖锦龙对“作者之死”进行了大力批驳,认为只要文学存在,作者就不会消亡[6];李勇把巴尔特与福柯的作者观树为靶子,一一攻破,然后呼吁作者的复活[7];刁克利不仅论述了《作者之死》所引起的各种争论,回顾了作者一直被责难的历史过程,还呼吁并且提出了作家重建的必要性和方向[8]。这些研究与争议启发了认识“作者之死”这个观点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方向,但是也容易夸大巴尔特的“恶意”,从而疏忽巴尔特在发展这一思想过程中的其他内容。所以厘清巴尔特对这个观点及支撑它的一些核心概念的发展,了解他的创作风格及思想变化对于客观认识这个观点是非常必要的。
巴尔特本人说过他自己写的东西大都是游戏性质的,如果攻击他,那就什么都没有了[9]。汪民安在《谁是罗兰·巴特》中用很大篇幅解读了巴尔特思想与创作中的游戏性。徐岱对巴尔特的研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巴尔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语言/文本爱好者,把玩语言成了他从事人文学术写作的最大动力[10]。同时,对巴尔特来说,文学批评不是去发现作品中预设的意义,评论文字本身应成为一篇独立的文本、一部小说。他的S/Z便是对巴尔扎克的《萨拉辛》游戏似的批评阅读,更像是一种重写。巴尔特这种游戏式的解读独一无二、不可复制。他是一个随笔式的文学批评家,亦是一个文学批评式的随笔作家。他把自己的理论融入自己的写作、阅读与批评中,亦庄亦谐地构建了自己的理论。后人再难以对其作品和理论来一次S/Z式或者《米什莱》式的批评与分析。了解他的创作和理论构建风格,有助于对他的思想尤其是看似极端的思想进行更客观的理解、阐释与批评。对“作者之死”尤其如此。
在推论“作者之死”这一观点时,巴尔特打着语言、文本和读者的旗帜将作者驱逐出去,宣告了“作者之死”。他借助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中对语言的论述,使语言取代了作者的主体性。在自己学生克里斯蒂娃互文本的启示下,他不遗余力地发展了自己的文本理论,让传统的作者成了一只“自动模仿已经存在的抄写姿势”[1]1468的手。他借助文学四大要素之读者彻底埋葬了作者。然而这其中,一如他的游戏作风,不无悖论,而这些看似矛盾之处也恰好是其趣味和思想魅力所在。笔者将以《作者之死》为主,兼顾《写作的零度》《米什莱》《批评与真理》和《文本的快乐》等作品,循着巴尔特的逻辑,围绕语言、文本和读者三个方面,来梳理 “作者之死”的产生、发展与矛盾之处。无意做其拥趸,更无意批驳,只希望能通过“转述的快乐”实现巴尔特所言之“阅读之快乐”。
一、 作者之于语言
语言是巴尔特消解作者主体性的重要工具。巴尔特在《作者之死》中援引马拉美、瓦莱里这些削弱、动摇作者中心地位的作家时,他们的语言观是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马拉美认为是语言在说而不是作者在说;瓦莱里重视语言,嘲笑作者。除了这些文学实践中生动的例子之外,巴尔特还借用语言学的原理来助阵。他认为语言学提供了摧毁作者最有价值的分析工具:言语活动中只有“主语”,没有“人”,而且作者只不过是执行写作动作的人,除此之外,无他。至此,作者的神圣性被冰冷的语言消解。巴尔特所钟爱的语言势不可挡地取代并且埋葬了作者这个昔日的王者。作者消失、逃逸于字里行间,语言的所指也消失,只剩了一系列的能指符号。巴尔特这种语言本体论很大程度上是受索绪尔的语言学影响。上个世纪40年代,格雷马斯向巴尔特介绍了语言学的知识,索绪尔的理论让敏锐的巴尔特豁然开朗,并将索绪尔的语言学观应用于自己的文学批评中,成为结构主义的巨匠。
在1953年创作的《写作的零度》中,巴尔特以语言学为基本出发点,倡导语言的零度、写作的零度和作者的零度即不介入。《写作的零度》是以萨特的《什么是文学》为创作背景,萨特在这部作品中主张文学介入。巴尔特在对写作的定义中指出“语言结构含括着全部文学创作”[11]7,作者无法介入,无法从中汲取任何东西。文学不是社会、阶级或作家的事,不是主体左右的作品,“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11]55。在这本书中,巴尔特明确提出把写作从主体的意识观念、社会的政治形态等外在因素中抽脱,将之重新归还给原本就是属于语言的财产。此外,语言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系统,不是作者控制语言,而是语言控制和制约作者。这里的字词是百科全书式的,所有的意义都包含其中。作者可以从中选择自己的表达方式。在这些地方,名词可以不加冠词而存在,并被引向一种零度状态,其中蕴含着过去或未来的一切规定性。可以看出,作者的主体性已经完全让位于语言。
巴尔特以语言形式的美学去代替价值伦理美学,事实上就是消解了主体。文学不再是主体对社会、人性等问题的关注,文学成了语言问题。那么在这个形式的神话里,作家不可避免地将成为其囚徒。作者的主体地位及其社会参与意识为语言的牢笼所囚禁。的确,作为理性的一种表现,人的主体性一直与语言相生相伴。当语言本身在解构的审视下不能自保其指涉客观事物的稳定性时,主体性便显得无枝可依、摇摇欲坠了。人丧失了主体性,转而膜拜无所不在的语言桎梏。语言曾是人的主体性的载体,而今却成了克星。当语言和风格只为其本身存在,作者与社会规则等外在因素被排除后,作者也就消失在这些符号中了。
然而,巴尔特不是让语言奴役并且埋葬所有作者的。爱尔兰唯美主义巨匠王尔德在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时,依然能找出理由钟爱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巴尔特有一样的矛盾性。他洋洋洒洒用语言的大旗将作者消解之后,在1971年创作的《萨德,傅立叶,罗犹拉》又将萨德、傅立叶、罗犹拉等作家称为“语言的创建者”[12]6。他认为他们的创作语言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在此处,被巴尔特驱逐并宣判死刑的作者俨然又有了王者归来的气势。
似乎在巴尔特的作品中总是存在着峰回路转,读者永远无需绝望或过于执着。消匿于语言中的作者会转身一变又成为语言的主宰。这就是巴尔特。他的矛盾性无处不在,在S/Z中,他把《萨拉辛》切割成561个单位,不亦乐乎。到最后《萨拉辛》不再是巴尔扎克的,成了巴尔特的,他硬是把这一可读性的文本给分析成了可写性文本,肯定了切割的必要性和意义。然而在《罗兰·巴尔特自述》中,他却无奈地说:“从前想必是美妙的;而后来,这种举动就变得疯狂了:郑重地划定一种界限,但这种界限又立即荡然无存,只剩下切割的一种智力余感”[13]55。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声称巴尔特认为作者从属于语言或作者消失于语言的无限延宕与绵绵无期中。同样我们也无从断言巴尔特认为作者从属于文本或将作者从文本中驱逐出去。
二、 作者之于文本
巴尔特在《作者之死》中用文本中心取代了作者中心,将作者边缘化,否定了作者之于作品本源性的意义。他认为“现代书写者”[1]1468(他用这个词取代传统的“作者”)与文本是同时产生,不存在传统文学史中的先后、父子关系。他借用语言学的理论指出所有的文本都是即时写作。在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本理论的启示下,巴尔特认为文本是来自无数文化中心的系列引用,也就是说,完全没有作者的原创之说。作品只是作者对早已存在文本的引用和模仿而已,而且作者只能将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引用混合在一起。他对之无能为力,而且也无以借此表达自己。因此,文本也不再承载作者的激情、幽默、感觉和印象等,而是成为了一本词典,是对永无终点、无限延宕的系列符号的模仿。巴尔特用文本的概念取代了传统的作品概念。对他来说,给文本一个作者,相当于终结写作本身。在此概念下,作者是可有可无、最好不要存在的一个角色,失去了先前与作品的天经地义的关系。
在1966年(《作者之死》发表的前一年)的《批评与真理》中,巴尔特提到了作者身体死亡的重要性。一方面暗指了索邦大学只能研究去世之后的作家的规定。索邦大学不允许写关于尚在世的作家的论文。要等到作家去世之后才可以,如此才可以“客观”地对待,这很像我们文化中的所谓盖棺定论。另一方面巴尔特也藉此指出作者身体死亡的意义是作者在文本上的署名可以变得不再真实,有作者署名的作品也因此可以成为无作者署名的神话。巴尔特认为卡夫卡之所以相信后代人对某个作者的评价比作者的同代人更准确,原因就在于作者的死亡。这样可以把作品从作者的意图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发现作品的神话性。除去了作者的署名,死亡找到了作品的真理,即“谜”[14]。简言之,作者身体的死亡可以模糊作者的本源性意义,从而彰显写作即文本的神话性。
一年之后,在《作者之死》中,巴尔特就宣告了作者在文本中的消亡。在1970年的S/Z中,巴尔特把文本分为可写性和可读性文本。其中可写性文本就是读者可以介入进行再创造的文本[15]4。在这样的文本中,作者不再是传统文学批评中的神祇性的角色,不再是文本“所指”的所在。而且巴尔特在本书的开篇也提到自己不会研究巴尔扎克的传记资料,也不会关注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探究的不是作品中的人物、主题等,而是借鉴摄影机的技艺,如同以慢镜头拍摄下关于《萨拉辛》的阅读过程一般,写下自己对这本小说的阅读。此时的作者相对于文本而言已是无足轻重的角色,渐渐被巴尔特驱逐出文本。文本所谓的意义也另换所在。“作者之死”带来文本与读者的狂欢。文本的意义不再是神学般的唯一,也不需要批评家与读者对之进行神学般的解读与阐释了。文本意义的多元性是巴尔特的落脚点。
作者之死不是巴尔特作者观的终结。他也不是如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中所言只是重复上帝、人和作者的死亡[16]。作者的死亡并没有让巴尔特停止对这个角色的探讨。在1971年的《从作品到文本》中,巴尔特说“文本”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改变了作者、读者和观察者(批评家)的关系[17]。这个观点其实是暗许了作者的存在。在同年的《萨德,傅立叶,罗犹拉》中,巴尔特提出文本的快乐包含着作者的一次友善的回归[12]8。他继而对这个回归的作者进行了一番解释,他声称回归的作者不是我们的制度(文学、哲学教会话语中的历史和说教)所认同者;他甚至不是一部传记的主人翁。来自其文本和进入我们生活的作者并不具有同一性,他只是一个诸 “魅力” 之集合,某些最小细节的位置,但确实是某些生动的小说光芒的源泉,一首不连续的友善诗篇,然而在其中我们却比在一部命运史诗中更肯定地读到了死亡。他不是一个(公民的、道德的)个人,他是一个躯体。如果说此时,巴尔特还在坚持作者之死观点的话,那到了1973年的《文本的快乐》中,他已经公开宣称在文本中他渴望作者的存在,“作者可以出现在他的文本中”[18]。而且在早年写自己所钟爱的作家、历史学家米什莱的传记《米什莱》时,作者也把米什莱个人的习性与其文本紧密相连。比如他提到了米什莱总是抓紧每一秒的时间来写作的习惯,并将之与米什莱因不断的间歇性头痛而产生的对身体与生命的担忧联系起来。他还发现米什莱对血的厌恶也反映在文本中,而且每每论述米什莱某一习性,巴尔特总是习惯性在后面附上米什莱的部分文本。在此处,读者难免会质疑这个巴尔特是宣称作者之死的那个巴尔特么?
无论是巴尔特把作品演变成文本,还是把作者演变成抄写者或者最终将其驱逐出文本,都是其解构之举,也是其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过渡的思想痕迹与转变。在S/Z的开篇,巴尔特讽刺了自己之前献身的结构主义:据说有的佛教徒经过修行能在一粒豆子中看到全部的风景[15]3。在其论战作品《批评与真理》中已经略显其过渡之意,待到《作者之死》宣判作者的死亡、S/Z把巴尔扎克《萨拉辛》切割得支离破碎之时,巴尔特已经成为一个十足的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者。这其中的转变可以按照另外一个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在《谎言的衰朽》中所言,“谁要前后一致的?”[19]
所以,当他在《作者之死》中高度赞扬了读者的地位,并宣布“读者的诞生要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时,我们必须明白,关于读者与作者的关系肯定不会如巴尔特所宣称的这样一种简单的对立。
三、 作者之于读者
读者是巴尔特驱逐作者的最后一道王牌。在《作者之死》的最后,巴尔特认为希腊戏剧中,总是存在一个角色对另一个角色的误解,这些误解是悲剧之源。他指出只有读者(此处是指观众)才能明白剧中词语的双重含义。从此得知读者的重要性。巴尔特认为,文本的整体性不是存在于其起源(作者)而是存在于其目的地(读者)。文本的解释不再由作者负责,读者成了文本意义的解读者。巴尔特继而指出他的读者并不像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作者那样需要考虑其生平、心理、传记等因素。这个读者是开放性文本多重意义的聚居之所。在此处,读者被巴尔特寄予很高的期望。按照这个逻辑,宣判作者的死亡、推翻作者的神话是最能彰显他对读者的重视和关怀的方式。在此时,读者的诞生已然湮灭了作者的形象和地位。
1966年,巴尔特在文章《写作,一个不及物动词?》中提出的不及物写作就切断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写作只是“不及物”的写作活动,没有交流的目的。在《作者之死》中,读者对作品的阐释再也与作者无关。两者甚至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一个的诞生必须以另一个的死亡为代价。在随后的《从作品到文本》中,巴尔特指出,读者的无限可能赋予了文本无限可能的意义,读者的每一次阅读也是对文本的再创造。巴尔特对于读者这个角色的侧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意欲突破结构主义封闭文本的特征,颇具解构色彩。解构作者的权威,解构文本的统一主题。童明指出根据巴尔特在《从作品到文本》的逻辑,可以把巴尔特的读者分为两种:一种是为阅读而阅读的读者,一种是具有批评眼光和创造性的读者[20]。事实上,只有具有批评眼光和创造性的读者才有可能做到巴尔特所倡导的解构式的阅读。对巴尔特来说,如果读者无法做到像他对《萨拉辛》那般具有重写欲望式的阅读,这阅读的解构性也就无从谈起。
巴尔特的“读者”是一种非常理想和抽象的存在,是个复杂的概念。他认为多种文化痕迹构成的文本其整体性在于读者。读者不是谁,只是“某个人”,文本所有意义的聚合所在。三年后,在S/Z的开篇,他讥笑佛教徒能在一粒豆子中看到全部景观。八年以后,在《罗兰·巴尔特自述》中,他再一次提起整体性:“整体性使人同时发笑和害怕,就像暴力那样”[13]259。无论是文本的整体性还是作者的整体性对他来讲都是很可笑的事情。他对《萨拉辛》的切割式解读打破了文本的整体性神话。如果不存在文本的整体性又何谈整体性是存在于作者还是读者呢?或许,读者,只是巴尔特的一种理想,又或许,他意并不在此,只是一个比喻性的描写。张静提出巴尔特的读者并不是指特定语境中的某个人,不是古典人文主义被动接受的读者。他只是一个虚化的概念,一个身份代号。巴特对读者的重视其实表现了阅读和阐释文本的自由[21]。刁克利则认为巴尔特“将抽象的读者作为文本阅读的终点,其实是一种虚妄”[22]。无论是“虚化”还是“虚妄”,都说明了这个读者的抽象与不真实性。同样认为读者举足轻重,他的“读者”不同于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的“读者接受批评”理论中的读者。巴尔特的读者与作者是楚河汉界的关系,而后者的读者则具体化多了,姚斯认为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积极参与成就了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23]。姚斯的读者是和作者共铸作品永恒的角色。
巴尔特的读者就如日本学者铃村和成所言之“难以形容”[24]6,他认为“难以把握,漂泊不定,这才是他终生不变的一贯特色”。当时一批法国学者的风格均如是,比如和他同时代的德里达、福柯等。铃村和成提到“仿佛作者言之有物,却又不知所云”[24]1是巴尔特批评的核心部分、关键所在。他把巴尔特及其思想的出现称为“怪物的诞生”[24]3。这些描述词非常恰当和准确地描述了阅读巴尔特作品之后读者的感觉。巴尔特宛若游戏中的一个顽童,不按规则,自得其乐。虽然巴尔特很不屑从传记材料出发去研究某个作者及其作品,但他的成长经历或许能启发我们对他思想独特性的认识。《罗兰·巴尔特自述》中提到他幼时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非常拮据,很难融入到其他小伙伴中去。读大学和服兵役的年龄得了肺结核被迫在疗养院度过,近乎与世隔绝。所有这些都养成了他思考问题的独特视角和方式。
巴尔特的作者消失于语言中,逃逸于文本外,让位于读者。处处可见作者死亡的痕迹,处处可闻作者死亡的号角。作者在巴尔特这里不再是语言的巨匠、文本的主人和意义的阐释者。但如上文所论,个中矛盾也处处可见。包括柏克在内的很多人都论证了巴尔特为说明自己观点所用例子的不合理性。加缪对巴尔特把他当作零度写作的例证而感到诧异。汪民安指出这是巴尔特一贯的特点:“一直不大作过多的论证,他甚至懒得举例。”[25]有了例证,他也懒得去解释,只是拿来服务于自己的观点。这大抵也是他的一种游戏方式。再者,这也是人类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降,历经洛克经验主义、康德超验的理性批判和实践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人的主体性得以确立;19世纪文学传统中,作者端居文学殿堂的中心。19世纪末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两度宣布“上帝死了”。20世纪60年代,福柯在《词与物》中宣布“人死了”。上帝与人都死了之后,兼具神性和人性的作者的死亡似乎就是迟早的事情了。所以巴尔特的“作者之死”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发生,即使不是由他提出也会有人提出。总之,将“作者之死”置于作者游戏的创作特点之微观维度及历史发展必然性之宏观维度的框架内,会得到更加客观、真实的认识,而不至于过度阐释。巴尔特的真实在于其矛盾与模糊性。纵使褒贬不一,但毋庸置疑,巴尔特把作者推入我们的视野。他让我们更加关注而不是忽视这个角色及他的主体性,甚至人的主体性。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于1969年2月22号在法兰西学院六号厅向哲学协会提交报告《作者是什么》。之后针对人们对他的“人之死”的责问回答说:“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人之死的主题就已经不断地出现了。这不是我的主题。我只是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了作者的概念。让我们收起我们的眼泪吧。”[26]所以,在福柯看来,无论是人之死,还是作者的自行消失,都是早已经存在的一种思想和现象,对他来说只是自己功能研究的一个出发点。我们可以借鉴来思索面对巴尔特的“作者之死”的方式与态度。收起我们的眼泪,去探究“作者之死”所反映的巴尔特对语言的痴迷,对文本概念的不遗余力,对读者的理想期望与模糊虚幻,以及对时代的深刻思索等。
参考文献:
[1]Barthes R. The Death of the Author[M]//Leith V B.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1.
[2]Lamarque P.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An Analytical Autopsy[J].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1990,30(4):319-331.
[3]Bennet A. The Author[M]. London: Routledge, 2005:9.
[4]Burke S. The Death and Return of the Author[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2:8.
[5]哈罗德·布鲁姆. 西方正典[M]. 江宁康,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29.
[6]肖锦龙. “作者死亡论”的悖论——从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谈起[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4):53-57.
[7]李勇. 作者的复活——对罗兰·巴特和福柯的作者理论的批判性考察[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9(1):64-70.
[8]刁克利. “作者之死”与作家重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0(4):134-140.
[9]路易-让·卡尔韦. 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M]. 车槿山,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154-6.
[10] 徐岱. 游戏批评:论巴尔特评巴尔扎克[J]. 外国文学研究, 2003(5):1-7.
[11] 罗兰·巴尔特. 写作的零度[M]. 李幼蒸,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12] Barthes R. Sade, Fourier, Loyola[M]. New York:Hill and Wang, 1976.
[13] 罗兰·巴尔特. 罗兰·巴尔特自述[M]. 怀宇,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4] Barthes R. Criticism and Truth[M]. London: Athlone Press, 1987:85-7.
[15] Barthes R. S/Z[M].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4.
[16] Foucault M. What Is an Author?[M]//Leith V B.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1: 1622-1636.
[17] Barthes R. From Work to Text[M]//Leith V B.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1: 1470-1475.
[18] Barthes R.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M].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5:54.
[19] 奥斯卡·王尔德. 谎言的衰落:王尔德艺术批评文选[M]. 萧易,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4.
[20] 童明. 解构[J]. 外国文学, 2012(5):90-119.
[21] 张静. 主体虚空与文本多义——论罗兰·巴特的作者观[J]. 福建论坛, 2010(8):117-121.
[22] 刁克利. 诗性的回归:现代作者理论研究[M]. 北京:昆仑出版社, 2015:24.
[23] Jauss H R. 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M]//Leith V B.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1: 1550-1564.
[24] 铃村和成. 巴特:文本的愉悦[M]. 戚印平,黄卫东,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25] 汪民安. 谁是罗兰·巴特[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45.
[26] Foucault M. Qu’est-ce qu’un auteur?[J].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 1969(3):73-104.
(责任编辑: 李新根)
A Re-examination of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SHIFeng-xi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Roland Barthes sentenced the author to death in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which has a profound effect. There have been constant debate and discussion regarding whether to support or repudiate it ever since. However, the comparative reading and analysis of such central concepts as the author, the language, the text and the reader in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with those in his other works will reveal the birth, development, change and reversal therein. I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 thoughts and his habit of playing with words, which is partly attributed to the intellectual progress of human beings. It carries mor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behind and beyond the academic debate. Placing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among Barthes’ thinking framework an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will contribute to an impartial and deep understanding of its complexity and profundity.
Key words:author; text; language; reader; Roland 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作者简介:史凤晓(1983- ),女,山东莘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西方文论研究。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0XNJ026)。
收稿日期:2015-06-16
doi: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1.018
中图分类号:I 0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6)01-01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