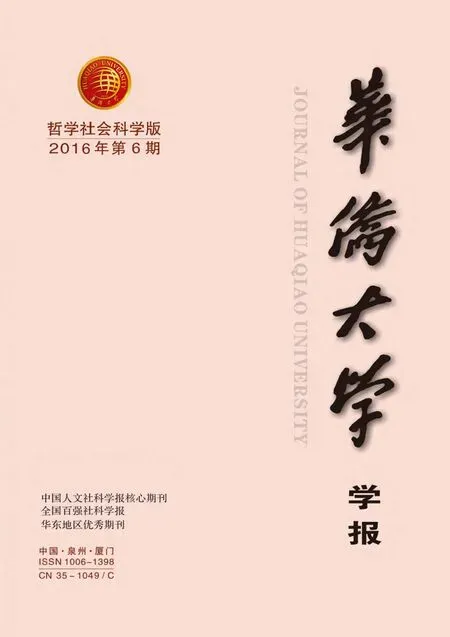古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对音与传播研究
○张进军 乌东峰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或软实力范畴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特别是冷战时期,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催生并强化了两大阵营互相妖魔化对方的国家形象的实践与理论。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关注中国形象的研究呈上升趋势。一般而言,国家形象的传播有两种类型:有意识传播和无意识传播。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研究成果丰硕,并提出诸多国家形象构建的途径,这些都属于有意识的国际形象传播。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意识的国家形象传播微不足道。相反,无意识的国家形象的传播无时每刻都在进行中,比如海外游客的言行举止、各级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跨文化交流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隐含着无意识类型的国家形象传播。历史上,国家形象的无意识传播更是占据主导优势。无意识类型的国家形象传播在我国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我国的国家名称在古代各国的对音与传播代表着古代中国在世界各国的基本形象认知。因微见著,本文力图从历史演变的角度,从中国形象的凝聚物“中国”一词的海外各国语言的对音演变史,来观察、分析中国古代国家形象的传播规律。通过分析为何中国的英文为China或Cina、其形态演变、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汉译及理据,追踪古代中国在周边甚至欧洲的国家形象演变史和古代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机制。
一 中西主流学者的相关研究
中西典籍中出现的Cina、其变体及其在不同语言中之变体(Thin, Thinae, Chin, Sina, Sinae,Cini, Cyn, Cynstn, Tzinitza, Tzinista, Mahachinasthana等。后来统一于今英文China)均明确无误地用作古代中国的称谓。中西学者对此基本无异议,争论焦点主要在于Cina的对音问题上,即Cina究竟为哪一名词的音译及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为何使用Cina指代中国。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精华主要集中于此。
1.西方学者主要观点
除了每个朝代的名号外(如夏、商、周、秦、汉、唐等),一般而言,中国自称华夏、神州、中华、中国等。国人对海外诸国如何称呼中国似乎并未太在意。被誉为“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在其1655年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Novus Atlas Sinensis)中指出“支那”出于公元前249—207年的秦国。*[法]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 交广印度两道考》,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90页。*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页。学术界一般将1655年视为争议的起点。世界范围内掀起Cina研究热潮,吸引了顶尖学者的注意力。法国鲍狄埃(M. Pauthier)亦主此说,并认为梵语之“支那”来源于战国时期的秦国而非秦朝。1877年,德国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其《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第一卷》(简称《中国Ⅰ》)中以“日南”说反对“秦”说*参见http://www.hudong.com/wiki/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之后,英国亨利·玉尔(Henry Yule)初赞成鲍狄埃,后又认同李希霍芬。法国拉克伯里(T. De Lacouperie)持“滇国”说反对李希霍芬。英国翟理斯(H.A. Giles)从对音的角度分析认为李希霍芬和拉克伯里皆“臆想之词,毫无根据”,力挺鲍狄埃。赞同鲍狄埃的还有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1910年德国雅各比(Herman Jacobi)著文反对“秦”说,认为秦朝后于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考铁利亚(Kaotiliya)的《治国安邦术》(又名《政论》)(Arthasastra)。该书多次记载了Cina一词。雅各比于是认为绝无用后来朝代之名用于前代之可能。*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555—557页。*因不熟悉秦国及秦朝之历史,雅各比之说有误。法国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主“后秦”说,伯希和亦驳之。*[法]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 交广印度两道考》,第190页。*伯希和是沙畹的高徒。
2.中国学者主要观点
中国学者张星烺、方豪、季羡林、饶宗颐交叉运用对音、地理位置等因素分析Cina之起源,均主“秦”说。*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555—557页。*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第45页。*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季羡林文集》(第四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110—111页。*饶宗颐:《中外关系史》,《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七),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264—272页。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是战国时期秦霸西戎的有利地理位置及其影响力。历史学家岑仲勉说:“西方人称我国为秦(China)、为契丹(Cathay),皆人所熟知,不至复生异议。”虽未做具体考证,可以看出岑赞成“秦”说是无疑的。*岑仲勉:《外语称中国的两个名词》,《中外史地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2页。翻译家杨宪益从“秦”字的语音演变角度分析,认为以上“秦”源自“羌”,与秦朝无关,所以Cina 为“秦”之对音不太准确,应为“羌”。他又认为“羌”“荆”“滇”同源,所以进一步认为Cina的“荆”“滇”等说亦可。*杨宪益:《译余偶拾》,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127—129页。著名古音专家郑张尚芳从上古音的清浊分析,认为Cina当为晋国的音译;秦国国力后来居上,随着秦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引起秦晋读音混淆,导致学者误以为Cina为秦的音译。*郑张尚芳:《夏语探索》,《语言研究》2009年第4期,第1—12页。也有学者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沈福伟认为“支那”一词并非起源于秦国或任何一地名,根据先秦时期中国已经以出产绮或丝而闻名,进而“揣测”其为“绮”或“丝”国的对音。*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29页。
还有许多民间学者的观点,如“瓷”说、“昌南”说、“茶”说、“齐”说、“粳”说等,虽不无一定合理推断,或许冥发妄中,因其想象力过于丰富,或考证偏离主题甚远,本文暂不加引述。
二 “隔境翻译”研究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看出中外学者对Cina的真实来源有很大的争议。仔细分析,不同说法的争议不外潜在地围绕着三点展开:基本对音、时间范围、传播路径。有些学者仅专注其中之一,或者是其中之二;也有学者三种因素全部分析,但仍不够细致、精密,或者剑走偏锋、顾左右而言他。下面我们将综合运用“隔境翻译”研究时应考虑的三大主要因素,将学者的主要观点重新审视。
1.基本对音
考虑对音时,不能以现在的读音为参照点,要努力重构其在事件发生的那个时代的读音。比如,李希霍芬主“日南”说;拉克伯里主“滇”说;杨宪益认为“滇”说可以接受。伯希和从历史语言学及音韵学的角度分析,认为此说皆误;因为“日南”在先秦时的读音为Nit-nam,与Cina的发音相去甚远。*[法]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 交广印度两道考》,第190页。杨宪益的“羌”说,从读音来看,尚不能排除其可能性。*杨宪益:《译余偶拾》,第127—129页。不过,别国称呼一国之名必来自该国之自称。羌,属他称,即当时中原部落对西部(今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四川)游牧民族的泛称。羌是民族的种号,因此该族之国民或政府与国外交流时,使用羌的可能性不大,而应使用该族所形成的政权名号。也就是说,当时羌族东方的中原各族政权确实以“羌”相称,但处于其西及南部的印度决不至于如此。由此可见,古印度以族名称呼羌政权为Cina的可能性极小,因为“羌”本是羌东方中原政权对其的“他”称。另外,杨认为“秦与羌本是一字”,亦可存疑。恐怕秦国的“秦“和”“羌”的读音大致相同是碰巧走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两者并没有本质的联系。秦族起源之传说,《史记·秦本纪》“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中华书局:北京,1999年,第125—158页。也就是说,秦民族是鸟图腾,和地处西陲的羌族没有必然关系。历史学家早就疑心秦虽地处西北,实乃来自东方。有没有证据呢?秦族和商朝民族起源之传说(《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何其相似乃尔!*程俊英:《诗经注析》(第二册),中华书局:北京,1991年,第1029页。《史记·殷本纪》亦有类似记载,可互相为证。*[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25—158页。对比之,可以看出两者均为鸟图腾。也就是说,秦族本和商族或同源。商朝被周(姬姓,发源于周地)击败后,秦族被周迁移至西部看家护院。后来发展壮大,独树一帜(按:古代国家之名称往往来自地名),如殷商、商、周、秦、汉、唐等,皆是也。古代中国国家之名称本为地名,实为常态。《史记·秦本纪》记载:周天子封赢于赵城,称“赵嬴”;另一部分“邑之秦”,称“秦嬴”。*[汉]司马迁:《史记》(第一册),第125—158页。秦,地名也。就是说嬴姓被分封在秦地,所以有了历史上的秦国与秦帝国。秦国之秦与羌同音实属风云际会。商族在商地建立商政权,自称商;迁至殷地又自称殷;赢族在赵地和秦地分别建立政权后,也自称赵、秦。后来的政权或其他各族政权也依照惯例称他们为殷、商、赵、秦。进一步证明,杨说或误。
2.时间范围
考察“支那”之起源,除了对音基本要正确以外(不必强求读音完全一致,因为当一种语言进入另一语言中,读音的变化是必然的),时间因素是另一重要参考依据。世界上最早提到中国这个国家的是波斯帝国(即今伊朗)。“支尼”(Cini)这个名称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出现在费尔瓦丁神颂辞中。*沈福伟:《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第20—21页。其次,中国以Cina之名出现在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古印度典籍《政论》中。书中记载了中国丝在印度使用的情况时使用了Cinapatta一词。该词由两部分组成Cina和patta(带、条),合起来就是“中国的成捆的丝”。由此可知:1. 中国丝不迟于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传入于印度;2. Cina确指中国且不同于“丝”。*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季羡林文集》(第四卷),第110—111页。*饶宗颐:《中外关系史》,《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七),第264—272页。Cina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唯一称谓。当需要表达丝的概念时,会有其他词语如Cinapatta等表述。由此可知,Cina为“丝“或“绮”的对音的可能性极小。进一步的合理推论是:Cina起源为“丝”或“绮”说是不对的。古代西方典籍中称呼中国有两套系统,“Cina”系统和“赛里斯(Seres)”系统。梵语独用前者,古希腊语及拉丁语兼用两者。顺便提及一点,推断Cina为“丝”说误,并不妨碍我们认为“赛里斯”系统与“丝”的密切关系。“丝”的古汉语读音为Sser,在朝鲜语为Sir,蒙古语为Sirkek,满语为Sirgh,古波斯语为Saragh,土耳其语为Sarigh,在今俄文为Shilku,今英语为Silk。*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第47—50页。各语言中的“丝”的读音均指向一个可能性:中国的另一个海外名号“赛里斯”源于“丝”。托勒密(Klaudius Ptolemaios)的名著《地理书》记载中国时说:“支那人(Sinai)的边境,北与丝国(Seres)一部分为界。”*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第128—130页。可见,古希腊对提及Seres时,总是和丝联系在一起,并且与Cina有明确区分。因其与我们要谈的主题关系不大,本文不做详细考证。
再用此标准审视一下“滇”说、“日南”说、“后秦”说,结论更加明朗。中国古代的确存在过一个古滇国。《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庄蹻奉楚顷襄王之命,攻略西南,戡定其地,正要返国,而楚国的巫郡、黔中郡在公元前277年时再度被秦国攻占,回国之路断绝,庄蹻遂留在滇池自立为滇王,号“庄王”。“滇”说非。汉代方设日南郡,“日南”说非。后秦(384年—417年,或称姚秦)是十六国时期羌族贵族姚苌建立的政权,“后秦”说非。清代学者薜福成在《出使日记》中记载:“欧洲各国,其称中国之名,英曰采依那,法曰细那,德曰赫依那,拉丁之名则曰西奈。问其何义,则皆秦之译音……揆其由来,当由始皇逐匈奴,威震殊俗,匈奴之流徙极远者,往往至今欧洲北土,……彼等称中国为秦,欧洲诸国亦相沿之而不改也。”*[清]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出版社,1985年,第328页。秦逐匈奴发生在秦始皇时期,谓秦始皇打击匈奴加深了秦人在西方诸国的影响则可,谓Cina之音起源于秦朝则否。“秦朝”说亦非。
3.传播路径
确定Cina之最早起源后,要求我们研究该问题时,不仅对音要以公元前4—5世纪的读音为参考,该读音的传播路径也要以这个时间段为出发点来考虑。伯希和、张星烺、季羡林、饶宗颐等学者研究认识到战国时期秦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影响力,但他们均认定梵语著作《政论》(公元前3—4世纪成书)为Cina最早出处,且不自觉地假定古印度为中西交通之唯一初始中介,排除了梵语及印度以外的其它最初传播途径之可能性。虽然论证精彩纷呈,但存在时间和地点的离位问题,似乎还有再商榷的余地。张绪山考察Cina一词在粟特文(古波斯语方言之一)、叙利亚文等中亚语言及古希腊语中的书写特点,判断该词的梵文可能转自古波斯语。*张绪山:《拜占庭作家科斯马斯中国闻纪释证》,《中国学术》,2002年第1页,第36页。沈福伟根据约公元前5世纪的古波斯文献费尔瓦丁神颂辞已使用Cini称呼当时的中国;另外,古波斯文对中国的称呼还有Cin,Cinistan,Cinastan。沈由此推论其他语言中的中国关于Cina的称呼均转译自古波斯语。*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6-29页。张和沈的发现对我们研究Cina的起源很是关键,尽管后者认为Cina与“丝”和“绮”有关(相关论证详见本文二(2)小结)。还有一点需要提及,古籍之记载总是滞后于事实之发生。虽然目前可以寻找出Cina一词的最早文献记载,但并不能排除支那一词更早进入其他语言的可能性。因此,观察各国的地理位置及中西交通史以判断Cina原音或对音时,应上推一段时间较为安全。略述公元前5—7世纪左右的世界版图中的中国及与西部各族政权的关系如下。
公元前6—7世纪为中国春秋初年,适值秦国看守东周西进之门户,通过不断地蚕食西部诸戎,在秦穆公年间(前659年—前621年)“灭国十二,开地千里”,取得“秦霸西戎”的地位。西部中国,秦国一国独大,扼守中西交通之关键,西方国家要想与周朝发生交往,秦国无论如何是无法越过的。大约同时代,亚述人先后征服两河流域、叙利亚与埃及,建立地跨亚非的亚述帝国。之后,加提人联合米太人消灭亚述,代之以“后巴比伦帝国”(约前625—前539年)。再后,波斯人灭之,建立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在大流士(Darius)统治时期(前521—485)国力极盛,不断西向与希腊争霸,秦国之威名于是广播伊兰高原,并以波斯语为中介传入希腊语与梵语中。*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第33—34页。周、秦以西之部落或政权只知有秦,无论西周、东周。郑张尚芳以为三晋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力远大于秦国,故支那成为中国之代名词。传播路线语言学上的证据充分表明Cina一词依次自东而西传播,而郑张强索于北,不亦南辕北辙(远)乎?*郑张尚芳:《夏语探索》,《语言研究》2009年第4期,第1—12页。就目前可以援引的文献来看,我们可以粗略地勾画Cina的传播路径:秦(Ch’in)→波斯语(Cini)→梵语(Cina)→欧洲其他诸国语言(Thin,Tzinitza, Tzinista等);最后演变为现在的China。因为国名之China与瓷器之china同音且同体,于是有人误以为中国因瓷器得名号。OED(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明确china源于chinaware(犹谓中国货)。可见先有国名China,后又器物china。
4.小结
综合基本对音、时间范围、传播路径三要素的考察,我们赞成卫匡国、鲍狄埃、伯希和、张星烺、方豪、季羡林与饶宗颐等学者的结论,即Cina源于秦国的国号(非秦朝),只是在其传播的路径上有些许不同看法。凡是主张Cina原音为地名说者,不论理由和结论如何,均指明“隔境翻译”这样一个事实:大中国周边国家或政权以与之较为接近的中国某个政权的国号代称中国整个地域。这是由于古代交通及通讯工具的局限性而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现象。为了使论证更加清晰,假设有甲、乙、丙三个国家分列左、中、右。左边的甲国要想与右边的丙国发生交往必须通过中间的乙国的中介才能完成。在甲丙两国没有直接发生交往以前,甲国或丙国对于对方的认知也主要通过乙国来完成。名称的约定俗成性也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说,一旦一个国家称呼另一国的名号确立后,该名号往往会在所称之国消亡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适用。例如,《前汉书·匈奴》载“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颜师古注曰:“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前汉书·西域传》载汉武帝之语“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颜师古亦注曰:“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史记·大宛列传》:“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前汉书》引用《史记》将“秦人”改为“汉人”。可见两者虽不同名却同一所指。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曰:“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至唐及国朝则谓中国为汉,皆习故而言。”*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第45—46页。以上诸例也可以进一步证明华族以外其他诸族称中国为“秦”源远流长。国号的约定俗成的威力有时甚至大于法令。试看另一例。《萍洲可谈》记载北宋时期边俗仍称北宋政权为“唐”,“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臣僚上言:边俗指中国为汉唐,行于文书,乞改为宋。诏从之。”*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第219—220页。今日远赴海外谋生的东南人民的海外聚居地仍称“唐人街”,可见国号的约定俗成性强过皇帝的诏令。
Cina是不是隔境翻译现象的一个孤例呢?再以中国的另一个海外名号Cathay为例。比如庞德的翻译诗集Cathay,学者翻译为《华夏集》《神州集》或《中国》。溯源而上,Cathay来自俄语Китай(kitai),原指契丹;并以此指代契丹以南的中国。契丹一词指中古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亦指该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辽河上游一带活动,唐末建立了强大的地方政权,于907年建立契丹国;改称辽是后来的事情。因为契丹地处操斯拉夫语系种族与中原政权之间,没有飞机、有线和无线通讯技术的古代,斯拉夫语系语族必须通过契丹方能与当时的中国中原政权发生文化交流与认知。久而久之,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斯拉夫语族的人便以契丹Китай(kitai)指称契丹建立的辽政权,后来再指称整个中国。斯拉夫语的Китай(kitai)后来进入其他欧洲语言,便有了现在的Cathay。通过这个事例,可以看出Cathay与China的产生、发展、演变都符合“隔境翻译”的规律,遵循着相同的机制。中国古代典籍载有“大秦”一国,史学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其真实所指恐怕也要考虑“隔境翻译”的特殊现象及规律方可有新的发现。
三 主要汉译佛典及古典中外关系史著述中Cina的翻译
其实卫匡国并非提出梵文Cina对音为“秦”的第一人,也不是最早注意到其具体所指的第一人。兹举几例。汉代翻译的《德护长者经》曾直译Cina作“脂那”,随后的《大方广大庄严经》的译者将其译成“秦”。这说明中国佛家学者对Cina的认识进一步加深。汉代的佛典还有将Cina译为“汉”的。《梁高僧传·道安传》载道安批评佛经翻译成流利的汉语会产生一定的乖讹,“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蒲陶酒之被水者也。”在《出三藏记集》中,道安转述赵政的话说,“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季羡林文集》(第四卷)第205页。其时,胡梵义近;此处的“秦言”或“秦”,显然指称汉语。也就是说,无论是道安还是赵政,都非常清楚梵文或胡文佛典中“秦”为中国的代名词。古代的佛学家或佛学翻译家以“秦”名中国,无疑是深受到梵文佛典的影响。魏晋南北朝及隋朝时的佛典翻译者又将它译成“晋”或“隋”。这些翻译虽然不一,但都明确Cina指代中国。*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8—29页 。
唐朝,玄奘也探讨了这一问题。《大唐西域记》译Cina为“至那”,载玄奘与印度戒日王的对话甚详,摘录如下:
王曰:“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少而灵鉴,长而神武。若先代丧乱,率土分崩,兵戈竞起,群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怀远略,兴大慈悲,拯济含识,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盛德之誉,诚有之乎?大唐国者,岂此是耶?”
对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昔未袭位,谓之秦王,今已承统,称曰天子。前代运终,群生无主,兵戈乱起,残害生灵。秦王天纵含弘,心发慈愍,威风鼓扇,群凶殄灭,八方静谧,万国朝贡,爱育四生,敬崇三宝,薄赋敛,省刑罚,而国用有余,民俗无究,风猷大化,难以备举。”
戒日王曰:“盛矣哉,彼土群生,福感圣主!”*[唐]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36页。
通过玄奘与戒日王的对话,我们可以尝试做出以下几点推论:1. 博学的三藏法师明确认为“至那者,前王之国号”,也就是说玄奘认为梵语中Cina确指中国;2. 戒日王“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可证明古代印度明了Cina确指中国,只不过借此机会确认一下而已。“摩诃至那”意为伟大的中国,梵语为Mahacina,是戒日王对中国的尊称;3. 玄奘虽未明确Cina具体是中国哪一个朝代或王国的国号,但他认为是前王的国号是无疑的。也就是说,玄奘认为“丝”说、“瓷”说等物品说或其他地名说是不正确的;4. 在等级森严、讳莫如深的封建阶级社会里,知识分子在涉及到皇室威权时,用词是非常考究及准确的,“帝”和“王”的意义在古代是不同的。玄奘用“前王”而不用“前帝”,足证明Cina虽是国号,却非一个统一的帝国国号。或许玄奘知道Cina的汉语对音。惜乎!玄奘并未明确指出Cina是哪一个王国的国号。稍后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也明确Cina指代中国,并将之音译为“支那”。*[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北京,1988年,第71页。*[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82页。*[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106页。
四 结 语
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在高效地互相交流时,离不开翻译。有时是两种语言直接互译,比如中译英或英译汉;有时要借助第三方语言,比如早期翻译马克思的著作,主要途径来自日语的翻译或转译。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还存在一种独特的翻译,不为翻译界所注意,姑且称之为“隔境翻译”。“隔境翻译”不同于转译。前者主要发生在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或中西交通史中某个国家或著名地名的海外名号或名称上。这种现象由于古代的交通及通讯工具相对简单而不得不借助于第三国来认识目的地或目的国所造成的;在古代曾普遍存在,比如中西交通史上的“大秦(Dasina)”“拂菻(Purum)”“昆姆丹(Kunmdan)”“桃花石(Taugast)”等。本文所探讨的中国海外名号“Cina(“支那”、脂那、至那、震旦)”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隔境翻译”范例。通过分析为何中国的英文为China或Cina、其形态演变、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汉译及理据,初步探讨“隔境翻译”现象发生及演变的规律。本文总结出探讨此类问题的三个标准:基本对音、时间范围、传播路径,为正确认识中国在海外的其他名称问题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其他类似问题提供行之有效、相对可靠的研究线路图。总体而言,近现当代的中西学者对Cina的对音分歧较为明显,但最广为接受的还是先秦时期的秦国的“秦”;西方汉学家和古代中国的佛学大家的观点较为一致,也认为是“秦”的对音,虽然唐及以后的佛经翻译有时直译为“支那”“至那”“脂那”,有时译为“汉”“晋”等。特别是后者,佛经翻译者绝不认为梵语Cina的对音是“汉”或者是“晋”,而是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便于读者接受而已。到目前为止,关于“隔境翻译”现象中Cina的对音上,我们还远不能说已经找到问题的终极答案。本文充其量只是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作者自己的一点拙见。中西古地理名词对音的考证的坎坷道路上遍布荆棘,相信凡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均有深切体会。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戈岱司(George Codès)辑录古希腊、古罗马文献中出现有关远东的记载时,曾形象地描述该领域探索的艰辛与陷阱,并最终无奈地概叹:“我于其中有意避免了有关古地理名词考证的全部争论:这一领域是一片流沙之地,不止一个人在此陷了进去。”*[法]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北京:中华书局:北京,1987年,第6页。在讨论Cina的汉语对音上,作者也可能无法避免地陷入这片流沙而不自觉。衷心希望有心的学者将这个有趣味、有意义的研究继续下去并能有新的发现,进一步梳理中国古代国家形象演变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