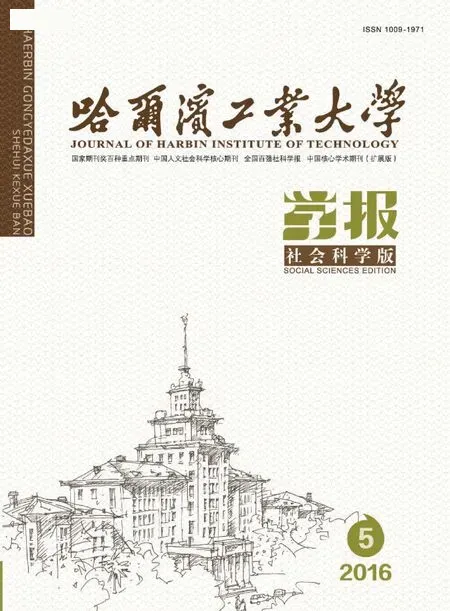学科话语与知识范式的建构
——“十七年”时期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学术史考察
刘 杨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学科话语与知识范式的建构
——“十七年”时期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学术史考察
刘 杨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十七年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是当代文学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着力建构当代文学自身的话语体系和学科意识,也成为日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奠基性话语。在当时,修史者秉持的是社会主义文学的观念,然而,他们在论证“当代文学”的进步意义和学科合法性时却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共享了同一种话语策略,即强调文学发展的历史渊源和文学进化观念。同时,这一时期的几部当代文学史也为当代文学修史探索了一种新的学术范式,也为后人留下不少值得正视和反思的经验、教训。这体现在坚持社会进化论为基础的历史观并强调文学史的进化逻辑、在文本分析时思想性优先的价值判断标准、确定了时期划分与文体分类相结合的当代文学史著体例、由个人著史转为集体写作文学史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上。
十七年;文学史;进化论;范式;学术史
相比于“新文学”,“当代文学”这个概念出现要略迟一些。按照有学者的说法“‘当代文学’的概念,解放初期还没有人提,直到1958年大学生大编教材时,于1959年(笔者按:该书正式出版是1962年)科学出版社推出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教材,才出现‘当代文学’的概念。”[1]“大跃进”时的北京大学“为了坚决贯彻厚今薄古的原则,中文系准备增设现代文学的课程,今年暑假后,即开出《当代文学》《民间文学》《中国文学思想斗争史》和《文艺讲座》等四门新课程”[2]。但最终并没有形成公开出版的文学史。在“十七年”时期,公开出版的、以“当代文学史”命名的著作其实只有华中师院和山东大学的师生集体编写的两部,再加上中国科学院(后称“社科院”)文研所集体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可以说十七年时期公开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有三部。
如海登·怀特所言:“学术领域反思自身的一个方法是回顾自身的历史”[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审视这一时期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不仅是一次学术史的清理和反思,也可以总结必要的学术经验与教训。
一、当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论证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写作当代文学史首先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当代文学”何以从新文学、现代文学这些概念下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学科并独立成“史”?因而对于任何一部当代文学史的作者而言,其必须面对的基本的问题是关于“当代文学”独立成史的“合法性”的自我确证(Self-confirmation),并论述它较之从“新文学”概念分化出来的“现代文学”有何区别。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些当代文学史的作者在论证“合法性”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时,正与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广为批判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显示出某种相似性。
第一,胡适以“白话”作为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纽带,为新文学找到了历史和逻辑上的“阿基米德点”。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以现代白话取代文言,以“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4]作为“文学的国语”来写作“国语的文学”。为了在自我确证的过程中展示自己的观念并非文学史的断裂,而是对古代“死文学”的遗弃和“活文学”的继承,胡适声称:“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做书了;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词了;八九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讲学了……”[5]2如此做法显然使得“白话文学”成为一个空洞化的能指漂浮物,它可以指称任何一个朝代民间文学,甚至必要时可用以指涉杜甫、李白部分诗作。在对历朝历代他所谓“白话文学”的推崇中,胡适赋予了“白话文学”语言之外的价值内涵,那就是:“庙堂的文学终压不住田野的文学;贵族的文学终打不死平民的文学。”[5]18并且断言:“一切新文学都来源于民间。”[5]20
返顾当代文学史的建构,修史者首先将“当代文学”的核心定位为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文学”,并以其前身“革命文学”为连接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纽带。应该看到的是,这些文学史在建构文学史体系的同时加入了“革命”的“装置”,试图从根本理念上更新文学史的“主潮”。“我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一开始就由无产阶级所领导,因此在当时的文学中就包含着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导因素”[6]33。现在看来,“权威”的论述虽然已经定下了基调,但只是一种概括式的结论,文学史作者则要更为具体地对这一思想做“合理化”阐释:
“五四运动中的新文学运动,按其性质来说,还是属于民主主义范畴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以后,包括新文学在内的整个中国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事实上已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为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所领导。但是,当时参加这一运动的好多人,包括最杰出的战士如鲁迅等人,对这一点并不自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的革命文学一直在党的影响和领导之下成长和发展。”[7]2
在此逻辑下后来的“左联”、延安文艺更是这一“革命文学”流脉的发展。由此可见,“革命”作为一个文学史逻辑的内在“装置”,其作用在于修史者要从革命的缘起、形成、发展、胜利的角度勾勒出一条文学史发展主线,即:无产阶级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学,但如同胡适把“白话”的概念严重扩大化一样,在当代文学史中包括鲁迅在内的“进步作家”在新文学之初的文学活动都被叙述为“无产阶级文化”的一部分,事实上也有过度阐释之嫌。不过,要指出的是在文学史写作中“革命化”现代文学肇始于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其中言道:“中国现代文学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学运动。”他并且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影响尽可能略去,而声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以及革命民主主义者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在这个运动中起了极大的影响和作用”[8]。
第二,胡适坚持进化式的文学观念,并以之划分文学的价值等级。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开篇就说:“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5]1并且“要大家都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是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5]2。而且在这样一种进化观念下包含着鲜明的价值判断,如“唐朝的文学的真价值,真生命,不在苦心学习阴铿、何逊,也不在什么师法苏李(引按:指苏武、李陵),力追建安,而在它能继续这五六百年的白话文学的趋势”[5]128。
回过头来看当代文学史写作,尽管有学者将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史著中的史观定位在“以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为支撑”[9]。但当时现当代文学的治史者无论是情愿还是不情愿都一定程度上把“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作为标签套用在文学史里。这反映在文学史中,即是胡适书中“白话/文言”“活文学/死文学”的二元对立被转化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进步/反动”的二元对立,日后演化为“社会主义/封、资、修”的意识形态二元对立。于是,在确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代文学”传统中的历史渊源和正统地位之后,编者在文学史中宣告:“在欧洲,资产阶级文学就早已过了它的向上发展的时期。追随没落的西欧资产阶级的中国资产阶级文学,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整个命运—样,不能有什么作为。它在新兴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面前,很快就和它的西欧的标本—起衰朽、没落了。”[7]2这段话,如同胡适宣告“古文学”在汉代就死了一般,宣告了资产阶级文学(自由主义、京海派文学、沦陷区文学等)的没落,也宣告了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学”独立发展的必然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文学独立成史的合法性论证与胡适的话语策略有同构之处。但需要指出的是,胡适当年的论证方式是其发动文学革命的话语需要,胡适后来的学术研究并非如此激进。而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在前三十年不仅是走向“一体化”的,更是走向激进化的,它在确立学科合法性的同时,把自身的源流论述得过于单一,既狭隘化了“现代文学”,也狭隘化了“当代文学”。直至如今,将十七年文学视为解放区文学全国化的看法依然很有市场,而这种片面的文学史认知则源于十七年时期当代文学史所确立的知识谱系。
二、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范式建构
虽然现在来看,十七年时期关于建构“当代文学”合法性的论证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支撑下有些偏政治化的判断,但是毕竟在当时完成了这一步才能建构独立的文学史范式。“反右”之后,对于要在“当代文学史阵地”插红旗的人来说,在批判地借鉴以往文学史合理性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新范式势在必行。概而言之,这一时期当代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建构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社会进化论支配下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固然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指引有关,恐怕也不会没有进化史观在中国的投射。顾颉刚曾言:“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来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10]可见在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们还深信进化史观。具体到当代文学史而言,当时的文学史叙述逻辑为:“党领导全国人民,为了在我国建立历史上一个崭新的制度——社会主义,在艰苦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作为这个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革命的文学事业,它的使命是要在我国建立历史上一种崭新的文学——社会主义文学。”[7]16在他们的叙述中:“11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一瞬间,但新中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1]不过要指出的是,这些文学史著对当代文学成就的评价,并非空穴来风也不全然是妄自尊大,从文学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当代文学尽管经历了几次批判运动,但还是有一定成绩的。据统计新文学读物,“从1950年的156种增加到1958年的2600种……发行数从1950年的2,147,700册增加到39,364,094册”[6]34。
第二,思想分析高于艺术评价。当代文学的修史者对于文学思潮和文艺斗争极为重视,纷纷将之放在文学史的开头并做相当篇幅的梳理和评述,以此作为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而非勾勒文学本体(审美)演进的历史轨迹,这也配合了修史者的历史观。如“反对右派和修正主义者的斗争的胜利,是文艺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决定意义的伟大的胜利”[7]13。若说这样的表述还比较中性,那么有的文学史写作已显露“文革”中“大批判”式语体特征:“一时间真是乌云滚滚,牛鬼蛇神完全显露了他们的丑恶原形……他们鼓动一切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仇视的人‘有仇报仇,有冤报冤’。”[12]
具体来说,这些文学史对于文学文本评价也首重思想性(政治性),如《红旗谱》的现实主义成就首先是在于“探索了几个世代农民的灵魂,追本溯源地发掘出来了那曾燃遍辽阔大地的熊熊之火的火种,那深埋着的绵延不尽的仇恨,那父传子继的不屈的意志,那天然的属于阶级本能的反抗心理”[7]16。若是客观地看,这几部文学史并未完全忽略艺术分析,这种文学史写作范式下,对文学文本的评价除了思想和社会历史维度之外,还往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和“两结合”、“民族化”等理论对文本的情节、人物、语言进行介绍,而那些思想“错误”的作品如果无法回避就采用全面批判的态度,后世学者因其政治的理念问题而诟病之也不能不说没有道理。
但话若说回来,一种文学史范式背后必有一套知识体系的支撑,我们自然要尊重艺术至上论者的话语权,然而不能忽略的是“现实主义”理论本来就认定:“只有那些和社会的要求保持活的联系的倾向,才能获得辉煌的发展。凡是在生活的土壤中不生根的东西,就会是萎靡的,苍白的,不但不能获得历史的意义,而且它的本身,由于对社会没有影响,也将是渺不足道的。”[13]因而笔者以为,学术史的研究要考虑到当时学术界的知识范式,在当时文学理论的框架下,这些文学史在考察文学作品时偏重于文学文本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反映是必然的学术选择。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这时期当代文学史写作范式,不宜脱离当时的文化环境以现在的眼光和理论完全否定之。当然,其中阶级斗争意识强烈的、上纲上线的批判式非学术论述要另当别论。
第三,分时期、分文体的文学史体例。文学史范式若分为理论和形式两个层面,除却理论上的指导思想,还要形式(体例)上考虑如何结构文学史。鲁迅在讲到文学史编纂时曾提出:“史总须以时代为经,一般的文学史,则大抵以文章的形式为纬。”[14]十七年时期当代文学史写作在总的框架一致的前提下出现了分时期与分文体两种体例。分文体的体例显然沿王瑶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一脉继续,这样的文学史体例是后来最为常见的,姚雪垠还曾主编过《中国当代分类文学史丛书》共计6册,从1990年起陆续出版。分时期的论述尤其是具体分期方法则受季莫菲耶夫的《苏联文学史》影响较大,这部文学史在新中国第一个十年曾被三家出版社出版,广为流传。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相关领导也否定了这种模式。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史写作分期问题也一直是学术界争议不断的话题之一,但必须指出的是,一旦文学史分期以政治发展分期为根据,便是一种将文学史的发展附骥于意识形态沿革史的做法,它有可能遮蔽文学本体演进的轨迹,忽略作家艺术创造超越意识形态限制的一面。
第四,集体修史的编纂模式。自“文学史”的概念进入中国后,从林传甲开始第一部文学史写作一直到王瑶等人在建国后写作的新文学史,个人著述是文学史写作的重要方式。然而自学术“大跃进”起,受之前“反右”时对所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成“名”成“家”批判的影响,一股集体写作文学史的潮流在中国大陆兴起并延续至今。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这场文学史集体写作的运动中,以集体写作取代个人修史固然有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也与写作者的身份有很大关联。当还在读书的大学生意图在“文学史阵地”上“插红旗”时,他们的知识储备、阅读范围都十分有限,几十万言的文学史毕竟不是不读作品仅仅靠马列主义先进理论就能写就的,故而集体写作也成为当时参撰者扬长避短、减轻负担的必然选择。
具体到当代文学史写作,与山大版、华中版相比,文研所版的集体写作阵容和方式都差别较大。在接下中宣部的任务后,与一群大学师生匆忙上阵而缺乏必要的篇幅节制和筛选眼光不同,社科院(当时称科学院)文研所有组织的开始筹划写作,据参与者回忆:
“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要写《十年文学史》,十年时间毕竟太短,还是用《新中国十年文学》吧。会议决定,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要在全所范围内组织力量,集体突击撰写《新中国十年文学》。随后从理论组、古代组、现代组、西方组、民间组抽调人员参加写作工作。”[15]
正是由于文研所版虽也是集体撰写,但参与者毕竟有一定文学研究功底并在文研所所长何其芳主持下进行的,所以现在来看大多结论和判断是留有一些学术余地的,也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其学术品质。这种由专家领衔、众学者联合写作文学史的相对独立而又有机统一的“集体写作”在当下也屡见不鲜。
对于此时兴起的“集体写作”,笔者以为有必要多说几句。如今,集体写作文学史已成常态。然而,集体写作的弊病正如郑振铎所指出的:“合作之书,出于众手,虽不至前后自相背谬,而文体的驳杂,却不可掩。”[16]十七年时期各高校组织师生集体撰写文学史(不独当代文学史)所秉承的意识形态观念和政治立场虽然已经被当前学术研究所摒弃,但也并非一无是处。那时的“集体写作”虽然参与者众多,但因其在统一的史观、史识下写作,并抱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兼有强大的意识形态规训,故而无论叙述风格、历史意识、评价标准都难得地做到了前后统一,既少有篇幅内容的重复,也鲜见前后观念扞格,如同一人独立著史一般。笔者承认,文学史编写方式应该是多样的,文学史写作当然也应该是自由的,但是在一本文学史内部前后基本观念的一致性且叙述的同质性则是其建构具有普泛意义写作范式的前提,否则把文学史搞成支离破碎的“论文(著)拼盘”反倒失了“史”字的严谨。反观当下文学史(不独当代文学史)的集体写作,有不少史著参编者水平参差不齐,有些态度不够认真以致东拼西凑,参编者撰写范围划分不够清晰而造成前后重复等等问题都值得反思。
结 语
在学术史的视野下来看,这一时期的当代文学修史实践显然缺乏足够的学术准备,也毋庸讳言,这几本著作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学术缺陷,主要体现在这三部当代文学史尽可能把社会主义文学的成就放大(文研所版措辞还较为谨慎),而体现出“当代文学”(内在的文学性质是“社会主义文学”)在中国文学的进化链中超越了“现代文学”。然而颇为讽刺的是,在这些文学史写作同时周扬在讲话中显然不认为“社会主义文学”超越前代文学发展的成就,他在1958年谈到新文学时说:“比之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和有四五百年历史的欧洲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学,时间就短得多了。怎么能拿衡量几百年、几千年中所产生的东西的尺度来要求几十年中所产生的东西呢?”[17]作为文艺战线实际负责人,周扬的这些话让这几部当代文学史对“社会主义文学”的鼓吹显得有些尴尬。此外,这些的文学史在出版后面临更尴尬的境地。毛泽东对《戏剧报》、文化部工作的两次批评和后来连发的“两个批示”显然几乎全盘否定了他们所力捧的“当代文学”,也使得当代文学史写作匆匆开始后即草草收场。十七年时期当代文学史写作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过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它为学科话语的生成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也为文学史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知识范式,其中的有些学术经验也值得后人借鉴或反思。
[1]许志英.给“当代文学”一个说法[J].文学评论,2002,(3):34.
[2]纪延.红旗插上了文艺教学阵地[J].文艺报,1958,(12):36.
[3][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G]//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60.
[4]林纾.林琴南致蔡元培函[G]//蔡元培全集:第3卷(1917—1920)[M].北京:中华书局,1984:274.
[5]胡适.白话文学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6]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J].文艺报,1959,(18).
[7]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
[8]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4-5.
[9]朱晓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06,(1):148.
[10]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3.
[11]华中师范学院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1.
[12]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134.
[13][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M].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543.
[14]鲁迅.致王冶秋[M]//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43.
[15]卓如.参加编写《新中国十年文学》的前后[G]//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岁月熔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33.
[16]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3:9.
[17]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J].文艺报,1958,(5):9.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and Knowledge Paradigm—Academic Study about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istory in“17 Years”
LIU Y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In 17 years,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istory writing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then became the foundational discourse.At the time,the author was to uphold the concept of socialist literature.However,when arguing Contemporary Literature's discipline and legality,they shared the same kind which emphasized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with Hu Shi who wrote the Vernacular Literature History.Meanwhile,several Literature histories in this period explored a new academic paradigm about how to writ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istory.This is reflected in the four issues:Adhering to the evolution of Literature is based on social history,while emphasizing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Literature history;During the text analysis,value judgment criteria is ideology;The book is divided into period combined with the style category;The writing of Literature history transformed from the personal into collectivization.
17 Years;literature history;evolution;paradigm;academic history
I206
A
1009-1971(2016)05-0092-05
[责任编辑:郑红翠]
2016-07-02
刘杨(1989—),男,安徽六安人,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