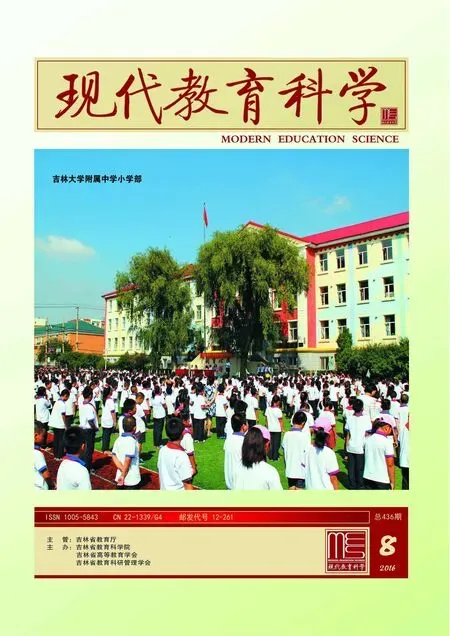学术救国:浅谈罗家伦的核心教育理念
李玉胜
(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3)
学术救国:浅谈罗家伦的核心教育理念
李玉胜
(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3)
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罗家伦毕生致力于“学术救国”的思想研究与实践。他肩负着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任,同时还承担着挽救国家危亡和改造社会的政治任务,具有教育与政治的双重角色。终其一生,他始终在“为学”与“为官”之间徘徊。尽管时常有“为学”与“为官”的选择冲突,但他所做之事仍多与学术密切相关。因此,罗家伦个人的学术成就和他在大学的学术管理,均可统一于他的“学术救国”的核心理念之下。重温罗家伦学术救国等大学教育理念与实践,可为现今大学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罗家伦 学术救国 核心教育理念
罗家伦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大学校长。他不仅是“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还是“中央大学”发展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32-1941年)。特别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央大学”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下西迁重庆,使得这所民国最高学府能够弦歌不绝,并成为大后方院系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一所国立大学。罗家伦掌校时期被誉为是中央大学的“黄金十年”。作为五四运动的健将,始终在“为学”与“为官”之间来回穿梭,这成为罗家伦人生道路的一个鲜明特色。他“不但对中国学术有所贡献,且其学术可影响社会和民族的将来”[1]。
一、博通中西:罗家伦的教育生涯及其历史影响
罗家伦,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897年 12月21日出生于江西南昌。幼年便开始接受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这为其打下了较为扎实的传统国学根基,初步奠定了其终身爱好文史的学术倾向。17岁时,罗家伦考入上海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中学部。三年学习期间,深受复旦大学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等学风的熏陶,深受启发,便时常发表杂文,针砭时弊。1917年,罗家伦考入北京大学,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恩师蔡元培与胡适。蔡元培对罗家伦颇为欣赏,为其提供了许多锻炼机会,并在经济上给予很大帮助。罗家伦也非常崇拜校长蔡元培,被其人格魅力和办学思想所吸引。后来罗家伦主持“国立清华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时,强调大学的使命在于学术研究,大学要重视师资,实行兼容并包、不拘一格的原则与作风,这都深受蔡元培思想的影响。罗家伦与胡适的友谊也比较深厚,在胡适的指导帮助下,罗家伦很快成长为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者和实践者,特别是创办《新潮》杂志来宣传思想解放与文学革命等主张。
1919年,罗家伦在五四运动前后奔走在北京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并起草了唯一的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在宣言中庄严宣告:“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2]被选为学生代表的他,冲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喊出了“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后深得民心,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健将”。之后,为避开军警的抓捕,1920年5月,罗家伦被蔡元培等选派赴美留学深造。赴美之后,便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历史和哲学。1921年华盛顿会议期间,他与爱国学生尖锐指出:“华盛顿会议不过是列强结成同盟,共同宰割中国而已。”[3]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受欺的事情刺激了罗家伦,表达了“仆仆于道路,而于国事无补,大足痛心”[4]的愤怒之情。之后,罗家伦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共选修了12门课程。1923年,在得到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的经济资助之后,罗家伦转赴欧洲,相继在德国的柏林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和英国的伦敦大学求学。在巴黎学习期间,他荣幸地成为巴黎亚洲学会的会员。1925年,罗家伦自马赛乘船归国。六年留学期间,罗家伦没有专门攻读学位,而是师从大师学习文学、哲学、历史、民族、教育等知识,极大开拓了他的学术视野,为其日后管理大学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回国后,罗家伦便供职于“东南大学”,教授历史。1927年,他受到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召见后,出任蒋的秘书,此后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新军阀阎锡山公开与南京国民政府决裂。阎锡山的势力控制华北之后,清华园内掀起了“驱罗运动”,罗家伦不能继续维持清华的局面,只好辞职。尽管上任只有两年的时间,但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贡献,仍然是卓著的,其中较为杰出的成就有两个:一是使清华改属于“教育部”管辖,为清华的发展扫清了制度上的障碍;二是从贪官污吏手中索回巨额清华基金,为以后清华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对此,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陈寅恪曾评价道:“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即不论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5]台湾地区学者苏云峰也感叹:“历史是不能切断的,罗家伦的成就,上承旧清华传统,同时开启了日后新的发展。人皆以为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实为梅氏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6]
1932年,罗家伦再次受命担任了“中央大学”校长,通过一系列改革,终于打造了一所名师荟萃、学术水平高、教学质量好的民国最高学府。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罗家伦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师生将“中央大学”的图书、设备、动物、植物等基本完好无损地搬到陪都重庆,这为保存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脉做出了杰出贡献。对于罗家伦的办学业绩,朱家骅后来回忆说:“我逼志希担任中大校长,苦了志希,救了中大。”[7]1941年1月,由于国民党内部高层之间的争权夺利,罗家伦被迫“主动辞职”,黯然离开了“中央大学”,虽然离开大学,但其对国家培养人才的贡献有口皆碑。之后,不甘寂寞的罗家伦又转入了政治之中,并于1969年病逝于中国台北。
二、“为学”:罗家伦教授的学术努力
尽管有学者认为,“罗家伦一直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求学与为政两难之间的取舍对于罗家伦来说并不是容易的事”[8]。但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之后,罗家伦曾反思说:“我的天性,确实在求学方面比事务方面见长。”[9]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尤其是赴美欧留学六年期间,他逐步明确了致力于推动中国学术独立的理想。他希望中国能够与世界接轨,组织各种学术研究机构,促进学术的繁荣,以增强国力。因此,留学时罗家伦不追求学位,他是根据学术需要到处游学,获取知识,博采众长。他回忆说:“当时大家除了有很强求知欲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其成,想在浩瀚的学流之中,另有会心,成一家言。”[10]正是基于此,罗家伦逐渐将历史学与哲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在任“东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期间,单独开设“中国近百年史”与“西洋近百年史”两门课程,并与其他教授一起开设了“近代西洋学术概观”课程。同时,他还与学界同仁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等人一道提出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并收集了大量资料,还提出建设一个中国近代历史博物图书馆的构想。在写给未来妻子张维桢的信中,他也提到:“现在的志愿,是学问上一件重大的贡献。我所愿过的是一种学者的生活”,“对于实际加入社会政治运动一层,我认为‘泥中斗兽’,决不愿以我更有效的精力,用在这种常得负号结果的事情上面。”[11]此时的罗家伦更愿将更多精力用于学术方面。
清华时期的罗家伦虽公务繁忙,但是仍兼顾学术研究。他得知清华历史系教员不够,立即亲任历史系主任并授课,同时还在北大兼任教职。他的女儿罗久芳回忆说:“每星期六上午进城到北京大学教一堂近代史课,下午去看外交档案,进行自己的研究课题。周末也常去故宫博物院看文物,去琉璃厂看画买书,或做访友郊游等活动……生活显得非常愉快。”[12]可见,他此前制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计划并未因为“为官”而中断,他好似在“为学”与“为官”之间找到了和谐相处之道。
1932年,罗家伦在一次东南大学毕业生晚宴中对学生说:“望诸位勿以中央大学新校长来看我,请以东南大学旧教授看我。”[13]这样说不排除与毕业生拉近关系,但也可见他对自己教授身份的眷念和钟情。在“中央大学”期间,他没有兼任教职,但也常常出现在讲台上,如多次进行学术演说,内容有“甲午之战”、“民族与文学”等等。1936年,他邀请秉志、何廉、翁文灏等与自己一起讲授“近代文化概论”课程。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也是罗家伦关注的重点,在海外游学期间他就收集了不少材料。任“清华校长”期间,他与历史学家郭廷以开设了“中国近代史”课程,郭廷以受到了罗家伦许多的帮助,学术上终于有所成就,后来主持了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开一代风气。罗家伦最具代表性的论著是1942年出版的《新人生观》和1946年出版的《新民族论(上)》。第一部著作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的几十年,均对中国无数青年产生了较大影响,被商务印书馆多次翻印,并销售一空。
罗家伦还是一个诗人校长。他一生爱好诗歌、艺术。大学任教与留学期间,他翻译了大量外国的诗歌。在中国白话新诗方面,与胡适等人一起进行了较早的尝试。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强敌入侵,亡国灭种的危机、爱国的真挚情感交织在一起,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创作了不少爱国诗篇。
三、“为官”:罗家伦校长的学术管理
罗家伦担任“国立清华大学”与“中央大学”校长期间,提出了学术立国的观点,明确了学术独立的办学方针,取得了卓越的办学业绩。罗家伦校长一系列的学术管理理念推动了“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发展,在中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注重以学术标准为聘用教师的基本原则
罗家伦到“清华大学”后认为:“一个大学要办好,最重要的就是要教授得人。”[14]他坚持以学术标准聘任教师,一方面辞退不合格的教授,另一方面千方百计聘请优秀教授。“清华大学”原有55位教授,他一下辞去了37个主要靠关系进来的或是不学无术的、滥竽充数的教授,其中包括洋教员6个。例如有一位美国教授史密斯,教授英文和拉丁文,不懂教学方法,上课时从不讲解,总是让学生轮流读课文,以此打发时间。罗家伦告知他清华改制为国立大学,教学水准提高了,因此无法终身聘用他。还有一位教钢琴的荷兰教授,授课时竟然非礼女学生,调查情况属实后,罗家伦立即将其辞退。而当时“清华大学”留下的洋教员詹姆斯(Jameson)、温特(Winter)几人十分优秀,不仅加聘而且加薪。他还请了许多外国知名教授到清华任教,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学系JannesT.Shotwell、芝加哥大学国际私法教授Quincy Wright、英国剑桥大学教授L.A.Richards等,他们为“清华大学”增添了学术气氛。
罗家伦上任后两个月内就加聘了19位教授,如工程系的孙瑞林、生物系的陈桢、数学系的孙镛、化学系的谢惠、物理系的萨本栋、哲学系的冯友兰、国文系的杨振声和钱玄同以及沈兼士、政治系的吴之椿和蒲薛凤、历史系的朱希祖、地理系的翁文灏和葛利普等。同时他也留下了一些诸如陈寅恪、金岳霖、陈达等博学之士。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愿意把任何一个教授地位做人情,也决不以我自己好恶来定去取。”[15]罗家伦还延揽了一大批青年才俊。他认为这些年轻人到清华后给他们一个安定的生活,较好的设备,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去教学、研究,三五年或则十几年大多能卓有成就。如社会科学方面的蒋廷黻、叶公超、萧迈、蒲薛凤等;自然科学方面的萨本栋、李继侗、周培源等;文学方面的朱自清、俞平伯、杨树达等人后来均成为清华大学著名专家教授。罗家伦除给新聘的教授们重发聘书外,还给教授的工资较前增加了40-70元。罗家伦还专门成立了教师聘任委员会,效法蔡元培教授治校制度,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这些做法得到教授们的一致肯定。
罗家伦在“中央大学”时也是从聘请教授入手进行整顿改革的。他说:“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我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职位做过一个人情。虽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16]罗家伦因为学校用人之事得罪了不少人,以致后来到中国台湾时,蒋介石拟任他为“考试院”副院长时竟有许多人反对,蒋介石询问王世杰原因时,王回答说:“据我所知,罗志希做大学校长时,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合,他不管是什么人,都不接受,因此得罪了不少人。”[17]在“中央大学”聘任师资时,他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挽留一些老教授,如黄侃、吴梅、胡小石、孙洪芬等,又新聘了十几位青年才俊,如留日的物理博士罗宗洛、留法的物理博士施士元、地理博士胡焕庸、留美的数学博士孙光远和曾远荣、化学博士庄长恭等。二是减少兼任教授,一改过去“中央大学”教授专任比兼任少的状况,有利于教师队伍的稳定和教学质量的保证。三是利用学术会议尽力邀请专家来中大讲学,如经济学家马寅初、建筑学家杨廷宝、政治学家张奚若、天文学家张钰哲、化学家高济宇、医学家蔡翘、农学家金善宝、著名诗人闻一多和徐志摩以及宗白华、艺术家张大千和徐悲鸿等等。
(二)增加图书设备、打造学术环境是学术研究的可靠保障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罗家伦校长是既要大师,又要大楼。他讲求师资与设备的平衡,既要重人,又要重物。他不仅重视师资,认为大学教育当然以师资为第一,但物质条件亦不容忽视。他多方筹集资金,发展硬件,尤其注重教学科研条件的改善。罗家伦认为,办大学,教学课堂之外,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三馆”缺一不可。图书馆是知识的宝库,也是学生自学的场所;科学馆是学术研究与科学实验的中心;体育馆是学生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也是学生吃苦训练、团结协作、全面发展的要件。所以,尽管经费紧张,“三馆”必须优先考虑兴建。他说:“大学知识的发源地,就在图书馆与实验室。”[18]在扩建清华图书馆时,他仿照外国名校的做法,在阅览室一层增加了二十间教师研究室,给广大教师提供研究的便利。他还为图书馆以后的发展预留了六七亩的空地。最终,新图书馆共计花费70余万元,成为当时国内大学中最大、最有发展余地的图书馆。与此同时,他反对将办公楼和学生宿舍建得富丽堂皇,认为这是助长享受的风气,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开展。
在《两年来之中央大学》的回顾中,罗家伦回忆了在中央大学时所增加的建筑及设备:加建图书馆;新建音乐室;新建农学院种子室;新建农学院温室;新建农学院昆虫研究室;新建校门;新建实验学校理科新教室;重修生物馆;重修加建教育学院之教室;重修教习房;重修学生新宿舍……图书仪器设备,除已定未付者不计外,实支付已达389280元,合计建筑及图书仪器设备费,共838742元[19]。尤其是耗资22万元加建了学校图书馆,落成后的新图书馆可以容纳千人以上,容量较前扩大了四倍,成为当时首都最为宏大和现代化的图书馆。从1932年到1934年,中大的建筑费用就高达449464元。到1937年,中央大学的图书达到186617册,杂志220586册,总计407203册,其中中文204514册,外文202689册[20]。关于仪器费用,从1932年至1936年四年实际支付费用达836397元[21]。到了1937年,中央大学教学所需“仪器机械标本模型等,种类即繁,数量尤多”,成为教学科研工作的主要依托。中央大学各院系实验室建设均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如教育学院的普通心理实验室,共有心理实验及测验统计仪器1900多件,模型150多件,实验用仪器1400多件。理学院的无机化学实验室,可供250名学生同时做实验[22]。
罗家伦认为学校建设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学术的)两个方面,而物质建设归根到底是为学术研究服务的,因此“宿舍……是为好学的、为学术、为民族、为人类造福的研究者的栖息的地方。生物馆……是期望于其中能产生Darwin,或是Huxley,或是Weiamann出来。如果有人只是以添盖几所房子为荣,而不计其学术的灵魂,那么,对于此种事业,简直是一种侮辱”[23]。后来他在中央大学新校址的选定上,就充分考虑到学术研究的环境、场所等问题,力图将中央大学建成他心目中“理想的学术都城”。
罗家伦在办学过程中致力于追求“硬件”与“软件”同步发展的教育方针,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条件与可能。由于罗家伦坚持“人”、“物”兼顾的远见卓识,使他掌校时的“清华大学”与“中央大学”成为当时高等教育界的翘楚。罗家伦的成功办学实践对于我们今天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蓝图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谋求学术独立与“创建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是学术救国的精神动力
1928年9月18日,罗家伦在北平(现北京)清华园宣誓就职“清华大学”校长。宣誓后他向全体师生和嘉宾发表了“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的演讲。他强调“国立清华大学”的宗旨即谋中华民族在学术上独立发展,以完成建设新中国的使命。“中国以往的教育方针是借贷式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转贩外国已成的学术。留美预备部,就是这种态度的具体表现。这种态度,当然有它片面的成立的理由,但是从民族的观点看,一个民族要求独立、自由、平等,必须在文化方面、学术方面,先求得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方可。中国近几十年来,派送了几万的留学生,他们学成回国后,对于本国,固有相当的贡献;但是要谋我国学术的独立,必须自己有独立的最高学府,仅仅靠了外国的教育,那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24]。这种反思,正是罗家伦提出学术独立的内在理由。
关于实现“清华大学”的学术发展与学术独立问题,罗家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他向“清华大学”董事会提出了“四化”方案: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四化”的核心是学术化,本质上就是学术独立。目的就是要把清华从以往留美预备学校转变而成国家的完整大学——“我们既是国立大学,自然要研究发扬我国优秀的文化,但是我们同时也以充分的热忱,接受西洋的科学文化”[25]。冯友兰先生曾说过,“清华大学”的成长,是中国近代学术独立自主发展过程的标志。罗家伦执掌清华,倡导清华国立化就是现代中国学术独立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一步。
其次,为了发展学术,罗家伦进行了院系学科改革。他赞同蔡元培的建议在“清华大学”设立研究院,也大力发展清华本科院系的规模,先成立了文、理、法三个学院,整理原来的学系,强化理学院,并增设研究院。除此而外,他还制定了《国立清华大学条例》,坚持学术独立的办学方针,撤销了留美预备班,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坚持独立的办学方针。
再次,“改隶废董”运动的成功为他发展清华去除了障碍。所谓“改隶废董”即是改变了清华原来由外交部与教育部共管的尴尬局面,明确了“国立清华大学,直辖教育部”,保留了评议会、教授会,并增加了评议会、教授会代表的人数。1929年6月教育部颁布了《国立清华大学条例》,规定“取消两部共管和清华董事会。国立清华大学基金,委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负责保管”[26],至此,罗家伦与清华师生终于争得了所需的资金,取消了董事会等重大目标,学校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基本铲平。“改隶废董”成功之后,罗家伦制定了清华发展的长远计划:增加图书仪器购置费、添建生物馆、学生宿舍、扩充图书馆、气象台、注重办理研究院,培养研究高深人才,为学术独立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罗家伦在阐述动用基金意义时表示:“是为创立国立清华大学的新生命而动用,是为树立中华民族在学术上独立的基础——也就是为谋进中国民族独立的基础——而动用,是为培养建设新中国的生力军而动用。”[27]罗家伦在清华一系列的改革,使清华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追求学术研究的风气,并赢得了清华人的赞赏。西洋文学系主任王文显就曾对吴宓说:“罗校长力图改革校务,并增善教授待遇,所认为庸劣及为学生攻击之教授,固在所必去;而优良之教授反增加薪金……罗校长励精图治,人心悦服。此校前途或可乐观也。”[28]
罗家伦在“清华大学”提出了学术独立,中华民族要发展自己的大学和文化,在“中央大学”呼吁中大师生以“创建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己任,希望“中央大学”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大本营。他认为,教育对于民族独立与国家强大有着重要的关系,教育落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和当时许多的教育家所持的“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理想是一致的。
罗家伦任职清华和中大校长之日,正是中国遭受日本疯狂侵略之时,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他认为这个时期的中国大学存在的意义就是要承担起延续中华文化命脉、振奋民族精神的使命。大学要想承担起整个民族的使命就要养成新的良好的学风,因此他在“中央大学”时对青年学生提出了以“诚、朴、雄、伟”为核心的人格教育思想。“诚”,一方面指要诚实,以诚待人,一方面指对待学问要真诚,读书明理,不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朴”,性情质朴,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朴质无华;“雄”,即要有雄心壮志,英雄无畏的气魄,男生要有大丈夫气概,女生无病态;“伟”,指的是要有伟岸高远的心胸,不拘小节,要有宽广的视野,着眼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诚、朴、雄、伟”四字很好地体现了罗家伦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基本内涵。这四字后来成了“中央大”学的校训,引领着莘莘学子高尚人格与精神的养成。
“中央大学”新学风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校内各院系成立了从事学术探究的各类学会,如心理学会、园艺学会、森林学会等等。各种各样的学会活跃了校园学术氛围,有助于师生增加学术兴趣。罗家伦认为这种学术社团对于学生的学术训练和团体意识的养成均有好处,应大力支持。他明确指出:“各种学会的组织,……我是非常赞成的,至于其他的组织,顶好不要参加。中央大学学会很多,总希望大家参加,使其逐渐学术化。”[29]在罗家伦校长的支持下,当时中大学会主要是通过组织学术演讲与出版学术刊物两个方面来营造学术研究的氛围。如在1933年9-11月生物学会聘请校内外专家的演讲就有7次;政治学会则每周请名人演讲一次;心理学会每月聘请著名教授轮流主讲一次……当时的学术报告常常安排在致知堂,由于报告较多,“撞车”事件时有发生。后来注册组要求事先申报安排方可演讲,才逐步解决问题。各种学会还出版了各类学术刊物,如心理学会出版了《中大心理半月刊》、土木工程学会在《国立中央大学日刊》上编有土木附刊、园艺学会出版了《园艺月刊》、政治学会出版了《政治学》杂志等等。另外学生会还出版了《新文化月刊》《大学生言论》《校风》等刊物。总之,罗家伦上任后积极整顿校风,深受学生爱戴,中央大学学术研究的风气变得更加浓厚。
四、结 语
由于战争环境的影响,罗家伦从为中华民族求生存的角度来审视大学教育。他曾说过这样的名言:“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30]在他丰富而独特的教育思想中,大学作为肩负着“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崇高使命,首先必须建立在独立的学术研究之上。罗家伦坚持学术救国的信念,借鉴德国柏林大学重视研究的学术风气,坚持大学学术性第一的教育理念。毫无疑问,罗家伦的一生都致力于其信奉的“学术救国”思想与实践。尽管时常有“为学”与“为官”的冲突,但他所做之事仍多与学术密切相关。因此,罗家伦个人的学术成就和他在几个大学的学术管理,均可统一于他的“学术救国”的核心理念之下。
罗家伦认为大学校长最大的日常工作就是为广大师生准备一个环境做学问,他说:“我们主持教育行政的人,乃是牺牲了自己做学问的机会,来为大家准备下一个环境做学问。这是大学校长的定义,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大学校长的悲哀。”[31]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罗家伦并不认为大学校长是一种高官,而是行政上的服务。他始终把自己“为官”的宗旨定位成为全校师生营造一个好的学术环境的创造者与维护者。正因有了像罗家伦那样的一批通晓学术研究的大学校长的引领,民国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才迎来了发展壮大的“黄金时期”。为此,中央大学后来的校长顾毓琇评价他:“罗家伦对于教育之贡献,上承北大蔡元培先生之道统,下启中央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北交相辉映,可垂史册!”[32]
[1][12]罗久芳.父亲在清华大学[A]..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11,123.
[2] [9]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册)[M].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76:1,435.
[3] 罗家伦.外交会解释九国公约之危险[N].国民日报(上海版),1922-02-22.
[4] [11]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补漏”)[M].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76: 344,389.
[5] [30]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2册)[M].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9:864,820.
[6]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28-1937)[M].北京:三联书店,2001:32-33.
[7] 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110号,第2册) [M].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264.
[8] 李欣然.教育与政治之间:罗家伦校长的双重角色解读[J].高教探索,2015(10):93.
[10] 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 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0册)[M].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76:79.
[13] [24] [25] [29]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M].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8:231,51-52,19,246.
[14] [15]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8册)[M].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401.
[16] [31] 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6册)[M].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8:75,98.
[17] 王世杰.我对罗志希三点特别的感想[J].传记文学,1977,30(1):1-4.
[18] 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 [M].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8:64.
[19] 罗家伦.两年来之中央大学[M].北京:中央大学出版部,1934.
[20] [21][22]罗家伦.两年来的中央大学[A].《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上卷)[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317,450,330.
[23] [26][27]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校史资料选编(二)[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207,18,142-145.
[28] 吴宓.吴宓日记(第6册)[M].北京:三联书店,1998:134-135.
[32] 顾毓琇.顾毓琇全集(第11卷)[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469.
(责任编辑:平和光)
Academic Salvation: the Core Education Concept of Luo Jialun
LI Yusheng
(CollegeofMarxism,NanjingUniversityofPostsandTelecommunications,Nanjing,Jiangsu210003,China)
The thought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he famous educator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Luo Jialun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academic salvation”. He not only shoulders the important task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but also bears the political task of saving national peri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with the dual role of education and politics. Throughout his life, he has always been in the “learning” and “official” between the two. Although often have “choice” and the “official”, but still much of what he was doing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academic. Therefore, Luo Jialun’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his academic management in the university can be unified under his core idea of “academic salvation”. Review Luo Jialun’s university educational ideas and practice about academic salvation, which can provide the beneficial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university education.
Luo Jialun; academic salvation; core education concept
2016-05-04
江苏省社会科学2014年度基金项目“民国大学校长治校理念创新与江苏高等教育现代化路径研究”(14LSB002)。
李玉胜(1970-),男,江苏盐城人,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教育史。
G40-06
A
1005-5843(2016)08-0137-07
10.13980/j.cnki.xdjykx.2016.08.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