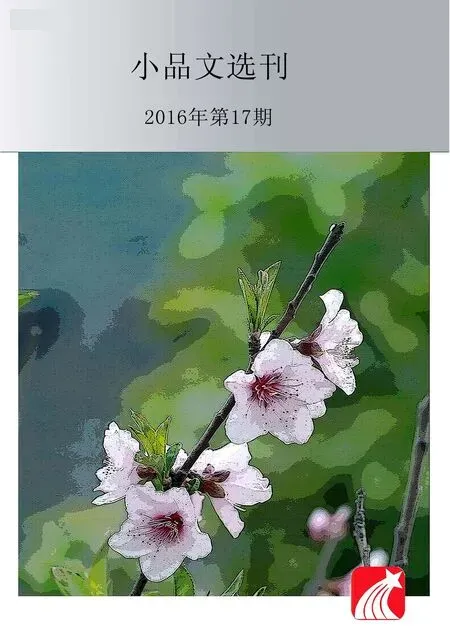野性的民族与劳作的人
吴 姝
(重庆三峡学院 重庆 404100)
野性的民族与劳作的人
吴 姝
(重庆三峡学院 重庆 404100)
中国人的脸上似乎总缺少点什么东西,但看久了又觉得似乎不缺。反而看西洋人的脸倒觉得有几分兽性。自然不必说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是本来就没有的呢,还是现在已经消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也渐渐净尽了而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是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
——鲁迅
从历史记载来看,近代中国的衰落是由鸦片所致。毒品使中国劳动力丧失殆尽,中国人民普遍萎靡,在点燃鸦片的时候也燃尽了野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民族失去了一种最重要的品质——野性。一头雄狮,垂下了高贵的头,停止了漫山遍野的奔腾,收低了嗓音不再咆哮,那也就意味着他此时已身处牢笼,成为人们的赏玩之物,做一辈子的囚徒。于一个民族而言,野性是必须拥有的骨气。民族的存在与发展,独立与尊严,将与野性息息相关。
中国作画大师徐悲鸿所画之马多为拼命奔腾之骏马,马之野性喷涌而出。此乃野性之魅力。那么,中华民族之马能丢掉野性而成为家畜吗?若让野马成为家畜,则马必丢其野性,失其草原,成其奴隶,终会灭亡。
做个才子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这是南唐后主李煜的悲剧命运。纵使曾写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千古华章,但肉袒负荆,请降于敌国,非才子之风流。鲁迅先生亦曾说过: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可见温柔的力量是有限的。止息暴力为武,在民族危难关头,野性才是救命稻草。
中国一直所谓“礼仪之邦”,男若书生儒雅,女若窈窕淑女,斯文亦恭顺,恭顺亦驯顺。而我以为,恭顺之人不足以成大器,恭顺之民族难以求独立。我们中华民族多了所谓斯文,然而在一连串的碰壁中又受了斯文的教训。当然了,温顺的耕牛或许能在奴役时少吃两下鞭子,但你必须劳作,无休止的奴役。农场主决不会因为你昔日是一个勤劳的奴隶而怜惜你,在你奴役至死的时候,也要剥下你的肉来,以达到“物尽其用”。这就是驯顺民族的结局。
我一直在思考,除了上述所谓野性的民族品格外,究竟还有什么原因是导致近代中国沦落的。鸦片在让人丧失野性的同时,还让我们丢掉了什么?
当吞云吐雾达到了一定的数量之后,吸食毒品就上升为一种社会现象,野性的丧失意味着精力的丧失,也就意味着劳动力的丧失。呵,我们的民族难道停止劳作了吗?
我不知道一个民族停止劳作有多么地可怕,只从后面的炮火恐吓中窥见一斑。停止了劳作,也就停止了吃饭,因为那样的民族已经无饭可吃。再肥沃的土地,失去了农人的耕耘播种,翻土施肥,也不会长出庄稼,就更别谈丰收了。我国纵使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不前进也就是倒退,不劳作也会衰亡。民族的惰性从来都是一个民族最致命的弱点。在猎人把缰绳套在我们脖子上的时候,连头都懒得摆一下,那就更不必再说反抗了。在鞭子的抽打下边做梦边奴役,为着不劳作付出奴役的代价,和着剩下的最后一点饥饿的本能,奴役着。懒散真是一大民族的悲哀。
蜀山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也许唐玄宗的爱情悲剧从他第一次选择寻欢作乐不上早朝的时候就已经注定。悲剧的承受者也是悲剧的制造者,而悲剧的制造者也往往就是那个最先放弃劳作的人。享乐是人的本能,而劳作一直都伴随着义务的强制。鲁迅先生曾说过:劳作或许当然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比起子弹从致命的地方穿过要好得远。起码劳作足以为我们明天的享乐打下基础,或是为我们子孙后代的欢愉做一个铺垫。没有劳作的享乐像没有封堤的水库,随时都有决堤的危险。
于是,民族的享乐需要的是稳固的幸福。为着这稳固的幸福,我们的人民必须劳作,当然,这所谓劳作到底是义务的强制还是责任的担当全在于人民的劳作之心。不过,为着民族的享乐而劳作,我相信这汗水不会是苦的吧。
一个民族的衰亡从他丧失野性开始,一个民族的衰落从他的人民放弃劳作的时候开始。

吴姝(1995-),女,汉,本科,重庆万州人,重庆三峡学院,汉语言文学(文秘与行政管理方向)专业。
G852
A
1672-5832(2016)05-004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