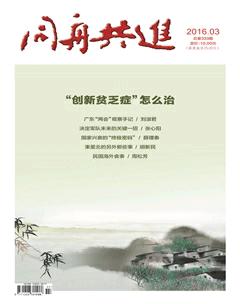电商打假的易与难
陶短房
2015年初,面对国内外纷至沓来的“淘宝成为假货平台”的指责,曾因“纳斯达克史上最大规模IPO”名扬世界的马云显得有些尴尬。他一方面表示“再难也要打假”“得罪人也要坚持”,另一方面也不免为自己辩几句。如果说最初“围攻”马云的,是以外国投资机构、知名品牌、竞争对手和民间组织等为主,那么到了2015年尤其年底,情况便转为以国内电商同业为主。那么,网络打假到底是容易还是困难,各家所述的道理到底谁更充足呢?
一些网购平台经营者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只是个平台,网店售假不是我们的责任”,这的确是网络电商发源地——北美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电商产业首次兴起以来所遵循的惯例,即只做不直接插手经营的“纯平台”,一般不因平台上的电商出售假货而被消费者或消费者组织追究直接责任。
但“只负该负的责任”可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负责任”。北美拥有全世界最发达、覆盖面最完善的信用体系,这种信用体系既适用于自然人,也适用于法人,且有严密、科学的业内评估系统,如果信用纪录恶劣,评分不佳,则会有非常严重的影响。对于自然人,可能意味着找不到好工作、难以升职、不能报考名牌学府,甚至申请不到房贷,而对于法人,则不仅会损失无形、间接的商业信誉、顾客口碑等,也会损失许多有形的、实实在在的利益——比如影响其IPO或其它各种融资信贷行为等。
正因如此,在北美很少有网络电商“纯平台”敢公然作出“我们是纯平台,挂靠商家售假和我们无关,我们想管也管不了”的姿态。尽管投诉者的确很难因平台上的商家售假,而直接把追究法律责任的矛头对准平台本身,但如此“我们不能作为”之类的言论一定会激怒市场、投资者和消费者,令自身商业利益和信用受损,也可能构成“不当言论”而受到投诉者的申诉和追究。事实上,前些年也的确有一些平台经营者(如亚马逊早期)“嘴硬”,有过类似姿态,结果在火冒三丈的消费者和消费者组织面前,“嘴硬”很快就被解读为“嘴欠”,最终不得不“自我消毒”了事。其实消费者和投诉者也非吹毛求疵,尽管平台并非直接经营产品销售的终端,但在权利范围内,的确该有重要且行之有效的打假防假手段。
众所周知,电商最有力的市场经营武器,是相对低廉的成本和价格,便捷的支付手段,和丰富、快捷、辐射范围广泛的网络信息传播途径。不论是在北美、中国或任何一个电商市场,这三点优势都必须借助平台来发挥效果,中小电商经营者才能实现“无实体店铺”的低成本运营模式,才能充分发挥互联网这个“信息传播倍增器”的潜力,让自己的商业促销行为事半功倍。就连支付和支付安全这个电商曾经的最大障碍,如今也已依靠第三方支付工具得以解决,电商平台是联结第三方支付工具和挂靠平台的中小电商间的纽带。
正因平台所起到的桥梁和事实上的信用“附加值”提供者作用,平台经营者完全可以通过设置“开关”,来有效遏制假冒伪劣的盛行。具体说,就是对那些经营假冒伪劣情况属实者,采用限制乃至中断某些平台功能等的手段加以制裁。挂靠平台的中小电商原本就多半存在利润薄、资金链紧张、市场营销和辐射手段有限等问题,倘因制假售假,被电商平台限制信息发布范围、限制或阻止第三方支付,便会面临现实的生存问题。由此可见,对假冒伪劣盛行的情况,平台经营者不仅有责任,而且是有办法的。
但认为打假很容易的说法也非全然正确。事实上,前面提到的许多在北美行之有效的平台打假手段,若在中国当前的电商环境中实行,恐怕仍会遇到较多阻力和局限。
首先,北美电商打假的有效性和杀伤力,很大程度上基于无所不在、威慑力十足的信用体系。不论是电商平台的自律、自查及自证,还是对加盟的中小电商的规范措施,都是相当到位的,谁也不敢拿自身的资信开玩笑。与之相比,中国大陆的资信体系(尤其个人信用体系)仍处于萌芽阶段,不论是法人的融资、信贷,还是自然人的升学、提职、加薪、申请按揭等,和信用分数之间的关系都远不是唯一的甚至直接的。如此一来,北美电商环境中最具约束力的一环,中国电商市场就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效运用起来。
其次,支付体系和网络推广体系紊乱,也让平台本身的打假增大了难度。不仅如此,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在电商市场上,确实存在着明知是假货却因价格低廉而购买的消费者;也存在着并不讳言出售的是假货、丝毫不担心客人不上门的经营者。这样的氛围,致使一方面不是所有人都为网络打假叫好;另一方面,不论经营者、消费者,都不免存在一些“明打假而实护假”,或“选择性打假”现象。
必须指出,在打假方面,电商平台经营者固然有办法,但法制和体制要更有办法得多。以加拿大为例,与任何国家的网上交易一样,加拿大网络交易中的假冒伪劣数量也不在少数,且呈逐年递增态势,那么加拿大是怎样打假的?
在北美,电商业务的主流并非基于电商平台的小店主,而是传统商业企业的网购业务,即俗称“水泥加砖块”式电商,尽管这些电商同样有大有小,且其中许多如今已完全转为电商模式,或仅将实体店当作变相样品展厅,而主要靠电商模式“走量”。对这类电商企业,传统的消费商业法规仍行之有效。加拿大消费法规规定了“免责退货”条款,即便并非假货,只要顾客买后反悔,在一定条件下都可“免责退款”,如果拒不执行,一旦被消费者起诉,后果是很严重的。如此一来,“水泥加砖块”式网店若敢造假售假,简直是自讨苦吃——要知道即便是贩卖真货,每年“节礼日”和复活节旺季销售后,反悔的“激情购物者”的退货狂潮,已让各网店忙碌不已。
当然,北美也有亚马逊、美国在线等电商平台,以及架设在诸如博客圈、BBS、电子看板甚至游戏区的平台附属性网店,对此加拿大采取了“切割责任”和“优先保护消费者”的规则:法律规定,如果能证明所买的商品是假冒伪劣,540天内可通知支付时使用的信用卡发卡公司,后者会承诺全额退款,所购假货自行处理。之所以如此规定,实际上是发卡公司有权根据商业契约向售假者索赔,而向售假者索赔的过程冗长繁琐,有时候还未必成功。如此,发卡公司会把售假者列入“黑名单”并取消用卡资格,这些售假者今后再申请用别家信用卡支付系统也很可能碰壁。
依靠体制和法制打假的好处,不仅可以把“追究责任”和“维护消费者权利”拆分成两个单元分别处理,从而化难为易,还可鼓励电商市场更多向打假防假的经营、消费模式倾斜。
对于我国的电商环境而言,除去前述种种措施外,加快个人/法人资信系统的建设和完善,健全相应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和北美等发达市场相比,基础性、框架性建设方面的差距更大。
2015年12月21日,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宣布,任命辉瑞制药副总裁兼首席安全官、曾在辉瑞公司和苹果公司负责过反假冒监督工作、曾任联邦司法部计算机犯罪与知识产权司检察官的马修·巴希尔为新设立的“全球知识产权执法负责人”,负责加强打假力度,应对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投诉。自2016年起,这位“淘宝首席打假官”走马上任。
在北美大企业中,往往设有或由副总裁等兼任专门负责知识产权纠纷的高级主管,但他们通常负责的是处理自身知识产权被他人仿冒侵害的问题。而淘宝2015年底设置的“全球知识产权执法负责人”,却是负责接受外界投诉,处理本平台假冒伪劣问题的“新生事物”。
这一不寻常举措进一步表明,一方面,应更多将控制电商假冒伪劣泛滥的责任和希望,寄托在法制和体制建设上;另一方面也要随时提醒电商平台经营者,必须清醒认识到自身在这方面的责任所在和作为之必须——效果如何固然是能力和条件问题,但做不做可千真万确是原则和态度问题。
(作者系旅加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