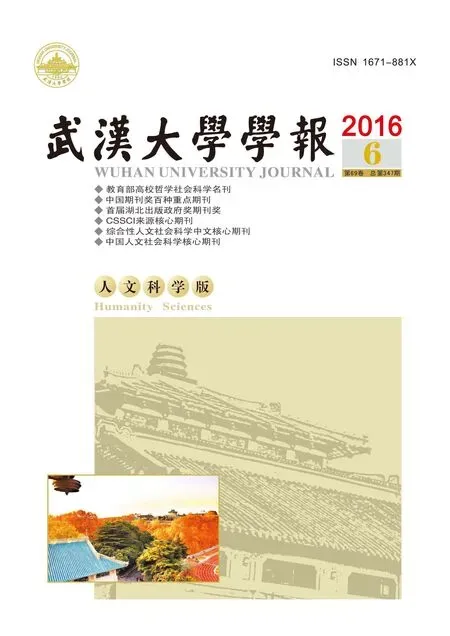易卜生对中国当代话剧创作的启示意义
汪余礼
易卜生对中国当代话剧创作的启示意义
汪余礼
中国当代话剧的发展仍然需要易卜生。这一方面与易卜生戏剧的精髓有关,另一方面与中国当代话剧的发展要求有关。易卜生戏剧的精髓在于“自审精神”“复象诗学”等,它们使易卜生戏剧最终达到了现代主义与先锋主义完美结合的境地,这对于中国当代话剧充分实现“现代化转型”是颇具启示意义的。借鉴易卜生戏剧的精髓,融会贯通灵活化用,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推进中国当代话剧的现代化转型:一是在创作主体方面,从迎合政教转向独立自审,逐步实现戏剧艺术精神的现代化;二是在表现对象上,从社会问题转向个人的内在生命,进而实现戏剧艺术的本体翻转;三是在创作手法上,从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转向丰富多样的现代主义手法,创造现代诗化戏剧。
易卜生; 中国当代话剧创作; 现代化转型
作为“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不仅深刻影响了欧美现代戏剧的发展进程,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戏剧的精神风貌,甚至间接参与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但是到了今天,易卜生是否已经过时?如果没有过时,他对中国当代话剧创作还有什么启示意义?或者说,我们还可以从他那儿学习什么?
在当代中国,不少学者、编剧认为易卜生只是一个现实主义剧作家,已经过时,或只宜绕开。在美国也存在类似情形。但有极少数学者、作家持不同看法。比如,中国著名戏剧理论家谭霈生先生认为,中国当代剧作家仍然“应该继承易卜生的艺术精神与戏剧传统“*谭霈生:《消除误读,走进易卜生》,载《剧院》2007年第3期,第38页。;美国当代剧作家阿瑟·密勒也认为易卜生并未过时,“其戏剧中的诗性和神秘主义还有待进一步挖掘”*阿瑟·密勒:《易卜生与当今戏剧》,刘娅译,载《对流》2015年第10期,第47页。。其实,易卜生戏剧中值得当代剧作家继承、借鉴、化用的东西远远不止于此。
在笔者看来,易卜生对中国当代话剧创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中国当代戏剧“精神萎缩”的背景下,易卜生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愈发显现出光彩照人、无法绕开的“大师”本色。下面试详论之。
一、精神衍变:从迎合政教转向独立自审
从戏剧精神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戏剧以“教化剧”为主流,中国现代戏剧以“问题剧”为主流;它们都是在戏剧之外寻求戏剧艺术存在的价值,骨子里带有迎合政教或配合现实社会种种需要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中国当代戏剧中依然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一点只要看看当今一些省市的重要剧院仍热衷于排演跑奖剧目便可知悉。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由政府主导的评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我国当代戏剧的迎合性、依附性,使得很多作品“少了些不应少的东西,多了些不应有的东西”*董健:《戏剧与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而真正有独立人格、有抱负有眼光的艺术家,要么只求艺术上的精益求精,要么深入反思、批判自身所处的社会与文化,是绝不愿意为了迎合某种实际需要而创作的。可目前缺乏独立精神的剧作确实比较多。正如著名学者董健所说,“90年代以来当代戏剧不可回避的总体特征是:虚假的繁荣掩盖着真实的衰微,表面的热闹粉饰着实质性的贫乏,其根本原因是戏剧精神萎缩,或曰戏剧失魂”*董健:《中国当代戏剧精神的萎缩》,载《中国戏剧》2005年第4期,第9页。。精神萎缩,正是中国当代戏剧必须直面的一个事实。
精神萎缩、自降为仆、迎合他者的作品,本质上不具有现代性。事实上,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转型仍然未完成。作为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它至少包括三个阶段:一是戏剧的内容从表现古人的情感、思想、生活转变为表现、反思现代人的情感、思想、生活;二是戏剧的形式从古典形式转变为现代形式;三是戏剧的艺术精神从古典精神转变为现代精神(即从和谐、寓教于乐转向分裂、自我批判,从同化于政教走向真正的独立、自律)。第三个层次的转变是最为艰难的,但只有实现这个层次的转变,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转型才算大功告成。回顾中国百年话剧的发展历程,前两个层次的转变已基本完成,但第三个层次的转变仍是个目标*谭霈生先生亦认为“转型已经成为时代对中国戏剧的一种潜在的要求”。他在《中国戏剧转型与学科建设思考》(载《四川戏剧》2009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戏剧已彰显出转型的趋势,或者说,转型已经成为时代对中国戏剧的一种潜在的要求。我说‘转型’,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戏剧在中国的生存状态开始转型,由国家全包、政府包办向市场文化、文化市场转型;另一方面是戏剧本体定位的转型,就是把戏剧从作为宣传教育工具向戏剧艺术的本体转型。”结合其相关论述可知,谭先生所谓“戏剧本体定位的转型”,是指戏剧从一种宣传教育工具转向一门具有独立品格的艺术样式,即回归艺术本体、坚守戏剧自身的独立品格。这实际上意味着戏剧艺术精神的现代转型。。换言之,中国戏剧在近现代的发展,主要是完成了从内容到形式的现代化转型;而中国戏剧在当代的发展,其历史使命是要完成戏剧艺术精神的现代转化。如何实现这一“现代转化”呢?易卜生戏剧恰好可以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
20世纪初叶,中国学人(如胡适、欧阳予倩、郭沫若、洪深、田汉等)汲取他们所理解的“易卜生主义的精髓”,创作了一系列新戏剧,开启了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历程。但中国学者、戏剧家对易卜生的学习,比较注重他敢于写实、敢于提问、敢于批判的那一面,而忽视其更为重要的独立自审精神。其实即便是批判社会现实,易卜生也是以人格独立为前提、以自我净化为目标的,这与我国剧作家的社会批判是有差异的。易卜生认为,“独立不倚的人才是最强大的人”*《易卜生书信演讲集》,汪余礼、戴丹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122页。。“诗人的使命不是为国家的自由与独立负责,而是唤醒尽可能多的人去实现独立自由的人格”*《易卜生书信演讲集》,第182页。。其对于个体精神独立是非常看重的。为了坚持独立写作,坚持批判立场,他不惜与整个挪威社会对抗,即便流亡国外也不改初衷。他宁可成为“人民公敌”,宁可与整个社会现实处于紧张的对抗状态,也绝不愿意自己的创作成为达致某个具体目标的手段。其作品中的不少人物也颇具独立批判精神,如布朗德、斯多克芒、罗斯莫等。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易卜生戏剧的世界里,“人们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即使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引自恩格斯写给保尔·恩斯特的信,载《易卜生评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第8页。。而这些独立之人,往往是全剧给人印象极深之人,感染力量也几乎是最强的。鲁迅就特别欣赏易卜生的独立批判精神,不仅赞其本人“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也称其笔下人物“宝守真理,不阿世媚俗”*鲁迅:《文化偏至论》,载吴中杰编:《魏晋风度及其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页。。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易卜生的独立批判不只是指向社会现实,也指向自我的一切。1880年易卜生致信路德维格·帕萨奇说:“我写的每一首诗、每一个剧本,都旨在实现我自己的精神解放与心灵净化——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他所属的社会的责任与罪过。因此,我曾在我的一本书上题写了以下诗句作为我的座右铭:生活就是与心中魔鬼搏斗;写作就是对自我进行审判。”*《易卜生书信演讲集》,第190页。他从早期到晚期的剧作充分体现了这种“对自我进行审判”的自审精神。无论是早期的“灵魂自审”,还是晚期的“双重自审”(灵魂自审与艺术自审),易卜生都确乎是站在一个非常高的峰顶上,以非常深远的目光来审视自我的内在生命,进而对人类的本性进行审察与批判。独立批判、内向自审可以说是贯穿易卜生创作始终的精神内核,也是他最终成为“现代戏剧之父”的根本原因*汪余礼:《重审“易卜生主义的精髓”》,载《戏剧艺术》2013年第5期,第46页。。
由此反观20世纪中国话剧史,其间的精神差异特别引人深思。中国现代剧作家,尽管多数具有批判、战斗精神(其中不少批判、战斗是应时而生、配合现实政治需要的),但极少敏于内向自审、勇于自我批判。即便是深受易卜生影响的曹禺,他对易卜生的了解、学习也还有不够深入之处。曹禺68岁时曾自述,“在中学时代,我就读遍了易卜生的剧作。我为他的剧作谨严的结构,朴素而精炼的语言,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所发出的锐利的疑问所吸引”*曹禺:《悲剧的精神》,京华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这说明曹禺对易卜生戏剧精神的感知,虽然很敏锐,但主要停留在“社会批判”层面。到了后期,曹禺力求符合当时社会的政治需要,批判精神大大减弱,这样他即便殚精竭虑、反复修改,还是没有写出传世之作来。对此,曹禺研究专家丁涛认为:“曹禺对人及人性的视野,始终拘囿于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之中,不论这个世界是地狱或者是天堂,而始终没有进入到人与人自身这一关系中来审视人及人性。毋庸置疑,倘若不能从人与人自身这一关系来表现人及人性,那么,曹禺的创作意识及创作实践就不具备现代性。”*丁涛:《戏剧三人行:重读曹禺、田汉、郭沫若》,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8页。此论虽然说得过于绝对,但确实道出了曹禺(至少是后期曹禺)戏剧的主要缺点。现在来看,曹禺当年没有突破的创作困境,在当代戏剧创作界基本上延续下来了;而且,中国当代戏剧的批判精神更弱,其突破困境的希望显得更渺茫。但其实,如果中国当代剧作家沿着早期曹禺的戏剧之路往前追溯,真正汲取易卜生的独立自审精神,在这个基础上展开深层次的自我批判与文化批判,那么还是很有可能开出新路,并有效推进中国戏剧艺术精神之现代化的。
二、本体翻转:从社会问题转向个人生命
从迎合政教转向独立自审,有可能带来戏剧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这就是实现戏剧创作上的“本体翻转”:把创作的基点从“外在的社会现实”转向“内在的生命运动”,把戏剧艺术的本体坐实在个人的内在生命上*这里所谓“本体翻转”,是指戏剧艺术从以社会现实为本体转向以个人生命为本体。这种翻转是“精神衍变”的逻辑后果,两者在层次上是完全不同的。养成独立自审精神是相对于剧作家、导演而言的,是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之后,戏剧作品才可能在实体内容、表现对象上有根本性的变化。。
在这方面,易卜生的创作实践同样是极富启示意义的。易卜生中期的四大社会问题剧尽管在欧洲以至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他赢得了巨大声名,但这些在易卜生深邃的目光中只是一个必要的环节而已。他的野心远远不止于此。作为一名戏剧诗人,易卜生很清楚,在创作中“为自己并且通过自己为别人弄清那些使我们的时代和我们作为其中一员的社会感到激动的、暂时的和永恒的问题”*《易卜生书信演讲集》,第368页。是必要的,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他去做。这就是把目光从社会问题转向个人的内在生命,以个体心理结构为标本反思欧洲文化传统与人类本性,创作出具有永恒性的作品。易卜生心里很清楚,很多社会问题,虽然表面上体现为利益之争、观念之争或党派之争、制度之争,但其深层的根源在于人自身,在于人的本性以及人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易卜生很早就认识到,“对外革命、政治革命等等,这些只不过是浅薄之事,最重要的是来一场人类精神的革命”*《易卜生书信演讲集》,第104页。。因此,他很早就开始朝人物的内心开掘,以自身为标本反思民族以至人类的心理与性格,并取得了卓著的成果。他中期受勃兰兑斯影响,一度特别重视揭示社会问题;但到了晚期,他立定心志,在内向探索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今天看来,易卜生最杰出、最具现代性、最有艺术魅力的作品正是他早期的两部诗剧(《布朗德》和《培尔·金特》)和晚期的八部戏剧。这十部剧作的主体内容都不是讨论社会问题,而是在内向自审中展开个人的内在生命运动,表现个体自我的灵魂风景,探索人性的深层结构和人类的终极命运,同时也反思艺术创作的本质与功能。这些作品意味着,易卜生的创作重心不在社会问题,而在个人的内在生命,或者说他把戏剧艺术的本体牢牢坐实在个人的内在生命上。为什么这样一来其作品可以获得真正的现代性和持久的生命力呢?或者说这种转向的必要性和意义究竟何在呢?
首先,转向个人的内在生命,才是真正找到了现代戏剧的表现对象。这不仅是因为,在现代社会“现代思想关于人的规定注重人的个体存在的特色”*彭富春:《哲学与美学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9页。,而且是因为,个人在特定情境下内在生命运动的状态、形式、节奏、规律等等(或者说个体灵魂内部的奥秘)才是现代观众真正感兴趣的,呈现出这些才能满足现代观众的审美期待。一个人想看的,往往是他(或她)平时看不到、不了解的存在;而人们最不了解的往往是自己的灵魂,是自己以及他人内在生命运动的状态、节奏与规律。这是一个无限深广的领域,也是大批现代艺术家去不断探索的领域。易卜生曾经说过:“现代文学创作的秘密在于个人的切身体验。最近十年来我在自己作品中传达的一切都是我在内心里体验过的。”*《易卜生书信演讲集》,第367页。卡西尔则把易卜生的这种思想说得更显豁:“现代戏剧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但是这些运动的形式、韵律、节奏是不能与任何单一情感状态同日而语的。我们在艺术中所感受到的不是哪种单纯的或单一的情感性质,而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是在相反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恐惧、狂喜与绝望——之间的持续摆动过程。”*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89页。这就说明,聚焦于“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或“人的内在生命运动”),在反复体验中看清这种内在生命运动的形式与规律,并以明亮而强烈的光将其照亮,才是戏剧艺术家应该用心、用力、用技之处。而且,戏剧艺术的剧场性,一方面最便于直观地呈现(或表现)人物的灵魂运动,另一方面也便于演员与观众在现场进行心灵的对话、灵魂的交流。如果丢掉这种优势去讨论社会问题,那么戏剧人如何比得上社会学家、新闻记者及其他公共知识分子呢?如果戏剧不关注人的内在生命运动而力求逼真地反映社会现实,那么戏剧又如何比得上电影呢?因此,转向个人的内在生命运动,是现代戏剧必然的选择,也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合适的表现对象。这是易卜生注重探索人的内在生命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他那些精于“灵魂自审”“双重自审”的剧作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第二,转向个人的内在生命,现代戏剧才方便投入精神解放与文化创造事业,才能实现自身独特的价值,真正尽到自己的艺术职责。人生天地间,外在的问题通常可以通过外在的办法或手段来解决(比如政府决策、学校教育等等),但内在的问题(比如情感节律、人格结构、人性冲突等方面的问题)则往往只能靠引起人自身的觉醒和反思来解决。一个人只有自己真正愿意认识自己、解放自己,然后别人才可能解放他(或她),才可能逐步走上解放之路、幸福之路。易卜生在书信中曾经写道:“我们每个人唯一能做和做得最好的事情是在精神上和真理上实现自我。”*《易卜生书信演讲集》,第240页。这也许正是易卜生为什么非常关注社会问题却把创作重心转向探索人的内心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领域的问题不发现、不解决,人的自由幸福就只能是空中楼阁。拿易卜生晚期的《野鸭》来说,该剧的重心不在于讨论要不要“说出真相”的问题,而在于揭示剧中人物灵魂的痼疾、显示“野鸭”们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的内在生命运动。只有揭出人物“灵魂的深”,以强烈的光照亮它,精神的解放才有可能。再比如《罗斯莫庄》,其表层内容写的是党派之争,在一般剧作家手里很容易写成一个意志冲突非常强烈的社会问题剧,但易卜生描写的重心显然不在于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激烈争锋,而在于人物灵魂在复杂情境下的“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他一层一层地剖露人物的潜意识,揭示出传统文化对人灵魂的无形桎梏,以及“传统思想的根子”与“人性自身的弱点”交互作用对于人走上自由幸福之路的深层影响。正是在这种对人内在灵魂极为深邃的反思与光照中,传统人生观的局限显示出来,新型人生观、价值观浮出水面,由此该剧参与了文化创造,也体现出了真正的现代性。而唯有如此专注于个人的内在生命(特别是情感生命、潜意识),现代剧作家才能找到自己的存身立命之地,才能实现出自己独特的生命价值。当然,做到这一点非常不易,它需要剧作家对自己以及同胞们有非常深入细腻的研究,把人物性格在心里琢磨透了,看清他们灵魂深处的隐患,洞见他们走向自由幸福、走向新生的可能性,并精确而巧妙地表现出来,如此才能引人深思、发人深省,才能尽到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职责。这也是易卜生及其优秀戏剧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综上,独立批判、内向自审,把创作基点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转移到个人的内在生命,是易卜生戏剧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艺术启示。
三、形式革新:活用多种手法创造现代诗化戏剧
对于中国当代话剧创作来说,确立独立自审意识、转向个人的内在生命是非常关键的两步;然而,走出这两步之后,又该如何具体地去写呢?“如何写”往往比“写什么”更难。萧伯纳着重借鉴易卜生戏剧的“讨论”技巧,创作了一批将讨论与动作高度融合的社会问题剧,最终获得诺贝尔奖*萧伯纳于1891年出版论著《易卜生主义的精髓》,对易卜生戏剧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他尤其欣赏易卜生的“讨论”技巧,赞其善于将戏剧与讨论合而为一。1892年,萧伯纳发表他的第一个剧本《鳏夫的房产》,此后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剧作。萧伯纳是易卜生在英国的忠实维护者,其剧作深受易卜生影响。;阿瑟·密勒着重借鉴易卜生戏剧的“回溯”技巧,创作了一批将过去与现在融为一体的心理现实主义戏剧,最终亦自成大家*阿瑟·密勒是深受易卜生影响的又一位伟大剧作家。据他自述,他的成名作《全是我的儿子》(1947年首演)是其“受易卜生影响最深的一部作品”(见密勒《易卜生与当今戏剧》)。1949年,密勒的《推销员之死》首演并获普利策奖,该剧借鉴了易卜生的回溯手法(密勒明确承认该剧受过易卜生影响)。1950年,他改编了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并自述“我之所以决定要改编《人民公敌》,是因为我暗中希望证明,易卜生在今天实在还很有用,他并没有过时”(见《阿瑟·密勒论戏剧》,郭继德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11页)。详见阿瑟·密勒:《易卜生与当今戏剧》,刘娅译,载法国学刊《对流》第10期(2015年10月出版),第49~50页。。在当今时代,我们还可以从易剧中获得什么灵感,进而寻求戏剧形式的革新呢?
首先,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复象诗学”*详见汪余礼:《易卜生晚期戏剧的复象诗学》,载《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83~93页。,作为易卜生最具独创性的艺术贡献,非常值得当代剧作家领会、化用。当代学者赵毅衡曾就当代文学发展趋势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反讽之后,下一步是什么?西方论者虽多,没有一人好好回答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一旦某种表意方式走到头,这种表意方式就只能终结,重新开头的将是另一种表意方式。”*赵毅衡:《反讽:表意形式的演化与新生》,载《文艺研究》2011年第1期,第25页。我觉得,易卜生以他的创作实践已初步回答了这个问题。易卜生早期戏剧以“反讽”(或“悖反”)为根本特征;在“反讽”之后,易卜生中期走向了“回溯诗学”*易卜生中期戏剧在艺术表意形式上以“回溯”为显著特征,这一点论者甚多,故本文避而未谈。需要说明的是,易卜生中期戏剧的“回溯”仍然跟“反讽”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包含“反讽”于自身的。;到了晚期,则进一步走向“复象诗学”。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复象诗学”,虽然也包含有“反讽”和“回溯”的因子,但毕竟有重大的创新,毕竟把人类的艺术表意形式往前推进了一步。这种推进,内驱力源于易卜生的“双重自审”,而最后达到的层次是进入了“元艺术”境界——一种反身自审、艺中有艺、楼外有楼、境界层深的艺术境界。比如,易卜生晚期的《建筑大师》,表面上是一个“以建筑总管索尔尼斯和年轻建筑师瑞格纳之间的对立为基础的、描写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戏剧”*玛莉·兰定:《〈建筑总管苏尔纳斯〉读后》,载《易卜生评论:来自挪威作家》,石琴娥译,金谷出版社2006年,第94页。,实际上则是一部描写艺术家回顾他一生的艺术创作道路并反思艺术创作之本质与功能的戏剧。该剧中的建筑师,实际上就是艺术家,因为艺术家就是“用精神在人内心建造空中楼阁的人”(易卜生语)。在该剧开幕不久,建筑大师索尔尼斯痛感他的“艺术成就”以毁灭自己和他人的幸福为沉重代价,然后逐渐反思到他在创作中是如何与“妖魔”结盟,以及在早期如何替上帝效劳,中期如何背离上帝,晚期又深感上帝的威力难以违抗,最后向往神性真在,登上塔楼想要与上帝交流,等等。这部剧作让人窥见艺术创作的隐秘机制,让人感悟到艺术的本质与限度,以及人类精神从艺术转向宗教的可能性,在艺术学层面颇具启发性,确实是“境界层深”。再如《野鸭》《复活日》,也都是具有元艺术品格的复象戏剧。这些戏剧是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不为其他任何目的而作,可以说是高度自律的戏剧,从中也可看出“现代艺术的灵魂”。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说,戏剧艺术在易卜生晚期戏剧中达到了自我意识,易卜生也因而成为“作为艺术家的艺术家”。在易卜生之后,20世纪的极少数文学艺术家(如皮兰德娄、契诃夫、乔伊斯、卡夫卡、奥尼尔、贝克特、阿尔比、斯托帕德等)也创作了一些颇具“元艺术”品格的作品,在人类文学艺术的长河里激起了一朵朵新异的浪花。这对中国当代剧作家真正走向“艺术的自律”,进入“现代艺术的灵魂”,亦当有所启发。简言之,“复象诗学”之于当代戏剧的意义,在于默默启示着一种高度自律的元戏剧形式,一种指向新艺境的现代诗化戏剧。
第二,易卜生把写实、象征、表现*这里所谓“表现”,不是一般性的表现情感,也不是克罗齐所说的“表现”,而是对“体验过的世界,一个从内部看到的、不可复制的世界审慎而坚决的剖白”(杜夫海纳语),是对“灵魂之深”的具象显现。融为一体的艺术手法,特别是易卜生那种独特的表现主义手法,非常值得当代剧作家借鉴。易卜生戏剧表面是写实的,即便晚期戏剧仍给人写实的印象,这使得他的戏剧具有可进入性(或者说能吸引人看下去),但他作品中的情境、人物、意象、场面、情节等等却几乎都具有象征性、多义性,而且往往指向与戏剧表象很不相同的另一个世界,让人看不太清而又想反复去琢磨。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易卜生的优秀剧作就像是一种比较容易入口、但逐渐会觉得其味醇厚且后劲十足的陈年老窖。这种效果的产生,跟易卜生那种非常灵活的表现手法有关。一方面,他善于让“象征像矿藏中的银矿脉那样隐蔽地贯穿整个作品”(勃兰兑斯语),另一方面,他善于用种种意象、场面、人物去表现主角的灵魂世界*易卜生写人的内心犹如描写实景一般,真实感人且不露痕迹;而不少剧作者则把写心的工具(如面具、锣鼓、转台等)露在外面,其水平高下,判然有别也。。易卜生式的表现主义,不同于德国表现主义,也不同于斯特林堡式的表现主义,而是常常直接用一个人物去表现另一个人物。比如,在《海上夫人》中,用陌生人表现艾梨达的内心世界;在《建筑大师》中,用希尔达开显索尔尼斯的精神世界;在《小艾友夫》中,用鼠婆子暗示吕达和阿尔莫斯的心理隐疾;在《复活日》中,用一个白衣女客和一个黑衣女士透示鲁贝克的灵魂之舞。这些镜像人物亦虚亦实,亦真亦幻,在剧中往往适应情境运动的需要而悄悄“步入画面”或“淡出画面”,有时让人感觉神秘莫测,很难用现实的逻辑去解释;但究其来源,乃是易卜生派来显其神通者也。他们虽是“使者”,但各有性格,亦仿佛现实中人,颇能给人真实的幻觉——以至于直到现在,多数学者视其为普通的剧中人,而仅有极少数研究者窥破其身份为主司表现功能的镜像人物。而且,这种手法还给作品带来了浓郁的诗意,令人品味不尽*Martin Esslin.“Ibsen and Modern Drama”.Errol Dubach(ed.).Ibsen and the Theatre.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0,pp.71~82.。总之可以说,易卜生这种把写实、象征、表现融为一体的艺术手法,成功地将戏剧性与诗性融合起来,体现了他善能融会贯通、独出机杼的艺术天才,特别值得今人琢磨、借鉴。
总之,易卜生戏剧中的“自审精神”“复象诗学”“写实、象征与表现融为一体的艺术手法”及其他技巧,在今天都有很强的生命力,对我国当代话剧创作仍然颇具启示意义。在中国当代话剧的发展进程中,如果一部分有抱负的剧作家能汲取易卜生的独立自审精神与丰富的艺术智慧,确立戏剧艺术的独立品格,矢志推进戏剧艺术精神的现代化,则善莫大焉。从一种开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在中国当代戏剧转型期,确实需要一批志存高远、善于学习的剧作家,汲取种种化为己用,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责任编辑:何坤翁
The Inspirations of Ibsen’s Plays to the Cre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
WangYuli(Wuhan University)
Ibsen’s plays are still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 This is because of the quintessence of his plays and also because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 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s plays includes “Self-examinations”,“Polyimage Poetics” and so on,all of which enables his plays to be a perfect integration of modernism and avant-gardism and can provide valuable inspirations to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 Learning 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s plays comprehensively and applying it flexibly can promot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 in at least three aspects: the gradual modernization of the spirit of drama art,with the play writers changing from catering to political education to independent self-examination; the ousia reversal of drama art,with the objects changing from social issues to individual inner life;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etic drama,with the writing techniques changing from traditional realistic style to diverse modernistic style.
Ibsen;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 creation; modern transformation
10.14086/j.cnki.wujhs.2016.06.0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WW023)
●作者地址:汪余礼,武汉大学艺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 sealight9999@126.com。
——评葛斯著《易卜生传》
——王忠祥教授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