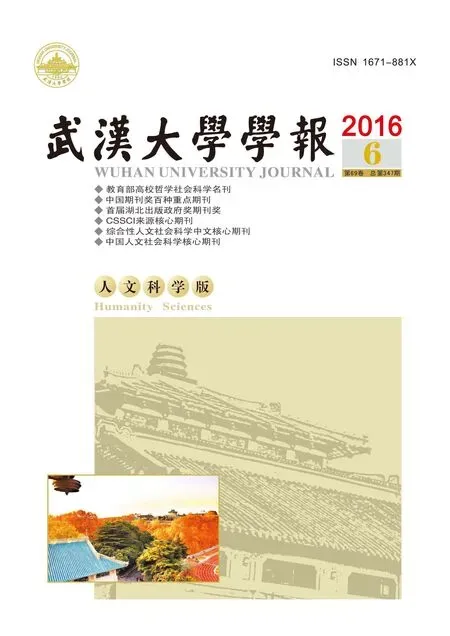论文学史的三重世界及叙述——对文学史内部构建的理论探讨
乔国强
论文学史的三重世界及叙述
——对文学史内部构建的理论探讨
乔国强
可能世界理论告诉我们,现实与虚构并不是截然分明地存在于这个可能世界之中的,而是因其可通达性以相互融合或交叉的形式存在。文学史也是一种以文本形式存在的交叉融合了真实与虚构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有三重,即虚构世界、真实世界以及虚构与真实因可通达而相关联的交叉世界。融合是指这三重世界的共同趋向,即因可通达性而共存于一个文学史文本之中,合力共同构建了文学史的文本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集合体;区别是指三重世界各有自己的属性、边界和功能。将可能世界理论运用到文学史的文本分析之中有助于揭示这些属性、功能的可通达性,并进而揭示出文学史的性质和内涵。
文学史; 可能世界; 虚构世界; 真实世界; 交叉世界
这篇讨论文学史三重世界的文章属于一种理论探讨,并非是对文学史写作,特别是对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梳理或评价。对文学史进行这种理论探讨,主要意图是探讨文学史内部的构建,并通过这种构建来看文学史写作的性质。这一探讨的理论出发点是可能世界理论。可能世界理论本身内涵丰富,运用到叙述学研究领域中,也有诸多拓展和创新。不过,本文所运用的可能世界理论,其内涵不是广义的可能世界理论,而是限定在叙述学研究领域内的可能世界理论;其方法不是对号入座式运用,而是在运用这个理论部分基本理念和话语的基础上,对叙述学领域里的可能世界研究做出一些修正,并提出自己的一些不同看法。
一、文学史与可能世界理论
可能世界理论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远溯至17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甚或更早。比如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曾提出了接近可能世界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他曾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64页。近期,再一次将这一理论提出并做出阐释的是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索尔·阿伦·克里普科(Saul Aaron Kripke)。他在1963年发表的《对模态逻辑的语义学思考》一文中,从语义学角度提出了模态结构,并对模态逻辑中可能世界问题做出了论证*Saul A.Kripke.“Semantical Considerations on Modal Logic”,in Acta Philosophica Fennica,1963,16,pp.83~94; Farhang Zabeeh,E.D.Klemke & Arthur Jacobson (eds.).Readings in Semantics.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1975,pp.803~814.以下所有对外文引用的文字均为本文作者所译,不再一一注明。。随后,相关文章和著作陆续出现,先后有S.K.托马森讨论《可能世界与许多真实价值》*S.K.Thomason.“Possible World and Many Truth Values”,in Studia Logica,1978,37(2),pp.195~204.、约翰·E.诺尔特阐释《什么是可能世界》*John E.Nolt.“What Are Possible World?”,in Mind,1986,380,pp.432~445.、卢博米尔·多勒兹论述《小说和历史中的可能世界》*Lubomír Doležel.“Possible Worlds of Fiction and History”,in New Literary History,1998,29(4),pp.785~809.等文章;另外还有玛丽-劳尔·瑞安从人工智能、叙述理论角度讨论可能世界的《可能世界、人工智能、叙述理论》*Marie-Laure Ryan.Possible Worl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Narrative Theor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露丝·罗南将可能世界理论用于文学研究的《文学理论中的可能世界》*Ruth Ronen.Possible World in Literary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约翰·戴弗斯对可能世界模式的界定和用“真正的现实主义”(genuine realism)等问题进行讨论的《可能世界》*John Divers.Possible World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罗德·格勒对可能世界的界定、对可能世界及其范域词、个体与身份、知识的可能世界、信仰的可能世界等问题进行论说的《可能世界》*Rod Girle.Possible Worlds.Chesham:Acumen,2003.等专著。在以上这些论述中,有些论者已经把可能世界理论与文学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关联,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未有研究者把可能世界理论引申到文学史的研究中来。从这个层面上说,本文也是对可能世界理论的一种突破与拓展,所以还需要进一步对这个理论予以简单地介绍与梳理。
可能世界理论在不同研究领域中有着不同的界定。莱布尼茨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点:(1)用非矛盾的方法来界定可能性,即只要事物的情况组合符合逻辑的一致性,这种事物的情况组合就是可能的;(2)事物发生的可能性是有理由的,即有因果关系;(3)现实世界是一种实现了的可能世界;(4)事物的发生具有双重可能性,即事物本身具有多种可能性和事物组合具有多种可能性*G.W.Leibniz.Theodicy,Charleston:Create 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Chicago: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86.陆剑杰:《莱布尼茨可能世界学说的哲学解析》,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4期,第51~59页。。随后出现的可能世界理论大都是围绕着他以上的这些观点构建起来的。比如说,约翰·E.诺尔特在《什么是可能世界》一文中曾说:“就‘可能世界’这个词语而言,就是它的字面意思,即世界。[……]要不是有真实世界的存在,我也不相信有可能世界。也就是说,我不相信它们的存在。但是,我一定要论证它们是可能存在的,理解它们的可能性是理解它们是怎样的一种方法。”*John E.Nolt.“What Are Possible World?”,p.432.诺尔特的这段话大致包含了三种意思,其一是因可能世界这一术语中“世界”一词使用的是复数形式(worlds),因此它指的是那些以多样形式可能存在的抽象世界;其二可能世界是相对于真实世界而言的;其三可能世界的存在是需要论证的,即论证是理解可能世界的一种方法。换句话说,在诺尔特看来,这个可论证的可能世界是与真实世界相互参照、互为补充的。它虽然只存在于观念之中,但是,通过论证我们对这个世界是可以理解的。
这种解释虽然能使我们从理论层面知道何谓可能世界,但是离着文学还有一定的距离。把上述的释说较好地引申到文学作品内部中来的,是叙述学界。他们对此的一般解释是,这个理论的思想基础是集合理论,并认为现实(想象的总和)是由不同因素组合而成的一个多元宇宙。在他们看来,这个宇宙是由相对立的一些特指因素分层构建起来的。特指因素是这个多元宇宙系统的中心,对集合体中的其他因素产生作用。另外,他们还认为,这个中心因素通常被称之为真实世界,环绕周边的因素仅被视为可能世界。在可能世界诸多因素之间,有一种可通达关系与之相关联。这种可通达性决定了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边界*Marie-Laure Ryan.“Possible Worlds Theory”,in David Herman,et al.(eds),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446.。
这个解释告诉我们,可能世界是从集合理论出发的,所研究的是与抽象物件构成整体相关的集合、元素及其成员之间关系等。用在叙述研究中,则主要是指对叙述文本这个整体内部各要素的集合及其之间的关系等所进行的研究。这个解释还特别强调了可通达性在区别可能与不可能之间边界的重要性。
显然在叙述学界,研究者们也只是把可能世界理论运用到文学作品的分析中去,而还没有运用到文学史的研究中来。本文之所以决定从可能世界理论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史,主要是基于三种考虑:
其一,可能世界理论是一种敞开式的理论,既探讨了世界的真实性一面,也探讨了世界的虚构性一面,把世界的“实”“虚”两面都关照到了,即最大程度地把世界的可能性面目呈现了出来。这种理论对拓展研究文学史的思路非常有益,如以往的文学史编撰者多半都是从实的层面上来考虑文学史,而忽略了虚的那一面。这个既注重实又注重虚的理论,对我们全面认识文学史的内涵及其属性会有极大的激发意义。
其二,可能世界理论告诉我们,现实与虚构并不是截然分明地存在于这个可能世界之中的,而往往是因其可通达性(accessibility)而以相互融合或交叉的形式存在。作为集合了各种文学史料的文学史,也是一种以文本形式存在的交叉融合了真实与虚构的文学世界。或确切地说,这个文学史的世界有三重,即虚构世界(fictional world)、真实世界(actual world)以及虚构与真实因可通达而相关联的交叉世界(cross world)。在文学史文本中,这三重世界既有融合,也有区别。融合是指存在于文学史文本中的这三重世界的共同趋向,即三重世界因可通达性而共存于一个文学史文本之中,合力共同构建了文学史的文本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集合体;区别则是指文学史文本中的三重世界各有自己的属性、边界和功能。将可能世界理论运用到文学史的文本分析之中有助于揭示这些属性、功能的可通达性,并进而揭示出文学史的性质和内涵。
其三,正如前文所言,在西方社会,可能世界理论已经被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来了,但迄今为止还无人将该理论运用到文学史的研究之中。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拟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研究对象的改变,即从原来研究的逻辑、文学作品、人工智能、数字媒介等转移到对文学史的研究上来;二是研究方法的改变,即在借鉴可能世界理论的基本理念基础上,将可能世界理论中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拆分开来或做出某些修正,运用到对文学史的分析之中,以期在深入分析文学史的本质和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可能世界理论或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不过,这里还需要说明两点:一是这里就文学史的虚构世界、真实世界以及交叉世界及其叙述分开来讨论,更多是出于讨论上的方便,而并非认为从整体上看这三个世界是以截然分开状态存的;二是可能世界理论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可能与不可能。在这篇讨论文学史三重世界的文章中,这种不可能由于文本化和可通达性而不复存在。这一点将在后文中进行论证。
二、文学史的虚构世界
在可能世界理论中,虚构是一个重要问题。许多学者针对这个问题做过专门论述。比如说,托马斯·帕维尔、戴维·刘易斯、基迪恩·罗森、彼得·孟席斯和菲利普·裴蒂特、露丝·罗南*Cf.Thomas Pavel.Fictional Worl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David Lewis.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Oxford:Blackwell,1986; Gideon Rosen.“Modal Fictionalism”,in Mind 99,1990,pp.327~354; Peter Menzies,Philip Pettit.“In Defence of Fictionalism about Possible Worlds”,in Analysis,1994,54(1),pp.27~36; Ruth Ronen.Possible World in Literary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等都曾运用逻辑或文学分析的方法,论证了虚构存在于可能世界中的问题。在这些学者看来,无论是从逻辑还是从文学的角度看,虚构既可以看成是可能世界的一个特征,也可以看成是可能世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已经不是个问题,甚至可以说已是个常识了。然而,在我们的文学史写作和研究中,虚构还没有作为一个问题受到重视;或者说,虚构在文学史中的性质、属性以及存在方式,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和论证的问题。
严格说来,文学史的虚构也不是一种单维度的虚构,而是至少有三重意义的虚构,即文学史所记载和讨论分析的文学作品的虚构、文学史文本内部构造与叙述层面意义上的虚构,以及文学史中各个相互关联的内部构造与外部其他世界之间关系的虚构。第一种虚构主要是针对研究对象而言的,即指出文学史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文学作品是虚构的。这种虚构不仅包括人物塑造和故事构建,而且还包括作者在叙说这些故事时所采用的话语和叙述策略等。第二种虚构是从文学史的本体上予以考察的,指出文学史写作如同其他写作一样,并非是对文学史全貌的照录,而是有着写作原则和编排体例要求的。这一点非常关键,这就意味着任何一种文学史写作都不可能是完全客观、全面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写作者价值观念的影响。譬如说,在某一段文学历史时空中存有100个作者、作品和事件,但由于文学史本的容量或其他问题,只能选取其中的30或50个写入文学史本中,这样一来不同文学史家的选择就会不同,写出来的文学史本也自然就不同。这种“不同”可能不单纯是对作者、作品、事件选择的不同,还表现在文学史结构形式及书写评价的语言、话语、术语等方面的不同。以上的诸种不同,足以揭示出文学史文本书写本质上的虚构性*参见乔国强:《文学史:一种没有走出虚构的叙事文本》,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第27~34页。。第三种虚构是从文学史写作的文化与社会语境层面上来予以考察的,指出文学史写作决不仅仅是文学史作者个人的事情,它还与塑造或影响文学史作者的文化传统、社会现实、时代精神、审查制度等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
在以上三种虚构中,第一种有关文学作品的虚构是显而易见和不证自明的,本文就不予以讨论了。下文分别讨论的主要是第二种和第三种虚构。先谈文学史的第二种虚构。
首先,我们可以从与客观现实的比照上来看文学史的第二种虚构,即假如我们把客观现实作为一个参照系,那么,文学史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个符合文学史作者思想结构和逻辑框架的一致性(这里的一致性既是指文学史作者预设的,也是指在文学史文本中呈现的一致性),就是文学史作者虚构出来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假如一部文学史的文本世界具有一致性是可能的,如文学史的编撰在编撰指导思想、价值取向、体例等方面应该取得一致,那么,文学史文本世界中的一致性是存在的。这种一致性可能主要体现在一部文学史写作的统一原则、体例、方法、价值观等诸方面。比如说,孙康宜在她与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序言中这样写道:
当初英文版《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辑和写作是完全针对西方读者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不是作为参考书,而是当作一部专书来阅读,因此该书尽力做到叙述连贯谐调,有利于英文读者从头至尾地通读。这不仅需要形式与目标的一贯性,而且也要求撰稿人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互相参照,尤其是相邻各章的作者们。*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文学史》,刘倩等译,三联书店2013年,中文版序言第1~2页。
从所引这段文字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样几层意思:其一,原来《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者们,在写作之前就预设了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编写目的(“当作一部专书来阅读”)和自己设置的,但并非所有参编者都十分明晰的期待视野或隐含读者(完全针对西方读者的)等;其二,他们为达到写作的形式与目标的一贯性的目的,要求编撰者相互协调(撰稿人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互相参照)。应该承认,从《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情况来看,这种经预设和协调而取得的一贯性是存在的。然而,诚如孙康宜所言,这种预设和协调出来的一贯性,在客观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或曰只是一种虚构的可能。
其实,几乎所有合作编撰文学史的编撰者们都会追求这种预设的一致性,但是这种协调出来的一致性与原来预设的一致性总会有程度不同的差异。比如说,《中国文学史》的编撰者在前言中曾坦承说,这部《中国文学史》由章培恒、骆玉明任主编,讨论、决定全书的宗旨与基本观点,经全体编写者商讨后,分头执笔,写出初稿。然而,编写者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看法只是大致近似,一涉及具体问题,意见互歧在所难免;至于不同的写作者所撰写各部分之间的不能紧密衔接,各章节分量的不均衡,文字风格的差别,更为意料中事*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从《中国文学史》编写这个例子中也可以看出,文学史文本世界中的一致性,不仅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而且在文本世界中也是难以实现的,充其量是人为地预设或协调出来的。即便如此,差异还是存在。从这个角度讲,文学史中的这种人为预设或协调出来的一致性,在现实层面上看具有一定的虚构性。
是不是个人独立编撰文学史就可以避免这类虚构性?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比如说,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中,所谈到的有关文学性的编写原则是重要一例。他说:“尽管‘文学性’(或‘审美性’)是历史范畴,其含义难以做‘本质性’的确定,但是,‘审美尺度’,即对作品的‘独特经验’和表达上的‘独特性’的衡量,仍首先被考虑。不过,本书又不是一贯、绝对地坚持这种尺度。”*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前言第15页。洪子诚的这番话说明一致性其实是一种人为的,既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很难绝对地坚持。另外一例是顾彬。顾彬在其编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序中,也声称自己“所写的每一卷作品都有一根一以贯之的红线”,即前文所说的一致性或一贯性。其实,假如翻看一下他编写的各章节的目录就不难发现,这根红线从一开始就被他所采用的错误的时空秩序给打乱了,即在分期中将表达时间概念的标题和表达政体概念的标题混淆使用。
由此看来,不管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文学史编撰,在写作中追求一致性是无可厚非的,但需要认清的是,这种一致性是一种主观诉求,其本质是文学史作者根据自己的写作目的和价值取向在预设的基础上虚构出来的。
其次,我们再从文学史内部的构成上来看文学史的第二种虚构。假设文学史主要是由五个部分组成的,即文本、人本、思本、事本以及针对这四本所做的批评五个部分*有关“文本”、“人本”、“思本”以及“事本”主要是由董乃斌提出并做界定的。参见董乃斌:《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101页。另增加的“批评”为本文作者提出。本文作者在使用这些概念时,也对部分内涵作出了相应修改。,那么与文学史书写相关的叙述和分析评论,自然也就是围绕着这五个主要组成部分展开的。
一般说来,这里文本主要指的是入选的历代文学作品与文学资料;人本主要指的是与文本相关的作者及与文学思潮、文学事件、文学活动(包括出版)等相关的人物*本文作者认为,董乃斌将“人本”界定为与“文本”相关的作者并将“思本”视为文学史中的次要因素等观点有欠周到,因此,在文中对董乃斌的这些界定将做出部分修改。;思本主要指的是有关文学的种种思想、观念、思潮*董乃斌:《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7页。;事本主要指的是具体的文学作品出版和文学现象与社会思潮、文学与社会事件、文学与社会活动(包括出版)等一切与文学有关的事情*董乃斌:《文学史学原理研究》,第90页。;批评主要指的是文学史作者和读者针对前面提到的四本所做的分析、讨论和评价。文学史在这一层面上的虚构性及与之相对应的叙述的虚构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假设在文学史中,文本、人本、思本、事本以及批评五个主要组成部分是共时存在的,那么,这五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事实上,这种绝对的共时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写当代文学史的作者也应该与这五个主要组成部分至少有部分不是绝对共时的。这种非共时性主要有三种情况:(1)文学史作者所讨论的部分作品出版时间,可能在他/她出生之前或至少是早于他/她开始文学史写作之前;(2)文学史作者与某些文学事件、某些文学活动等,在发生时间和空间上是非共时的;(3)文学史作者在精神维度上与某些文学作品的作者、文学思潮、文学批评等是非共时的。文学史作者在这么多非共时的情况下,要想通过自己的写作来将这五个组成部分关联起来,叙说或阐释它们之间的互动情况,投射或表达自己的文学观点和价值取向,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建立起一套用来构建和认知这种共识性的逻辑规则。所以说,从严格意义上看,文学史作者所使用的那套架构文学史的逻辑规则是虚构出来的。这样一来,作为(部分)与之非共时的文学史作者,在这样一套具有虚构性假设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推演,即便这套逻辑规则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推演和书写的过程也必定带有一定的虚构性。
第二,文学史的虚构性还体现在上面提到的那些用来构建文学史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之中。以文学史中的文本为例。需要指出的是,文本应该不仅仅是指文学作品,而且还指与文学史写作相关的其他文史资料,如与作者和作品相关的史料、批评文献、文化政策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文本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人本、思本、事本以及批评都有程度不同的关联。从这个界定来看,文本内部(除文学作品之外,还应该包括与文学作品相关的史料等)与文本外部(包括批评文献、文化政策等在内及与人本、思本、事本以及批评相关的所有史料)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依赖于一种具有可能性的虚构假设之上。比如说,文学史作者需要假设哪些组成部分与文本之间有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哪些组成部分虽与“文本”同时出现,但只是某种附带或偶发现象。
文学史作者既需要确定直接或间接原因与附带或偶发现象之间的关系,也需要确定直接或间接原因与先在或潜在意愿之间的关系。这种确定工作是在对文本进行细致研究基础上进行的。从逻辑层面上看,这种研究本身需要在一定的预设模式指导下进行,因此带有很强的虚构性。从众多作家的创作实践来看,作家们在创作时,对自己的经历、精神漫游、交往的人物、走过地方、所受的教育以及阅读或听说的故事等,有些是能够说得清楚,知道哪些对自己创作有直接或间接的启发,而有些则很难或根本无法说得清楚。
问题随之而来了:既然作家本人都无法讲明白,文学史作者如何使用?办法只有一个,即依据预设的逻辑模式进行推演。譬如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运用了全新的叙述技巧,剖析了小说主人公狂人的心理。为了解释清楚鲁迅塑造狂人心理的逻辑依据,有外国学者“拿1911年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照鲁迅的《狂人日记》,得出结论:‘我们不知道鲁迅到底读了多少心理学方面的书,因此无法准确判定狂人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鲁迅的现代心理学理论的知识,但它至少证明了狂人所显示的症状跟现代医学著作所谈论的相当一致。’”*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2~53页。这段引文意在说明,研究者包括文学史作者在勾连这些关系并描绘出它们之间的互动时,所依据的并非是鲁迅本人所明言过的资料,而是在写作中依据预设的标准,把并非是天然联系的作品与史料勾连在了一起。因此可以说,判断一部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思想、情愫等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与外部资料相互关联,其实更多还是停留在具有可能性的假设之中。这种可能性的假设,说到底就是一种虚构。
第三,文学史的虚构问题还可以从文学的形式方面进行探讨。按理说,一部文学史不应只从有用的信息出发对文学思想的内容进行单义的解读,还应该包含对看似无用的文学形式(如小说形式的出现、发展以及各种变体等)进行多义的阐释。一部文学史中所包含的文类有多种,甚或说是异质的,文学史作者不仅要对作品的主题进行研究、评价,而且还要对作品文本的构成要素等进行分析和阐释。
从现有的文学史来看,大都集中在记叙和讨论有关文学思想的方面,而很少甚或几乎没有提及有关文学的形式问题。常识告诉我们,文学形式是文学思想认识的基础,缺少这个基础就不可能准确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以小说为例。随着小说创作的发展,小说的叙述策略出现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不仅给小说创作带来了形式上的创新,而且还折射出了作者和时代的精神维度,为准确把握小说创作的精神实质、文化意蕴以及时代脉搏提供了讨论的基础和依据。所以说,只揭示思想内涵而没有反映形式嬗变的文学史,其实是一种未反映文学发展全貌的文学史,因而也是一种带有片面性的文学史。这种片面性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学史的虚构性。
第四,还可以从叙事话语层面来看文学史的虚构性,如文学史叙事的表达形式、视角、时空、结构等多个方面都可以来探讨。因篇幅原因,本文仅以文学史的叙述视角为例。从文学史的叙述视角入手,可以说文学史书写的虚构性主要是通过文学史作者所采用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来揭示的。采用这种叙事视角的文学史作者会像上帝般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而且还必须严格保持视角的统一。事实上,这对于任何一位文学史作者来说都是极难做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文学史作者不仅要解决自己以及文学运动、思潮等当事人的视角问题,还要解决文学作品中的视角问题。也就是说,文学史作者不仅要对社会的和文学的历史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了如指掌和把握准确,而且还要分析作品中任何一个人物都可能不知道的秘密——这几乎是一件不可为而必须为之的事情。这样一来,文学史作者为了充任这样一个上帝般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就不可避免地以掺入主观臆断的方式为之代言,听凭自己的理解和想象虚构出一些假设和判断来。或许某些文学史作者会采用所谓纯客观叙事的视角来彰显自己叙述的客观性。然而,即便如此,文学史作者所看到的和所写下的也并非都是纯客观的,相反也都是有所选择和评判的。比如说,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大体上采用了这种纯客观叙事的视角,即坚持只叙说所谓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他在叙述历史事实之后,还是避免不了地做了一些介入性的评判,如他在介绍了吴晗《海瑞罢官》的内容和成为重要的政治事件的前因后果之后,还是忍不住补上了一句结论性的话,“从根本上说,写作历史剧、历史小说的作家的意图,并非要重现‘历史’,而是借‘历史’以评说现实”*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64页。。这里所提到的意图尽管也有可能是一个事实,即吴晗在写作《海瑞罢官》时果真是这样想的,但更多的还是他的一种主观判断*或许会有学者认为可用“主观性”替代“虚构性”。不过,二者却有许多不同之处,如“主观性”更多的是指“述体”的主观性;而“虚构性”除了指“述体”主观性外,还指话语文本化等方面。,即他对历史剧和历史小说的一种认识。从微观上来看,文学史中介入性叙述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如洪子诚在谈及部分作家在文革前后的际遇时指出,“60年代初,从创作思想到艺术方法都相当切合当代文学规范的长篇《刘志丹》(李健彤),在未正式出版时就受到批判”*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64页。。这句话中的“都相当切合”几个词语就是一种叙述介入。上面所说的主观判断和介入严格来说其实都具有虚构性。
类似于洪子诚的这种主观判断和介入其实还折射出文学史书写的第三种虚构,即文学史各个相互关联的内部构造与外部其他世界之间关系的虚构。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虚构主要体现在文学史文本话语层面与真实世界之间所存在的模仿关系上。对文学史作者而言,这种模仿关系尤其表现在文学史作者对反映在虚构作品中的真实世界所做的阐释中。换句话说,任何一位文学史作者在对一部虚构的文学作品进行价值判断时,都或多或少地试图通过一种具有内在结构的话语将其中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场景等与真实世界勾连起来。这种勾连的书写行为导致了两种结果:一是文学史作者通过价值判断将虚构的文学作品真实化;二是文学史作者在将虚构作品真实化的过程中,又将文学史这一表达真实认知的价值判断虚构化。这种勾连的悖论关系使文学史的书写,既具有一种历史相对主义的品质,又具有一种文学的虚构性。在对这种悖论关系的具体表述中,特别是在对文学作品进行价值判断时,文学史作者不得不采用表达可能的预设话语结构来把虚构的内容说实了。比如说,在钱理群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赵树理最具魅力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此后,又接连发表一批更加紧贴现实,为配合社会变革而揭示现实的小说,包括揭示农村民主改革中新政权的不纯以及批判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李有才板话》(1943年),形象地解说地主如何以地租剥削农民的短篇小说《地板》(1946年),以一个村为缩影,展现北方农村从20年代到40年代巨大变革的中篇《李家庄的变迁》(1945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8页。
赵树理的这几部小说的确具有时代的政治痕迹,但是,无论具有怎样的政治性,也不能把小说完全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等同起来。毕竟他笔下写的是有人物、有故事、有结构的小说,而并非是政治资料的汇编。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就必须得承认,这些小说除了具有真实性之外,还应该有虚构性。但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的作者,没有给这种虚构性留下一点生存的空间,相反用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阐释系统,使之具有一种带有真实性的普遍意义。
然而,这种阐释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其最根本问题是,它除了将文本与当时的政治做了直线关联以外,还把与其他相关联的因素统统都割裂了开来。这样一来,既未能阐释小说具体语境中的种种因素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未能说明小说的虚构模式与现实非虚构状态,以及事件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结果就是在阐述中虚构了一个符合文学史作者阐释框架的新文本。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意外,因为这种阐释并不来自虚构小说的具体人物或故事原型,也就是说不是从这些小说文本中总结出来的,而是预设了这些人物、故事理所当然地存在于阐释者的阐释体系中。这样一来,这种阐释便容易陷入一种悖论之中,即如果把小说中的人物或故事看成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那么,这种阐释在获得所谓现实意义的同时,虚构的人物、故事就被消解了,从而瓦解了这种意义所依赖的虚构基础;而如果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或故事被使用或保留在阐释之中,那么这种阐释的基础则不具有完整的现实意义,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虚构的品质。总之,无论是哪种情况,以上两种假设中的阐释所依据的都是作品文本虚构的世界,即便阐释分析出来的价值是真实的,其所依据的材料仍然是来自虚构的作品。
三、文学史的真实世界
真实世界在可能世界理论中主要指的是我所在的世界,或“从本体上看,与仅仅可能的存在不同。在仅仅可能的存在中,这个世界本身代表了一种独立自主的存在。所有其他世界都是大脑想象出来的,如梦境、想象、预言、允诺或讲故事”*David Herman,et al.(eds.).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446.。与仅仅可能的存在不同,我所在的世界指的是现实社会。然而,实际上,它不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存在,而是一种因无矛盾性和可通达性与其他世界相勾连的存在。一句话,可能世界语境下的所谓的现实社会并不是单纯指眼睛所看到的世界。
叙述学借用可能世界这一认识,把可能世界中的真实世界细分为作者、人物和读者三个层面:其一是“想象的和由作者所宣称的可能世界,它是由所有虚构故事中呈现出来的被当作真实的状态所组成的”;其二是“人物所想象、相信、希望等的次一级的可能世界”;其三是“在阅读过程中存在读者所想象、所相信、所希望等的次一级的可能世界;或虚构故事被实在化或反事实化”*David Herman,et al.(eds.).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p.448.。
上述认识和界定对我们分析文学史中的真实世界具有两个方面的借鉴作用:其一是文学史中的真实世界也不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存在,而是一种与其他世界相勾连而存在的世界;其二是也可以考虑从作者、人物以及读者三个层面,来划分和讨论文学史中的真实世界。不过,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文学史中的这个真实世界是在可能框架下的真实,而并非是绝对意义上的实际发生或真实存在。它与一般意义上的真实世界不同,一般意义上的真实世界就是指一种绝对的客观实在,而文学史中的真实世界则不是这种绝对的客观实在,而是一种遵循叙述和阅读规律,经过文学史作者、文学史中的人物以及文学史读者各自或共同加工制造出来的,且与文学史中的其他世界相互勾连的真实世界。这种真实世界看上去好像不那么真实,但实际上它是一种符合逻辑的和可以论证的存在。基于这种认识,下面拟从文学史作者、文学史文本以及文学史读者三个层面,对文学史的真实世界进行讨论。
(一) 从文学史作者来看文学史中的真实世界
这个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在文学史写作之前,存在一种由先文本构建而成的文学史真实世界。前文说到,文学史并不是一个由单一或同质组成部分所构成的叙述文本,而是由文本、人本、思本、事本以及针对这四本所做的批评等内外相关联的多种同质或异质组成部分所构成的一个文本结构层。文学史的真实世界首先是指文学史先文本的真实世界,即指那些先在于被作者所选和未选的与文学史写作相关的所有史料。这些史料共同构成了先于文学史文本存在的真实世界。对文学史作者而言,这些史料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否则,假如不真实,文学史作者在撰写文学史时应该不会予以考虑。这个由先文本构建而成的真实世界的存在,揭示了文学史写作的性质,即说到底,文学史写作是从真实世界出发的,而并非是凭空而来的。
其次,虽然说文学史文本中的真实世界所依据的是由先文本构建而成的真实世界,但在本质上说它是经过作者筛选和撰写这两道工序加工制作出来的真实世界。文学史作者并不是可以任意进行“筛选”和加工制作而不受任何内在和外在的影响或限制。恰恰相反,他(们)/她(们)既要受到与自己相关的诸多因素,如个人成长、个人学养等方面的影响,还要受到他(们)/她(们)所处的时代、地域或环境等方面的限制。通常,我们会赋予文学史作者许多名称不同,但意思大致相同的身份,如称他(们)/她(们)为“把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搭建起来的写作者主体”“话语产生的中心”或“努力表达身体感受经验的理性的人”*高概:《话语符号学》,王东亮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页。。这些称谓说明,文学史中所呈现的真实世界,实际上融入了与文学史作者相关的诸多要素,如其真实身份、文学史观、价值取向、所处时代、写作过程等。这诸多要素及文学史写作过程中对其所发生的某种程度上的融入便是一种真实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真实存在也就是文学史另一个层面的真实世界。因此说,真实世界既存在于文学史文本之内,也存在于文学史文本之外。就文学史文本而言,则主要是体现在文本之内和文本之外相重叠的那一部分,其中包括文学史作者对材料的筛选、运用、构建以及评价等。
最后,文学史作者在写作时,所使用的部分叙述逻辑和策略也是属于真实世界的一部分。这种属于真实世界的叙述逻辑,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作者在叙述中对已有文献和作品的直接引用,如姜玉琴在谈及对中国新文学肇始时期不同看法时,就采用了一种真实世界的叙述逻辑。她在文中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不少主将,都赓续了严复、梁启超以来的社会在‘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以及‘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思想。[……]鲁迅曾说过一句话,‘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1917年以来的事。’”*姜玉琴:《肇始与分流:1917-1920的新文学》,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7页。姜玉琴的这段引文中引用严复、梁启超以及鲁迅的文字的出处分别为,严复:《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载《国闻报》(1897年10月16日至11月18日);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2页;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关系》,载《新小说》第1号(1902年);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37页;鲁迅:《〈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7页。因行文方便,未采用姜玉琴引用时的注释,在此补注。在这段引文中,严复、梁启超以及鲁迅的话都是源自于真实世界的,即都是从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或著作中直接引用过来的。对作品的直接引用不仅包括作品的作者、作品的名称、作品的出版时间(版本)等,还包括从作品中直接引用的与史实相符的人物、地点、建筑物等的名称及其相关文字段落等,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谈及变文结构时,大量引用了《维摩诘经变文》中的“持世菩萨”、《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伍子胥变文》等的内容*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第126~128页。;他在讨论宋、金杂剧词时写道:“宋、金的‘杂剧’词及‘院本’,其目录近千种,(见周密《武林旧事》及陶宗仪《辍耕录》),向来总以为是戏曲之祖,王国维的《曲录》也全部收入(《曲录》卷一。”*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170页。这里提到的引用《维摩诘经变文》中的“持世菩萨”、《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伍子胥变文》等的内容和周密的《武林旧事》、陶宗仪的《辍耕录》以及王国维的《曲录》等书目,都是真实的辑录,属于真实世界的一个部分。
第二种是文学史作者对已发生的有关个人的和社会的史实做出的陈述,如王德威在谈及黄遵宪的职务变化及变化后黄遵宪的个人阅历时所说的那样:“1877年,黄遵宪的一次重要职务变动对他后来的诗学观念造成了直接影响。他不再从传统仕途中谋求升迁,而是接受了一个外交官职位的礼聘。在此后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他遍游美洲、欧洲和亚洲多国。”*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文学史》,第471页。这段引文中所说的黄遵宪在1877年的职务变动是一件事实,黄遵宪在职务变动后游历欧美亚多国也是事实,它们无疑都属于真实世界的范畴。另如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所附的“中国当代文学年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453~504页。等此种文献类文字,也属于真实世界的范畴。
第三种是作者对已明确发生的因果关系的陈述,如王德威在谈及黄遵宪因职务变化和海外经历对其创作所带来的变化时说:“黄遵宪的海外经历促使他在全球视野中想象中国,于是,他的诗作中呈现出多样文化、异国风情的丰富面貌,以及最有意义的、富有活力的时间性。”*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文学史》,第471页。这些变化可以从黄遵宪出国任职和游历之后创作的《樱花歌》《伦敦大雾歌》《登巴黎铁塔》以及《日本杂事诗》等作品中看得出来。具体地说,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黄遵宪在这些作品中”形成破格,内容新异,促使读者重新思考传统诗歌在审美和思想上的局限性。”*孙康宣、宇文所安:《剑桥文学史》,第471页。以上这些引述无疑说的都是黄遵宪由于生活的变迁而引起诗歌创作风格的变迁,即对一种因果关系的客观陈述。
需要指出一点的是,文学史写作在陈述因果关系时,需要注意区别有效的与无效的,清晰的与不清晰的两对不同的因果关系。前者属于对真实世界的陈述;而后者则属于对虚构世界或交叉世界的陈述*对交叉世界中因果关系的陈述折射出覆盖率项下因与果的问题将在下一节中讨论。。当然,在讨论因果关系的叙述时,还需要考虑到“覆盖律”的问题,即把一些看似直接或清晰的因果关系纳入一个一般规律来考虑,或者说用一般规律来覆盖它,比如说,因“物质位移”而产生的“精神质变”、国家文艺政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等。这类对在覆盖律项下发生的因果关系的真实叙述,是文学史叙述中极为重要的叙述,也是文学史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
(二) 文学史中的真实世界还可以从文本的层面来看
要阐释这个真实世界,我们首先应该找出文学史文本真实世界存在的前提。
文学史写作不同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它需要对作家及其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等进行分析、阐释和评价。这种分析、阐释和评价的过程就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即文学史作者要把与文学史写作有关的史料、作品等从客观存在的对象转换为主观认识的对象。毋庸置疑,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文学史作者的个人的文学修养、价值观念、判断能力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除此之外。文学史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区域或国家等外部因素,有时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文学史作者的选择、评价或判断。这些都是文学史文本真实世界存在的前提。
在这个前提之下,文学史文本真实世界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存在的呢?亚里士多德当年对历史学家和诗人的看法,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文学史文本真实世界存在的形态,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他在《诗学》中指出,“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伍蠡甫:《西方文论选》,第64~65页。。亚里士多德虽然谈的是历史家与诗人,但文学史的写作其实在有意或无意识之中将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历史家与诗人融合起来。尽管文学史作者谁也没有直接宣称是受到了亚里士多德上述观点的影响,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文学史作者在文学史文本中既要叙述已发生的事,也要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谓的已发生的事就是指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可能发生的事就是指文学史作者对文学史的构建、对文学作品的评判等,后者因带有普遍性的特征而成为了高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
简言之,文学史文本中的真实世界就是由这两种真实构建而成的。所不同的是,文学史作者在对待可能发生的事的时候,既要像诗人那样去描述,也要像历史学家那样去叙述、分析和评价。具体地说,在文学史文本的真实世界中,已发生的事所包含的内容很多,其中有与文学作品、作者相关的真实资料(如作者的名字及其已出版的文学作品)、与文学事件相关的真实资料(如事件所处的时代和地点等),还有与以覆盖律面目出现的真实资料(如国家文艺政策、自然灾变、瘟疫、内乱或战争等)。可能发生的事所包含的内容也有很多,如文学史的构建、文学史作者对文学作品的评判、文学作品文本内所叙述的故事、文学作品的作者在创作实践中的心理路程及其与社会现实的内在关联或互动、文学作品的作者及其作品的接受情况等。不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不管是已发生的还是可能发生的真实资料,尽管在文学史的真实世界中看作真实,但它们绝不是完全以原有姿态出现的,而是由文学史作者经过自己所选择的文化代码和价值取向处理过的。譬如,同样都是写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学,顾彬与洪子诚这两位各自背负不同文化符码、价值取向、期待与顾虑的文学史作者,所采取的书写策略就有所不同。顾彬在讨论这一时期文学时,在章节的概述及其具体讨论中,都扼要地陈述并分析了一些受冲击甚或受迫害的文学家的遭遇和缘由*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第261~369页。;洪子诚则采用百科全书式的体例,只是将发生在那个时期文学界的矛盾和冲突,做一简单扼要的无分析性陈述*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37~55页。,而将发生在那一时期的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分散到随后的各个小节之中。
另外,从叙述的角度来看,文学史作者对这类真实世界的叙述也是按照一般叙述规律进行的,比如说要预设一套能够表达自己文学史观的叙述要点、叙述顺序、叙述节奏等框架结构,同时还要预设一位(或多位)代表文学史作者的叙述者,来叙说有关文学史方方面面的故事或问题,并在叙述中考虑(隐含)受叙者的接受情况等。这种按照一般叙述规律进行的文学史叙述,也是真实世界在文学史文本中的一种表现。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叙述规律在文学史的叙述中虽然似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它是一种客观存在——只要有写作者的存在,它就存在。它既是文学史中真实世界得以存在的另一个前提,也是构建文学史中真实世界的唯一途径。
(三) 文学史中的真实世界还可以从读者的层面来看
这里所说的读者主要是指文学史的读者,而非泛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的读者。这个层面上的真实世界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文学史进入流通领域后所发生的各种与流通相关的行为(如购买文学史和阅读、讲解文学史),是可能世界中的一种真实存在;其二是阅读过程中读者产生的种种反应,也是可能世界中的一种真实存在。
各种与流通行为相关的真实存在相对好理解一些,只要查看统计一下销售记录、讲解文学史的情况等就能够不证自明;而阅读过程中的读者反应则是一个需要论证的问题——一则需要说明读者为何在阅读中会对所阅读的内容做出反应;二则需要对读者为何对某文本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反应做出合理的解释。
20世纪的美国新批评理论,反对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其中之一提出的就是感受谬误(affective fallacy)的观点,认为“把作品与它的效果混为一谈(即它是什么和它做什么)是认识论上怀疑论的一种特殊形式”*史亮:《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丛书:新批评》,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55~56页。。新批评的这一观点显然是有问题的。不过,应该承认,他们所捕捉到的阅读现象倒是真实的,即读者由于受时代、文化因素以及认知能力等影响,对同一客观事物会有着不同的反应。这一现象的真实存在,对理解文学史的读者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与阅读文学作品一样,文学史的写作与阅读都属于认知活动,即都需要有一个信息处理的过程。换句话说,只要牵涉到阅读,处理信息的过程可能方式不同,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是一种客观实在。在对信息处理的过程中,由于所处时代、所从属的文化以及所具有的认知能力等原因,读者会对同一作品或文学史中所提到的同一事件,产生不同的理解和反应。这也是一种实情。
以吴晗的《海瑞罢官》为例。洪子诚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者,《海瑞罢官》是其文学史中所关照到的一个对象。洪子诚在文学史写作中面对这一对象时,融合了读者与作者两种不同的身份,即他既要按照一般读者(或观众)的阅读方式读完这个剧本,也要以文学史作者的身份来审视这部戏剧。因此,他在架构他的文学史框架时,不仅扼要地介绍了《海瑞罢官》这部戏剧的主要内容,而且还对吴晗的身份、《海瑞罢官》一剧出台的缘由以及这部戏何以成为“重要的政治事件”*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63页。作了说明。在经过对这些信息处理之后,他对这个政治事件的性质做出了借古讽今的判断:“从根本上说,写作历史剧、历史小说的作家的意图,并非要重现‘历史’,而是借‘历史’以评说现实。”*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64页。同样,顾彬在他的那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也谈及吴晗的《海瑞罢官》及其相关的政治事件。不过,他作为读者与文学史作者在面对《海瑞罢官》这部戏剧时,与洪子诚的情况并不那么一致。他在姿态上还比洪子诚显得更为单刀直入。他在介绍吴晗及其《海瑞罢官》之前,就首先告诫读者:“1949年之后,政治争论所拥有的社会空间越来越受到挤压。”尔后,他又告诉我们,“当时政治局面之复杂,不是简单叙述能够交代清楚的。[……]双方都明白,争论的焦点不在海瑞和海瑞所处的时代,而是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大跃进政策”*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第286~287页。。与洪子诚相比,顾彬这个读者与作者非但不隐讳政治,而且还把这部戏剧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及相关人物直接而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显然,作为《海瑞罢官》的读者和阐释者,洪子诚和顾彬对其有着不同的阐释维度:洪子诚在作者与读者之间保持了比较好的平衡;而顾彬则明显地倾向于文学史作者。
同样,作为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读者,由于处理信息方式、思想观念或价值取向的不同,既会对《海瑞罢官》这一戏剧有着不同的理解,也会对这两部文学史有着不同理解。这些不同理解是阅读中的一种真实存在。它既反映了不同层面的读者对文学价值、地位以及意义等问题的理解,也折射出读者对文本、语境、环境的利用、认知能力以及个人的信仰等问题。
四、文学史的交叉世界
文学史中的交叉世界可以借用可能世界理论中的可通达性(accessibility)来进行讨论。可通达性的基本理念是指模态逻辑理论中用模型结构来描述其中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可能世界集(possible worlds)、可能世界集合中的二元关系(relation)以及赋值函数(valuation)之间的关系。可能世界集中存在若干个次级的可能世界;次级可能世界之间所存在的一定关联被称为可通达关系。可通达关系有真有假,也有强弱之分,赋值函数用来判断其真假和强弱。
文学史的可能世界也符合这种模态逻辑,各种次级可能世界之间也存在着这种可通达性。它勾连起文学史可能世界中的两个次级可能世界——虚构世界和真实世界,从而形成一种虚构世界和真实世界相互交叉存在的状态,即交叉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赋值函数主要有强弱之分,而较少有真假之辩。
进入文学史中的交叉世界视角有多个,因篇幅原因,本文只从文学史作者和文学史文本这两个方面来加以探讨。
(一) 以文学史作者为轴线的交叉
从文学史作者的这个层面看,总体上说,文学史作者再现的现实并不是现实社会中真正存在的那个现实,而是经过作者筛选和加工处理过的现实。在这个筛选和加工处理的过程中,文学史作者尽管可能并不知道有个什么可能世界理论,但在实际操作中确实暗合了可能世界中的那条可通达性的原则,即将真实与虚构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真实与虚构相交叉的世界。下面探讨二者相互交叉的内在机制及其赋值。
从以文学史作者为轴线来看,环绕在这个轴线周边的因素会有许多,如文学史作者所生存的社会、所秉承的文化传统、所受的教育、所发生的(文学)事件、所阅读的作品等。这其中有真实的,也有非真实的或虚构的。诚如前文所说,文学史写作并非是简单地将这些真实的、非真实的或虚构的史料完整地记载下来,而是有所选择、有所综合,也有所评判。在这选择、综合、评判以及意义的构建过程中,文学史作者不仅融进了自己的情感、价值观等因素,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文艺政策等这类带有覆盖律性质因素的指导或制约。显然,文学史写作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体。文学史作者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些诸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真实性、非真实性或虚构的因素勾连起来,整合成一种适合文学史写作内容和逻辑的线索。简单地说,这种整合的过程就是一个虚与实相互交叉的过程,这种过程所勾连、呈现出来的世界,就是文学史中的交叉世界。
文学史作者在构筑其文学史本时,其实就是遵循着这样的一个原则进行的。比如,奚密在《1937-1949年的中国文学》中谈及这段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学时,她首先叙说了抗日战争的起因及其影响:“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城西南的十五公里的卢沟桥一带进行演习。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由,他们要求进入宛平县内搜查。当他们遭到驻守宛平国军的拒绝时,竟以武力进犯。”奚密对发生在1937年7月7日的事件,有选择性地作了简短而真实的陈述。但是,奚密在这里并没有首先提及并解释日军为何要在北平城西南驻军,而且还竟敢在卢沟桥一带进行演习;而是在随后的文字中才扼要地提及“九·一八事件”、西安事变这两件发生在1937年7月7日之前的事件。她采用倒叙这样一种带有虚构性质的叙述策略,来追叙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在彰显她对“七七事变”这一事件认识的同时,强调了先叙的“七七事变”这一事件,给其后的中国社会、中国文学艺术等所带来的影响。
这种释说可能有点抽象,不妨把上述内容转换成这样的说法。奚密是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及随后出现的文学现象这两大层面来构建文学史的交叉世界的。具体地说,奚密在架构这段文学历史中的历史事件时,采用了一种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策略:实主要指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九·一八事件”、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等这些历史事实——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文学史中的真实世界;虚则是指对这些事件进行倒叙的安排,即没有按照事件原来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叙述,而是把后发生的事件作了前置处理。这种叙述手法所达到的效果是,在凸显了七七事变与后来发生的抗战文学等因果关系的同时,也虚构了这些事件的因果关系链,而且还弱化甚或隐去了统摄“九·一八事件”和西安事变、“七七事变与”随后出现的抗战文学等文学现象的中日社会发展、中日关系、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等因果关系及其演化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历史事件的实与对这些历史事件进行叙述的虚,共同构成了一个实与虚相交叉的世界。
当然,文学史作者对历史事件作虚实之处理,也是有着明确的目的和想法的,就像奚密之所以要采用这种倒叙,也就是虚的手法,其目的就是想强调抗日战争爆发这一事件,而并非是这些事件的前后关联。强调这一事件的目的,又是为了方便她在后面叙述中所提出的与此相关的“抗战文艺”“统一战线:重庆”“日趋成熟的现代主义:昆明与桂林”“沦陷北京的文坛”“上海孤岛”等话题的论述*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文学史》,第619~655页。。然而严格说来,这一虚的背后又是实,因为不管是从上面的命名来看,还是从随后而来的记叙中,都会发现作者主要还是停留在实的层面上,基本上属于事件描述性的和主题阐释性的。这种表述,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或实虚相间,这是文学史书写中最常见的一种实与虚的交叉形式。从奚密书中的另外一段话,也可以看出这种实与虚的交叉:
比起此前的侵略行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直接威胁着中国之存亡。它对中国文学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其冲击既是当下的也是长远的。种种文化体制——从大学和博物馆到报业和出版社——遭到破坏或被迫迁移,无以数计的作家也开始了流亡的生活。[……];另一方面文学在战争期间提供了一个慰籍与希望的重要来源。*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文学史》,第620~621页。
这段文字中的实就是指日本对华全面战争的爆发。从大处着眼,威胁到中国的存亡;从小处着眼,影响了作家的正常创作,以上这两方面都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而虚则是语焉不详的“文学在战争期间提供了一个慰籍与希望的重要来源”或“种种文化体制——从大学和博物馆到报业和出版社——遭到破坏或被迫迁移,无以数计的作家也开始了流亡的生活”等文字。实事求是地说,这些表述是模糊的,它既没有具体的事实,诸如哪些大学、哪些博物馆、哪些报业、出版社遭到了破坏以及如何遭到了破坏,更没有解释清楚文学何以“提供了一个慰籍与希望的重要来源”等。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奚密该处的虚是没有价值的,或者说没有把握好写作的尺度,那倒不是,因为该处的虚可以追溯到实那里去,二者是有着紧密的因果逻辑关系。换句话说,这里的一实一虚合情合理地把前后几个事件勾连了起来,共同构建了一个以实为主,以虚为辅的指向明确和寓意深刻的交叉世界。
(二) 以文本为轴线的交叉世界
毋庸讳言,以文本为轴线与以作者为轴线,会有许多相同或重叠之处。这样一来,将两者分开来谈似乎就显得有些形而上或片面。其实,以文本为轴线讨论文学史写作并没有割断文学史作者与文学史文本之间的关联,而是依据可通达性原理,将文学史作者融进了文本之中。或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将文学史作者作为文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隐含作者来看待。从这个角度说,提出以文本为轴线来讨论文学史的交叉世界,有其独到的方便之处,即可以从话语叙述的角度对某一具体的文学史文本做出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评价。
一般说来,文学史文本的交叉世界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文学史文本内部组成部分(如文本、人本、思本、事本以及针对这四本所做的批评)的相互关系上来看,在实际写作中,这些组成部分是被交叉整合在一起的。另一种则是从结构上来看,很多的文学史读起来好像千差万别,但分析起来大都脱离不了这样的两个价值维度,即明和暗的价值维度:所谓的明指的是能给人带来直观系列感的外在篇章结构,如这部文学史是由几章构成的、每一章的大小标题是什么等等,总之,是能一眼看得到的东西;所谓的暗则是指隐含在这些篇章结构的背后,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文学发展规律的那个脉络。当然,分开论述是这样区分的,其实合起来看,在具体的文学史文本中,它们之间不但具有可通达性,而且还总是以一种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状态出现的。不过,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两种不同价值维度的特点和运作机制,本文还是要把它们分开来论述。
1.文学史文本内部和外部组成部分之间的交叉。这个问题可以从文学史文本内和文本外两个方面来讨论。
先说文本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文学史文本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有多种形式的关联,比如说,文本、人本、思本、事本以及针对这四本所做的批评之间的关系,有些属于附带现象(epiphenomenon)关系,而另有一些则不属于这种附带现象关系。
附带现象研究认为,实际发生的事件对思想有直接的影响,甚或说它就是思想的诱因。文学史文本中针对这四本所做的批评,大致说来属于一种因果关系陈述,即是这种附带现象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这也不难理解,文学批评就是建立在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之上的,没有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也就没有文学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文本中各组成部分之间所存在的这种附带现象关系,是对各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真实反映,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学史文本的真实世界。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附带现象研究的关系是一种单向关系研究,比如说,事本只能对思本产生影响,而思本不能反过来影响事本。但是纵观现有的文学史,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文学史中呈现给我们的有事本与思本相互影响的关系,也有它们相互之间不产生影响的关系。这样一来,文学史中事本与思本的关系就不只是单纯的附带现象关系,而是包括附带现象关系在内的多种关系的组合。因此,前文中所说的由表现附带现象关系构成的真实世界,在文学史中只能是部分的存在,而并非是全部存在。如此说来,附带现象研究并不完全适用于对文学史文本内部关系的分析。换句话说,文学史文本中普遍存在的是事本、思本等各个构成部分的交互关联的关系。即便是现实中并没有发生这种相互之间的影响,但由于线性书写的原因,原本只是一种时序前后、相加并列或邻近的关系,也会给人造成一种相互关联或具有某种因果关系的印象。这样一来,其结果就是文学史文本从整体上来看,形成了一种虚实相间的关系,即我们所说的交叉世界。
再说文本内与外的相互关系。文学史文本内与文本外也有一种虚与实共生的现象。如前面提到的鲁迅的《狂人日记》中主人公的精神状态,与1911年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提到的有关心理症状相吻合一例。鲁迅或许了解《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有关词条,或许并不了解。但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狂人日记》是先后出版的,形成了一种同存共生的关系。还有一例,即中国戏剧界有学者曾讨论过曹禺的《雷雨》与俄国戏剧家A.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之间的关系*参见袁寰:《〈雷雨〉与〈大雷雨〉轮状戏剧结构比较》,载《求索》1985年第6期,第109~112页;杨晓迪:《悲剧框架中的〈大雷雨〉与〈雷雨〉》,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68~71页;马竹清:《婚姻道德和情爱人性的悲歌——浅谈〈雷雨〉〈大雷雨〉》,载《戏剧之家》第14期,第49页。。假如将这种原本(没有)发生相互影响的事例写进或不写进文学史中,都会既有其真实的一面,也有其不真实的或虚构的一面。从这个角度看,真实与虚构也是同生共存的。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这种文内文外的共存性,也构成了文学史文本组成部分的交叉关系网络,即交叉世界。
这种同存共生现象还可以从反事实因果论(counterfactual theory of causation)的角度来看文学史文本内、外组成部分之间的交叉问题,即比较真实世界和虚构世界之间的相似性。一般说来,文学史文本内外有许多相似的真实或虚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级差:越靠近事实的就越真实;距离事实越远的就越虚构。实际上,文学史文本写作并没有按照级差的顺序来安排内外同生共存的史料,相反它一般是将不同级差的史料,按照不同的需要来重新排列组合的。多数情况下是交叉存在着不同级差的真实与不同级差的虚构。这种不同级差的交叠存在,共同构建了一个个真实与虚构交叉互存的世界——“交叉世界”。
2.文学史文本结构上明暗两个维度的交叉。文学史文本中明的结构,主要是指文本章、节等篇章结构。这个结构既有其真实的一面,也有其虚构的一面。比如说,从总体上看,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突出“对具体作品的把握和理解”,并着重“对文学史上重要创作现象的介绍和作品艺术内涵的阐发”*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前言第6、7页。。具体到每一个章节的写作,则“以作品的创作时间而不是发表时间为轴心”,或“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第8页。。这样的写作纲领和章节安排就是一种虚、实相结合的安排。
当然,这里的虚和实都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指陈思和等编者,人为地想“打破以往文学史一元化的整合视角,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第7~8页。。他们的这种共时性写作意图是真实的,与当时重写文学史的时代诉求相一致。然而,从他们的文学史写作安排本身来看,却又具有一定的虚构性。这看上去好像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悖论,其实是必然的。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那样,文学史写作从来都是两个维度的写作,即既需要共时性的视角,也需要历时性的审视。他们撇开历时,主张从共时这单一的时间维度来撰写,就与文学史的真实发展情况相违背了。此外,文学史和文学创作整体观虽然有不少重合之处,但毕竟还不完全是同一个层面上的事。以这样的一种文学史观构建出来的文学史,自然不贴合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理论构架不过是一种虚构。
第二层意思是指这部文学史各章节间的排列组合和章节内部的安排方面也存有一定的虚构性,也就是说整部文学史是通过文学史作者预设的某种意群组合而成的。这种意群组合通常的做法是把一些相同或类似的作家或作品放在一起进行介绍和评价。然而,这种相同或类似更多是文学史作者所判定的相同或类似,而并非是这些作家或作品的一种天然相同或类似。这些作家或作品之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文学史作者也可能会采用以点带面的方式来构建这样的意群。比如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一章的第二节中,编者撇开颂歌类的作品,单独挑出了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作为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来讨论,既没有体现出编者所主张的共时性——既然是共时,就不应该省略了同时期的其他颂歌,也没有兑现其所许诺的要“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既然是整体观,就需要大量的同类作品作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节的编写并没有如实地叙说,而是虚构了那个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这个问题不单存在于这一章中的这一节中,而是整部文学史中都存在这个问题。
这样分析并不是说这种编排没有意义。与其他的同类作品相比较,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的确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作品,而且编者对其的分析也有说服力,较为真实、具体地阐释了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点。从这个层面来说,展现在这一节中对胡风长诗的阐释与评价的文字又具有一定的真实性。这种虚与实交叉结合的写法,便构成了虚与实交叉结合的世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所构建的文本世界,可以说基本上都是类似于这种虚、实相互交叉结合的世界。
文学史文本中暗的结构,主要是指隐含在这些篇章结构背后,能把文学发展规律揭示出来的那个脉络。《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编写的虚与实,在暗这一维度上也依旧能得到体现。譬如,尽管我们在前文中也指出了这部文学史中的一些虚构问题,但是,从这部文学史的章节安排中,不但可以看出隐含在这些章节标题背后的当代文学史的大致发展脉络,而且还可以看出隐含在这些章节标题背后这一时期文学的总体精神和价值取向。换句话说,将各个章节联系起来就勾勒出了中国当代文学演变的大致轨迹。即便是对单个作家的分析和评价,也隐含了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还以胡风为例:这部文学史教程对胡风事件的历史过程未作详细介绍,但却通过将他的作品和他所遭受的政治打击进行对照叙说。这种写法在暗示了胡风命运的必然性的同时,也揭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些特殊时期的发展走向及其必然结果。在这里,虚与实得到了相互关联,构建了一个交叉的世界。
顾彬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则是另外一种虚与实交叉的类型。我们从这部文学史的篇章结构中看不出隐含其后的文学发展脉络。具体地说,这部文学史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写的是现代前夜的中国文学,第二章写的是民国时期(1912-1949)文学,第三章写的是1949年后的中国文学:国家、个人和地域。第一章和第三章的标题,指向的是一个大致的时间概念;第二章则指向一个政体所代表的时期,而与之相对应的政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则被放在第三章的第四小节中。从这样的一种篇章安排中我们只看到了时间的展延,而看不出作者揭示出什么样的文学发展规律。也就是说,这样的文学史章节安排既没有反映出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的精神脉络,也没有揭示出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的演化规律,因而带有很大的虚构性。不过,从这部文学史各章内小节之间的承接关系看,如第二章的第一节先后讨论了苏曼殊、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冰心、叶圣陶等的创作,将他们的创作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的真实情况。总体说来,顾彬主编的这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整体框架的虚中嵌入了部分内容的实,而部分内容的实又融入了虚的框架之中,从而构建起了另外一种虚、实相间的交叉世界。
概而言之,从上面所做的论述来看,文学史的文本世界并非是单一的,而是三重的。三重的文本世界是文学史所独有的特征,也是文学史独具的一种本质。文学史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前者处理的主要对象之一是虚构类的文学作品,而后者几乎不涉及或很少涉及此类作品。这就意味着对文学史的研究不能完全按照历史研究的理路来进行。把文学史的内部构建分为三重,不但有助于我们搞清文学史内部构建的多重属性,更重要的是,还有助于我们从多个视角、多个层面来打量、分析和构筑文学史,一改过去那种平面式的文学史观。文学史处理的不仅是现实、艺术标准等问题,而且还包括虚构和想象等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文学史的方方面面,我们应该采用一种分析和概括相结合的方法来认识这些方方面面,即将文学史内部的构成因子、结构特点等拆分开来进行分析和评判。从这个意义上说,借鉴并运用可能世界理论来剖析文学史的三重世界或许会为我们提供一种有意义的认识途径。
●责任编辑:涂文迁
The Three Worlds and Their Accounts in Literary History:A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Literary History
QiaoGuoqiang(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The theory of “possible worlds” indicates that the actual world and the fictional world are not two clearly distinct worlds in the “possible world”,but worlds that exist in the form of mutually merged or crossed through accessibility.Literary history,which aggregates all kinds of literary materials,exists in the form of a literary text that merges and crosses actual and fictional worlds and therefore,constitutes a literary world.Or rather,this literary world is threefold,namely,“fictional world”,“actual world” and “cross world” that is merged through accessibility.In the text of a literary history,this threefold world is both merged and distinctive.Being merged refers to their general orientation of the threefold world in the text—the threefold world exists in a text of literary history owning to the accessibility and thus commonly constitutes a unique set; while being distinctive indicates that the threefold world in a literary history has their own attributes,boundaries and functions.To apply the theory of “possible world” to the textual analysis of literary history will help reveal these attributes,functions and accessibility,and therefore,expose the nature and substance of a literary history.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 worlds; fictional world; actual world; cross world
10.14086/j.cnki.wujhs.2016.06.008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专项资金项目(2015-2020)
●作者地址:乔国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上海 200083。Email:qiaoguoqi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