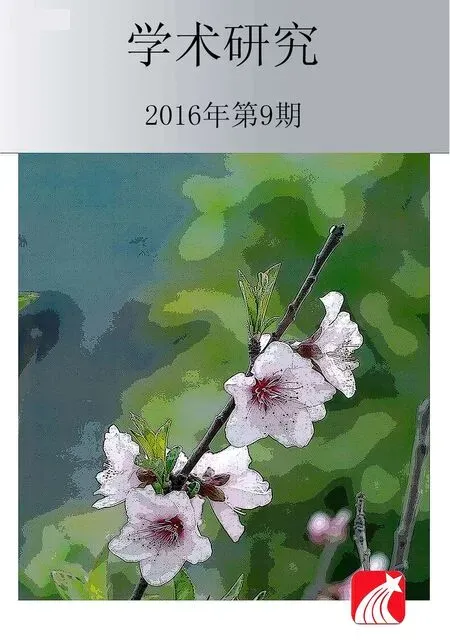论“五四反传统”的传统
张 宁
论“五四反传统”的传统
张 宁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描述了清代学术思想以复古为解放的过程:
纵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至矣。[1]
这是一个时间上的回溯:若解放现在,便只有复古,以古为今地启动解放资源。但这个对既往的时间回溯,总有一个尽头,“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之际,便无古可复。对新的解放资源的寻求,就逻辑性地从时间转向空间,由复古走向西学——这就是“五四反传统”的历史逻辑。不然,对当下的“解放”,便终止于无。其中深意值得细究。
1.“五四”反传统,反的是什么传统?1921年,新文化运动已走入低潮,《新青年》也迁往上海。在一场文化运动总结期到来之际,胡适为即将出版的《吴虞文集》作序,称吴“只手打孔家店”,遂有后来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一个经典概括——“打倒孔家店”。
这里遇到了一个文化记忆问题,即由文化的细节理解文化的整体;而且这个细节经由人们两次追认:胡适事后追认,后人又再追认。而在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现场,并无人提出“打倒孔家店”。
用“打倒孔家店”概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是否准确?当然很准确的。但需要做一个重要区分,即“打倒孔家店”并非打倒孔孟,“五四”先驱们在新文化运动中已自发地启动了后世西方文化研究中关于文化的区分,他们反对的不是儒家文化经典这些理想文化和文献式文化,而是整体生活方式中那些业已窒息生命和阻碍历史进步的内容,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方式等等”,[2]更有作为专制制度灵魂的政治文化。后者像空气一样弥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也浸透在人们的灵魂之中。
2.孔家店≠孔孟,更不等于中国传统文化。孔家店只代表孔孟之学的独尊地位,即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垄断经营。“打倒孔家店”既解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被压抑的其他思想学派——如易白沙《孔子平议》称:“各家之学,也无须定尊于一人。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为中国一国之学。”“打倒孔家店”也解放了孔子本身——如张申甫20世纪30年代回溯时所言“打倒孔家店,解放孔夫子”。对此,不少学者包括严家炎先生都曾著文指出。[3]
而在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现场,先驱们则表达了对儒家历史作用的肯定。如:
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陈独秀《古文与孔教》)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本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陈独秀《复辟与尊孔》)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其实,历史的这一面今天几乎都已是常识。
3.“五四”反传统,是否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如果着眼于中国现代性进程,那么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是多年后的另一种力量:政治。新文化运动在当时影响并不大,多局限于新青年与已经成型的现代教育和学术界。整个社会仍沉浸于传统的道统里,整个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仍以三纲五常为灵魂。康德所言的“程度更大的公民自由”(政治制度变革)此刻似乎已经落地,却摇摇晃晃;但康德所言的“程度较小的公民自由”(思想自由),那“逐步地反作用于人民的心灵面貌……并且终于还会反作用于政权原则,使之发见按照人的尊严……看待人”[4]的东西,却依然处在萌芽之中。
“五四”反传统为人们平等地看待一切古代传统和一切外来资源,冲开了屏障,铺平了道路。但对当时的政治,却并无太大影响。唯一产生显著政治影响的在国民教育方面。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法令,规定从当年秋季起,国民小学的国文教科书启用白话。1922年又颁布了《暂行课程标准》,对国文课本的文白比例做了规定:“文白比例采用逆升递降法,即初一,3∶7;初二,4∶6;初三,5∶5;高一,6∶4;高二,7∶3;高三8∶2。”[5]
从今天台湾高中语文课本选文比例来看,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化教育,在国民的普通教育中仍然得到了保证。大陆1949—1966年的中学课本,也保持了一定的文白比例。只是“文革”期间,内容骤变,但改变的却不只是文白比例,而是对整个教科书选文的颠覆,乃至对整个国民教育的颠覆。然而,现代国语(白话文)的兴起和普及,本身就会影响传统文化的传播,普通文化人几乎被挡在古代文献大门之外。
语文是初中生的必修科目,初中语文教学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语言学习能力,因而,初中教师的课堂语言教学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语言学习,对学生而言,语言学习是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模仿和自我感悟才可以学到,而当前的语文教学形式和内容主要围绕着应试,这与新课改的要求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就使得语文教师要有一定的语言能力,将语文课程通过形象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而提高初中语文教学效果。
4.“五四全盘反传统”只是一种文化记忆。这种记忆从新文化运动发生时就开始了,但却主要是这场文化运动的反对者的记忆。钱穆先生就曾指责“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一切重新估价’”,并暗示先驱们引导公众“要把中国以往历史痛快地一笔勾销”。[6]唐君毅则在1974年发表《五四纪念日谈对海外中国青年之几个希望》也告诫青年:“千万不要学五四时期以来,若干刻薄文人,如吴虞、鲁迅等,轻易侮辱自己生命的祖先,侮辱中国历史上大家共同崇敬的人物。”[7]
两位当代大儒,尤其是在唐君毅那里,记忆的情绪性跃然纸上。这种由后人带有情绪的文化记忆,形成了一种历史叙事。
而真正提出“五四全盘反传统”的是林毓生。他在那部启人心扉却争议极大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开篇即言:“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其“直接历史根源,……尤其可以追溯到1915—1927年‘五四运动’时代所具有的特殊知识倾向。”[8]随后便以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为例,对所谓“五四全盘反传统”做了激烈的批判。他认为他们“共同得出了一个相同的基本结论:以全盘拒斥中国过去为基础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是现代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根本前提。”[9]
林毓生观点传入中国大陆,适逢弃旧布新的20世纪80年代,因而迅速得到了部分知识者的热烈回应。有学者沿着这个逻辑,进一步把历史叙述成如下模样:
主导“五四”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与文化激进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其表现为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全盘否定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10]
其中“打倒孔家店”止于独尊儒术的原本含义,便被叙述为全盘否定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
5.“历史的狡计”和真诚的本质论。如果说钱穆、唐君毅等新儒家的文化记忆包含过多的情绪性,但他们在措辞上仍谨慎的话,那么林毓生“五四全盘反传统”论,着眼于20世纪后半期中国曲折的历史,则落入了历史的狡计。林先生显然是隔着太平洋体味作为中国人的历史苦难的,他之“五四全盘反传统”论更体现了一个学者的社会关怀和面对苦难历史的焦灼。但他的立论却以历史结果推论历史过程,他找到了“文革”的如下思想起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又重新出现五四时代盛极一时的“文化革命”的口号,其中最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就是1966—1976年间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决非偶然。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11]
但“历史的狡计”正在于它总是让人部分失明。就在论者看到焚烧古代典籍,怒砸孔庙圣象,乃至“打倒孔老二”响彻云霄之际,火烧圣尼古拉教堂(哈尔滨),点燃所有被抄出的“四旧”书籍,“埋葬帝修反”也喊得同样震天价响。那场“对文化的革命”,不仅全盘反传统,也全盘反西方,全盘反苏东,却被“历史的狡计”摒除于视野之外。政治逻辑也因之被替换为文化逻辑。
事实上,林毓生并非没有进行历史考察。他意识到反传统有两种不同类型,却又拒绝体认“五四”反传统的真正意图,执意把“反对崇拜传统”解读为摧毁传统,执意错置“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应然”和“实然”。他把“五四反传统”替换成“五四全盘反传统”,其根据的只是这种反传统的激烈性: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说成是全盘的反传统主义。”[12]对“全盘”之含义,“此处用来严格描述一种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总体拒斥原因的意识形态信奉”。[13]而他重点考察的三个人物——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却既未对中国文化传统总体拒斥,更少“意识形态信奉”。倒是论者本人执意抱着以结果推断过程的本质论思维,尽管其背后含有痛苦和关怀,一如中国大陆30多年来层出不穷的真诚的本质论者。
6.“五四反传统”的传统。“五四”的确留下了一个“反传统”的传统。它在发生时既是针对儒学在所有传统文化中的统治地位——“孔家店”的,也是针对存在于空气里、浸透于骨髓中的当下政治社会文化的,具体就是:君臣观念、纲常名教和封建伦理。那时民国初建,在宪政外壳下充斥的仍然是传统的政治文化、社会文化和道德文化。中央政府提倡读经,举行祭孔的国家仪式,同时孔教也呈现被立为国教的趋势,更有两次帝制复辟。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五四反传统”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鲁迅这样谈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
以这种历史感觉去体味“五四反传统”,包括它的某种激烈性,就不会形成含有太多负面情绪的记忆,也不会把“五四反传统”错认为全盘反传统。因为,其中既有“做奴隶的奴隶”的历史沉痛,也有对民国价值的坚定捍卫。可见,“五四反传统”包含着相互交叉的两个面相:一是对把儒学奉做神圣而加以膜拜的反拨;二是对以君臣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以等级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以人身依附为核心的道德文化的批判。同时,它在发生时就携带上了民主、科学和自由的基因,并有着充分世界化的明确方向。
以此观之,“五四反传统”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未能成为主流。在20世纪30—40年代,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岁月里,它仅为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所具有。而在20世纪后半期里,它曾在中国大陆几乎完全消失,直到70年代末才重新复苏。在80年代的文化热里,它曾像彗星划过天空一样璀璨过片刻,随即便淹没在90年代的国学热里。即便在那璀璨的时刻,它也没有形成有力的论述,反而更多是作为一种面对形为现代、实为复古之政治文化的曲折视野。在这种视野下,一个小小的类“五四”思潮,借助出版、报刊和讲坛,正从思想学术界漫向社会公众。
如今,“五四反传统”的传统已无显著的行迹,它更多是作为一种心情而存在于各种知识分子和部分公众那里。怀有这种心情的人们,早已不再把儒学的三纲五常视作敌人,反而有可能向孩子们推荐《三字经》《弟子规》;倒是对国学热中不断出现的“逾越界限”和“推行教派”保持着警惕。而对以君臣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以等级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以人身依附为核心的道德文化,则始终保持着敏感和批判。
进入新世纪,人们对任何“激烈的全盘否定”形态,已不再归咎为某种学说、理论或文化的内容,而是反思到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倒是扎根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只不过它不在传统经典文化中,而在像空气一样弥散着的传统社会文化里。
[1]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页。
[2]罗钢等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页。
[3]严家炎:《“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之考辨》,《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
[4]康德:《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0-31页。
[5]赵晓霞:《民国时期中小学语文教材出的勃兴、特点及启示》,《出版发行研究》2012年第9期。
[6]钱穆:《中国历史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5、16页。
[7]《唐君毅全集•卷七卷八: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第338页。
[8][9][11][12][13]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0、6、6、11页。
[10]陈来:《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东方》1993年第1期。
责任编辑:陶原珂
I206.6
A
1000-7326(2016)09-0154-03
张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51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