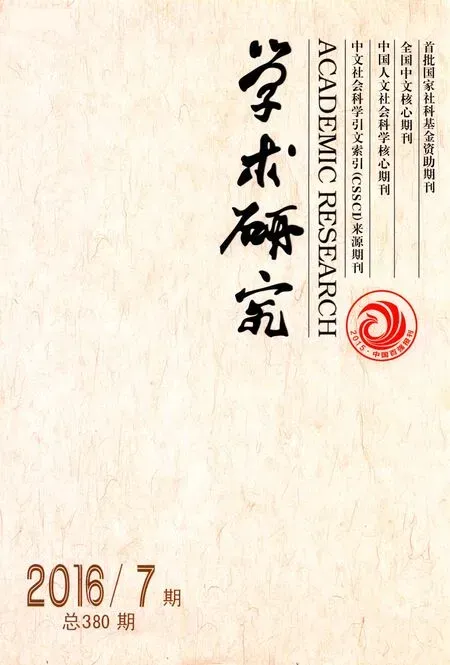挽救危机的失败:“二十一条”交涉后的袁世凯政府
高翔宇
挽救危机的失败:“二十一条”交涉后的袁世凯政府
高翔宇
“二十一条”交涉后,朝野上下为应对外交危机,在内政方面兴起了一场挽救统治危局的运动。不仅各级官吏、名流、士绅纷纷进言献策,袁世凯也一度表现出对修明内政的附和。尽管北洋政府就教育、实业、军事、自治、民生、减政、吏治、立法等方面尝试了短暂性的改制举措,然而,内政整顿不仅未达如期目标,反而激化了政府的信任危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最终转向帝制道路,不仅导致这场挽救危局的努力迅速湮没在洪宪帝制浪潮中,而且使得民初政局发生了深刻的逆转。此外,这场由政界同人主导的、以整饬内治为诉求的努力,与思想界同步发起的 “新文化运动”,共同构成了同时期改造中国政治与社会的思潮。
“二十一条”袁世凯政府挽救危机洪宪帝制
1915年5月7日,日本向中国提出答复 “二十一条”的 “最后通牒”。因受外患刺激,朝野上下围绕如何挽救统治危局,展开了相关的讨论和实践。然而,目前学界对于 “二十一条”交涉后的朝野回应关注程度并不够。王奇生提及了 “二十一条”交涉引发的危机动员仅有救国储金及排斥日货两种形式,且认为规模及影响远不如五四、五卅运动。①参见王奇生:《亡国、亡省与亡人:1915—1925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演进》,柯伟林、周言主编:《不确定的遗产》,郑州: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03-128页。罗志田勾勒出了 “二十一条”交涉结束后民间主导的救亡活动,以及思想界动向与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内在脉络。②参见罗志田:《救国抑救民?“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0-108页。两位学者对于 “二十一条”交涉后民间反应的论述贡献颇多。然而,关于政府在因应时局方面的动向,学界则鲜有涉猎。本文拟以相关史料的梳理为基础,以期对 “二十一条”交涉后袁世凯政府的研究有所补益。
一、统治危局下的 “条陈时代”
“二十一条”交涉的失败,使得袁世凯政府陷入空前的统治危机。革命党人掀起了 “倒袁风潮”,其将外交受挫归咎为袁世凯 “一人政治”的恶果,视 “二十一条”为袁世凯与日本交换帝制之条件,直呼以挽救国难 “非以万众之力推翻袁政府”。[1]民间一面激烈抵制日货,一面由上海商会发起扩展至全国的“救国储金”运动。不仅欧战的纷扰使得外交环境紧张,而且继 《中日新约》,政府又有 《中俄蒙协约》之签署,利权持续外溢。
对于袁世凯而言,为因应外交危机的负面影响,象征性地发表了系列救亡 “痛言”。其在讲话中称,内政孱弱是外交失败的重要根源,“历观史册兴亡之故,不在外祸之可虑,而在内政之不修”。[2]外交受挫应为内政兴革提供动力,“苟国内政治修明,力量充足,譬如人身血气壮硕,营卫调和,乃有以御寒煖溼之不时,而无所侵犯。故有国者,诚求所以自强之道。”[3]故而,袁以政界摒除私见、交相勖勉为号召,并鼓励救亡条陈的上达。
政府同人及在野政治家,同样有呼唤厘革内政的诉求。5月20日,都肃政史庄蕴宽等领衔上 “救亡条陈”,提出以 “减省军费以充军实”、“严核浮冗以裕财政”、“整饬吏治以恤民生”、“广求人才以应时变”为 “治标”之策;“治本”之方,一在普及教育,二在振兴实业。[4]袁世凯接到条陈后回应,“汰无用之冗兵,裁不急之浮费,慎选爱民之良吏,勤求适时之人才……至普及教育,以增进人民之道德智识技能,振兴实业,以利用国家之地力人工资本,尤为百年之大计。”[5]肃政史条陈即刻引发了关于救亡时局的讨论,各级官吏、社会名流、地方士绅或上书中央,或撰文论政,为袁世凯政府进言献策。
在军事方面,袁世凯对肃政史上书中的 “核减军费”做出了批示,正式陆军 “额不必多,但求精练,务使有一兵即能得一兵之用,俾财不虚糜”。[6]然而,潼关县知事胡瑞中对肃政史的意见不表苟同,认为救亡大计之 “主药”当在速行征兵与设兵工厂,而非教育、实业等 “辅药”之方。[7]山西将军阎锡山上书,认为非采取强迫制征兵不足以强军,并须知国民教育、实业之发达,地方警察、自治之实行,为征兵筹备的前提。[8]萨镇冰建议整顿各地兵工厂,使统归陆军部直辖,避免与中央权限分歧,且调配、划一各厂枪械数目。[9]康有为通过观察欧战中的军事较量,倡以国家军力强弱尤在军械完备,故建议目下讲求治械,当延请德、美之名技师,并 “先广购美及智利之良枪炮、潜水艇以应急需”。[10]袁世凯亦表赞同,“假如财政有百元之宽余,即以五十元完整军备,二十五元扩张教育,二十五元振兴实业。而完整军备,对于军械问题尤须特加注意。”[11]复兴海军成为时人议题。严复以日本依海军雄厚实力,先后在甲午之役、侵覆德人山东半岛租地中获胜,号呼兴办海军之必要。[12]谭若森以整顿江南船坞为例,提出设立完备之军港,以为 “修造军舰与舰用机器等物之便利”。[13]有建言者进一步提出,在造舰、筑港两项外,培养海军专门人才乃 “振兴海军之根本基础”。[14]
在实业方面的建议中,伯因对专注军事改革的条陈提出相反的见解,倘仅 “汲汲求于简单武力之国防”,而不重视经济实力之培育,不啻舍本逐末,惟有制造国货、广筑工场、挽回利权,方能树国家万年之基。[15]张謇探讨 “救国储金”之用途,认为5000万元捐募目标,“言教育,不足支全国应设置大学开办经常等费,言海军,不足造一头等战舰,言陆军,不足当全国一岁费也”,不如为实业备费,“五千万之棉织业兴,足抵五百万兵之一战”。[16]政事堂参议王鸿猷称,不妨以 “救国储金”兴办劝业银行,专以劝农通商惠工为性质,务以引起企业家投资心理为宗旨。[17]袁世凯回应,可招股资本500万元,投资于水利、森林、畜牧、矿业、工场等项。[18]又,财政总长周学熙建议筹办 “民国实业银行”,拟定资本2000万元,股份由官商各认其半。[19]袁世凯给予批示,并以专事运输、保险两业为银行经营之业务。[20]安徽巡按使倪嗣冲则视农业为实业之根本,“中国工商欲与东西洋先进之国互相角逐……窃恐难收速效”,不如兴植垦牧、讲求水利,以藏富于民。农业兴,“则兴学、练兵自能蒸蒸日上”。[21]中国银行总裁李伯芝同样认为,“奖励农业为今日发达国民经济之最要政策”,故当设立一种农业金融机关。[22]该条陈为袁世凯所注意,并交由财政、农商部筹议,增设 “农工银行”条例,贷款牛皮、蚕丝、粮食等农产品,以周转融通农工资金。[23]
持教育救国论者络绎不绝。前参议院议员李国珍呈文袁世凯,提请设立教育厅 “专兴学之责任”。[24]汪家栋呼吁关注社会教育,如设立露天学校及各种补习学校。[25]康有为瞩目军事教育,提议将 “救国储金”设立飞天、遁地、潜水、驰陆、百工博物院五校,“以广励物质之学识,以成一切工程之才”。[26]亦有论者称,练兵所造就者有强健体格,而无爱国精神;兴学所造就者具爱国精神,而乏强健体格,惟 “军国民教育”兼具二者之优。[27]值此外交紧迫背景下于天津召开的 “全国教育界联合会”,最重要的提案即将 “义务教育”定于宪法,如是可防因 “修改普通法令,手续至为简易”而造成的朝令夕改之弊。[28]教育部遂拟启动 “义务教育施行程序”,包括划定学区、调查学龄儿童、普设小学、划一学制、造就良好师资等。[29]
在澄清吏治方面,安徽巡按使韩国钧批评称,近日条陈或为振兴实业,或曰提倡教育,实不知治国之经纬当自整顿吏治始。[30]官场腐败已成士人共识,冯国璋表达了 “欲整顿吏治,非用武力解决”的决心。[31]国务卿徐世昌提出以考核政务厅、甄别县知事、考核盐务官为清理积弊之要素。[32]王鸿猷劝诫总统当以 “学术、经验、节行、声名、所言、所事”为官员任用之标准,务必破除情面,禁绝滥竽。[33]关于县级民政之推动,韩国钧称虽值财政艰处,然必以增加各县知事办公经费为要义。[34]熊希龄认为,对县知事应由 “内务部查照中外吏治良法,定立功过表则”。[35]对于吏治条陈,袁世凯表现出特别的重视,既要使官吏严自检束、慎防中饱,又要避免以一知半解之徒滥充官场,专门行政必须访求专门人才。[36]
至于肃政史条陈及整顿内政的建议,孙洪伊表示并不看好,完善内政仅系枝节性的改革,改良政体才是兴国之根本。若仍以专制精神谈维新之政治,一切努力难免徒劳。[37]杨永泰回应,所谓修明内政,整饬吏治不过 “多杀几个王治馨”,振兴实业不过 “多借数千万磅之外资”,提倡教育不过 “多编几种教育纲要”。惟有改良政治组织,是为 “根本的疗治”。[38]
共和立宪实行的要素,应以广开言路,制定宪法,恢复国会、省议会、自治为目标。徐傅森反对袁世凯的独裁政治,并解释 “强有力政府”在西方语境是 “强而善之政府”的含义,呼吁从 “建设尊重真正民意机关始”。[39]在林长民主笔、政事堂八参议共同起草的条陈中,明确表示 “宪法为国家之根本,不立宪则国家政治无统系”。[40]政事堂参议曾彝进谏言速行地方自治,征兵、退伍、整理财政、调查户口等行政事务 “有委讬于自治机关而克收指臂之效”。[41]四川将军胡景伊提出以速开国会为基础,整理全国财政、扩张海陆军、实行军国民教育、广设兵工厂。[42]进步党人视此际为立宪复兴良机,提出重建地方议会。[43]阅毕上述建议,袁世凯表面上深与嘉许,一方面宣称 “宪法为立国要典,关系至为重要,全国官民必视均极重视”,[44]未来宪法制定中 “宜使立法部权力略为伸张……每年一加修改,俾民权渐次扩张”,[45]另一方面,又言恢复立法机关,“尤以立法与行政相辅,乃能共谋国是”。[46]费樹蔚的论述更进一步,认为在复议会之外,亦应联络海外革命党人,存政党、收暴徒,因暴徒中不乏超杰之才。该建议固难为袁世凯接受,袁批示 “精神可嘉,但有不合情理之论述”。[47]
然而,部分人士对整饬内政及改良政体均持保留态度。杨永泰认为 “政治为枝叶,社会为根本”。[48]梁启超阐明 “政治基础在社会说”,鼓励聪智勇毅之士 “共戮力于社会事业,或遂能树若干之基础”。[49]黄远生反省时局,认为当以改造个人为改造社会的前提。[50]金天翮在上大总统书中提倡从学术、文化为入手,视 “正人心,端学术”、“研究性理,崇言陆王之学”为治本之策。[51]社会改良会雍涛发出 “多妻乃中国人之大病、嫖赌足以亡国”之警告。[52]马相伯、英敛之强调,宗教可拔去中国人的懒根性,且认定一个 “真宗教”而归依之,为改良中国社会之要素。[53]袁世凯亦认同以 “倡兴宗教”,挽救日渐堕落之道德。[54]然而,就改良政治与社会何者为先,章士钊批判梁启超 “政治基础在于社会之说”,认为此系防止革命之举。社会事业之进行,不能离乎政治之外,恶政治之下,难以培植出良善社会。[55]
从某种意义上讲,“二十一条”交涉结束之初,朝堂内外形成了一股上书、建议、昕夕讨论的救亡气氛。《申报》评论称,正可谓一段 “无日不有所见”的 “条陈时代”。[56]曹汝霖亦回忆,政府一时曾力图振作,以期百废俱举,“每次会议,必有新提案提出讨论”。[57]可以看出:一方面,对于政府同人及在野政治家而言,即便老生常谈之条陈居多,但毕竟受外交失败之刺激,乃有一番表示振作之决心,这实际上仍沿袭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以来 “外患—救亡”的传统路数。另一方面,就袁世凯本人而言,其虽对部分上书做出了相关回应,但从来往函件的批复中看,似多为因应条陈者的“应景之作”。对于纷繁琐碎、杂乱零散的建议,袁世凯无心加以整理、提炼,更谈不上在整饬内政中间通盘的统筹与整体性的战略设计,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袁世凯不仅缺乏改制的诚意,而且缺乏对于时局清醒的认知。
二、内政改制与政府信任危机的激化
在内政整饬中间,由于袁世凯全局意识的缺失、顶层设计的混杂、厘革方向的迷失,不仅决定了继之而来的实践活动必然仅是流于琐屑的小修小补,而且暗示了极为有限的成效。
教育一项,教育部在小学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做出部分调整。在小学教育层面,首先是7月31日 “国民学校令”与 “高等小学校令”的发布。前者为义务教育性质,自此令颁行,民国元年 “小学校令”及 “初等小学校”即行停废、更名;后者系以增进国民学校之学业,并完成初等普通之教育为宗旨。[58]俟二令通行后,教育部拟定以八年为期的普及小学教育计划。8月6日,教育部再颁行“地方学事通则”,明确以地方自治区为义务教育办理之学区,并负担区内办学经费各项。[59]随后,教育部从京师小学入手,检定教员,期将不称职之教员,悉从沙汰。[60]就师范教育而言,教育部以统一师范精神为要旨,于8月10日至28日间,邀请全国各师范学校校长暑假来京会议,讨论国民人格教育与生活教育并重、国民适用之文字与高等文学异趣、师范学校招考学生及毕业生服务任用法等论题。[61]社会教育方面,7月18日,教育部颁布 “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专事小说、戏曲、讲演研究,为移风易俗之辅用。[62]
在实业方面,农商部的举措主要表现在劝业委员会及国货展览会的筹办。6月8日,农商部颁布“劝业委员会”章程,并下设工业试验所、工商访问所、商品陈列所,以编纂实业法令、培养工业技术人才、调查海内外工商状况、提供企业咨询等为导向。[63]为使国货云集,“观摩互益、发扬国粹、标本广陈、声誉增高”,[64]6月18日,农商部特设 “国货展览会”于京师,并 “责成各商会就地调查,并由县知事督同劝募,汇详巡按使,解交本埠”。[65]为鼓励起见,政府特免展品入京之税厘。9月1日至10日,内务总长朱启钤于先农坛组织 “京都出品协会”为导引,并借以改进京都百工凋敝之象。[66]10月1日至20日,国货展览会开幕,除江西、新疆、黑龙江、云南、贵州未备齐物品外,其余各省均有特产陈列其间。张謇喜赞,“凡此诸品……或足应国内之需要,或足扩国外之销场,倘从此更加讲求推广产额,自不难发展经济,裨益国本。”[67]
军事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征兵制度的启动。征兵之议于前清 “北洋时代”已启首端,但民国以后因手续至繁而屡经搁置。军界同人表示军备整顿、扩充兵工厂皆为小修小补之功,根本仍在征兵制度之改良。故而,统率办事处拟设立 “征兵讲习所”,以陆军部闲置咨议为学员,分赴各省广宣征兵要义,[68]并计划组成以陆军总长王士珍为会长、原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蒋方震为主任的 “征兵研究会”,磋商以直隶、河南、山东为先行试办区域。[69]未久,京兆征募局、河洛道征募局先后开幕。[70]
至于地方自治的复办,若就全国范围推行,工程浩瀚,实属不易。审计院顾问葛诺发遂上 “建设模范行省”条陈,不如先就一省妥慎推行,从京兆一隅先行试验。既可足表政府改制的真心,又可收 “由一隅而推及全国”之效。[71]袁世凯于7月21日发布 “筹办京兆地方自治事宜令”:京兆为全国所具瞻,当定为特别区域,以作自治模范……务仿西国都市之政,东邻町村之规,心摹力追,日久完备”。[72]关于模范自治之内容,按照内务部设想,涵盖了 “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务”、“慈善”、“公共营业”等方面。[73]
实际上,尽管改制名目繁多,但变革举措的枝节性、实施时间的短暂性、办理成效的微弱性,使得教育、实业、军事、地方自治等项,皆不啻为政府施政进程中的常态,实难副厘革之盛名。并且,因主持者在民生办理、减政推行、吏治整顿、立法筹备等方面的失当,致使挽救危机的努力非但未能如愿奏效,相反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政府信任危机进一步激化。
先言民生办理方面,目标与结果适得其反。黄远生曾以合办平民生计与平民教育,向徐世昌提请组织 “全国生计委员会”:“平民生计发达,即可为国家增加税款,平民教育普及即于练兵前途大有裨益。”[74]6月14日,袁世凯发布于政事堂内 “筹办全国生计委员会令”:“无论财政如何困难,而民事决不可缓。总期通国无无用之物,亦无无用之人。”[75]然而,“全国生计委员会”的设立不仅未能赢得好感,反而迅即招徕了批评。首先是会长人选互相推诿。最初外间传请姚锡光担任会长一职,但因其为 “五族同进会”会长,故打消此议。[76]张一麐亦表力辞,杨度又以 “不屑小就”而推托,严修同样未行履任。最终,汤叡勉强允任,政府迟至半月之久才确定该会委员名单。[77]其次是各方意见纷杂不一。对实施区域,一种主张缩小范围,以京师为首区,一谓宜于各省同时调查进行,胡瑛则建议 “先从生计尤困之各省着手”。[78]以致该会成立一月有余,不仅章程未能成立,而且尚未正式开会。[79]再则是政府的不实报道尤为失信。先前多传办事员已离京分赴各地考察,但实际上并未出发,“所有各报喧载均系一种推测,毫不足据”。[80]时各省水灾相继,该会行动之迟缓,不禁令观者叹息此惟 “空作远大难行之论”。[81]批评者忿然视 “全国生计委员会”不过 “在政事堂多挂一种空牌子而已”。[82]有建议者进一步扬言,与其纵任该会毫无所表现,不若将此赘瘤机关予以裁废。[83]
在减政裁员的行动中,政府表现得更是有心无力。袁世凯采择肃政史条陈中的减政建议,以总统府内裁汰冗员为各行政机关减政之倡,且逐一规定各部职官员额、每月薪俸,并令各总长 “不能再以裁无可裁之呈文,敷衍了事”。[84]未久,各部裁减人员见诸报端:外交部裁减30余人,陆军部减少顾问、谘议百十余人,财政部淘汰部员69人,总统府及政事堂裁去办事员28人、顾问及谘议47人,[85]盐务署撤销人员13名。[86]然而,减政并非一帆风顺,其迅猛的实施速度,遭遇了各部激烈的反应及 “不合作”之困窘,如教育部即抱怨无员可裁,[87]财政、农商部称 “洋员顾问皆以合同关系,不能裁撤”,陆军部以多半军官系 “有功民国者,待遇不得不稍优也”,[88]海军部则擅行特别之法,将应减人员暂缓裁汰并改为谘议。[89]
在吏治整顿层面,此间的 “五路大参案”,使得政府与刷新吏治的初衷南辕北辙。参案始于肃政史联名请查办津浦、京张、京汉、京奉、沪宁等五大铁路舞弊营私案。6月18日,津浦铁路局长赵庆华首先被撤职查办。[90]6月20日,袁世凯又以交通部次长叶公绰与此案最有关系,将其停职候传。[91]随即,京张铁路局长关冕钧、京汉铁路局长关赓麟、京奉铁路局长李福全、沪宁铁路局长钟文耀次第被弹劾。参案发生伊始,时人多将 “五路大参案”的处置视为澄清吏治之契机,热忱期待政府严格尊重法律,有效惩治,“驱除官邪……有现实之一日”。[92]未久,舆论发生逆转,有论者揭其内幕,虽以表面观之,官吏变动是整顿官方之举,但内中实含有粤系、皖系 “政党倾轧”意味。[93]许宝蘅亦指此案乃 “门户之祸,恐将累及国家,颇欲上书论之”。[94]皖系者,以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周学熙为代表,粤系者,以梁士诒及交通系组成。杨士琦与梁士诒结怨素久,遂拟利用肃政史弹劾之笔,企图推翻交通系势力。各界哗然,政府 “面子上虽若为察弊除贪起见,而黑幕之中……谁败谁成,无非鸡虫得失,一进一退,且同鹬蚌交持”。[95]由今日之人心以言中国,“则多一党派,即多一蟊贼”。[96]本是一场整顿吏治之 “五路大参案”,不惟沦为党派斗争之工具,而且平政院在审理案件中并未能发挥实质性作用。特别是政府禁刊有关消息,在秘密状态下办案,亦不免令外间浮想。许久,参案预审未见动静,外间感喟不啻官场五分钟热气之作风。[97]最为失望的是该案 “雷声大,雨点小”的结局。8月20日,京张铁路案审理结果公布,仅褫去关冕钧职。[98]10月19日,袁世凯申令,仅将赵庆华着付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惩戒,又以叶恭绰被劾各节查无实据,销去停职处分。[99]12月5日,京汉铁路案收尾,关赓麟交付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100]
立法院的复办更是遥遥无期。此际,袁世凯一度流露出恢复共和立宪的意图:5月25日,袁颁发国民会议组织法选举施行细则令、国民会议暨立法院议员初选资格调查期限令,[101]6月10日,又下达尅期成立立法机关令,[102]7月1日,参政院拟推举李家驹、汪荣宝、达寿、梁启超、施愚、杨度、严复、马良、王世瀓、曾彝进等十人为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103]一时间,立宪曙光普照,民国社会似有 “百世之基亦可从兹巩固”之相。[104]然而,在欣喜之余亦免不了疑虑者的担忧,或恐将来立法院之成绩,“决不能大异于现在之参政院,将来国民会议之成绩,亦决不能大异于已去之约法会议”,[105]或是揣度“此次所起草者,名为宪法,实则不过将约法略为放大耳”。[106]此外,宪法起草中禁止旁听的神秘主义,同样 “不足以昭其慎重也”。[107]时隔不日,“筹安会”粉墨登场,使得方兴未艾的共和立宪悉归泡影。舆论黯然神伤,此不啻 “神经病之中国”。[108]
政府在办理民生、减政、吏治、立法等层面的失误及 “偏转”,俨然使得当局者标榜的内政改制,信用丧失殆尽。批评者谓,朝野上下无不弥漫着 “垂头丧气”之相:官吏争权、军政窳败、司法黑暗、风俗惰偷、社会龌龊,已全无新国气象。[109]如是,不仅挽救危机的努力显得疲软无力,而且进一步激化了各方势力对于政府的积怨之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袁世凯在整顿内政中间敷衍与虚伪的态度使然;另一方面,此际袁世凯已将注意力逐渐转向称帝的目标,这使其再也无暇兼顾进行中的内政厘革诸业,而朝野上下挽救危局的努力归于失败,必成定局。
三、洪宪帝制与 “无果而终”的改制结局
改制自身的 “先天不足”、外交形势的干扰以及 “帝制派”的阻挠,注定了无果而终的结局。
首先是改制本身存在着重要的缺陷。其一是经费难产。对 “全国生计委员会”而言,任务不但极形重大,且关系甚为紧要,故所需经费极多。然而,财政部一再表示 “现值财政艰处,实无筹拨之处”,[110]后虽经屡次争取,最终该部仅允认 “可供给调查之实费而已”。[111]期间教育总长汤化龙力谋的 “设立教育厅”草案,卒以经费未能解决,未及实践便胎死腹中。[112]实业计划中的 “农工银行”,囿于财力不济,实施范围惟以京兆通县、昌平为限。[113]
其二是人才匮乏。以京师甄别小学教员为例,考核结果实未尽人意,教员国文无根底者居多,故考试结果惟迟迟不发,该试验终作无形之取消。[114]再如 “劝业委员会”,进行之初颇显五分热血之朝气,然因会长雍涛于做官一事本不在行,未久便往西山避暑,卒留洋顾问数位敷衍门面,遂成虎头蛇尾之势。 [115]
其三是施行缺乏必要的准备,有操之过急的倾向。以减政裁员为例,实行之过速,迅即引起了各部恐慌,有识之士注意到其中要害在于善后之策缺失,故建议对被裁人员谋求安置之法。[116]再如京兆自治的办理,政府亦颇显激进化姿态:8月初尚决议分四期进行,以半年为一期,第一期为筹划时期;[117]然一月以后,则提出加速之方,即以 “八、九、十三个月为筹备时代”;[118]或言明春完成京兆模范自治,下半年各省成立分会,后年全国各县通告完竣。[119]
其四是政策自相矛盾。对减政而言,前述 “安置裁员”建议一经采纳,复呈一番 “互相抵触”之景观,“一方裁汰若干人员……一方又新设某某局所以位置旧僚”,增、减经费相较,哑然为自欺欺人之事。[120]再以 “全国生计委员会”言,政府一面称筹办平民生计,一面又行反民生之举,吴贯因历数政府与民争利之例,虽不盼望该会裨益民生,但求 “禁止官吏之夺国民之生计”;[121]政府一面标榜 “减政主义”,一面又巧设生计会 “位置冗员”。[122]
其五是条例的形式主义。政府虽制定出诸多实业方案,但就真正落实情况看,确如张謇批评,“内不过条例,外不过验场”。[123]再如紧随 “京兆模范自治”而至的各种模范之声:模范军警、模范工厂、模范商店、模范农场、模范俱乐部等悉为涌现。然 “模范热”背后,浮于空言者比比皆是。[124]莫里循感叹,“这里看不见有作为的政治家气魄,没有始终如一贯的目标……一切精力都用在草拟那无尽无休的规章法令上,改革只是口头说说”。[125]
其次是动荡的外部环境的冲击。“二十一条”交涉的结束,并非意味着中日关系得到妥善解决。相反,日本围绕未竟条款,继续与中国展开新一轮的争锋。期间发生的案件主要有间岛交涉、辽西杂居事件交涉、中日长白军警冲突、张家湾设警案等。日本或强解条约,或故意延宕,牵涉有关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诸问题,始终未获彻底解决,使得袁政府无法获得喘息的改制环境,相反在处理条约体系等外交事务中捉襟见肘。①参见高翔宇:《〈南满东蒙条约〉的签订与中日间岛交涉述论 (1915—1916)——“二十一条”交涉后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侧面》,《历史教学》2014年第9期。
再次,“帝制派”的活动,使得内政整顿的方向发生逆转。袁克定在 “洪宪帝制”中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早于民国元年,袁克定即欲以 “北京兵变”效黄袍加身故事,②参见尚小明:《论袁世凯策划民元 “北京兵变”说之不能成立》,《史学集刊》2013年第1期。此后一直在私下活跃,“设总部于中南海里的一个岛——瀛台,在这个首都的中心接待拥护帝制的死硬派”。[126]至于此间袁克定作梗的 “五路大参案”与帝制运动的促成具有直接关联。1915年初,袁克定曾于汤山就国体问题会晤梁启超,未获支持性表态,遂将目光转投 “交通系”头目、素有 “财神”之称的梁士诒。袁克定先行拉拢了素奉行君主制主张、且与梁士诒结有宿怨的政事堂左丞杨士琦,随后唆使杨士琦借助肃政史王瑚、蔡宝善之笔,参劾 “交通系”。[127]袁克定既知梁士诒心有余悸,便邀其谈话,单刀直入请其支持帝制之事。梁当夜即召集交通系人员开会,并以 “赞成不要脸,不赞成就不要头”相询,结果大家表示 “要头”。次日,梁表示回报克定。[128]交通系各员遂约定 “不干则已,干起来则不必遮遮掩掩,一定要大权独揽,有声有色”。[129]梁士诒与袁克定的 “结合”,亦与其在粤、皖两系斗争中反客为主的策略相关。粤系求以迎合之法,独任帝制运动之财政,得以重觅权力。[130]袁克定利用了皖、粤系矛盾,先与杨士琦结盟,迫使梁士诒就范,次使得皖、粤二系在帝制目标下暂时 “合流”。
袁克定亦利用杨度在立法院筹备中混淆视听。早在辛亥前,杨度即以君宪自命。俟共和后,杨因谋交通部职务不成,与梁士诒成仇,且颇有怀才不遇之憾。③杨度在 《乙卯春致杨雪桥师书》中称,“度虽有救国之心,然手无斧柯,政权兵权皆不我属……当局之用人行政亦与度不尽相同”,刘晴波主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65页。然杨仍图谋重用之机,遂有人告以 “与其谓接近项城,不如谓接近克定”。[131]袁克定先使杨度于日媒造成在 “参政院提出变更国体建议”之舆论,[132]再将其安置宪法起草委员会,以 “旧派”思想左右其间,[133]后利用其炮制 《君宪救国论》,与古德诺的 《共和与君主论》呼应。袁克定既收抚了原本不和的杨度、梁士诒,以杨为先锋,成立 “筹安会”,再以梁组织的 “三次国体请愿”紧随其后。尽管杨、梁矛盾并未随帝制运动的进行而消除,④当参政院将国体问题付诸国民代表大会,“筹安会”实无用武之地,于10月13日更名 “宪政协进会”,梁士诒取代杨度成为了复辟帝制活动的主要人物。杨云慧:《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第62页。但接连的帝制鼓吹,迎合了袁世凯的称帝野心,使其沉醉在 “民意”的声浪中,获得了重塑权威的满足与虚幻感。
遗憾的是,此间的内政改制伴随洪宪帝制的发生而宣告破产。由于袁世凯对帝制权力的急切欲望,故而未能将这场挽救危局的努力持续下去,并错失了 “二十一条”交涉后中国内政厘革的一次契机。
应当认为,内政改制的奏效,尚需一段时间的沉淀。周学熙表示,内政整顿中 “凡此应办之事,苟能次第进行,则中国富强并非无望”。惜 “洪宪议起,大局忽变,一切悉归泡影”。[134]梁启超则认为,君主立宪万不可取,但可在总统制下推行内政改制,“今大总统能更为我国尽瘁至十年以外,而于其间整饬纪纲,培养元气……是故中国将来乱与不乱,全视乎大总统之寿命,与其御宇期内之所设施。”[135]稍后梁与英报记者谈话,“国体与政体绝不相蒙,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毋宁因现在之基础,而徐图建设理想的政体于其上。”[136]汪凤瀛表示,治今日之中国,非开明专制不可,自 《新约法》颁布以来,“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进行较利,财政渐归统一,各省皆极其服从,循而行之,苟无特别外患,中国犹可维持于不敝。”[137]贺振雄称,“现方筹备国会,规立法院,整饬吏治,澄肃官方……四年之间,国是已经大定。”若由袁连选连任,不十年间,“必能驾先进之欧美,称雄地球”。[138]
变更国体这一极端化的手段,亦使中国政治卷入翻云覆雨的漩涡。梁启超描绘了这一现象,“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139]朱峙三在日记中困惑于 “局势转变如此,则人民所不及料者”。[140]更为关键的是,复辟帝制不但令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且使得在内政改制中间政府信任的危机愈加激化。傅熊湘以传兵符、税烟酒、制民意、改账簿为题,讽喻改行帝制社会生活之惨状。[141]莫里逊观察,民众积怨亦是 “联合起来破坏帝制的一些力量。缺乏这类因素,鼓动家就没法煽起足以造成叛乱的情绪”。[142]严修对时局转折的分析颇为精辟,“为中国计,不改国体,存亡未可知;改则其亡愈速。为大总统计,不改国体而亡,犹不失为亘古惟一之伟人;改而亡,则内无以对本心,外无以对国民。”[143]而袁世凯堕入洪宪帝制的深渊,其 “窃国大盗”之妖魔化面孔亦随之迅速建构。①1916年 《袁氏盗国记》出版,序言即以 “袁世凯固今代一妖孽也……只一狭邪无赖之权诈而已”为盖棺定论之词。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页。
“二十一条”交涉结束直至 “筹安会”成立之间的这段 “被遮蔽的历史”,100年来被尘封在史料深处。一方面,应当认为,在此间的3个月里,对于民初政治史的叙述而言,与 “帝制派”酝酿复辟运动的同时,还存在另一条历史主线,即因外交受挫的刺激,朝野上下为寻求救亡与厘革内政而做出了种种的努力。另一方面,如果将研究视野延展至思想史领域,可知这场由政界同人主导的挽救危局的尝试,不仅构成了 “二十一条”交涉后中国政局上鲜为人知的一个侧面,更与同时期由思想界悄然兴起的 “新文化运动”互为表里,两者实共同构成了国人改造政治与社会思潮的多元实践。只是,由于袁世凯未能以诚相待这场内政厘革,随之洪宪帝制发生,暴露了其欺骗性的面目,这不但使得这场挽救危局的努力付之东流,更令中国的政治情形愈加败坏,以致一度陷入持久性的军阀分裂。而在这段 “被发现的历史”中间,虽有精彩,但充满了无奈。
[1]《宋渊源所散播传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中日关系史料·二十一条交涉》(上),1985年,第406页。
[2][3][6][11][46][75][91][102]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31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6、427-428、464、654、535、564、601、535页。
[4]《都肃政史庄蕴宽等呈》,黄纪莲编:《中日 “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1-243页。
[5]《大总统申令》,《政府公报》第57册,第1911号,第253页。
[7]《为敷陈救亡大计之肃政史进一解》,《神州日报》1915年6月25日第4版。
[8]《军国主义谭》,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山西民初散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6-105页。
[9]《兵工厂事务督办萨镇冰关于拟请整理各省兵工厂详细条陈详细条件清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第53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第536-545页。
[10][26]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6-239、252页。
[12]《新译 〈日本帝国海军之危机〉序》,王栻主编:《严复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48-349页。
[13]《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为钞送威克斯厂谭若森条陈整顿江南船坞及处置上海制造局办法致兵工厂事务督办萨镇冰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第53卷,第508页。
[14]《论培养海军人才之必要》,《顺天时报》1915年7月21日第2版。
[15]伯因:《烟突主义》,《正谊杂志》第1卷第9号,论说三,第1-20页。
[16]《张謇对于救国储金之感言》,《申报》1915年5月23、24日第11版。
[17]《王鸿猷主张以储金办银行》,《申报》1915年5月24日第10版。
[18]《筹设劝业银行之大概》,《时报》1915年8月9日第2张第3版。
[19]《财政部呈筹办民国实业银行拟具章程并变通营业及招集股本办法请钧鉴文》,虞和平、夏良才编:《周学熙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95页。
[20][36][44][45][47][58][72]刘路生、骆宝善主编:《袁世凯全集》第32卷,第335、46、67、118、476-479、215-221、149页。
[21]《为倡农而后兴学练兵致徐世昌函》,李良玉、陈雷主编:《倪嗣冲函电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4-245页。
[22]《今日之银行政策》,《申报》1915年7月12日第6版。
[23]《财政部呈为拟定农工银行条例缮单仰祈钧鉴文》,虞和平、夏良才编:《周学熙集》,第626-627页。
[24]《李国珍对于改良教育之建白》,《神州日报》1915年6月19日第3版。
[25]汪家栋:《救国兴学方法以外之意见书》,《时报》1915年8月17、19日第3张第6版。
[27]《军国民教育救国论》,佚名编:《国耻痛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90页。
[28]《1915年第一届全国教育会联合大会议决案之一:请将义务教育列入宪法案》,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三·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25页。
[29]《教育部为准义务教育施行程序致大总统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第90卷,第23-30页。
[30][34]《安徽巡按使韩国钧呈筹拟整顿吏治办法当否请示文》,《政府公报》第61册,第1149号,第192页。
[31]《闲评一》,《大公报》1915年6月29日第2版。
[32]《整顿内治之动机》,《申报》1915年6月5日第6版。
[33]《王参议忠言谠论之一斑》,《时报》1915年5月20日第2张第3版。
[35]《为省亲沿途考察地方情形呈大总统文》,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五),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7-303页。
[37]孙洪伊:《对于肃政史救亡条陈之意见》,《正谊杂志》第1卷第9号,杂纂,第1-11页。
[38]杨永泰:《今后国民应有之自觉心》,《正谊杂志》第1卷第8号,论说四,第6-9页。
[39]徐傅森:《强有力政府之效果》,《正谊杂志》第1卷第8号,论说六,第1-16页。
[40]《八参议请实行宪法》,《申报》1915年6月30日第6版。
[41]《内务部呈遵议政事堂参议曾彝进条陈提前实行地方自治暨整理财政办法併案呈明请示文并批令》,《政府公报》第57册,第1914号,第394-395页。
[42]《胡景伊亦请速开国会》,《神州日报》1915年6月27日第4版。
[43]《进步党上大总统书》,《神州日报》1915年6月12、13日第4版。
[48]杨永泰:《黑暗政象之前途》,《正谊杂志》第1卷第7号,论说四,第8页。
[49]《政治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九),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793-2797页。
[50]《忏悔录》,王有立主编:《黄远庸遗著》,台北:华文书局印行,1936年,第103页。
[51]《金天翮上大总统正本救亡大计呈》,《大公报》1915年9月22、23日第3版。
[52]《中央公园之盛况》,《时事新报》1915年5月28日第3张第4版。
[53]英敛之:《社会改良会演说词》,《大公报》1915年6月26日第1、2版。
[54]《讨论倡兴宗教进行办法》,《大公报》1915年6月4日第2版。
[55]《政治与社会》,《章士钊全集》(三),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427-455页。
[56]《条陈时代》,《申报》1915年7月20日第7版。
[57]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第102页。
[59]《教育部为准地方学事通则致大总统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第90卷,第39-45页。
[60]《教育部呈遵谕考验京兆各属小学教员详拟甄别规程缮单请示文》,《政府公报》第62册,第1167号,第285-286页。
[61]《教育部采录全国师范校长会议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第90卷,第59-82页。
[62]《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文化》第3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2-103页。
[63]《将劝业委员会章程缮具清折恭呈钧鉴》,《政府公报》第58册,第1110号,第404-407页。
[64]《农商部之公函》,《北京日报》1915年7月1日第3版。
[65]《农商部呈限期征集商品开设国货展览会请示遵文》,《政府公报》第59册,第1120号,第153页。
[66]《市政公所筹设国货展览会京都出品协会通告》,朱启钤:《蠖园文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83-184页。
[67]《关于国货展览会办理情形致大总统呈文》,沈家五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78页。
[68]《举行征兵制度之先声》,《顺天时报》1915年6月29日第2版。
[69]《设立征兵研究会之开幕期》,《盛京时报》1915年7月6日第3版。
[70]《京兆征募局概况》、《河洛道征募局概况》,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9-201页。
[71]《葛诺发请建设模范行省之条陈》,《大公报》1915年7月21日第3版。
[73]《京师试行模范自治之嚆矢》,《神州日报》1915年7月27日第4版。
[74]《平民生计教育合办政策之建议》,《新闻报》1915年6月11日第2张第1版。
[76]《关于国计民生之根本政策》,《顺天时报》1915年6月21日第23版。
[77]《生计委员会之人物及章程》,《时报》1915年6月26日第2张第4版。
[78]《师范校长会议与生计委员会议》,《申报》1915年8月23日第6版。
[79]《生计委员会之闻见录》,《盛京时报》1915年7月30日第2版。
[80]《生计会进行之真相》,《时报》1915年8月25日第3张第5版。
[81]《生计委员会之抽象观》,《时报》1915年8月19日第2张第4版。
[82]《生计会与劝业会之将来》,《大公报》1915年6月26日第2版。
[83]《生计委员会表见之一端》,《亚细亚日报》1915年9月21日第2张第3版。
[84]《中央减政之大霹雳》,《神州日报》1915年7月24日第3版。
[85]《各部被裁人员之总数》,《顺天时报》1915年7月21日第2版。
[86]《盐务署裁汰人员》,《东方杂志》第12卷第9号,1915年9月,中国大事记,第3页。
[87]《教财两部之裁员情形》,《申报》1915年7月23日第6版。
[88]《中央举废之新计划》,《新闻报》1915年7月23日第2张第1版。
[89]《海军部裁员之特别办法》,《时报》1915年8月8日第2张第4版。
[90]《北京电》,《申报》1915年6月20日第2版。
[92]友箕:《驱除官邪之希望》,《神州日报》1915年6月25日第1版。
[93]《北京电》,《申报》1915年6月23日第2版。
[94]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36页。
[95]《闲评一》,《大公报》1915年7月8日第2版。
[96]《党派之新名词》,《申报》1915年7月3日第2版。
[97]《闲评二》,《大公报》1915年8月5日第3版。
[98][100]岑学吕编:《三水梁燕孙 (士诒)先生年谱》(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270、271页。
[99]刘路生、骆宝善主编:《袁世凯全集》第34卷,第157-158页。
[101]《公布国民会议组织法选举施行细则令》、《公布国民会议暨立法院议员初选资格调查期限令》,刘路生、骆宝善主编:《袁世凯全集》第31卷,第419-420页。
[103]《参政院呈报推举李家驹等为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文》,《政府公报》第60册,第1137号,第293页。
[104]《宪政进行之曙光》,《顺天时报》1915年6月12日第2版。
[105]《闲评一》,《大公报》1915年6月12日第2版。
[106]《闲评一》,《大公报》1915年7月3日第2版。
[107]友箕:《异哉马叟秘密起草宪法之主张》,《神州日报》1915年7月26日第1版。
[108]冷:《神经病之中国》,《申报》1915年9月10日第2版。
[109]默:《无新国气象》,《申报》1915年8月2日第7版。
[110]《生计委员会之经费问题》,《顺天时报》1915年7月9日第2版。
[111]《生计委员会之前途观》,《顺天时报》1915年8月6日第2版。
[112]《设置教育厅之变通法》,《申报》1915年8月13日第6版。
[113]《全国农工银行筹备处核拟通县昌平农工银行放款规则详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金融》第3辑,第414-415页。
[114]《甄别小学教员发表之迟缓》,《大公报》1915年10月5日第3版。
[115]《劝业委员会之虎头蛇尾》,《顺天时报》1915年7月14日第2版。
[116]《北京电》,《申报》1915年7月13日第2版。
[117]《京兆模范政区之分期筹办》,《大公报》1915年8月2日第2版。
[118]《京兆办理自治之程序》,《大公报》1915年9月1日第3版。
[119]《自治推行之顺序》,《亚细亚日报》1915年9月20日第1张第1版。
[120]《减政其名焉耳》,《顺天时报》1915年8月15日第7版。
[121]吴贯因:《敬告全国生计委员会》,《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9期,1915年9月,第1-6页。
[122]《平民生计会之结束》,《时事新报》1915年8月17日第2张第2版。
[123]《复周自齐函》,张謇研究中心等编:《张謇全集》(一·政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25页。
[124]冷:《模范》,《申报》1915年7月18日第2版。
[125][142]莫里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912—1920》(下),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438、539页。
[12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译:《顾维钧回忆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5-96页。
[127]周志俊:《粤皖系之争与帝制活动》,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226页。
[128][131]《洪宪遗闻》,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77-78、200页。
[129]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第235页。
[130]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23页。
[132]《帝制谣》,《神州日报》1915年7月10日第3版。
[133]《宪法起草委员会之近讯》,《神州日报》1915年7月14日第4版。
[134]周学熙:《周止蓭先生自叙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年,第50页。
[135][139]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二),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1021、1025-1027页。
[136]《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82页。
[137]《汪凤瀛参政致筹安会杨皙子论国体书》,《大公报》1915年9月5日第4版。
[138]《贺振雄诛奸救国之原呈》,《新闻报》1915年8月20日第1张第3版。
[140]严昌洪编:《朱峙三日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62页。
[141]《乡谈小乐府四首》,颜建华编校:《傅熊湘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6-77页。
[143]王承礼辑注:《严修先生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第345页。
责任编辑:杨向艳
K258
A
1000-7326(2016)07-0127-11
高翔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