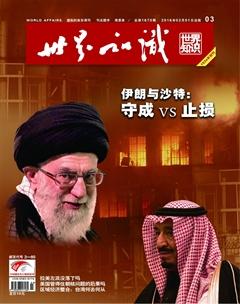欧洲复发“极右症”
周谭豪


2016年新年钟声敲响之际,德国科隆突发具有“移民背景”的大规模性侵事件,为贺岁狂欢掺入刺耳杂音。随后,欧洲多地连发“极右”排外街头运动,并演化为骚乱。德国及欧盟对难民“门户开放”政策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也与此前欧洲选举中的“极右热”相呼应。
事实上,自法国大革命期间诞生“左”、“右”之说以来,“极右”势力便作为另类“衍生品”而与欧洲政治如影随形,但除二战期间臭名昭著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外,鲜有作为。然而,近年却日渐“显山露水”,特别是2015年12月法国大区选举中险些染指半壁江山,令自诩“西方民主滥觞”的法国惊出冷汗,更促使欧洲各国深省:“极右”早已非昔日之“添头”、“插曲”,而俨然成为在欧式民主内部潜滋暗长的“病毒”。
“极右症”发作愈频
欧洲“极右”声势上扬大致可追溯到世纪之交。彼时的旧大陆,因“千年虫”忙中出错的不仅有计算机程序,亦有民主程序,其中最具“镜头感”的事件有二。一为2000年,因公开支持希特勒而声名狼藉的“奥地利自由党”进入奥地利联合政府,引发轩然大波,更招致欧委会对奥史无前例的外交制裁。二为2002年,将纳粹集中营轻描淡写为“历史插曲”的法国“国民阵线”创始者让-马丽·勒庞(老勒庞),在该国总统选举首轮爆冷,击败呼声很高的社会党领袖若斯潘,迫使传统党派罕见搁置前嫌,在次轮联手组成“共和阵线”予以抵制,以免“民主选举产生非民主结果”。此后,尤其是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极右”政党民意基础日渐扩大,如2010年“瑞典民主党”首次进入议会;2011年“正统芬兰人党”在芬议会选举中支持率较上届猛增15个百分点,与主流政党不分伯仲;女承父业的玛丽娜·勒庞(小勒庞)“青出于蓝”,成为法国“最受工人阶级欢迎的政客”,2012年总统大选首轮中创纪录斩获18%的选票;匈牙利“尤比克”党近日则“荣膺”欧洲“最孚民望的‘极右’政党”称号,支持率直逼执政党。意大利、瑞士、荷兰和比利时等国的“极右”政党甚至历史性“入阁”或成为议会决策中的“关键少数”,特别是丹麦的中右翼少数政府至少在十年时间内,唯依靠“极右”的“丹麦人民党”支持得以“苟延残喘”。即便是长期对“极右”思潮“高压严打”的德国,“国家民主党”、“共和党”、“德意志人民联盟”和“德国选择党”等形形色色的“极右”党派也获得滋长空间,并进入多个地方议会。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各国“极右”势力普遍取得历史性突破,合力拿下1/5议席,刷新1979年欧洲议会开始直选以来的纪录,尤其是英国“独立党”、法国“国民阵线”等政党的支持率在本国登顶,“德国选择党”首次参选即获7%选票。法国总理瓦尔斯因此惊呼,欧洲遭遇“政坛地震”,“陷入黑暗”。
显然,2015年12月的法国大区选举,正是“极右病毒”滋扰欧洲老迈躯体的又一缩影。事实上,当年初的省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支持率就已高达近25%,超越执政党五个百分点,年中更一度突破30%。尽管本次大区选举次轮中,“国民阵线”再遭“共和阵线”联合绞杀,未赢得任何大区,但所获议席数量较上届猛增三倍,且两轮选举得票数基本持平,在几个大区的支持率甚至逾四成,显示其已经营出一批忠实“拥趸”,在法政坛造就“三足鼎立”既成事实。玛丽娜·勒庞春风得意之余高调放言,称“国民阵线”“已是法国第一大党”。意大利总理伦齐警告称,欧盟若再不改革,“民粹主义赢得某次选举只是时间问题”。
“症”从何来
众所周知,纵使再致命的病毒,有时也只是长期潜伏体内,因此病毒携带者不等同于病人。病毒真正发挥“负能量”,迫身体表达症状,需积聚多种内外条件。“极右症”之“表达”亦是如此。
首先,欧洲整体“免疫力”下降,放宽“病毒”发作条件。各方为促进欧盟“消化吸收”,推进一体化,让渡大量经济主权,一大实质就是北欧国家及法国、意大利等南欧大国成为欧盟预算净出资国,通过为其他国家提供大量补贴,换取后者开放市场。这一模式为单一市场建设按下“快进键”,但也带来巨大隐患:除德国、荷兰等少数北欧国家外,大部分欧洲国家并未因此搭上发展快车或倒逼改革,如南欧国家“罹患”产业空心化“通病”,经济竞争力显著弱化;一些中东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已入盟者日益依赖欧盟补贴,安于现状,未入盟者则大多谋求尽快入盟,欲强行对接高标准,改革反有“揠苗助长”之嫌。同时,欧洲国家无不秉承高福利理念,政府、企业负担沉重,欧债危机爆发前勉强靠较高经济增速“硬撑”,但财政赤字及公共债务比例亦纷纷超标。欧债危机的爆发普遍重创南欧、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民众福利受到削减、失业率高企,即便法、意等大国也自顾不暇,更无力承担欧盟出资、互助义务及吸纳北欧出口,民主制度“严重赤字”。2015年12月,欧盟经历多年来“最艰难”峰会,英国脱欧、希腊债务及财政紧缩等问题集中爆发、矛盾公开化,意大利总理伦齐更罕见地炮轰德国总理默克尔,进一步加剧了欧洲民众对主流政坛及一体化的失望与不满,从而促其加以改变。
与此同时,“病毒”自身也在加紧“更新换代”。以老勒庞为代表的老一辈“极右人”多放浪形骸、口无遮拦,从而被牢牢贴上“新纳粹”、“反欧”等极端保守标签,令人唯恐避之不及。但以小勒庞为代表的“新生代”则致力于为“极右”党派“去妖魔化”,重塑“亲民”的“温和右翼”、“全民政党”形象。玛丽娜·勒庞主政“国民阵线”后,第一时间与其父“划清界限”,强调“他是他,我是我”,近期不仅公开抨击老勒庞“新纳粹”言论,更将其驱逐出党,生生将87岁的老父气成重病,以此换取舆论好感。玛丽娜·勒庞还力求政策主张“可操作化”,一方面努力“用普通人的方式讲政治、说真话”,向民众阐释其“草根”立场,另一方面适度弱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色彩,包括将“国民阵线”传统的“脱欧”立场改为“疑欧”,包装“正常党派”形象。就连法国左派舆论阵地《解放报》也不得不承认,玛丽娜·勒庞主张“吸引人两分靠亲近,八分靠好奇”。欧洲其他“极右”政党亦“依样画葫芦”,纷纷高举“爱国”、“为民”旗帜,引诱选民摒弃“既无新意又无生机”的传统政党,尝试“新选项”,并从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所在地)拿回“应有利益”。
移民、难民的涌入为“病毒”的扩散和蔓延铺设了“快车道”。欧洲国家并非传统移民国,但因二战后巨大的重建需求及特殊的地理位置,数十年来大量中东非基督徒移民涌入,仅穆斯林群体就已逾2200万。这些移民往往固守自身文化传统,不愿主动融入欧洲社会,加之职业素质、技能相对较低,亦不具备成熟的融合条件,因而长期徘徊、积聚于欧洲社会边缘,形成“城中城”、“城中村”。欧洲本土白人亦不习惯异族大量“酣睡卧榻之侧”,从而因过度警惕引发误解、偏见甚至歧视。近年,欧洲经济低迷及近来难民危机更加剧了双方的资源争夺,放大了文化差异。伊斯兰极端势力亦推波助澜,加大对欧渗透,蛊惑移民“圣战”,倒逼欧洲收紧移民政策,乃至停收难民,为双方的紧张关系再绷新弦。2015年11月13日巴黎恐袭当晚,法国北部的加来难民营就遭纵火。“极右”势力趁机利用欧洲民众安全忧虑陡增,将移民、难民问题与恐怖主义“作关联”、“划等号”,并重弹欧洲“绿化”老调,渲染“排外”、“恐伊”情绪;同时渲染“文明冲突”,称问题“不在穆斯林,而在伊斯兰教”,企图化身“卫道士”。欧洲“极右”政党还欲“举一反三”,促欧管制规模更大的盟内移民。“丹麦人民党”前主席、现丹麦议会发言人凯斯高强调:“我们愿与邻和睦,但我们之间应有道篱笆。”
欧洲主流政坛开始接受“携带者”现实。传统上,欧主流政治系左右大党轮流坐庄,选民大多具有明确的价值观倾向,遂能“从一而终”,保障政治“和谐振动”。但年深日久,主流政党政策日显趋同,法式“左右共治”、德式“黑红大联合”渐成常态,欧洲一体化的深入也不断压缩各国政府政策的调整空间,改革往往雷声大雨点小,限于“维稳”式的小修小补,而难有质变。随着欧洲各领域问题积重难返,传统政党的应对捉襟见肘,原有“票仓”不断流向“极右”势力,不得不“向右看齐”,甚至视“极右”为制约其他对手的“平衡木”。如法国中右派领袖萨科齐,在2015年12月的大区选举中公开拒绝致力于主流党派合作阻止“国民阵线”的“共和阵线”,反欲吸引“极右”选民,幸遭党内抵制;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巴黎遭袭后亦与玛丽娜·勒庞“共商国是”,并在边境控制及难民等问题上事实上部分吸纳“极右”主张。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立陶宛等中东欧国家公开抵制欧盟难民配额,与“极右”主张“不谋而合”。同时,法国主流政党亦欲仿效二战后允许“极左”派参政的先例,引导“极右”政党真正“正常化”。近年欧洲“极左”、“极右”政党参政,乃至希腊“极左”政党掌权的经验亦表明,即便其真正上台,也只能“热闹一阵”,最终难免回归“正轨”。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欧洲主流政党对“极右”态度暧昧,“既承认又搪塞其危险性”,甚至纵容其壮大。
恐成欧洲长期“隐痛”
近年,欧洲“极右”政党虽竞相“粉墨登场”,但仍只是博人眼球的“跳梁小丑”,并未也很难撼动传统政党的“主角”地位。欧洲民众曾深受纳粹、法西斯戕害,对“极右”思潮的警惕心根深蒂固,随着欧洲经济逐步复苏,民众激进心态也将缓慢平复。此外,欧洲成熟的选举制度亦早已为防止极端势力上台设计了单一选区赢者通吃(以英国为代表)、二轮混合决选(以法国为代表)等模式,仅欧洲议会采用一轮选举并按得票比例分配议席的选举方式,缝隙较大,但鉴其实权有限,“极右”政党即便大量进入,也难兴风浪。
然而,“极右”势力已成功利用欧洲处于危机的多发期坐大,在欧式民主制度下“尾大不掉”。欧洲的政治“碎片化”、经济分化及社会多元化等趋势长期化,族群对立尖锐难缓,恐袭警钟长鸣成为“新常态”,这些因素造就了“极右”生存发展更肥厚的土壤。欧洲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思想恐进一步回潮,一体化阻碍上升,欧盟自由开放、多元一体的国际形象亦面临挑战。此外,当前乌克兰等“东部伙伴国”的“极右”势力也迅速扩张,有些还已经入阁,这些现实令欧俄博弈更趋复杂。从更大范围看,近来部分亚洲、拉美国家乃至美国也出现政治“右风劲吹”的趋势,国际政治风向值得各国密切关注。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