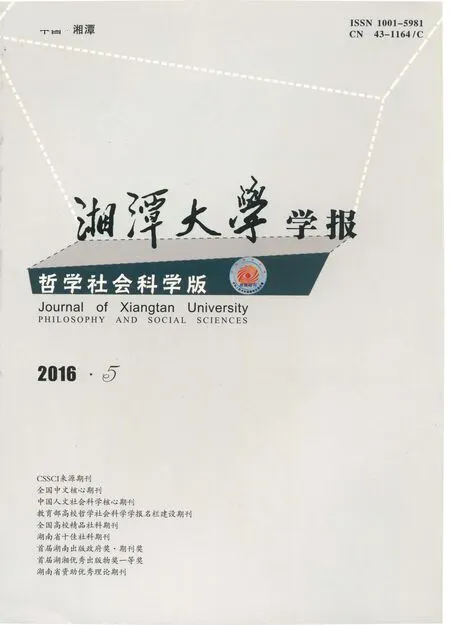奥尔多·利奥波德土地伦理及其理论困境*
简小烜
(湖南师范大学 科技哲学与科技政策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6)
奥尔多·利奥波德土地伦理及其理论困境*
简小烜
(湖南师范大学 科技哲学与科技政策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6)
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开创了生态整体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影响非常深远。但是在义务论、自然主义和整体主义方面,它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和诘难。义务论方面,它没有将人类价值放于优先位置,导致当出现多种义务时难于抉择的困境;自然主义方面,它直接从“是”推出了“应当”,抹杀了“是”与“应当”二者的区别;整体主义方面,由于把共同体的善置于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之上,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环境法西斯主义”。整体主义环境哲学杰出代表贝尔德·克里考特对利奥波德的理论进行了辩护与发展,提出了“同心圆”模型以及二阶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土地伦理的理论困境,生态整体主义也为环境问题打开了一个伦理探索的新维度。
奥尔多·利奥波德;土地伦理;生态整体主义
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年)是美国著名生态学家,被誉为“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生态伦理之父”。他的土地伦理(The Land Ethic,也被译为大地伦理)开创了生态整体主义以及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1]43-62; [2]26-30。环境史研究专家福莱德指出:土地伦理“表达了一种几乎是不朽的关于人和土地的生态伦理观”[3]209;纳什认为土地伦理“是现代生物中心论或整体主义伦理学的最重要的思想源泉”[4]80;马洛里则认为土地伦理是“环境伦理的起源,对可持续发展有巨大影响与作用”[5]59-89。利奥波德土地伦理可说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但是,由于其在义务论、自然主义以及整体主义方面陷入理论困境,因此受到一些学者的抨击与诘难。后来,整体主义环境哲学最杰出的代表——贝尔德·克里考特(J.Baird Callicott)对利奥波德的理论进行了辩护与发展,他提出的“同心圆”模型以及二阶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土地伦理之理论困境,而生态整体主义则为环境问题打开了一个伦理探索的新维度。
一
利奥波德在他的环境伦理经典著作《沙郡年记》(也译为《沙乡年鉴》)中,从人类对土地的义务视角出发,以义务论为理论建构方法,系统地阐述了土地伦理。利奥波德指出:“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可以规范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土地上动植物关系的伦理法则。土地就像奥德修斯的女奴一样,被人们视为财产。人和土地的关系仍然遵照经济法则,人们对土地只要求特权,而无需尽任何义务。”[6]196利奥波德认为,这导致人们滥用土地,不利于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因此他提出,我们不能只考虑人类权利而忽视自身义务;不能只对土地拥有权利而没有义务;应将人类的义务范围拓展至动物、植物和土壤,“应该确认植物、动物、水和土壤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6]197。“自然环境保护的含义是人与土地的和谐共存”[6]200,因此,人类有义务尊重和保护地球上的植物、动物、土壤、空气和水。
利奥波德还采用了生态学理论、整体主义哲学观和达尔文进化论作为他的伦理思想来源。他认为,伦理规范的扩展也是一个生态进化的过程;他指出,人类伦理处于不断进化之中,最原始的道德关系起源于家庭成员之间,后来合作关系逐渐扩展,脉络为:家庭—氏族—部落—公民社会—土地共同体。所以,“把伦理规范扩展到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中,在进化上是可能的,在生态上是必要的”[6]197。他还指出,“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伦理规范是限制生存竞争中的行动自由的标准”[6]196,这源于“相互依存的个体或群体进行合作的态势,生物学家称之为共生现象”[6]196。“迄今为止,所有的伦理规则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那就是个人属于群体,群体中的成员则相互依存。”[6]197正是基于生态学、整体主义哲学以及进化论的理解,利奥波德论述了个体和整体的关系:是整体决定了个体,而不是个体决定整体。他的革命性思想——生态整体主义由此诞生,从此在伦理思想史中驻足并日渐彰显其影响。不但在西方掀起了一场伦理思想的革命,现代的生态中心论和环境整体主义哲学更是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
利奥波德土地伦理的核心概念“土地共同体”,来源于生态学的基本概念生物群落、生态系统。在利奥波德眼中,“土地共同体”当然不仅仅指土壤表层,还包括土壤之上以及土壤之中的所有事物,如土壤、空气、水、气候、动植物、人类等[6]157。与生态系统一样,土地共同体也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是一个平衡有机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就像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组织一样,相互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6]158;“如果有机体整体能健康运转的话,就意味着它的各个部分也运转良好”[6]160;“其整体的稳定性表明,这是个高度复杂而有组织的结构,其运作依赖于各个部分的互相合作与竞争”[6]207。总之,土地共同体就是以无数的依赖关系,以及长期的稳定性和整体性为特征的。一棵橡树死了,但其他物种因为“消费”了它而获益;一只鹿被吃了,但其能量永远在系统中循环。
在土地共同体之中,个体只是共同体的构成成员,共同体对于个体才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必须保护共同体的善。利奥波德指出,对土地伦理而言,判断行为对错的伦理标准就是:“如果有利于土地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误的。”[6]216“完整”是指共同体之完整无缺,包括了生物的多样性与完整性;“稳定”是指共同体功能发挥之有序性、稳定性;“美丽”主要指共同体生态之美。
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考虑,利奥波德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像大山一样思考,即要尽量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在利奥波德看来,人类不再是自然界的征服与统治者。“我们对土地负有义务,这些义务超越了、也高于那些受自利原则支配的义务,这些义务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之上,人与大自然的其他构成者在生态上是平等的。”[6]103利奥波德指出,“从生态学对历史的诠释来看,人类只是生物群中的一员”;他还运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行说明:“自从达尔文让我们瞥见物种起源的一角以来,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知道了以前各代旅人都不知道的事,即在进化的过程中,人类和其他生物是平等的同路者”[6]97。利奥波德在《沙郡年记》中描绘出一幅幅健康和谐的人与土地共处的画面,就是要把人类这个以征服者、统治者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土地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这意味着人类与非人类具有了平等的地位。从这个角度而言,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开创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冲破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藩篱,具有革命性意义。
二
《沙郡年记》是利奥波德的工作日记和随笔,它多以故事性、叙事性方式来描述万物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妙图景。不过由于全书较少采用学术性语言,导致其土地伦理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和质疑。
(一)义务论困境。当出现多种义务时,人们该如何选择?当各种义务发生冲突时,该维护谁的利益?这是利奥波德土地伦理陷入的义务论困境。
在自然界中生存了若干年的人类,始终未离开过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利奥波德并不反对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只是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很可能破坏生物栖息地,危及其他生物的生存,如果出现该怎么办?如何权衡?比尔·肖(Bill Shall)指出,土地伦理不可能阻止改变、管理或使用作为资源的大地,利奥波德实际上也承认这一点,并且承认土地共同体中的不同组成部分处于相互竞争中——“一方面,他(利奥波德)无疑好像认为生物共同体的完整是土地伦理的基本关怀。然而,他也承认生物共同体的不同组成部分处于相互竞争中”[7]194,但是,对于如何能成功地裁夺土地共同体领域中各种竞争性的利益,同时又能成功地坚持支配土地伦理的义务论范式,利奥波德却未能给予回答[8]137-142。比尔·肖因此质疑土地伦理:“当猫头鹰的栖息地对人类共同体有经济价值时——当需要古老的森林建造温暖的房屋,让我们的伐木工有工作时——猫头鹰的情况会怎么样?受土地伦理鼓舞的人应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这种伦理学是否内含某种优先权会证明牺牲物种(首先是栖息地,然后是猫头鹰)在纽约、加利福尼亚或德克萨斯州再开发一大片住房是正当的?”[7]97土地伦理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它并未将人类价值放于优先位置,人类和其他自然物处于平等的位置上,这就更容易出现人类的利益与其他存在物的利益相互冲突却难以解决的困境[9]127-131。利奥波德自己也多次指出:即使是生物学家,对于究竟怎样才能保护共同体的整体性和稳定性问题,也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
(二)自然主义谬误。自然主义谬误在于抹杀了“是”与“应当”之间的区别,直接从“是”推出了“应当”。利奥波德土地伦理中的著名判断——如果有利于土地共同体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无疑陷入了自然主义谬误。为什么有利于土地共同体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就是对的呢?为什么要将有机整体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作为评价标准呢?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生态学事实来论证利奥波德的判断,但实际上不管采用有机模型、群落模型还是能量模型,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10]188-195。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个达到规范性结论的基础,然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解释学又对此提出了强烈的质疑——生态系统并不总是保持稳定性,它总是在进化之中。众所周知,生态系统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在某区域和短时间内可能是对的,但对别的区域或在较长的时间内就不见得正确了。另外,土地伦理并不适用于功利主义和个体论,我们无法用功利主义和个体论来进行解读,因此我们必须认为土地共同体是有其目的论目标的,然而地球的目的何在?生态群落的目的何在?质疑之中,目的论模型彻底崩塌。总之,生态学事实本身不能“证明”土地共同体的完整、稳定与美丽是有价值的。
利奥波德认为,对土地的爱、尊敬与尊重或许是“是”与“应当”之间的桥梁。“我在此坦言,如果没有对土地的热爱、敬畏与赞赏,或者不能高度重视土地的价值,那么人和土地间的伦理关系就不可能存在。当然,我所说的价值远比单纯的经济价值更广,我指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6]]215利奥波德指出,只有当人们转变对土地的态度,才会做出有利于土地共同体的行为,并且,人类心理上的这个转变必须通过道德教育才能完成。“如果缺乏良知,义务也就毫无实际意义,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人的道德和良知运用到对土地的敬畏之中。”[6]202这就意味着,我们评价生态系统是因为我们爱它、尊敬它,而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善。
土地伦理把完整、稳定与美丽赋予大地、赋予生态系统的事实和有意义的基础,但“这些事实如何与价值性结论相联系仍是个问题。”[9]127-131学者多恩·玛丽塔也指出,如果把土地共同体或者说生态群落的完整、稳定与美丽作为判断行为正确与否的唯一重要理由,肯定是不恰当的;尤其是仅仅将人当做生物性角色是不对的,人类在自然界中不仅仅只是拥有生物性角色。
(三)整体主义困境。利奥波德整体主义强调关系先于实体,强调整体对于个体的功能与作用,为了保护共同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为了生态系统的善而牺牲个体的权利,因此遭到强烈的反驳与抵制。卢风指出:“个体成员的生命权与生命共同体的结构是不相容的,所以,土地伦理不授予个体以生命权”[1]43-62。克尔认为“土地伦理的整体主义是专制主义”[11]127-131。克兹则指责整体主义削弱了个体的内在价值[12]241-256。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汤姆·里根的批评:“土地伦理强调整体或生命共同体,否定或抹煞了个体的道德权利,所以,土地伦理被贴上环境法西斯主义的标签是很恰当的,而且任何试图调解二者的企图终将失败,因为环境法西斯主义与(动物)权利的观点就像油与水一样是无法混合的。”[13]362
三
为了解决土地伦理的理论困境,许多学者如玛丽塔、赫夫勒、莫林、克里考特等都积极提出解决方案,并为生态整体主义作阐释与辩护,推动了土地伦理的发展与完善。其中克里考特最具代表性。作为土地伦理坚实的捍卫与继承者,他对利奥波德的理论进行了最为深入、全面的辩护与发展,被誉为“土地伦理在当代的代言人”[14]116-124。
针对义务论困境,克里考特提出两条二阶原则以解决道德责任的优先性问题。原则1:在更古老、亲近的共同体中的责任重于晚近出现的无人格共同体中的责任。此原则“要求行为者优先考虑更值得尊敬、更亲密的共同体成员的利益”。例如,每个人的家庭责任重于社会责任。原则2:源自较强利益的责任重于源自较弱利益的责任[15]76。此原则要求“行为者优先考虑处于争论中的较强利益”。例如,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有权优先照顾自己的孩子,但是,如果你孩子要求满足的是奢侈愿望,而你邻居的孩子正遭受冻馁之苦,则此时,你满足邻居孩子基本需要的责任重于满足你自己孩子奢侈愿望的责任。
很明显,两个二阶原则给出了具体情境下德性(责任)的优先顺序。克里考特认为,按照二阶原则,人们可以通过对具体情境的分析来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以保护花斑猫头鹰为例进行分析。限制伐木就意味着有伐木工人失业,根据原则1,我们的同胞跟我们的关系比猫头鹰跟我们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应该反对限制伐木;但根据原则2和猫头鹰正面临绝种危险的事实,我们应该赞成限制伐木,而伐木工人失业的损失可以通过经济措施进行补偿。很明显,运用克里考特的二阶原则很好地解决了义务论困境。卢风指出,克里考特预设了自然与文化的区分,要求在人类文化共同体内部采用人权原则,在土地共同体内部运用土地伦理标准,因此,二阶原则能很清楚地指导我们,“当保护人权与保护生物个体发生冲突时,优先保护人权,但当保护生态系统与满足人们的奢侈欲望发生冲突时,优先保护生态系统。”[1]43-62
对于自然主义谬误,克里考特诉诸于达尔文—休谟情感社群主义伦理传统加以解决。休谟告诉我们,对于谋杀,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不赞成”,这种最真实的情感就是“同情心”。达尔文认为,父母与后代之间感情与同情的联系就是社会情操,它可以以家庭为起点进行扩散,最终扩散至整个种群。那么,依达尔文—休谟伦理传统,人类具有同情心,这种对他人的同情心即为伦理的起源,这种情感可以从个体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克里考特提出了一个同心圆模型,认为我们的感情首先是对自我,然后是家庭,之后逐渐扩展至更广大的群落[15]228。这样,联系事实和价值的桥梁——道德情操(同情心)得以建立,并从个体扩展至社会范围,世界的事实和来自有关我们的事实成为“应当”的来源,从事实判断合理推出了价值判断,自然主义谬误得到解决。克里考特说:“这是由‘是—陈述’到‘应该—陈述’的完全合法的推导。这或许不是严格逻辑意义上的演绎,但即使根据休谟自己的标准,也算是令人信服的实践论证。”[16]121也有学者认为,克里考特在他的阐释中,其实消解了事实与价值的截然二分,这样“不仅为土地伦理的论证提供了条件,也瓦解了现代伦理学的基础”[1]43-62。
作为整体主义环境哲学最杰出的代表,克里考特都是从整体主义视角出发对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进行捍卫与发展的,同心圆模型和二阶原则的提出便是例证。同心圆模型是克里考特辩护的理论模型,并为生态整体主义的深入探讨奠定了基础,而二阶原则则是他为整体主义辩护的实践标准。这个实践标准消解了极端的个体主义和极端的整体主义,化解了一般意义上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矛盾与冲突,个体不再总是“牺牲自我而贡献于整体之善”。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按照此二阶原则,既可以保护个体主义的人权,又可以保护整体主义的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既坚持了生态整体主义,又避免了环境法西斯主义。
正是克里考特对利奥波德土地伦理的辩护,使得生态整体主义越来越被重视与接受。戴斯·贾丁斯指出:“首先,整体主义伦理是在进行资源管理决策时最可行的方法。其次,生态学中认识论上的整体主义已暗示了整体主义伦理。最后,整体主义伦理承认生态总体的形而上学现实。”[11]215可以说,在目前自由个体主义任意扩张的形势之下,生态整体主义为环境问题打开了伦理探索的一个新维度。
[1]卢风.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对现代性的挑战[J].中国社会科学,2012(9).
[2]吴玑超.大地伦理学的理论建构[J].西安社会科学,2010(2).
[3] Leopold,A.A Sand County Almanac[M].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1949.
[4][美]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M].杨通进,译.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5] Mallory,C.Acts of Objectification and the Repudiation of Dominance[J].Ethics &The Environment,2001(6).
[6][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郡年记[M].王铁铭,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7] Bill Show.A Virtue Ethics Approach to Aldo Leopolds Land Ethics [A].Ronald D Sandler,Philip Cafaro.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C].Lanham MD:Rowman&Littlefiled Publishers,2005.
[8]王希艳.美德伦理学视角下的“大地伦理”[J].道德与文明,2012(6).
[9]董玲.大地伦理是环境法西斯主义吗?——克里考特的类型学分析与论证[J].伦理学研究,2010(4).
[10][美]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M].林官明,杨爱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1] Kheel.M.The Liberation of Nature:A Circular Affair[J].Environmental ethics,1985.summer.
[12] Organism.E.K.Community and the Substitution Problem[J].Environmental Ethics,1985(7).
[13]Regan,T.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14]包庆德,夏承伯.土地伦理: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先声——奥尔多·利奥波德及其环境伦理思想评介[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5).
[15]Callicot,J.B.Beyond the Land Ethic: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
[16]Callicott,J.B.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A].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C].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
责任编辑:饶娣清
Aldo Leopold’s Land Ethic and Its Theoretical Dilemma
JIAN Xiao-xuan
(InstituteofS&TPhilosophyandS&TPolicy,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06,China)
Leopold’s land ethic,which inaugurated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of ecological holism and non-human centralism,has exerted profound influences, but it is in the dilemmas of deontological theory,naturalism and holism, and criticized and challenged by some scholars.As a deontological theory, it does not give priority to humaninterests, which leads to the dilemma of being difficult to make decisions when there are many obligations.As the naturalism, it deduces “should be” from “be” directly and igno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As the holism, it is considered by some scholars as “environmental fascism” since it places the good of the community above the right and freedom of individuals.Th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holism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Baird Callicott debated and developed Leopold’s theory and proposed the concentric zone model and second-order principles, which to some extent solved the theoretical dilemma of land ethic.Leopold’s ecological holism opens a new dimension of ethic exploration fo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ldo Leopold; land ethic; ecological holism
2016-06-12
简小烜(1976-),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科技哲学与科技政策研究所博士生,长沙大学思政课部副教授。
B82-058
A
1001-5981(2016)05-014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