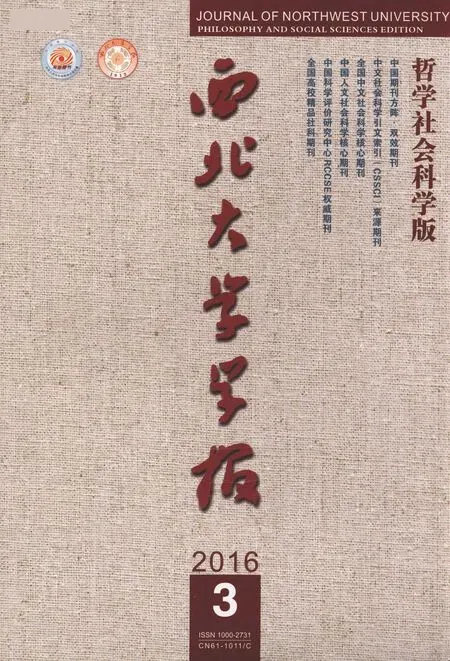弗兰克·莫莱蒂的三重文学空间观
陈晓辉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文学研究】
弗兰克·莫莱蒂的三重文学空间观
陈晓辉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069)
摘要:弗兰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称自己是“地图制造者”。他绘制文学地图,认为地理形塑文学的情节、叙事风格和结构。在地理因素的影响下,文学内部形成乡村空间、城镇空间和国家空间。乡村空间是自足的、诗意的空间,人们拥有自由的身体;城镇空间是半开放的、过渡的空间,联系着乡村和未知世界,人们拥有半自由的身体;国家空间是开放的空间,是各种因素的镶嵌和拼贴,人们只拥有压抑的身体。莫莱蒂的三重文学空间观充斥着意识形态性,凸显了现代性危机。
关键词:莫莱蒂;文学空间;乡村空间;城镇空间;国家空间;现代性危机
弗兰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是当代著名的意大利文学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在欧美学界声名鹊起,影响斐然。但截至目前,国内还没有人研究过他的文学空间观。莫莱蒂的文学空间观立足于坚实的文学地理学基础,然在研究方法上却与常见的利用地形地貌、气候生态等自然因素研究文学者有异。莫莱蒂以自己绘制的文学地图*仅在《欧洲文学图集》一书中,莫莱蒂就绘制了91幅文学地图,用以说明并论证文学作品所塑造的空间形式、地理因素对文学空间的影响等问题。读者若有兴趣,可参见本书原文。作为研究工具,相信“地图是(各部分)精确的、有形的联系——将允许我们洞悉一些迄今已避开我们的意味深长的关系”[1](P3)。在他看来,地图联结文学与地理,能够揭示易被忽视或易被遮蔽的更深层次的空间问题。
莫莱蒂称自己是“地图制造者”。他清楚地知道,和地理学家绘制真实环境的空间地图相异,文学地图是文学研究者绘制的虚构世界的地图。虚构世界的地图和真实世界的地图构成文本呈现的两个不同空间。虽然真实地理空间和虚构地理空间并不完全对称,但在地图中,“真实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经常以难以理解的比例共存”[2](P63),因此通过绘制文学地图,不但可以在文学与地理之间建立联系,而且可以展现地图对文学及其叙事的形塑过程。莫莱蒂以欧洲为例,绘制了小说的地图,不仅揭示了地图对情节、叙事结构和风格的影响,而且利用地图构建了乡村、城镇和大都市三重不同的文学空间。
一
社会文化学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与空间联系密切,空间是文化存续的重要载体。“文化空间”就是公众参与的、相对固定的、用于文化交流和交往的公共场所[3]。迈克·克朗(Mike Crang)认为文学与地理之间存在一种双向作用关系,文学本身有地理学的属性,不仅文学世界就是由位置和背景、场所与边界、视野与视域组成,而且“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塑造这些地理景观”[4](P55)。与此不同,莫莱蒂只强调地理对文学的影响。地理是叙事形式的基础,地理因素会影响文学叙事,什么样的地理会塑造什么样的文学叙事形式。因为具体的故事要发生在具体的空间,并且在文学中“不同的形式居于不同空间,……每一个类型都拥有自己的空间,每一个空间也都拥有自己的类型”[1](P34-5)。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莫莱蒂博采众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地理观。莫莱蒂说:“先前读过的布罗代尔(Braudel)的作品影响了该书源起。例如,克里斯汀·萝丝 (Kristin Ross)关于兰波(Rimbaud)的著作《社会空间的浮现》,它反映了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或者弗里德里希·詹姆逊,他总是从空间的视角‘观照’文化——受日本小说影响……受佩里·安德森《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影响:在第一页描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学术领域时,我忽然明白怎样用地理学解释文化史。”[1](P9)细究之,布罗代尔对法国历史空间化的研究使莫莱蒂产生了绘制文学地图的念头,萝丝提醒他能在文学与地理之间产生联系,詹姆逊使其从空间角度思考文学类型的增殖与缩减,安德森则让莫莱蒂的文学空间阐释充满意识形态性。这样,莫莱蒂逐渐通过绘制文学地图,在文学与地理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并以此为据分析地理对文学情节、风格、结构的形塑功能。
通过文学地图,莫莱蒂发现地理因素可以影响情节的发展。莫莱蒂说:“作为民族-国家的象征性形式,小说有一种功能,它不仅不消除民族内部的分离,而且还设法使其转变为一个故事。”[1](P20)众所周知,情节是由人物及其言行构成的事件序列,莫莱蒂认为人物的言行由其所在的地理因素决定。在情感小说中,他以简·奥斯汀对英格兰婚姻市场的描述为例,发现她在小说中建构了一个中等规模的世界。这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的中介空间,其中的人物都有越过这一具体、相对空间,向以伦敦为中心形成的中心区域移动的倾向,特别是妇女,在肉体和精神上出现双重移动,因而地理上呈现出集中化倾向。与情感小说相反,历史小说有一个远离中心、穿越边界的倾向,“它为19世纪的欧洲提供了一个边界现象学”[1](P35)。莫莱蒂从普希金《上尉的女儿》、司各特《威弗利》、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等作品中主人公的行动看到,历史小说中有外部边界和内部边界。外部边界存在于国与国之间,它经常是人物冒险的地点,人物穿过边界线,面对未知的敌人,二者在相反的领域发生冲突。故事因而进入一个危险、惊奇、猜疑的空间;内部边界存在于既定国家内部,它是一个可见的空间,不仅是一个政治军事界限,也是一个人类学的边界。人物往往因为好奇、爱情等无意识的原因而背叛,他一方面因参加另一个团体而突破邻近的边界,进入一个新空间,另一方面因为参加不同团体而体现出时间上的次序,人物突破邻近边界的行为变成在空间中阅读时间的方式,使“内在边界成为历史小说的开关”[1](P38)。最终,历史小说的故事变成人物的民族归属感和本地归属感之间的内斗。而在殖民地小说中,人物也出现向英国之外去寻找财富的地理迁移,因而造成小说情节中更多的有关殖民地与宗主国差异、矛盾的叙述。莫莱蒂通过分析情感小说、历史小说和殖民地小说中人物的地理位移和越界趋势,使我们看到小说中地理空间的分布差异如何在不同的小说类型中形成有别的情节。
莫莱蒂认为地理不但影响小说情节,也影响小说的叙事风格。风格是文学作品呈现出的独特的、持续的、整体性的特征。莫莱蒂在历史小说中发现,在邻近地理边界的位置,小说叙事的喻形性(figurality)*根据莫莱蒂的解释,此处的“喻形性”从修辞角度讲,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复杂性”,See Moretti, Franco. Signs Taken For Wonder: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ry Forms[M].New York: Verso,1988.P.270.会急剧增加,人物也大多分布在此,这会导致不同叙事风格的出现,所以莫莱蒂说:“具体的地理位置决定风格的选择。空间作用于风格,它会从19世纪普通的、‘严肃的’‘现实主义的’风格登记簿中产生一种双重背离(朝向悲剧或喜剧,朝向‘高’或‘低’)。”[1](P43)此刻,地理和修辞相互纠缠,修辞依赖于地理空间。因为社会是一个语言空间系统,常常被迫对外开放,“国家建构需要清除物理障碍,不可逆转地减少行话和方言,使之形成单一的民族语言的洪流”[1](P45)。基于地理因素而形成的民族语言使小说的叙事修辞透露出明显的地域文化色彩。19世纪小说叙事风格就是在地理因素的左右下而形成的这样一个消减和集中化的过程。在此意义上,莫莱蒂认为小说是民族国家的象征性形式。
除了影响小说的情节和叙事风格,莫莱蒂通过绘制文学地图,认定“地理形成了欧洲小说的叙事结构”[1](P8)。通常,叙事结构被认为是小说的情节和叙事风格得以呈现的框架结构。莫莱蒂写道:“因为风格事实上与空间相关,空间又与情节相关,所以从普罗普到洛特曼,空间边界的穿越通常也是叙事结构的决定性事件。比喻、空间和情节之间是一种三角关系。”[1](P46)莫莱蒂专门列举了道路在流浪汉小说中的作用。非常有趣的是,莫莱蒂从桑丘·潘萨的骡子身上发现端倪。在《堂吉诃德》中,伴随桑丘环游的是一匹骡子,而骡子能够成为出行的伴侣是因为陆路交通的发达。随着大量道路的出现,“欧洲小说叙事永远地改变了”[1](P48)。这是因为小说叙事的重心已从海洋转向陆地,小说的叙事内容已从开放性的海洋冒险转向琐碎的、乏味的日常生活,因此小说的叙事结构也发生转变。小说的叙事结构逐渐分叉,长篇小说和短小故事也都形成相对固定的叙事结构,分别构成稳定的线性叙事模式和特殊的环形叙事模式。
二
如上所述,情节、风格、叙事结构的变化都受地理因素的影响,进而引起文学空间的变化。莫莱蒂发现欧洲文学地理中存在乡村空间、城镇空间和大都市空间,而且这三种文学空间呈现了一个从乡村空间到城镇空间,再到大都市空间逐渐进化的过程。
在为玛丽·米特福德(Mary Mitford)的村庄故事绘制文学地图后,莫莱蒂发现米特福德勾画出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学的乡村空间。这个村庄坐落于伯克郡,距雷丁市十二英里,方圆三英里,是一个只有二三百人的小村庄,人们在此以亲缘关系形成统一的群体。在乡村空间中,村民们以自己所居的村庄作为核心,劳作、休闲,安排一切日常生活。村庄既是他们的工作场所,也是他们的休闲场所。特别是在闲暇时候,村民们会“乡村散步”(the country walk)。他们从村庄的任何方向向外游走,在欣赏沿途如画般的美景之后再返回到村庄,显示出自给自足生活的舒心与惬意。乡村空间是一个“有限的地理范围,满足人的日常需要,只具备基本的服务功能”[2](P49)。
在为这个村庄绘制文学地图后,莫莱蒂发现叙事空间在此不再是线形的,而是环形的。小说形成环形的叙事模式和地理系统,地图独一无二地呈现出了乡村叙事的环形模式。这是“由于《我们的村庄》中的叙述者自由移动,像雏菊的花瓣一样,均匀地向四周传播,一个环形的模式就此建构”[2](P38)。在莫莱蒂看来,这种环形空间意味着一个自足性空间,“一个圆环是简单的、‘自然的’形式,它对接近‘微观世界’中心的每一个节点都极为重视,同时封存那些存在于广阔的宇宙周界之外的形式”[1](P44)。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相对封闭的空间,但这是一个人们熟悉的空间或熟悉人们的、没有裂缝的整体性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的人们拥有一个自由的肉身。在我们看来,莫莱蒂所勾画的这种村庄叙事模式将村庄本身变为叙述的核心。叙事者的视角发生转变,他以村庄为中心叙事,形成新的时空体,建构了新的叙事空间。村庄叙事改变了小说的叙事结构。通过这种改变,小说建构了一个别致的乡村空间。这个空间是一个没有被现代化所浸染,如画的、诗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们的生活是简单的,世界是可知的,内心是纯净的,身体是开放的,生命是自由的,精神是愉悦的。在莫莱蒂的论述中,乡村空间是文学作品以牧歌式的方式给我们创造的一方人类生活的净土,为我们的精神还乡提供了便利。这正是为乡村故事用环形模式来组织结构的缘由。
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乡村逐渐被侵犯和挤压,文学作品中所刻画的乡村空间也逐渐被城镇空间所代替。1820年代约翰·高尔特(John Galt)的《教区年鉴》(1821)是这种城镇空间的代表作品。莫莱蒂认为城镇空间一头联系着乡村,另一头联系着大都市等外部空间,它是一个低都市化的空间。在这种空间中有两条线索,一条是由鞋匠、铁匠、木匠和泥瓦匠等普通人物和出生、劳作、爱、婚约、死亡等人生最基本的生活过程组成,仍然体现着乡村空间中恬静、质朴和单纯的日常生活,但另一条则由法国教师、帽商、时尚的裁缝,赛马、椰子、咖啡等许多新奇事物组成,隐含着地方与许多大城市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长距离商品贸易,一系列不可知的、充满魅惑的外部世界和富有趣味的新鲜生活。城镇空间是一个联系着“家乡”和“世界”的中介空间,也是一个半熟悉的空间。城镇空间为惠及尽可能多的顾客而坐落于城市的中心,为人们提供专门化的服务。“服务越专门化,城市也就越‘中心化’。”[2](P44)银行业、行政机构、教堂、学校、剧院、专业的和商业的组织,市政设施一应俱全,教师、律师、邮差、医生等分工明确。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基本功能,都能有效提供相应服务。但是如果有人需要这样的服务,就必须按照这个部门的空间位置去寻找、接受它相关条规的约束和限制。在此,人们只拥有半自由的身体,不能像在乡村空间中那样随心所欲地生活。而且在这个空间中,本地与外界建立起强大的商业网络,出现了民族市场,“每周都有人穿过它的中间地带,要么就是每天都有合格的新鲜事物——书籍、报纸、政治活动(所有的都是复数的)——它将保持着多样化的情态贯穿整个工业化的19世纪”[2](P49)。如果人们再将目光投向日常生活,就会发现那已不再是一个熟悉的空间,而是一个不可通约的世界,充满了诱惑和危险。我以为,莫莱蒂的城镇空间是一个过渡性的、半开放的空间,这个地方的人们拥有的是半自由的身体,他们一方面既可以回归田园生活,介入乡村的诗意空间,又可以跨入外部世界,进入都市空间,另一方面既可以享受乡村空间带来的自由和愉悦,又要受到一定城市分布和劳动分工的掣肘。
在以上两个空间之外,莫莱蒂还分析了第三个空间,即大都市空间或国家空间。伯特赫尔德·奥尔巴赫(Berthold Auerbach)写于1843到1845年之间的《黑森林里的乡村故事》最具代表性。随着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继续深入,世界各地形成了大量的大城市或超大城市,如伦敦、巴黎、彼得堡、米兰、马德里、罗马等等。相对于乡村空间和城镇空间而言,这些大都市空间“的确是另一个世界”[1](P64),代表了国家的权力意志,在文学作品中表现独特。莫莱蒂认为在城市空间中,居住的群体、形成的文化氛围以及城市的功能,均独树一帜。一般来讲,老年人在乡村,年轻人在城市,城市化貌似主要为年轻人而设。城市里到处都是年轻人,而且没有代代相连的亲缘关系和固定的居住场所。他们是陌生人,不过居于一个流动性很大的空间罢了,因而城市空间还是一个陌生人的空间。与此同时,由于住满了年轻人,城市空间不再是低调、平稳、朴实的农业劳动场所,而是充满猎奇、冒险、投机的工业劳动空间。城市之间的差异也“不再是文明程度的不同,而是时尚的差异。这种伟大的大都市观念专为年轻人设计”[1](P65)。它充满了开放性,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机会与更大的限制,机会与限制的碰撞,造成城市内部空间的不同划分。一个城市空间的内部还可以分成不同的部分,贫穷的伦敦、富裕的伦敦、工人阶级的伦敦和资产阶级的伦敦,完整空间成为部分空间的镶嵌和拼贴,如“伦敦不仅变成一个大城市,而且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城市,允许更丰富、更不可预期的交互作用”[1](P86)。莫莱蒂在对巴尔扎克的巴黎和狄更斯的伦敦进行分析后发现,一方面都市空间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的生产、消费能力的开放性空间,充斥着制造业、银行业和服务业,并把它们的触角肆无忌惮地伸向乡村,影响乡村生活,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准国家空间,布满法庭、监狱、军营等类似机构,强化着对城市的统治。在城市中,“一个获得合法的暴力垄断的残酷决断将放逐整个地区的传统,违背人民的意愿而转移他们,如果他们逃跑,就将他们送上法庭,审判他们……”[2](P51)笔者认为,与前两个空间相比,莫莱蒂的城市空间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但也是一个压抑的空间。人们在其中并不自由,仅有被压抑的身体。
三
1945年约瑟夫·弗兰克(Josef Frank)针对《包法利夫人》中的“农业展览会”场景首次提出小说空间形式的问题,他认为小说中的时间流被终止,不同场景并置,需要读者反复阅读并对不连续的片断、瞬间意象整合后才能整体把握小说的意义[5](P3-4)。弗兰克立足小说本身的空间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引发了一场由米切尔、瑞恩、米克尔金、拉布森、凯斯特纳、佐伦等理论家参与的学术讨论,使文学空间研究成为一时显学。然而,这些人的研究一直立足于文学的空间叙事技巧和文本呈现出的空间样态,未能思索造成这种空间化现象的原因,也未能追究小说形式之外的变化与小说空间化之间的关系。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认为空间并非填充物体的容器,而是人类意识的居所。巴什拉说:“即使‘形式’已经在‘约定俗成’中被认识,被感知,被塑造,在受诗的内部光线照亮以前它只不过是精神的单纯对象。而灵魂将会开创形式,居于其中,怡然自得。”[6](P8)这种空间实指的是人类的精神空间。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与巴什拉相似,认为文学的空间正在于“语言的完成与语言的消失的偶合之点上”,它“设法把作品变成通往灵感的路”[7](P26,190)。人们只有在对语言所提供的路径的体验中把握文学空间。在布朗肖那儿,文学空间也是作者、读者的精神体验。这种文学空间研究立足文学文本和人类的精神,是一种文学化、艺术化的空间研究。如果以此类比莫莱蒂的文学空间研究,他显然不属这一阵营。扬弃福柯、列斐伏尔、哈维、索雅、迈克·克朗等人的空间思想,莫莱蒂关注文学与外部空间的关系,重视空间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关联。莫莱蒂相信文学形式是具体社会关系的抽象表征,它背后隐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意识形态力量的对抗与妥协。莫莱蒂文学空间理论的复杂之处在于,他的研究既建基于文学本体之上,但又不是纯文学或纯审美批评,而是一种社会批评,內斥明确的意识形态性。
在文学空间研究中,莫莱蒂通过绘制地图,建构了一个由乡村空间、小城镇空间和大都市空间组成的文学整体性空间。从莫莱蒂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虽然从表面看来是地理因素影响了文学空间的构成,但实则地理的变化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故而从根本上说是意识形态影响了文学空间的形成。在莫莱蒂的观念中,地理永远都具有社会性,它和经济、政治,甚至文化霸权密切相关,因此莫莱蒂的文学空间是一个聚集了地理空间、艺术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综合体。不过这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空间,在不断地对话和斗争中演变发展。
在莫莱蒂的论述中,乡村空间主要展现的是一种“闲暇空间”,而非“劳动空间”。人们在乡村中的诗意散步展现的正是他们的闲暇生活而非日常生活或劳动生活。“闲暇生活”的抒写遮蔽了他们劳作之艰辛、生活之悲伤。乡村那种完美而诗意的空间感是由如画的、已通过艺术化处理而完全美化的自然景观所塑造出来的。小说的“每一页都充满了装饰性,在那儿小心翼翼地精确描述了超过二十种的花和树”[2](P39)。而这种塑造的愿望恰巧是工业化愈加严重,乡村空间被严重挤压和破坏之后,读者,特别是城市读者对它行将消逝的一种挽歌式的哀悼,饱含了浓浓的乡愁和哀伤。同时,这种如画的乡村空间看似一种自身的满足,但其实也是对人类被现代工业和新兴科技高度异化后灵魂无所归依时的历史回望,承载着众多的精神期冀和修复创伤的热望。“乡村反过来成为现代都市的一个象征性的乡愁之所。”[8](P21)貌似独立的乡村空间,实际和它背后影响其形成的意识形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它的叙事圆环的“不是精神状态,而是意识形态”[2](P42)。
城镇空间联系着乡村和城市,家乡和世界。在迈克·克朗的眼中,地理中的家乡也“表现了社会意识形态,而且社会意识形态是通过地理景观得以保存和巩固”[4](P55)。城镇空间力图坚守乡村的淳朴和单纯,但在高速发达的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的商贸网络和民族市场,日趋细化的劳动分工和专门服务,更加稳固的资本帝国和城市化的蚕食下,它的地方归属感逐渐被民族国家的归属感所挤压,固守乡村空间的愿望逐渐消退。在历史的洪流中,它一边唱着不愿离去的悲伤歌谣,一边又义无反顾地进入城市空间,成为城市网络中为数众多却又不可或缺的珠点。
以巴黎和伦敦为代表的大都市的出现,本身就是英法工业革命、经济发展和殖民扩张的产物,所以城市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极其密切。文学建构的大都市空间是一个准国家空间,显示的既是劳动的场所,又是功能齐全、相互关联的意识形态地图。大都市空间内存各种各样的政治机构,规约着人们的行为和生活。在这种准国家空间中,“国家等同压抑”[2](P51),空间等同压抑的空间。文学作品中城市空间的出现,意味着乡村空间的没落。当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之后,就形成地方归属感和国家归属感之间的矛盾。“故乡反对国家”,[2](P51)本地的归属感朝向一个古老的、微小的乡村空间,顽固地抵抗其整体进入城市空间。“乡村缓慢、寂静的整体性生活,同城市生活的碎片一样的瞬息万变形成对照。”[8](P19)即使在城市内部,城市空间的不同分隔,体现的是不同群体、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表面是经济利益驱动、资本运作的结果,实则是受政治权力的影响。莫莱蒂写道,如果说“米特福德的圆环是村庄的引力推动其正在漫步的叙事者的结果;巴尔扎克分裂的巴黎是老贵族和雄心勃勃而又小气的资产阶级青年战争的场所”[2](P57),到处充斥着意识形态的魅影。
四
虽然莫莱蒂的三种文学地理空间各自不同,但其内在的机理却别无二致地凝聚于现代性,体现了现代性的危机。莫莱蒂的三重文学空间是多元的、开放的、互文性的建构,在相互的映射中揭示了莫莱蒂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意识形态特征。莫莱蒂本想将文学本体研究和关系研究结合起来,但在具体论证过程中,因其确信文学形式是社会关系的抽象表达,内含各种类似或敌对的力量,从文学形式中可以解读隐藏其后的真实意义这一观念,因而逐渐忽视了以文学的方式研究文学本体,使研究变成单向度的关系研究,二者结合的理想自然落空。在莫莱蒂那里,给文学绘制地图并非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心,解读地图中潜藏的各种地理因素之间的关系才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莫莱蒂说:“和地图在它们中间显现出的关系相较,位置本身似乎不能被看做是有意义的。位置之间的关系比位置本身更有意义。”[2](P55)这也是地理学和文学对地图这一研究工具的不同要求。地图并非研究的结果,而是起点。从地图中揭橥所涉诸要素间的相互关系才是莫莱蒂绘制地图的根本目的。地图呈现的内部和外部力量,一方面改变了文学的叙事结构,另一方面重塑了人物的性格和小说的主题。莫莱蒂认识到,正是利用地图,我们“从乡村的阶级斗争,工业腾飞,‘转变’了19世纪田园牧歌形状的民族构型过程中领略了各种各样的趋势”[2](P64),从而抵达对文学地理空间的真实理解。换言之,正是在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的对照中,莫莱蒂才发现了文学的意识形态特征。正如蒂莫西·莫奈尔(Timothy Mennel)所说:“就其本身而论,莫莱蒂不仅想取得一个文学目录的分类法或一个有关作品精神和地图间关系的新观点,而且想建构一个社会政治的地理读本。”*Timothy Mennel,“Reviewed to Graphs, Maps,Trees: 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Theor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96,2006.其判断甚为精当。在我们看来,莫莱蒂的文学空间研究,在地理与意识形态之间建立联系,并以此类文学地理空间的构型作为各种对抗性力量的合力作用,贯彻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构想。
更为重要的是,莫莱蒂所谓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正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如果从莫莱蒂对以上三种空间的描述以及对其流变的分析来看,他的三种空间是农业社会、半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在文学作品中的对应性表征。莫莱蒂已经看到,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剧,人类的生存空间愈加狭隘和恶劣,从乡村、城镇,再到大都市的文学空间转变,正是这一社会环境恶化现象的真实反映。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世界充满了张力和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现代性危机的具体表现。波德莱尔坦言:“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和偶然。”[9](P483)人们在这种短暂性、瞬间性和偶然性的现代社会中,一方面饱尝现代生活的便利和美好,但另一方面则无所适从、孤独和迷失。现代性内部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莫莱蒂已经发现其矛盾性,而且客观地展示了这种矛盾的演化过程,并且强调了其意识形态性,但他忽略了“常有偶发因素导致重要突变”[10](P120),但他没有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这样,莫莱蒂的研究虽然不乏批判意味,但却失去了现实效用和价值立场。
参考文献:
[1] MORETTI F. Atlas of European novel:1800-1900[M].New York: Verso,1999.
[2] MORETTI F. Graphs, Maps, Trees: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M].New York: Verso,2005.
[3] 邵敏.论文化空间视界下的黄梅戏传承与保护[J].江淮论坛,2015,(3).
[4]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 约瑟夫·弗兰克等.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M].秦林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6] 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7] 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M].顾嘉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 汪民安.现代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9] 皮埃尔·波德莱尔.波德莱尔论文选[M].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0] 约瑟夫·马格利斯,谷鹏飞.后达尔文主义:一种文化与美学的新选择[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责任编辑赵琴]
Franco Moretti′s Triple Literary Concept of Space
CHEN Xiao-hui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NorthwestUniversity,Xi′an710069,China)
Abstract:Franco Moretti said he is a “maker of map”. He draws a map of the literature, which is considered as the plot, style and structure of the geograph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factors, the formation of countryside space, town space and the big city space is formed in the literature. Countryside space is a self-sufficient, poetic space where people have the freedom of the body; the town space is a semi open, transitional space, linked to the country and the unknown world where people have a semi free body; the big city space is open space, is a variety of factors and collage, people only have suppress the body. Moretti′s three literary space concept is full of ideology, and it highlights the modernity crisis.
Key words:Franco Moretti; literary space; countryside space; town space; big city space; crisis of modernity
收稿日期:2015-03-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4ZDB087);陕西省社科项目(13J040);陕西省教育厅专项资助项目(14JK17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晓辉,男,陕西千阳人,文学博士,西北大学副教授,从事文艺学与美学、创意写作理论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6-03-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