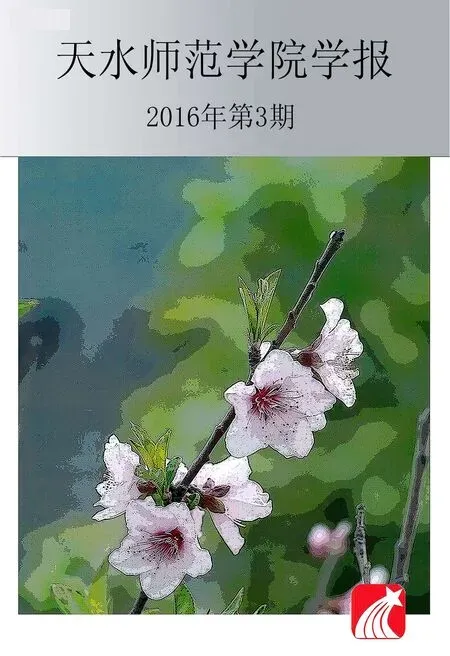《风》诗“非民歌说”平议
廖越
(天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风》诗“非民歌说”平议
廖越
(天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关于《诗经·国风》作者群体的身份判断问题,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即“民歌说”与“非民歌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非民歌说”意见的学者们重新开始了他们对“民歌说”的批判。他们通过考察《国风》诗文中所出现的器物、《国风》的文学艺术水平、先秦时代各礼仪场合中贵族赋诗言志等细节问题,认为《国风》应为贵族阶级所创作。“非民歌说”是通过对于历史的考察来证明其正确性的,但其对于先秦时代历史的认知——如先秦时人的解诗方式、平民阶层的受教育情况和生活水平等问题——却多有舛误。故此,“非民歌说”认定《国风》必定出于贵族阶级手笔的观点仍然是有待商榷的。
《诗经》;《国风》;非民歌说;平民阶级
关于《诗经·国风》究竟是否属于“民歌”范畴,古今学者们的判断并不统一,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派,即“民歌说”与“非民歌说”。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这样写道:“《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有学者认为,据此可以认定司马迁在《国风》作者争论中属于“非民歌说”一派,表明了司马迁“认为包括《国风》在内的全部《诗经》作品都是‘圣贤’所作,其作者在社会身份上属于上层统治阶级。”[1]然而,这种判断未免失之武断了。尽管我们知道,汉人治学,主张通经致用,将《诗经》三百五篇皆当做谏书看待。如《汉书·儒林传》中记载:
(王)式为昌邑王师。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乱废。昌邑群臣皆下狱诛,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以数谏减死论。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亡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归家不教授。[2]3610
既然三百五篇皆是谏书,自然应是“圣贤”所作而不属民歌了。此种观点,于一般儒生口中说出,固然可以理直气壮。只是司马迁作为一代史学巨子,又生活在儒学独尊的元、成之世以前,故而在表达这种缺乏依据的观点时仍然留有余地。其言:“《诗》三百篇”,而不言:“《风》百六十篇”;言:“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而不言:“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其间区别,可谓一目了然。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推测:司马迁之所以要将《诗经》的作者大抵归于“圣贤”,也无法排除是为了以“倜傥非常”的圣贤们为榜样,勉励自己发愤著述的缘由。身为“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的刑余之人,通过心理暗示的方式从“意有所郁结”的先贤们身上获得鼓励与安慰,又何尝不在情理之中?
到宋代,朱熹重拾早已存在于《礼记》、《公羊春秋传解诂》等古书中的“采诗”之说,在其《诗集传·序》中提出:“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3]2的观点后,“古今学者……确立了民间作者作为《诗经》中国风的创作主体的观点。”[4]进入20世纪后,在顾颉刚等人“疑古”思想的影响下,《国风》“民歌说”更加深入人心,成为19世纪《诗经》研究中的主流思想。但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对“民歌说”提出批判,坚持《国风》“非民歌说”。笔者认为,无论“民歌说”与“非民歌说”,在观点的论证上,都存在着不够严密的地方。本文仅就其中“非民歌说”的部分观点进行检查,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讨论《国风》究竟是否属于民歌的概念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对“民歌”作出合理的定义。鲁洪生在《关于〈国风〉是否民歌的讨论》中指出:“民歌的含义有狭义、广义之分。其狭义乃是指‘劳动人民的集体口头创作’,若用这个标准去衡定,莫说《国风》,就是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民歌,乃至今世的民歌集《红旗歌谣》中也没有几首是道地的劳动人民的集体口头创作。”[5]由于这个原因,鲁洪生主张以广义的民歌概念进行讨论,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分别是:音乐、艺术形式、作者与内容。其中作者与内容两项标准,已为鲁洪生自己所否定,认为前者“已不是判定是否民歌的决定因素”,后者“已很难笼统地将民歌与文人诗加以区别”,故笔者于此不再讨论。现将鲁文中关于音乐与艺术形式的表述抄录于下:
“首先是音乐,民间乐调节奏明快,轻松活泼,不同于朝廷正乐的雍容典雅,也不同于宗庙祭歌的板滞凝重。”
“其次是艺术形式,民歌语言通俗、浅近,结构句法多重章叠句,修辞手段多套语比兴,风格自然质朴,活泼清新,不同于文人诗的使事用典、炼字炼义的精巧细密,委婉含蓄,绚丽华贵。”
众所周知,《诗经》原本配有乐舞。《礼记·乐记》云:“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6]582即是此意。以今日而论,与《诗》配套的乐舞固然早已失传而不可复得,然《史记·孔子世家》有言:“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7]1936《雅》《颂》正为鲁氏所谓“雍容典雅”、“板滞凝重”者,已不待言。而所谓《韶》、《武》者,则又分别为“舜乐”与“武王乐”,即《论语·八佾》所谓:“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8]68既然三百五篇皆合于此四乐之音,或合于以此四乐为代表的官方音乐,则鲁洪生“风是相对于朝廷雅乐祭歌而言的‘民俗歌谣’”的说法,恐怕是不合适的。至于艺术形式这一标准,鲁洪生所列举的民歌与文人诗的特点,乃是建立在文人诗不能学习、借鉴民歌这一假设上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李煜词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9]7然而读其《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诸篇,则可知“士大夫之词”未尝不可以“语言通俗浅近”、“风格质朴清新”。至于结构句法上的重章叠句,则与乐章的推进、反复有关,并不能作为民歌独有的特点。
由此可知,广义的民歌定义,其边界过于模糊。对于一首诗是否属于民歌的判断,其理由往往东拼西凑:某项标准用与不用;所选标准孰主孰次,并没有统一的、严格的规定,不能排除研究者本身情感、立场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不适合作为学术判断的标准。反观狭义的民歌定义,概念简明而严格,合之则是,不合则非,绝无主观臆断之可能。鉴于《国风》“民歌说”与“非民歌说”两派的争论,集中在《国风》作者从身份上来说是否属于贵族阶级这一问题上,我们不妨为这场论战中的“民歌”定下这样的标准:作者身份低于贵族阶级(具体到西周春秋时代,则为平民、农奴、奴隶等)的作品,属于“民歌”;贵族所作作品,则不属于“民歌”。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学术上因判断标准不同而引发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式的“论战”,且同时能解决鲁洪生所提出的狭义民歌定义极大压缩民歌边界的担忧。下面,笔者将对持《国风》“非民歌论”学者的部分观点分别列出并进行检查。至于某些已经被批驳过的观点,则不再讨论。
一、民歌地位低下,且无教化、为政功能
在先秦时代,贵族在宴饮、外交等场合常常赋诗言志;在朝堂上往往引述《诗经》内容来进行劝谏或发表评论。同时,《诗经》也是友教贵族弟子的教材,以此对其进行道德教育,并可作为其日后为政的参考。故而有学者认为,《诗经》“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左传》中大量记载了诸侯君臣赋诗言志的事例。称引诗句,来讽谏劝戒,评论抒情,在上层人际交往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诸子百家在著述中引诗,也很常见。……从这些功能来看,很难想象,一个严肃的朝廷之上会唱民歌,一个严肃的祭祀场所,会用民歌祭祀神祖,一个礼乐规整的外交场所,官吏们大唱民歌。……孔子正诗的目的是要‘可施于礼义’的,民歌显然不适合”。[10]
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人解诗、赋诗的方式与今人不同。我们可以引《论语·子罕》中的一段材料来说明问题:
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8]115
在衣着华贵的人面前,子路虽然穿着破旧的袍子,却并不因此而感到羞耻,正符合孔子所教导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8]71故而孔子引《诗经·邶风·雄雉》“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句来称许子路不追求虚荣。我们再将此诗原文抄录于下,以作对比:
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
雄雉于飞,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实劳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
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3]
依此诗原意,乃是一女子因丈夫外出建功立业,久不归家,以致心中有怨。“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两句,是希望丈夫不要追求功名,老实回家过安稳的日子。而孔子曾问众弟子“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说:“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论语·先进》)。[8]129-130子路之志,与《邶风·雄雉》中女子所批评的“君子”,实一般无二,都渴望在功业上有所成就,而不是安心于日常的家庭生活。此外,孔子也曾当着子路的面,说只有自己和颜渊能做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8]95可见,孔子引诗赞美子路“不忮不求”,与《邶风·雄雉》原诗中的“不忮不求”,并不完全是同一个意思。
若在上面这个例子中,引诗者之意与原诗还稍有相通之处,不能完全说明古人解诗时并不看重原诗诗意,而更强调对其所作的解释的话,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例:
瞻彼旱麓,榛楛济济。岂弟君子,干禄岂弟。
瑟彼玉瓒,黄流在中。岂弟君子,福禄攸降。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载,骍牡既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岂弟君子,神所劳矣。
莫莫葛藟,施于条枚。岂弟君子,求福不回。[3]
此诗为《大雅·旱麓》,是歌颂周文王的诗篇。其中“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两句,属于“兴”,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3]1并无太多实际意义。然而《中庸》有言:“君子之道费而隐。……《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8]22-23这番解释,与原诗全无相干,不过借用原诗诗句而已,可谓断章取义之典范。对此,笔者认可李山先生的观点:“正是因为经学对《诗经》作了一番政治、伦理的阐释,对后来文化的发展才产生了很大作用。这就是一部经典的作用。如果想要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发展历程,就必须重视这些经典在各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这已不再是文学史的话题,而是进入了思想史、精神史、文化史的领域。《诗经》作为一部经典的文化著作,在几千年间就是这样参与了民族精神的构建的”。[11]29《诗经》除了是一部文学作品外,也是华夏文明的经典。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古人解诗时对诗句作断章取义乃至牵强附会的解释这一行为。至于原诗是否具有教化、资政等作用,并不是古人所关心的重点。同理,无论是否为贵族所作,如果不能被理解为“可施于礼义”或有资于治道,也会在孔子删定《诗经》时被删除。如《论语·子罕》中有逸诗:“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对此,孔子驳斥道:“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8]116或许是因为口是心非的缘故,这首诗在孔子删定《诗经》时被删去了。
二、平民无法创作《国风》
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在《诗经》产生及编订的时代,“民”这一群体“被限定在‘国’(即都城)之外,……孔子和他的门徒,当时会把很多远离社会政治中心的‘民’所创作的歌谣编入《诗经》么?换言之,当时的‘在野’之‘民’,有机会参与和了解属于统治阶级范围内发生的‘大事’,进而写出因被孔子学派乃至后来历代统治者尊为‘经典’而流传百世的著名诗篇么?答案不言而喻应当是否定的。”[12]其二,“就国风的艺术成就来看,……没有文化修养的庶民百姓,是难以创作出来的。……如果说风诗来源于民间,经过了文人或乐师的修改润色,这正说明文人善于作诗。……春秋时代的都城文人和乡间百姓相比,究竟谁擅长于作诗,还用得着争辩么?我们所说的‘文人’,指国君、贵族、官吏等有文化修养的人,……。在春秋前期,文化被统治阶级垄断,书写条件极端困难,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是不可能被书之竹简流传后世的。”[13]
要解释这两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弄清楚西周春秋时代平民阶层的构成情况。西周春秋时期,在我国历史上属于贵族政治时期。在世卿世禄制下,贵族们掌握着政权。而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宗法制——尤其是其中的嫡长子继承制——为当时各项制度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由于必须区分出大宗与小宗,使得越来越多的贵族子弟身份不断下降,其子孙后代逐渐沦为丧失贵族身份的平民。郑志强之所以认定“民”这一阶层没有机会参与《诗经》的创作,就是因为没有搞清楚“国人”、“民”的身份。他认为“至少在孔子讲学时代,‘民’和‘人’还是两大不同的阶级。‘人’主要指贵族阶级中的人,连最低一级的‘国人’,也多是‘都人士’、‘庶人之在官者’,并不是我们今天概念中的民;而今天的‘民’,在那个时代则以‘戎丑’、‘丑类’、‘鄙夫’、‘黔首’、‘苍头’、‘小人’称之,不过是被限制在‘国’(即都城)之外、生产生活于广袤田野上的‘野人’、‘群氓’,是‘老农’、‘老圃’、‘播民’以及‘舆’、‘隶’、‘仆’、‘台’这一阶层中的一部分人。”
那么,在孔子的时代,“人”与“民”真的是如郑志强所描述的那样么?我们举《论语》中的例子来检查: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8]91-92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8]102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8]134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8]138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8]153
从上述五条引文中可以看出,“民”即“全民”,并不特指野人与奴隶。否则的话,何以只有“民”要称赞泰伯,又何以只有“民”才受管仲功业之赐?这类的例子在《论语》中还有很多,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
再来看“国人”的概念。朱东润在《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中认为,国风不是平民而是统治阶级所作,“国人二字之的训,实为最关重要之事。……国人实与国之君子,国之士大夫同义,亦为统治阶级之统称”。
然而,朱东润的论证过程,不过是列举出《诗经》中四处包含大夫与士阶层的“国人”的例子,以此即认定“国人”与“统治阶级”同义。但是,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所谓“国人”,即生活在国都中的人,是一个“兼有仕、农、兵、工、商的职业阶层”。且“至少在春秋中期以前,……,偶尔有将大夫杂入国人的记载”。[14]可见,在西周春秋时期,“国人”这一概念下既包括着贵族,也包括着平民。“因西周推行宗法制,分封的贵族非嫡系子孙的后代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源源不断地被抛入非贵族阶层,构成国人中的上层”。[15]如果因为某些记载中,大夫、士被划入了国人的行列,即断言国人与大夫、士同义,那么张正明在《春秋楚国庶人浅析》一文中指出,“楚国的贵族在文献中也可以被称为‘民’”。[16]难道我们可以据此得出结论称,“民”与楚国的贵族同义?显然是不可以的。
同时,贵族后代除了因为宗法制的原因而沦为平民外,由于社会动荡,处于贵族阶级最底层的士,其地位也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我们可以引《史记·孔子世家》中的一段文字说明这个问题:
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7]1907
从出身来说,孔子无疑属于士这一阶层。然而因为幼年失怙,家道中落,以至于其贵族身份也遭人否定,无法出席季氏举办的士这一阶层皆可参加的宴会。若非孔子好学且学礼有成,以至于获得孟僖子与鲁昭公的认可,或许就自此泯然于平民之中,而其贵族身份终不被人所承认了。类似的例子还有《史记·管晏列传》中管仲的一段自白:
管仲曰:“始吾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7]2131-2132
“贵族的疏属已沦为平民,但一旦显示才能,有功于国,便可重新踏进贵族的门槛,不过在春秋时代,还首先要取得贵族的资格。”[17]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管仲以经商终老,或战死沙场,其贵族身份得不到社会承认,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再来看没有获得贵族身份的平民:
(僖公)三十三年春,秦师……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18]406-407
弦高是郑国的商人,经商途中偶遇前来偷袭郑国的秦军。情急之下,假冒郑国使臣,入秦军劳军。而秦军统帅在与其交谈的过程中,并未发觉其真实身份。则弦高虽为商人,其必受过教育,具备贵族间交往所应具备的基本礼仪素质,殆无可疑。又如《论语·宪问》有言: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8]158-159
又如《论语·微子》: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8]184
由这些记载我们可以推知,当时一般平民并非皆如某些学者所想象的那样,手胼足胝而胸无点墨。失去贵族身份的贵族子孙,固然有从事体力劳动以谋生的可能,但未必丢失其文化与教养。这些在文化水平上并不输于贵族的平民,既有机会“参与和了解属于统治阶级范围内发生的‘大事’”,又不是“没有文化修养的庶民百姓”。既然如此,参与到《风》诗的创作中来,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顺便提一点,尽管朱熹在《诗集传·序》中提出“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的说法,但这句话本身并不能说明问题。且不说朱熹并未提供说这话的依据,仅仅“吾闻之”三字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而即便是生活在“里巷”中的人,其身份也是不能确定的。如孔子为贵族而行教于阙里,颜渊为平民而居于陋巷。这也是学者们在支持或反对朱熹的说法时,所应当注意的。
三、诗中器用非民间所能有
有学者认为,《国风》许多诗篇中所提到的器物,平民是不可能拥有的。如朱东润在《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中写道:“《竹竿》此诗相传为卫女思归之诗,诸家无异词。四章,‘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则此诗卫女所自作也。三章,‘佩玉之傩’。按佩玉为统治阶级之习尚,《礼记·云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又云:‘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君子佩玉,则其妻女亦必佩玉可知。”这是典型的“想当然耳”了:
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谓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试勿衣紫也?谓左右曰:‘吾甚恶紫之臭。’”于是左右适有衣紫而进者,公必曰:“少却!吾恶紫臭。”其人曰:“诺!”于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国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19]394
有道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礼记》中说的是:“古之君子必佩玉”,却并没有说“古之小人必不得佩玉”。岂能因为君子佩玉,便推导出佩玉之人必为君子?平民模仿贵族,群众模仿明星,实在是一种极其常见的社会现象,又岂能说明佩玉者的身份?那么,平民有财力佩玉么?
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无大绩于民故也。[20]476
由此可见,“无寻尺之禄”的富商们,其财力何止于佩玉,甚至“金玉其车”亦可。况且诗人作诗,所写之物未必即所用之物:李白诗中每言“金樽”,未必只有真持金樽时方能如此写诗;言“玉碗”,也未必唯以玉碗饮酒时方得写“玉碗”。朱文以诗中有“琼华”、“琼英”等物即言必为统治阶级无疑,又焉知诗人不能指燕石而称琼英?
朱文又说:“《击鼓》三章,‘爰居爰处,爰丧其马。’按春秋有车战而无骑士,旧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据此知一车四马,甲士三人,此三人者,一为车右,一为御,一为中军,与《清人》诗所谓‘左旋右抽,中军作好’者合。诗人自言‘爰丧其马’,其位置必不在甲士之下可知,则亦统治阶级也。”此处所谓“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云云,应是出于《周礼》。只不过现今版本的《周礼》却并非周公所作。春秋“有车战而无骑士”不假,“步卒七十二人”却不是事实,此点早为钱穆在《读史随札》之《春秋车战不随徒卒考》一文中考证过,此不赘言。[21]况且国人亦得参军为甲士,如: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18]222
西周春秋时代的国人,每每参与到政治斗争与军事冲突中。从西周的国人暴动驱逐天子,到春秋时各国国人驱逐国君或帮助国君向卿大夫的军队作战,皆然。故而诗中人的身份,实不能简单地因其是否为甲士即判断其是否为统治阶级。
四、结 语
在评论诗作时,我们常说诗人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然而我们读《国风》则会发现,诗人们往往一味地抒情,对于那些引发自己诗兴、灵感、情绪波动的事件本身,却少有交代。换言之,诗人作诗,重在抒情而非叙事,这一点大大增加了后人判断诗人身份的难度。今日的我们与《诗经》的时代之间,已经远隔了两千五百年以上的岁月。在材料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强行断言《国风》中的诗篇究竟是出于哪一阶层古人的手笔。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实是我们今日学习、研究《诗经》所必须具备的治学态度。
∶
[1]檀作文.20世纪以来的《国风》“民歌说”与“非民歌说”之争[J].中国韵文学刊,2006,(1).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钱志熙.从歌谣的体制看“《风》诗”的艺术特点——兼论对《毛诗》序传解诗系统的正确认识[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5]鲁洪生.关于《国风》是否民歌的讨论[J].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96,(2).
[6]朱彬.礼记训纂[M].北京:中华书局,1998.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王国维.人间词话[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10]孙丽娟.“《诗经》没有楚风”论释疑——兼论《诗经》中没有民歌[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11]李山.风诗的情韵——李山讲《诗经》[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12]郑志强.《诗经》没有“民歌”论[J].中州学刊,2005,(6).
[13]翟相君《国风》非民歌说——邶鄘卫非民歌考论[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14]蔡锋.国人的属性及其活动对春秋时期贵族政治的影响[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
[15]张兢兢.从“国人”身份地位的变化略窥周代社会形态的演变[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
[16]张正明.春秋楚国庶人浅析[J].江汉论坛,1984,(8).
[17]沈星棣.春秋战国时代平民参政的社会潮流[J].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4).
[18]杜预,等.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19]《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20]左丘明.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1]钱穆.读史随札[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王小风〕
Comments on the Idea that the Poems in National Customs are not Ballads
Liao Yue
(School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Tianshui Gansu741001,China)
There have always been two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e identity of National Customs:ballads or non-ballads.Since 1980s the non-ballads believers restarted their criticism of ballads idea,and came to think that National Customs should be created by the nobility.The paper believes that this idea is questionable and is open to discuss.
The Book of Songs;National Customs;non-ballads;third estate
I207.22
A
1671-1351(2016)03-0078-06
2016-03-02
廖越(1990-),男,湖南郴州人,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