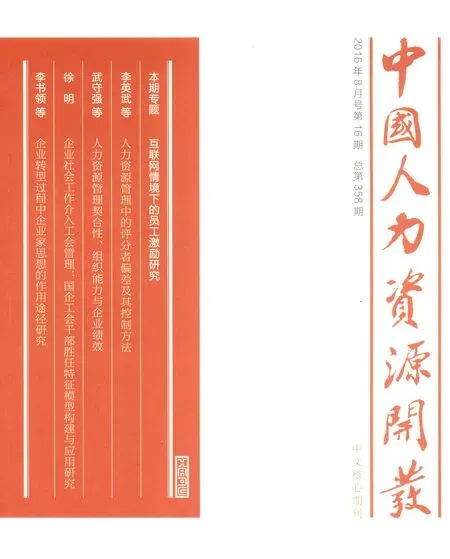趋同存异:经济全球化下中美劳动关系比较研究
· 王潇 刘明巍
趋同存异:经济全球化下中美劳动关系比较研究
· 王潇 刘明巍
经济全球化导致中美两国劳动关系系统既趋于相同又存在差异。一方面,全球化强化了两国的市场力量并传播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产生了一些相似的劳动关系结果,包括更大的雇佣灵活性,更大的工资收入差距,社会安全网络恶化以及工会边缘化。另一方面,由于中美两国原本就在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关系中的国家地位以及工会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中美两国在工人行动、雇佣实践、工会改革以及劳工政策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差异。
经济全球化 经济自由政策 比较劳动关系 工会
一、重思比较
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国和美国——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愈加密切,甚至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作“中美经济共生体”(Ferguson & Schularick,2006)。近年来,学界一直重视对两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系统加以比较,并普遍认为较我国来讲,美国拥有相对完善的劳动关系系统,其工人的待遇也更高。虽然这个观点有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显然不能因此就效法美国来构建我国的劳动关系系统。本文通过梳理比较劳动关系的文献,探究经济全球化下中美劳动关系的共性和差异,进而为两国劳动关系的改革提供思路。
二、趋同抑或多元:关于劳动关系发展趋向的争辩
(一)关于国际劳动关系发展趋向的研究
多年来,比较劳动关系领域的一大争论是各国劳动关系将趋于相同,还是继续保持多样化。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发达国家的劳动关系趋势,并且尚未达成一致观点。
1.持趋同观点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因为发展中国家之间具有产业趋同化的驱动力,其劳动关系系统将越来越趋同于某个模型,这点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相类似(Kerr et al.,1960)。但实际上这一观点有待商榷,因为即便发达国家也未曾有充足证据表明这种趋同化倾向。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发展引发了学界劳动关系趋同化的更为激烈的争论,并产生了一些强有力的论点。最关键的一个论点是,强劲的国际竞争、贸易、资本流动、宽松的政策以及最佳模式的广泛传播极大推动了国际劳动关系模式的趋同化。尤其是由于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强劲的经济和雇佣增长,一些学者宣称新的国际趋同趋势正朝着以灵活劳动力市场为特征的英美新自由主义市场模式发展(Paul Krugman,1996)。
2.持趋异观点的研究
持趋异观点的学者反对新自由主义观点,认为制度安排实际上牢牢扎根于单个社会的特定历史传统,并且全球化对各个国家的影响有很大差别,对社会主体利益和策略的影响也是千变万化。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相对于协调型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更大,例如德国和美国之间的比较(Peter A. Hall & David Soskice,2001)。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劳动关系并非趋同于某个独立模型,而更可能趋同于一个混合模型,即来自不同系统的因素整合到一起并保留了各自独特的传统(Robert Boyer et al.,1998)。比较劳动关系领域的学者已经提出一个相似的观点——“存异趋同”,即国家间的劳动关系模式在呈现出相似性的同时,国家内部的劳动关系系统正趋于分散化(Katz & Darbishire,2012)。
(二)关于我国劳动关系发展趋向的研究
对我国的比较劳动关系研究来说,劳动关系趋同还是趋异的争论成为重要主题之一。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初级阶段,一些学者曾认为,由于中日两国在文化和传统上的相似性,一部分国有企业正趋同于日本的组织导向模式(Anita Chan, 1995;Anita Chan & Jonathan Unger, 2009)。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学者认为市场经济改革和全球化正将我国的劳动关系转化成西方的灵活雇佣模式(Sarosh Kuruvilla & Christopher Erickson,2002;Mary Gallagher,2005;Mingwei Liu,2010)。然而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劳动关系趋向于一种混杂模型,这一模型结合了西方或东亚的雇佣实践以及中国特色(Malcolm Warner, 2000 )。还有一些学者则更加谨慎,认为没有政治改革,仅仅由经济改革引起趋同是不可能的(Gordon White et al.,1996),而另一些则强调劳动关系模式存在极大的不同,尤其是不同企业类型和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Bill Taylor,1999;Daniel Ding et al.,2000;Anita Chan,1995)。还有学者认为,中美劳动关系转型的共同特点是打破沿袭几十年的劳动关系制度框架,中美两国虽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但拥有相同的时代背景,虽然转型目标不同但有着相似的劳动关系格局(张立富,2010)。
三、经济全球化下中美劳动关系的共性
经济全球化并非一个新现象,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已经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例如贸易壁垒的消除整合了产品市场,对资本流动限制的解除刺激了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科技跨国传播,跨国生产等(Franz Traxler et al.,2001)。这些特征明显增强了市场间的竞争,增加了资本在国家间的流动性,并加强了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相互依赖。因此,几乎每个国家的劳动关系都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尽管学者们在劳动关系系统是否趋同方面的意见并不一致,但是不可否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已呈现出一些共同的变化,例如,工资和劳动雇佣方面的灵活性加强,以及劳动相关标准的向下探底竞争(Gary Gereffi & Timothy J. Sturgeon,2004; Kuruvilla & Erickson,1996)。
中美两国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尤为明显。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美两国都越来越多地参与并活跃于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2012年,美国位于全球最大投资国之首,中国位列第三①。两国的跨国公司活动日趋活跃,包括在非洲开展活动。中美两国贸易占GDP的百分比分别从1980年的21.65%和20.76%急速增长为2010年的54.24%和29.1%(世界银行,2011;中国统计年鉴,2011),而且两国都在外资直接投资的输入和输出方面有明显的增长。
(一)经济自由政策对中美劳动关系的影响
中美两国的经济全球化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得益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市场是确保物质繁荣最有效的方法,受这种观点影响,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都转向经济自由政策,包括减少或免除关税壁垒,资本和投资流动性增长,以及我国明显加剧了企业间竞争以及国企私有化(David Harvey,2005)。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逐步将中国经济转化为融合了市场机制和中央计划的混合型经济。虽然政府在经济协调中仍然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市场机制在资源分配方面则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中国这种很大程度上依靠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将国企暴露于更严峻的国际竞争,而不是单纯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竞争。
对美国来说,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日益增长的国际竞争直接引发了新自由主义经济转型,强调以市场为中心,国家资源私有化,以及逐渐削弱国家保障。20世纪80年代,里根的经济刺激政策进一步加速了在生产、金融和劳动力市场领域的放松管制,这些都导致了美国企业面对更严峻的竞争。而且,信息技术进步支持下的自由贸易竞争为美国公司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将工作外包给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如我国。另外,经济全球化也带动了移民增长和国际间人口流动,这些都为美国创造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中美两国的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都明显增加使用劳务派遣,灵活工作时间及裁员,减少员工福利,并且努力削弱工会的力量。因此,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的增长已经导致了中美两国劳动关系某种程度上的融合,也就是说,两国都经历着越来越普遍的雇佣灵活化,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护下降,以及劳工运动边缘化。
1.对中国的影响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依据政治资源运用行政手段分配利益,当时的劳动关系利益主体“三位一体”,即政府既是资方代表又是劳方代表,同时又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黄河涛、赵健杰,2007)。劳动者实际上享有隐形的“终身契约”,享受着终身雇佣,标准、稳定、平均化的工资,以及“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系列福利政策。然而,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浪潮打破了这个“铁饭碗”。
(1)从终身雇佣制到劳动合同制
逐步建立起来的劳动合同系统已经将雇佣从终身制变为合同制,授予公司在雇佣解雇方面的自主管理自由。虽然有些工人拥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包括无合同工人、派遣工以及学徒工或技校学生实习工在内的各种临时工、短期合同工和下岗工人,在工作场所已经相当普遍了(Gallagher,2005; Lu Zhang,2011)。虽然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率先使用了各种灵活雇佣劳动,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私企也迅速地掌握了这种方法。例如,每天12小时每周6到7天的工作制不仅仅在港澳台企业中十分普遍,在内地的盈利国企中也常常可以见到(Lance Compa,2004)。另外,根据劳动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在1996到2005年间由于企业重组,大约有7000万工人下岗,其中大部分是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职工。在2013年7月有关劳务派遣的条款修改之前,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实际上促使劳务派遣工人的数量的急速上升,从2007年底的2000万上升为2010年的6000万,主要集中在公有制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部分央企甚至有超过2/3的员工都属于劳务派遣工人(降蕴章,2011)。
(2)从政府决定工资到老板决定工资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浪潮影响下,我国政府由唯一的利益主体向协调人角色转变(黄河涛、赵健杰,2007),并且由于“资强劳弱”现象广泛存在,雇主对市场具有一定支配力,工资实际上成为一种管理/管制价格(Kaufman,2010)。虽然早在1996年我国就引入了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但基于“自上而下”的建制模式,这一制度却带有很强的形式化烙印,不具备法律效力。政府主要更注重集体合同的签订数量,轻视集体合同的内容和履行,仅仅提供一般的雇佣条件及条款,对于合意的实效性基本不予关注(Simon Clarke et al.,2004;郑桥,中国劳动关系变迁30年之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2009;三方机制完善与改革课题组,2010)。在企业层面,工会通常是管理者的助手,集体合同的签订过程也仅仅由管理者决定,几乎没有工人参与,很多工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签订过集体合同(三方机制完善与改革课题组,2010)。
由管理方单方设计出的各种灵活工资和薪酬制度,包括计件工资和绩效工资,极大地扩大了工资差距。尽管学者们对我国基尼系数的测算差异很大,但即使是根据官方相当保守的估计,我国前10%最富人的收入至少是10%最穷人收入的23倍(Dexter Roberts, 2011)。而且,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调查,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已达18倍,2008年20个行业门类收入差距最高达10倍,2002至2009年,我国GDP年递增幅度10.13%,职工工资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8.18%,有23.4%的受访者在2002到2007年间没有涨工资,并有75.2%的受访者认为目前的收入分配系统不合理②。虽然国家仍然在宏观层次上保留对工资水平、结构和增长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也在逐渐消失。
(3)从单位保障到社会保险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个人缴费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取代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系统。不仅是原来享有各种社会保险的工人的福利降低了,而且仍然有大量的工人,尤其是农民工,仍然被排斥在社会保险制度外。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截止到2012年底,四种强制社会保险(医疗、养老、工伤、失业)的覆盖率,城市职工分别为62.99%,56.60%, 40.08%, 和51.77%,农民工分别为17.65%,20.19%, 9.99%,和30.51%。另外,有42.98%的城市职工享有强制生育保险,而统计没有显示农民工的生育保险报告,可能是因为其极低的覆盖率。
(4)传统工会的转型压力
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给中华全国总工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加剧了工会的边缘化。全球化下和新自由主义形势下,政府抽离了对工人的代表,资方势力日益强大,但工会还未摆脱传统模式,劳方制度性参与机制还未形成,造成劳权的极大弱化(常凯,1995)。
首先,从1984年开始实行企业改革之后,中国工会的密度开始下降特别是,由于国有企业大规模的重组和裁员,以及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建立工会的困难,中华全国总工会从1992年到1999年损失了1630万会员,导致了工会密度从41.85%下降到了26.77%。 然而,相反的是由于全国性的私企运动,2000年后,工会密度呈现了上升趋势。集体合同自从1994年正式引入后,其覆盖率也呈明显上升趋势,从1996年的12.9%上升到2008年的34.06%(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 2009)。然而,由于缺乏明显的工人参与以及工会组织和协商过程具有很强的形式主义特征,这种在数量上的增加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Mingwei Liu,2010)。
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重组使得管理方被授予了裁撤工会干部的权利,行政部门改革是的公共组织规模缩水,这些都致使中华全国总工会遭受了严峻的人力资源危机。工会干部的素质已变得很低。由于大多数工会干部缺乏必要的集体协商和争议处理知识和技术,新角色给工会干部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也许,工会最严峻的危机就是他们日益与工人相脱节。虽然工会在地区和国家层次能够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工人的某些利益,但在企业层次,由于雇主的直接抑制或控制,企业工会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最薄弱的环节。
2.对美国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劳动关系以安全长期的雇佣、稳定的工资、强有力的工会以及集体谈判为特征,这些都有效地改善了劳动条件和福利。在工作安全和优质的附加福利方面,美国大型企业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有企业十分相似。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主义改革,以牺牲重要工业部门,例如卡车、航空和通讯等行业的工人利益为代价,消除了对这些行业的管制。许多政府部门的工作私有化或外包了,并且赚取中低等工资的工人被置于与发展中国家那些赚取更低工资的工人直接竞争的境地。
(1)从全日制工作到灵活雇佣
首先,日益增长的国际竞争和新自由主义促使美国雇主寻找更低的劳动成本和更大的雇佣灵活性,这逐渐打破了内部劳动力市场那种工人全日制为特定雇主工作并且在职业阶梯上稳步晋升的标准雇佣模型(Peter Cappelli,1999)。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平均工作任期上存在普遍的下降,尤其是在中年白种男人那种传统意义上受到内部劳动力市场保护的组织中(Peter Cappelli,2008;Henry Farber,2008)。这导致了所谓的“风险社会危机”——频繁的大规模的裁员成为商业改革策略的一个基本要素,这点是对该问题的最好反映(A. L. Kalleberg,2009)。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2004年,由于进口商品的生产条件更符合国际厂商的期望,超过3000万的全日制工人被迫失去了工作(Louis Uchitelle ,2006)。这个失业规模与中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下岗规模相差无几。北美自由贸易法案通过后的五年里,仅仅流向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工作岗位估计就有440,000个。
可能在经济下滑时期大规模裁员(50人及以上)不足为奇,但劳工统计局(BLS)显示甚至在经济景气时期(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大规模裁员的数量也持续走高。然而,裁员并不限于制造业,也蔓延到了各种高科技行业。有估计称,在21世纪初有500,000到800,000个高科技工作岗位流向海外(Derek Schultz,2006)。甚至在2008年到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前,惠普公司就在2005年裁撤了15,000个工作岗位,因特尔公司则在2006年裁撤了10,000名员工(Stephen Sweet & Peter Meiksins,2012)。
其次,灵活雇佣包括合同工作和临时工作也急速增长。企业已经增长了对低端和高端劳动力市场的外包服务工作。然而,在1979到1995年间,临时服务供给业的工人从每日435,000人次增长到240万人次,11%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美国非农雇佣增长率的五倍之多(David Autor,2003)。
最后,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在美国工作场所急速扩张。工人不得不适应各种工作安排,包括非全日制、倒班、全日制、加班和周末加班。在2009年,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做非全日制工作,四分之一的人工作时间超过全日制时间,将近十分之一的工人每周工作60小时或更多(Sweet & Meiksins,2012)。延长工作时间的趋势对那些为赚取相当低廉的最低工资而奋斗的工人来说显得尤为突出,最低工资是新自由主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之一(OECD,2011)。
(2)收入差距扩大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已经扩大了美国收入差距的不平等性:虽然最富的美国人从贸易和财政自由中赚到很多,大部分美国人尤其是最穷的那部分人却遭受了放松管制和来自发展中国家工人竞争的深刻影响。1979到2007年间,美国百分之一最富人群的税后平均家庭收入增长了275%,其余前20%最富人群的税后平均家庭收入增长了65%,然后最穷的20%人群仅仅增长了18%(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2011)。百分之一最富人群的国民收入份额为18%,比1980到2008年间的8%增长了两倍还多。然而最穷的20%家庭在2008年仅仅得到了国民收入的3%,比1970年的份额还少(Sweet & Meiksins,2012)。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在比较CEO们的收入和普通雇员的收入时显得尤为突出。根据美国劳联产联高级管理人员工资报表,1980年CEO的平均薪酬与普通雇员之比是42:1,但是在2011年这个比例暴增到380:1。贫富差距由于新自由主义税率政策而进一步扩大,这项税率政策将最高收入人群的边际税率从1970年的42%削减到2003年的23%,并且资本受益税从1978年的35%削减到目前的15%(Robert Lenzner,2011;Sweet & Meiksins,2012) 。
(3)逐步削减的社会福利
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也侵蚀了工人福利。在1979到2010年间,享有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计划(雇主至少支付部分保险费)的员工与享有由现任雇主提供的某种退休金计划的员工分别下降了12.9%和7%(John Schmitt & Janelle Jones,2012)。社会福利制度的下降,例如1996年用工作福利代替福利,这致使工人参与低工资雇佣成为关键(Robert Zieger & Gilbert Gall,2002)。而且,基于雇佣的健康保险和退休计划的质量也随着雇主让雇员承担更多的份额和转嫁风险而不断下降(Lawrence Mishel et al.,2007)。这些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当2004年美联航宣布破产以后,其120,000个雇员损失了他们的大部分退休福利(Alexandra Marks,2004)。另外,诸如失业保险和社会援助保险福利的削减使得员工福利进一步恶化。甚至以往相对稳定的公共部门养老金计划也逐步受到威胁。
(4)工会力量下降
从20世纪70年代起,全球化和放松管制严重威胁了美国工会并加速其衰落。美国工会密度从1980年的23%下降到了2010年的11.9%,下降了近一半。工会会员数量的减少在私营部门尤为严重,从20世纪中期的1/3下降到了2011年的6.9%(BLS,2012)。虽然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会会员数量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得到明显增长,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会不断受到2008到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威胁。甚至像威斯康辛州和俄亥俄州这样的有很强工会传统的州也开始加强了对公共服务部门工会的法律限制。
三分之一的工会削减是拜全球化所赐,最直接的失业威胁来自于海外工作外包,焦点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化,以及增长了对灵活雇佣工人的依赖(Kate Bronfenbrenner,1998)。另外,新自由主义劳动力市场政策加强了在工会组织方面和集体谈判方面的管制,如南部各州的就业权法案(废除了要求非工会会员向其代表付费工会合同)(Rick Fantasia & Kim Voss,2004;Leo Panitch & Donald Swartz,2003)。因此,集体合同的覆盖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25.7%下降到2011年的13.0% (Barry Hirsch & David Macpherson, 2012)。更糟的是,工会的谈判力量由于国际竞争和资本流动增强而被严重削弱。特别是工会的罢工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有2,468,000名工人参与到318起大规模罢工中,在2010年只有47,000工人参与到仅仅11起大规模罢工事件中(Sweet & Meiksins,2012)。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会频繁在工资和福利方面做出让步,这在30年前是很少见的(Dan Clawson & Mary Ann Clawson,1999 )。
工会政治的效力也减弱了,例如,他们曾在限制里根总统1984年连任上遭到失败,近期也在限制民主党总统及其国会颁布的雇佣自由选择法案为形式的劳动法改革上遭到失败(Robert Bruno,2011)。在这种环境下,公众对工会的支持在过去10年,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急剧下降。根据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2009年仅有不到一半(48%)的美国人支持工会,达到7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Lydia Saad,2009)。虽然在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工会受欢迎程度的下降方面没有一致意见,有国际竞争和放松管制引起的高昂的失业率似乎是重要因素之一。一项研究估计称,失业率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工会的支持率就下降2.6个百分点(David Madland & Karla Walter,2010)。
四、经济全球化下中美劳动关系的差异
从前面分析来看,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已经导致中美劳动关系系统某种程度上的趋同。然而,全球化对中美劳动关系的影响也由于两国经济、政治和制度的差异而呈现出明显不同。这部分将从经济发展阶段、政府角色和工会结构三个方面度量经济、政治和制度三个因素对于全球化下中美两国劳工的影响。
(一)工人的就业与收入水平
1 .中国:就业与收入水平提高
由于贸易和金融自由以及科技进步允许全球资本通过外包形式将业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国大部分工人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估计称,尽管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小时薪酬成本大幅提高,2008年其成本也只有美国的4%(Judith Banister & George Cook,2011)。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改革和持续增加的外资流入已经为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制造业雇佣数量迅速增加,其后由于国企和集体企业大规模下岗,其雇佣数量下降,后又因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而再次增加(Banister & Cook,2011)。仅外资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雇佣数量就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0增加到2010年的1823万,甚至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也持续增加(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2011)。而且,尽管如前所述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改革也确实极大地增加了普通中国人的收入。1980到2010年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从220美元增加到4270美元,并且贫困率(一天1.25美元)从1981年的84%下降到2008年的13%,超过6亿人摆脱了贫困(世界银行, 2012)。
尽管对于我国工人的工资还缺乏可靠估计,但毫无疑问我国工人的劳动报酬增加了。城镇工人的平均名义工资在1980年到2010年间增加了47倍(从762元到36,539元),而且全中国的最低工资近来也明显增加,例如,广东深圳的月最低工资从1992年的245元,增加到2012年的人民币1,500元(中国统计年鉴2011)。
2.美国:就业与收入水平下降
与中国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多数美国工人,尤其是制造业工人,经历了全球化和经济自由主义形势下经济的下降。虽然在过去20年间,美国整体雇佣数量大规模增长,但其实增加的雇佣全部来自非贸易部门。然而,由于与每个工作较低附加值相关的全球供给链的职能外迁,大多数制造业的雇佣数量急剧下降(Michael Spence & Sandile Hlatshwayo,2011)。根据BLS的数据,1980到2011年间,制造业雇佣数量下降了36.6%,涉及683万人。
虽然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损失伴随着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但生产力的提高并没有导致工人报酬的增加。服务部门的雇佣在同一时期大幅增加,但这事实上对真实工资来说有向下的压力,由于服务业每个工人的真实报酬只相当于制造业工人报酬的一半(Ann E. Harrison,2007 )。另外,考虑了通货膨胀率后,2010年最低工资实际上比1979年低了15% (Schmitt & Jones,2011)。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中等收入美国人赚的钱不仅几乎没有增加,反而在千禧年的前十年倒退了7%。男性工资的下降尤为明显(Annalyn Censky,2011)。在1969到2009年间,30到50岁美国男性的平均工资下降了27%(Mike Dorning, 2011)。为克服工资下降的影响,美国工人不得不增加他们的工作时间或者让其另一半儿和其他家庭成员进入劳动力市场。根据一项估计,21世纪初,美国家庭成员的工作时间跟1970年相比,相当于每年增加了一个月(Jerry Jacobs & Kathleen Gerson,2004)。即使如此,大多数美国人的经济状况相较于1970年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Sweet & Meiksins,2012)。而且,工人有个好工作——薪水每年至少37,000美元,享受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和退休计划——的比例从1979年的27.4%下降到2010年的24.6%(Schmitt & Jones,2011)。许多失业的工人发现找工作特别难,或者不得不接受低工资的工作,这导致中产阶级迅速缩水(Sean Reardon & Kendra Bischoff,2011)。2008到2009年间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了这个局面,2010年生活在官方贫困线(2010年四口之家22,314美元)以下的美国人数量达到了4620万,是五十二年来美国人口统计局公布贫困估计的最高值。
(二)资方的雇佣实践
1.中国:高剥削模式
来自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外资企业,还有港澳台资企业,实行泰勒制的管理模式,极大地剥削了我国工人的劳动成果,如给付极低的工资,恶劣的工作条件,这些问题后来还扩散到了私企和国企(Anita Chan, 2001;Compa,2004; Gallagher,2005)。有大量雇主把最低工资设置为一般工资,加之劳动法律执行力度较弱,导致我国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非常低(常凯,2008)。甚至还有些雇主还使用威胁和扣押身份证件等手段限制工人的自由。国内外许多学者将中国低工资、高剥削的现象称之为“血汗工厂”。
2.美国:高绩效模式
虽然“血汗工厂”在美国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比起我国少了很多。随着经济全球化下业务外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美国雇主认识到他们不能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成本相比,必须依靠创新和效率来创造利润。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雇主通过授权一线员工参与的高绩效雇佣实践,例如生产团队,问题解决团队,雇员授权,广泛培训以及激励工资等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Eileen Appelbaum et al.,1999)。
(三)政府的角色
1.中国:强干预
我国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强干预作风有着深刻的历史传统。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劳动关系的调整几乎全部依赖行政指令,虽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政策已经推行30多年,但劳动行政依靠惯性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政府强干预仍然是我国劳动关系状况的关键特征。不仅如此,国家的强干预还渗透到对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的管理当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和雇主协会在某种程度上行使政府的部分职能。首先,《中国工会章程》总则明确指出,“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同时也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党通过工会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到工人群众中去”。这就使得劳方组织不仅仅代表工人方面的利益,同时还要兼顾到企业的生产发展,实际上行使了政府的一部分职能。其次,我国的雇主组织主要是企业家联合会和全国工商联,作为资方代表的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其成员主要是国有和集体大中型企业,直到2011年5月召开的“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第一次执行主席会议”上,政府才原则上同意增加工商联作为雇主代表参加三方会议。即便如此,现存的这些组织也没有覆盖整个雇主群体(刘湘国,2012)。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十余万起,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群体性事件属于工人抗争。为保持工业和平和社会稳定,我国政府采取三项主要政策应对劳资冲突问题。首先,政府将工会组织渗透到私营企业中去,2000年以后通过指标式的工作安排,迅速提高了地方上私营企业的工会密度,加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基层上的控制力度;其次,政府自上而下地建立了三方协商机制试图化解集体性劳资冲突。目前省级三方机制全部建立,市级建制率达到82.7%,县级建制率达到80%以上。但从实践中功能的发挥来看,我国三方机制在化解劳资矛盾、提高工人待遇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常凯、李琪,1998;李德齐,2003;汪洋,2006;乔健,2010;黎建飞,2010;杨观来,2011;李丽林,2011等)。再次,政府通过劳动力市场的重新规制来平衡劳动保护和经济发展。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颁布或修改了大量规制雇佣条件和劳资关系的劳动法律,例如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工会法以及社会保险法,这些都为工人对抗残暴的雇佣实践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护。尤其是2008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明显增加了个别劳动合同的覆盖率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雇佣实践(Chang-Hee Lee & Mingwei Liu,2011)。另外,政府已经建立了各种活跃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为贫困劳动者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及过渡性援助,为失业工人提供再培训及再就业服务,并为雇佣失业工人的企业减免税费。政府还为农民工这一劳动力市场最弱势的群体提供免费的或补贴性的技术培训以及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险系统。
2.美国:弱干预
在美国,尽管20世纪60到70年代的公共政策意在增加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地位和力度,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因此,并不让人感到奇怪的是,美国政治领导人不像中国领导人那样感到恢复国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规制作用具有必要性。在劳动力市场规制仍然很合适的地方,政府提供源头保护的能力被削弱了。虽然雇佣关系问题的立法创制权,诸如最低工资,种族和性别歧视,健康和安全,以及家庭和医疗休假,以工作为基础的雇佣福利和工作场所权利已经逐渐减少,在雇佣关系政策上仍然没有随意雇佣这种说法,并且劳动政策持续干扰工会形成。
在2008年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州政府并不是重新规范市场,而是试图进一步削减工人的权利。例如,威斯康星州在2011年对公共部门的工会施加了重大立法限制。在2012年,印第安纳州成为了在中西部和东北部原先工会实力较强大的州中第一个实施劳动权利法的州。此外,那些试图帮助受到全球化不利影响的工人们的美国项目也已经弱化。根据经合组织的通知,在2007年,美国对劳动市场项目的公共支出仅仅占到GDP的0.43%。
(四)工会的结构
1.中国:金字塔式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我国唯一合法工会,它明确承认本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在政治上自觉接受政府领导,在行动上与政府决策保持高度一致,这就决定了工会组织不仅仅代表工人的利益,其行动更多是出于国家政治的考虑。它采用了一种金字塔式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该组织由国家层面、地区层面和基层组成。在底层,基层工会根据企业工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而上层工会则沿着产业线及在地理界限内进行组建,拥有和政府管理部门平行的组织机构。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工会领导是由共产党任命,而企业工会主席通常是由雇主任命甚至兼任,这就是说,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工会是政府主导的,在企业层面的工会是雇主主导的,因此我国工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由于工会结构一元化而引发的代表性和独立性问题。
近年来,各级中华全国总工会已经努力提高其代表性。国家层面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地区工会已经积极参与到劳动立法和政策制定中来,将一些保护工人的条款写入劳动法律中,并向那些受到全球化和市场化影响的工人提供更多的援助和福利。此外,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许多地区分支已经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为陷入劳务纠纷的劳动者提供免费法律服务,包括在劳动仲裁委员会和法庭上提供咨询、调解和代表服务。甚至一些行业工会和企业工会为提高代表性,加强了其集体协商功能或引入工会主席直选。然而,由于工会的结构限制,所有这些改进依然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2.美国:分散化
美国有两种主要的工会形式,即行业工会和产业工会,行业工会仅包括特定行业或职业的工人,而产业工会包括所有工人。美国劳工运动有一个联合机构,该联合机构由带有地区机构的国家部门工会组成,隶属于地方工会。大部分的部门工会都隶属于国家劳工中心——美国劳联-产联(AFL-CIO),其主要作用是促进工人的政治目标。美国劳联-产联在每个州及主要城市都有直属中央机构,在更广大的农村地区拥有地区联合会。尽管美国劳联-产联协助其会员工会开展集体谈判活动,但是它对这些活动没有正式的权威,并且很少直接参与其中,其作用是为特定的工会谈判活动从其他工会调动支援(Katz and Kochan,2007)。自治国家工会是大部分美国工会的主要机构,这些美国工会监督着广阔的国家层面的规划,从事政治活动,磋商公司层面或产业层面的集体协议,招募和组织新成员,并协调工会和美国劳联-产联之间的关系(Kim Voss & Rachel Sherman,2000)。地方工会在许多国家工会中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它直接为会员或会员代表提供服务,包括当地合同的磋商,投诉处理以及指导罢工和纠察活动。地方工会和国家工会的领袖是通过民主选举程序定期选举产生的。
美国劳工组织的分散结构阻碍了集体行动的能力,劳动法的变化使得工人加入现有工会或组建新工会比以往更容易了,而组织分散化使得工会难以应对这一新变化,进而导致了工会密度的下降。
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工会组织仍然沿袭了二十世纪中期的经济结构,仍然将服务业工人、专业技术工人和白领工人(不包括在公共部门工作的)排除在外。美国劳联-产联自1955年合并后没有组织工会的职能,只有行业工会有组织吸纳工人的职能。因此缺少一个国家层面的协调组织来避免各级工会之间频繁地互相竞争会员。另外,许多国家工会和地方工会正逐渐转向关注招募新的成员。然而,许多地方工会都曾抵制新组织政策,他们害怕新的成员将会稀释现有的工作机会(在行业工会中)或者导致服务层次下降(在产业工会中)(Susan J. Schurman & Adrienne E. Eaton,2012),更倾向通过协同磋商和实施工作规则来巩固现有成员,而不是招募成员(Clawson & Clawson,2000)。由于地方工会在他们的活动中享有很高的自治权,所以国家工会就只能说服他们开发新的组织策略(Voss & Sherman,2014)。尽管一些地方工会领导已经意识到组织的重要性,但是这样的运动常常因会员缺乏兴趣和动机而受到极大阻碍(Robert J. Flanagan,2005;Strauss,2000 )。此外,由于美国工会并非按照产业线组织的,因此在许多产业中可能会有许多工会争相做工人代表的现象,这大大增加了工会认可的难度(Bruno,2011 )。此外,受到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工会在政策和工作优先事项方面的偏好各异。
因此,美国工人组织的分散结构限制了工人组织整体的政治有效性。另外,也有一些工会正关注大量被排除在劳动法的保护之外的工人,这些工人也没有雇主和他们进行集体谈判,因此,这就给工会的组织、代表提出了新要求。
五、结论
本文比较了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中美劳动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中美两国来说,全球化已经推动了一定程度的劳动关系会聚,而就经济发展阶段、国家作用和工会的本质而言,两国之间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差异,这些差异已经导致了两者在劳动关系发展上的不同路径。因此,本章重申了特定国家政治、经济和结构因素在塑造全球化在不同国家背景下作用方式方面的重要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三个关键结论:首先,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政策对工人待遇有不利影响。虽然大多数我国工人的劳动报酬增加可能得益于全球化和市场化,然而这种增加是建立在严重剥削基础上的,近年来大规模频发的集体性劳资冲突可能表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正接近工人的政治和社会极限。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我国工人在广泛的泰勒管理模式的下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于我国没有完全接受新自由主义,我国政府的强干预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次,独立性对于工会有效的代表工人来说是一个必要条件。尽管美国工会在会员数量上大幅下降,但是他们拥有高度独立性和自治权,在维护工人权益上也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而我国工会的独立性从国家层面到企业层面均受到一定制约。虽然近年来努力改革,但其代表性的提高始终存在困难。第三,工人组织的代表性不是万能的,还需要强大的执行力。对于我国来说,虽然近年来的一些自发罢工中,工人们通过民主选举派出代表与雇主讨价还价,然而由于缺乏工作能力和权威,这些代表常常陷入无法统一工人的诉求和缺乏谈判能力的尴尬境地。
注释
① 排名根据联合国《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
②全国总工会张世平:近四分之一职工五年未涨工资,石家庄日报,2010年3月10日。
1.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2014年。
2.Chan A & Unger J, A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 under the reforms: What model of capitalism?, China Journal, 2009, 62(62) : 1-26.
3. Kuruvilla S & Erickson C,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in Asian IR, Industrial Relations , 2002, 41( 2): 171-228
4. Ding D et al., The end of the “iron rice-bowl”: Wither Chines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00 ,11(2):217-36
5. Liu M, Union organizing in China: Still a monolithic labor movement?,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2010, 64 (1): 30-52
■ 责编/ 孟泉Tel: 010-88383907E-mail: mengquan1982@gmail.com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Labor Relations und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ang Xiao and Liu Mingwei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Relations, China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Labor Relations, Rutgers University )
Globalization has led to both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Labor relations systems. On the one hand, globalization has strengthened market forces and spread neoliberal policies in both countries, resulting in some common labor relations outcomes including greater employment flexibility, wider wage and income gaps, a deterioration of social safety nets, and marginalized un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labor relations in each country is mediated in particular by the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labor relations, and the structure of trade unions. These variables have resulted in different impacts on workers' actions, employment practices and labor policy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Based on those former studies, we analyze and induct the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labor relations system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revolution of Chinese labor relation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Comparative Labor Relations; Trade Union
王潇(通讯作者),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讲师、劳动经济学博士。电子邮箱:13426253320@163. com。
刘明巍,美国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管理与劳动关系学院,助教授、产业与劳动关系学博士。
本文受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青年项目”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