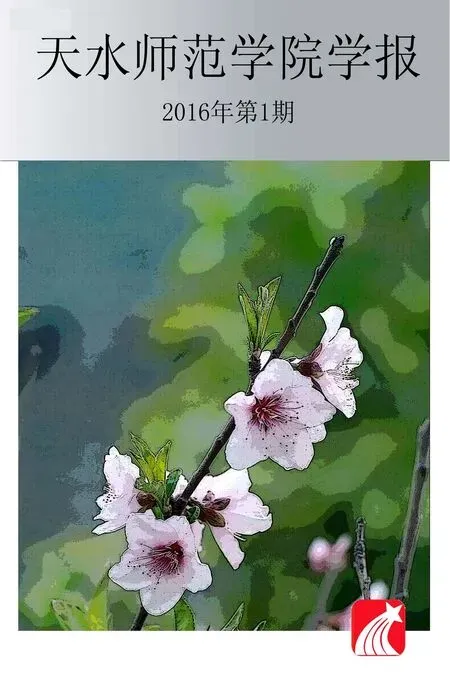高加索冲突研究的现状与理论突破
贾迎亮
(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天水741001)
高加索冲突研究的现状与理论突破
贾迎亮
(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天水741001)
国内外学术界对高加索冲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主义、文学与宗教、经济发展与大国争夺等方面。但是研究者没有认识到历次高加索冲突的共性和主要因素,使得这些方面之间缺乏有机联系,进而不能采用一种较为普遍的分析模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可作为分析高加索冲突的一种有效的理论模型。
高加索冲突;民族认同;国家认同
自20世纪80年代始,高加索地区的冲突与动荡至今仍未停歇,未来的形势也不容乐观。高加索冲突一方面在短期内不会得到彻底解决,另一方面深刻地影响了当今和未来的国际关系格局,甚至有西方学者不无危言耸听地指出高加索冲突将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1]125当前高加索地区还成为在乌克兰冲突中西方牵制俄国的“第二战场”。正因如此,国内外学术界对后苏联时期高加索冲突的研究至今未衰;我国学者对高加索冲突的研究可以为我国外交政策、能源战略、民族和宗教政策等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高加索冲突有四层含义,一是前苏联末期高加索各民族与苏联中央政府的冲突;二是苏联解体后北高加索各民族之间以及与俄罗斯联邦中央政府的冲突;三是外高加索各国之间和国内的冲突;四是俄罗斯及其北高加索地区与南高加索尤其是与格鲁吉亚之间的冲突。国内外学者对高加索冲突的研究大都着眼于民族主义、领土纷争、原教旨主义与恐怖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资源争夺和大国博弈等方面,而民族主义是他们首先关注的问题。
一、民族主义与高加索冲突
欧美学者在谈到苏联解体以及高加索冲突的原因时,一般都认为帝俄与苏联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了境内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美国学者鲍里·托克等认为沙俄对境内各族人民实行了残暴的统治,俄罗斯帝国是各民族的监狱,[2]20因而沙俄时代的民族征服和不平等民族关系便为苏联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埋下了伏笔;美国学者S.帕特等则指责苏联政府在解决民族问题时出现了许多失误,例如将“格鲁吉亚事件”①格鲁吉亚事件指苏联成立前后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争取以独立民族共和国身份平等加入苏联而与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共(布)中央部分领导人进行坚决斗争的事件。的影响扩大化等,为苏俄遗留了许多未能解决的民族问题,成为苏联民族问题复杂性的原因之一。[3]96-98美国学者乔治·理波认为苏联民族政策的一些重大失误(例如民族迁移、民族驱逐、民族融和等政策)使其民族矛盾长期以来非常尖锐;[4]27-32大卫·科兹等人则指出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导致苏联境内各民族民族意识的增强,促成了苏联的解体。[5]186-193
近些年来学界尤为关注苏联时期的“民族融合”政策。我国学界和社会一般认为民族融和政策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苏联时期的“民族融合”政策却导致了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美国学者罗伯特·康奎斯特、唐科斯等学者认为苏联的民族政策前后有变,初期提倡民族自决与民族平等,而到后期则要消除民族差异,要强行将各民族融为“苏联人民”,这反而激起了民族分离主义倾向。[6]我国学者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民族融合”政策也有所认识,在钱乘旦主编的《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一书中详细地阐述了“民族融合”政策的产生和实施。[7]238-241但非常可惜的是该书并没有深入探讨下去,尤其是没有能够指明“民族融合”政策与民族分离主义之间的关系。
美国学者斯万·E·科内尔与康奎斯特的认识相反,他认为民族自治而不是“民族融合”政策催生了民族分离主义。他认为前苏联时期的民族自治共和国在边界、群体认同、国家公共机构、领导层和大众传媒等方面为民族分离主义的形成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他特别指出了苏联解体后高加索冲突的逻辑与规律:自治少数民族比非自治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更大、与中央政府的冲突更多。[8]9-19
民族主义因素在后苏联时期的高加索冲突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安德鲁·福克斯尔在其《后苏联时代的民族关系:北高加索的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一书中认为,虽然苏联是以和平的方式解体了,但其民族关系却恶化了,并对俄罗斯国家的稳定及其未来的发展构成了主要的威胁。[9]作者对民族关系和民族主义因素在历次北高加索冲突中的作用作了细致的分析,强调了民族划分、民族认同与民族特性在冲突中的决定性作用。
司法恩特·E·康奈尔是西方学者中首位对高加索冲突作全面、系统研究的学者,在其《小民族、大权力:高加索民族政治冲突》一书中系统介绍了高加索地区自1783年车臣达吉斯坦叛乱至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的历次民族冲突和战争,还阐述了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对高加索的政策与争夺,指出了民族争端和大国争夺是高加索冲突的主要原因和内涵。[1]
针对高加索地区的一些具体冲突,西方学者也多有从民族主义方面论及的。叶卡捷琳娜·萨基利亚斯卡娅在《意识形态与冲突:十年战争期间和之前的车臣政治民族主义》一文中探讨了车臣民族主义与俄政治冲突的关系。她认为车臣提出国家独立的要求虽然是较近时期才出现的,但与车臣民族四五千年以来形成的民族认同是直接相关的,继而探讨了自俄国征服以后产生的车臣民族的集体记忆:冤屈、胜利和多文化共存。正是这些集体记忆强化了车臣民族的民族认同,到了1991年左右便产生了反对俄国同化的民族分离主义情绪。[10]102-138
维克多·A·施尼热尔曼在其《奥斯特科霍伊族的复兴》一文中则从相反的方向探讨了民族认同与领土争端的关系,即领土争端造成民族认同的加强。奥斯特科霍伊族本已在历史长河中融入了车臣民族和印古什民族,有的自称为车臣人,有的自称为印古什人,并长期居住在车臣和印古什共和国边界地区。但当1991年后车臣与印古什发生领土争端时,却强化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意识,又开始自称奥斯特科霍伊人。[10]139-147
二、文学与宗教视角下的高加索冲突
从民族主义或民族认同的角度来探讨高加索冲突固然抓住了问题的重心,但对一部分读者来说还不能满足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更加丰满的认识,于是从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中来管窥高加索的民族主义和冲突亦成为一些学者努力的方向。当然,因为这些学者研究的文本主要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作品,所以他们探讨的主要是19世纪俄国文人认识的高加索人和俄国与高加索的冲突。
西方学者苏珊·雷顿的《俄国文学与帝国: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时期对高加索的征服》就是这一领域的一部力作。该书主要以19世纪俄国的文学作品为文本,分析了文人们对高加索战争即俄国帝国主义的态度以及对高加索民族的认知,并最终形成了对自己半欧洲半亚洲身份的认同。[11]
我国学者刘亚丁在其《19世纪高加索战争的文学再现》一文中以来蒙托夫和托尔斯泰为例,从他们的传记与作品中勾勒出了俄罗斯帝国军队与反叛山民的关系以及作者对帝国拓疆政策和反叛山民的态度。他认为俄罗斯作家的高加索题材写作揭示了高加索各民族真实的心理结构,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12]30-46
近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高加索冲突的认识越来越多维化,除了继续探讨民族主义、文化差异、文学视野中的高加索冲突等方面外,还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扩张、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资源的争夺以及大国博弈等方面来审视高加索冲突。研究范围的扩大是与21世纪初以来高加索冲突中实际因素增加的事实相一致的。
几乎在前苏联解体的同时,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开始兴起,并对高加索冲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学者们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了高加索冲突的宗教(伊斯兰教)因素上。摩西·盖墨在其《从民族主义的挑战到伊斯兰教的挑战:以达吉斯坦为例》一文中认为达吉斯坦的统治精英最初遇到了国内众多民族民族主义的挑战,但随后则遇到了国内瓦哈比教派的威胁;在车达冲突中许多国内的瓦哈比派教徒加入到了车臣一方,并在战争结束后返回达吉斯坦,构成了国内的反对派。该文指出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高加索冲突中的作用。[10]179-193
布赖恩·格林·威廉姆斯在其《安拉的战士:车臣叛乱中外国战士和基地组织的作用》一文详细介绍了在车臣战争中外来参加圣战的士兵和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组织成员的数量及其作用,认为虽然俄国政府夸大了他们的数量和作用,但是他们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10]156-178我国学者赵龙庚也强调了北高加索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对该地区的冲突所起的恶劣影响,并提出了防止极端势力的一些方法,例如重视宗教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推行稳妥的宗教政策、发展民族和贫困地区的经济、封堵国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13]36-38
罗伯特·W·沙弗是西方学者中对北高加索地区伊斯兰教派分析较为细致的学者,并充分认识到了伊斯兰教的教派纷争,尤其是原教旨主义对该地区冲突所起的作用。他在其《车臣与北高加索的冲突》一书中分析了北高加索地区的教派源流,指出了该地区占统治地位的苏非派与瓦哈比派之间的对立加剧了该地区的各种冲突。[14]
俄国学者阿·亚尔雷卡波夫在其《高加索的伊斯兰教及其对俄罗斯地区冲突的影响》一文中同样细致入微地分析了今日高加索地区伊斯兰各教派,指出了伊斯兰教政治化的倾向和各教派的分离主义倾向、未来国家理想,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与地区冲突的联系。他还认为伊斯兰教填补了后苏联时期高加索地区的意识形态空白,并成为冲突各方掩盖自己真实目的的一面幌子。[15]28-37
三、经济问题、大国争夺与高加索冲突
高加索地区内部的经济问题和外部的大国争夺进一步加剧了冲突。无论是民族分离主义还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出现,都是有其社会经济因素的,这一点也得到了多数国内外学者的一致认可。欧美学界一般认为前苏联的一些经济政策导致了高加索等地区经济落后。自沙俄时代起,俄国便开始对包括高加索在内的被征服地区进行经济上的掠夺和压制。鲍里·托克认为沙俄在三百年间一直掠夺被征服地区的土地,同时还实行移民政策,更加重了对当地人的掠夺;多米尼克·理温认为沙俄政府禁止在民族地区发展工业,企图使这些地区沦为俄罗斯中央地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并征收大量苛捐杂税,结果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苏联时期的某些经济管理制度和政策加深了高加索等民族地区经济的落后和离心倾向。例如,美国学者理查德·波顿认为苏联的集权管理使民族地区丧失了经济发展的自决权,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苏联政府的不满;[16]116-274M.列维认为苏联政府迫使民族地区搞单一经济,使其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从而成为俄联邦的经济附庸。[17]102-106
到了苏联末期和后苏联时期,国内外学术界一般认为因为高加索各国以及国内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加剧了民族矛盾和冲突。我国学者钱乘旦认为阿塞拜疆政府对纳卡地区投资少,导致该地区经济发展迟缓,从而成为纳卡问题的原因之一。[7]293不过西方学者埃德蒙·赫兹格等人认为纳卡与阿塞拜疆其他地区并无明显的经济差异,因此不能从经济因素来考察纳卡问题。赵龙庚指出,高加索地区长期的经济落后和人民贫困是该地区局势不稳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北高加索,车臣和达吉斯坦在后苏联时期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相比,社会经济发展明显滞后,失业率和赤贫现象比较严重,成为动荡的重要诱因。[18]39
后苏联时期高加索冲突的外部因素则主要是大国(国际)的争夺。我国学者赵龙庚认为在地缘政治上高加索是俄罗斯南部的屏障和通往西南亚和中亚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美国在苏联解体后对外进攻战略中的桥头堡,二者冲突在所难免;从地缘经济来看,高加索附近的里海油气资源丰富,成为俄、美、土耳其、伊朗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等国家和组织的必争之地。[18]39-40这样,大国争夺加剧了高加索冲突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四、存在的问题与理论突破
国内外学者对高加索冲突的认识似乎已经较为全面和深刻,但是细究之下可以发现,对高加索冲突的研究虽然涉及到了很多方面,但是这些方面之间却缺乏有机联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研究者没有认识到这些冲突的共性和主要因素,进而不能采用一种较为普遍的分析模型。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则可以为研究高加索冲突提供一种有效的分析模型。
民族认同是对本民族的起源、种族、历史、文化、宗教和习俗等的认同,而国家认同是公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前者是文化地域上的概念,后者是政治地理上的概念,两者是不同层次上的认同。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挪威著名学者艾达·布洛姆认为,在多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种族、民族、性别、阶级、宗教等不同的身份认同都会削弱对国家的认同,[19]263-265他实际上更多的是将民族认同等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对立了起来。
美国学者海斯认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是西方18世纪以后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政治在民族范围内更加有效)、宗教信仰的衰落(民族主义是超自然宗教的替代品)、进步历史观的兴起(民族国家有利于民族的进步)等“根本趋势”的产物,[20]225-238他实际上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等同了起来,而且论述的是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中二者的关系,忽略了多民族国家中二者之间的关系。
我国学者陈茂荣认为两者是一种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存在矛盾斗争的一面,也存在同一和统一的一面,因此要创造一系列条件促使二者的一体化才能解决现实境遇中二者的矛盾和斗争。[21]56-67对近代以来形成的西方多民族国家而言,解决二者矛盾的方法,历来有“同质化”和“多元化”之争,法国学者吉尔·德拉诺瓦或许为此提供了最好的回答,他认为从国际上来看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有其正当性,但也不能形成报复殖民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而应尊重历史进而超越历史;从多民族国家内部来说,只有保障少数族群的权利、尊重个体对文化认同的选择权,民主共和的政治共同体或政治民族才能建立起来。[22]7-8这样,德拉诺瓦便使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了起来。
笔者认为历次高加索冲突虽然包含了众多因素,但共同的和根本的一点是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事件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在研究高加索冲突时应注意考察哪些因素导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分裂,尤其要考察俄罗斯在高加索的殖民主义史和高加索各民族反殖民主义的历史,考察俄国和高加索各国政治制度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所带来的影响,考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大国斗争是如何加深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分裂。由此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在多民族国家的我国有无可能以及如何避免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分裂,甚至有无可能以及如何由民族认同上升到国家认同等。因此,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作为分析高加索冲突的理论模型,这样的研究既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又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SVANTE E.CORNELL.Small Nations and Great Powers:a study of ethno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Caucasus[M].London:Curzon Press,2001.
[2]GREGORY GLEASON.Federalism and Nationalism:The Struggle for Republican Rights in the USSR[M].Colorado:West view Press,Inc.,1990.
[3]S.PATE.The Geopolitics of Leninism[M].London:HSS,1982.
[4]JORGE LIBO.The Soviet Unions’National Policy during the 20s of the 20th Century[J].Nation and Race Studies,1991,(1).
[5]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M].曹荣湘,孟鸣歧,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6]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M].刘靖北,刘振前,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7]钱乘旦,主编.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8]斯万·E·科内尔.作为冲突来源的自治:关于高加索冲突的理论探讨:上[J].胡敬萍,译.世界民族,2007,(1).
[9]ANDREW FOXALL.Ethnic Relations in Post-Soviet Rus sia:Russians and Non-Russians in the North Caucasus[M]. Hoboken:Taylor and Francis,2014.
[10]MOSHE GAMMER,ed.Ethno-Nationalism,Islam and the State in the Caucasus:Post-Soviet Disorder[C].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
[11]SUSAN LAYTON.Russian Literature and Empire:Conquest of the Caucasus from Pushkin to Tolstoy[M].Cambridge: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12]刘亚丁.19世纪高加索战争的文学再现——以莱蒙托夫和列·托尔斯泰的行旅和创作为例[J].俄罗斯研究,2011,(2).
[13]赵龙庚.中亚和北高加索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活动及警示[J].亚非纵横,2006,(6).
[14]ROBERT W.SCHAEFER.The Insurgency in Chechnya and the North Caucasus:from Gazavat to Jihad[M].Santa Barbara: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2010.
[15]阿·亚尔雷卡波夫.高加索的伊斯兰教及其对俄罗斯地区冲突的影响[J].齐昕,编译.俄罗斯文艺,2013,(4).
[16]RACHEL DENBER.The Soviet Nationality Reader:The Disintegration in Context[M].Colorado:Westview Press Inc.,1992.
[17]M.LEWIN.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18]赵龙庚.高加索地区的问题及症结[J].现代国际关系,2000,(10).
[19]夏继果,杰里·H.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D].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0]海斯.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M].帕米尔,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1]陈茂荣.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J].学术界,2011,(4).
[22]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三联书店,2005.
〔责任编辑艾小刚〕
On Current Situation of Caucasus Conflict and the Theoretic Breakthrough
Jia Yingliang
(School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Gansu 730020,China)
Scholarsfocused on nationalism,literature,religion,economical development and contest between great powers in the studies on the conflict in Caucasus,but neglected the key factor in the conflicts.So,they could not adopt an universal analytical model,which is disadvantage to us understanding more deep.The relation between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s an effective theoretical model to analyze the conflict in Caucasus.
the conflict in Caucasus;ethnic identity;national identity
D73-62
A
1671-1351(2016)01-0110-04
2015-12-23
贾迎亮(1980-),男,河北邢台人,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
天水师范学院中青年科研资助项目(TSA1408)“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视阈下的后苏联时期高加索冲突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