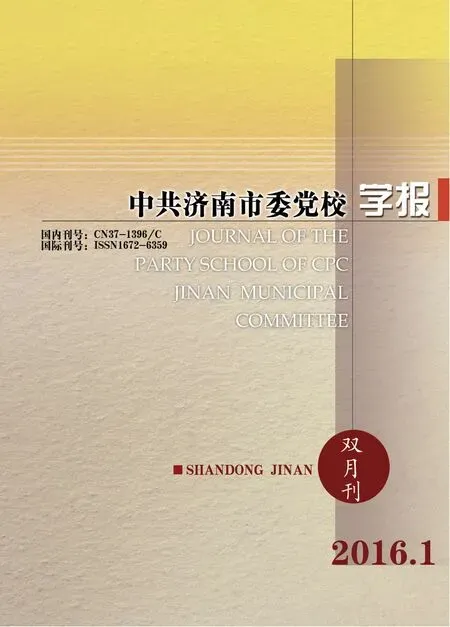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心态演变
王 军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心态演变
王军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从懵懂无知到逐渐了解再到热烈拥抱的过程,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也或急或慢地从傲慢抗拒到无可奈何再到心悦诚服。直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才在西方文化面前慢慢树立起不卑不亢、从容自信的心态。对于一个国家、民族而言,文化自信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强大,而强大的硬实力则是文化自信的支撑和保障。历史启示我们,无论何时都要对西方文化秉持积极、开放、包容的态度,这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自觉的体现。
关键词:西方文化;历史境遇;文化心态;文化自信;文化自觉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不管是高兴还是痛苦,鸦片战争将中国卷进了西方列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落后的东方民族、农业社会、君主专制在帝国主义的枪炮、机器、资本面前一点点败退、瓦解。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这样急剧的短兵相接中,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从懵懂无知到逐渐了解再到热烈拥抱的过程,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也或急或慢地从傲慢抗拒到无可奈何再到心悦诚服。直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才在西方文化面前慢慢树立起不卑不亢、从容自信的心态。回顾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历史境遇,以及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时的心路历程,对于我们今天处理好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开明接纳和傲慢自负:鸦片战争前的西学东渐
明末清初之际,西方新航路开辟正如火如荼,大量传教士追随殖民者的足迹开始了向东方传播“福音”的艰难使命。不过早期的传教士为了让中国人接纳他们,采取了迂回的策略,因而首先充当的是自然科学老师的角色。随着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在中国的成功,西学在中国的影响逐步扩大甚至影响了康熙皇帝。
在清朝历代皇帝中,康熙无疑是最开明的一位,他本人也成就了一段西学东渐的佳话。康熙帝不仅鼓励和提倡学习、模仿西方科学文化,选拔一批满汉青年交由耶稣会传教士学习,而且因为中西历法的争论,自己也开始对科学事物尤其是数学发生兴趣。[1]康熙第一个外籍老师是南怀仁,负责教授天文学和数学。此后又找了几个传教士教授医学、化学、药学、人体解剖学。康熙非常好学而且热情高涨,不管天气炎热还是刮风下雨,传教士们都要去给康熙上课。[2]
然而随着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日大,天主教内部就如何翻译“神”的称谓和是否同意中国信徒保留祭祖和祭孔的传统习俗产生了所谓的“礼仪之争”。1700年(康熙39年)康熙皇帝介入了礼仪之争,声明祭祖祭孔属于中国传统习俗,不属于宗教活动。1704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公然下令,禁止中国教徒举行祭祖、祭孔等活动,禁止把“上帝”和“天”作为“天主”的别称并派特使来华谈判。康熙皇帝得知后大怒,认为此举属于干涉中国习俗,并降旨称:“谕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之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经过几番讨价还价,罗马教皇被迫让步,于1720年宣布同意中国信徒举行非宗教性的中国礼仪,康熙帝则下令只准许尊重中国礼仪的传教士居留中国并禁止公开传教。[3]
“礼仪之争”后,康熙皇帝对传教士的态度急转直下,传教士作为沟通中西文化桥梁的作用也随之受到极大削弱。继康熙皇帝之后的雍正皇帝,因为传教士中的一些人曾经在他的继位问题上明显地站在他的反对者一边,因而对传教士采取了比其父更为严厉的限制措施。雍正帝认为,天主教作为外来宗教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只能引起中国人的憎恶,大清王朝如果允许这种宗教在中国流行,只能有损王朝声誉。基于这种认识,雍正帝对西方科学技术也不像康熙帝那样热心。到了乾隆时期,尽管乾隆皇帝爱好收藏西方的艺术作品,甚至让传教士郎世宁参与设计了具有意大利风格的圆明园,但是他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文化却采取了极端蔑视的态度。[4]
至乾隆后期编纂《四库全书》,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明末以来传到中国的西学作了总体评价,并影响了鸦片战争后国人对西学的认识和策略。纪晓岚在评价《西学凡》一书时认为,西学“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在介绍明末传教士傅泛际译《寰有铨(诠)》条目中,纪晓岚又评论西学道:“欧逻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千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从上述观点来看,纪晓岚对西学的评价可谓两极分化,一方面认为西学科技“实逾千古”,另一方面又认为西学是“器数之末”;一方面认为西学“以格物穷理为本”与儒学相似,另一方面又指责西学“所穷之理支离神怪”、“议论夸诈迂怪”,由此总体视西学为“异学”、“异端”。鉴于这种矛盾的认识和评价,纪晓岚认为“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是明智且富有远见的。然而,殊为遗憾的是,纪氏虽然迂腐但又不失开明的观点却在后世知识分子那里彻底简化异化为保守排外,以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还要小心翼翼地摘录纪氏观点作为“师夷长技”的论据和免遭守旧派讨伐的护身符。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无论是守旧派还是开明派的主张基本上都没有超出纪氏对西学的认识和评价。[5]
回顾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和态度经历了一个倒U型的曲线:从明朝末年到清康熙是处于上升时期,这一阶段统治者对传教士的态度总体上是越来越开明,传教士为中国带来了丰富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眼界。从清康熙到乾隆时期则是处于下滑时期,统治者对传教士趋向严苛、对西学的态度也走向保守排斥,因而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越来越萎缩。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在西学东渐的上升时期还是下滑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自尊自信乃至自负都是始终如一的,即使是徐光启、李之藻这样深受利玛窦影响并信仰天主教的西学中坚人物也无不认为中国文明自有长处,即使与西学相比有弱点和不足,但依然是西学所无法比拟的。[6]另外,康熙后期至乾隆时西学东渐走向偃旗息鼓,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固然是导火索和重要外因,但最根本的恐怕还是此时正处于经济繁荣的康乾盛世,汉族民心已归,满族统治者也逐渐“从夷变夏”并开始以华夏正统、中华文明的捍卫者和继承者自居,一个突出的例证便是乾隆帝毕生致力于文学事业,一生创作4万多首诗词(且不论质量或代笔之作),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二、无力抗拒和自我安慰:洋务运动时的西学中源
“西学中源”①说在洋务运动时期达到鼎盛并几乎成为开明知识分子对西学的一种普遍认知。鸦片战争后,最早觉醒的林则徐、魏源等知识分子提出“制夷——悉夷——师夷”的主张,后终于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明洋务派中成为现实。但是,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步履维艰,因为守旧派坚称西方科技是“奇技淫巧”,而且与立国之本的伦理纲常绝不相容。为争舆论制高点,“西学中源”说就成为守旧派和开明派互相攻击的论据。守旧派认为西学剽窃中国古学从而贬低排斥西学,洋务派则认为西学既然是中国古已有之而后传到西方的,那么西学与中学本是一家,而不是什么与华夏文明不相容的夷狄之学。既如此,学西学不过是“礼失求诸野”,是找回失落的中华文明、继承祖宗文化遗产的义举。应该说,“西学中源”说在开明派这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守旧派给开明派扣的“用夷变夏”的罪名也就难以成立。[7]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中源”说成为开明派大胆采用西学的自信依据和护身符。
1865年,李鸿章为了论证派人去西方学习机器制造并不违背中国传统,曾舌灿莲花地写道:“无论中国制度文章,事事非海外人所能望见,即彼机器一事,亦以算术为主,而西方之借根方,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亦不能昧其所自来。尤异者,中术四元之学,阐明于道光十年前后,而西人代数之新法,近日译出于上海,显然脱胎四元,竭其智慧不出中国之范围,已可概见。……中国亦务求实用,焉往不学?学成而彼将何所用其骄?是故求遗珠不得不游赤水,寻滥觞不得不度昆仑。”如果说李鸿章生搬硬套“西学中源”说还有作为“策略”的考虑,那么当时中国的一些饱学之士,在接触、了解西方近代科技后推测其古代源头可能出自中国,则有着无可怀疑的真诚和自信。例如,被称为“中国照相机之父”的海南学者邹伯奇(1819-1869年),就曾经论证过“西法皆古所有”,并且作出了“西学源出墨子”的判断。[8]
不单是洋务运动早期国内开明派官员和知识分子持“西学中源”论,即使到了洋务运动后期,有着丰富海外阅历和深厚西学功底的人士也如此认为。遍游英法诸国、长期居于香港、后又考察日本的王韬(1828-1897年),这位最早提倡废除封建专制的彻底西化论者,也对西学出自中源笃信不疑,他写道:“中国,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当尧之世,羲和昆仲已能制器测天,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而兄弟四人分置于东西南朔,独于西曰昧谷者,盖在极西之地而无所纪限也。”他还以数学、乐器、船舰、指南车、霹雳炮、测天仪器、语言文学等为例,说这些都是“由东而西,渐被而然”的。到了90年代,担任驻外使节、与西方各界知名人士有着密切交往、对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着切身体会的薛福成(1838-1894年)在日记中依旧相信西学源出中国,他说:“即如《尧典》之定四时,《周髀》之传算术,西人星算之学未始不权舆于此。其他有益国事民事者,安知非取法于中华也?昔者宇宙尚无制作,中国圣人仰视俯察,而西人渐效之。今者西人因中国圣人之制作而踵事增华,中国又何尝不可因之?”[9]
但是它却说明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是历史上的常态,而且暗含的逻辑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影响(古代由东向西、近代由西向东)。回顾“西学中源”说的发展史,还让人不得不感叹,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是如此的自恋自信自负(当然也不乏阿Q似的自我安慰)。
除了“西学中源”说,另一个被开明派用来抵挡守旧派口诛笔伐的文化武器是“中体西用”。不过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开展,开明洋务派实际上一直在突破“西学中源”、“中体西用”文化理论范式的束缚。“洋务运动发展到80年代初,许多人已经把学习西方的重点,逐步转向筹建和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机制。他们不只是谋求军事上之强,而且要谋求经济上之富;不只是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主张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或者可以说,当时许多先进的思想家们,事实上已经提出了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为模式,来改造中国的时代使命。”[10]
三、深入了解和热烈拥抱:甲午战争后的西学启蒙
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一个衰弱的中国引发了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此后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既是以西学救亡图存的不断尝试,又是一次次冲破传统文化的桎梏、实现思想启蒙的艰辛旅程。率先奔走呼号、行动起来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物。早年游历香港的见闻以及此后中法战争的刺激,使康有为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早在1890年前后,康有为在所著的《实理公法全书》中就大力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11]此后在“托古改制”时,康有为又将人权、民主、平等、选举、议院等资本主义精神、制度变成“孔子改制”名下的内容。在变法“新政”中,康有为提出兴乡学、开民智的普及教育主张,是最光辉、最有价值的一项建议,最能体现汲取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精髓。[12]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1895-1903年)能成为与其师康有为齐名甚至青出于蓝的思想领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提倡全面学习西方民主主义文化。在大部分知识分子认可的科学技术之外,他还注意到了一些人们不够重视的领域。比如,梁启超把政治和法律摆到突出地位。他说:“国与国并立,而有交际,人与人相处,而有要约,政法之所由立也。中国惟不讲此学,故外之不能与国争存,内之不能使吾民得所,夫政法者,立国之本也。……故今日之计,莫急于改宪法,必尽取其国律、民律、商律、刑律等书,而广译之。”[13]与将“纲常名教”视为立国之本的传统文化观念相比,将法律当做“立国之本”无疑是巨大的飞跃和进步,也和封建专制的“人治”划清了界限。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上,梁启超能成为激励一代青年奋起的启蒙大师,是与他对西方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与运用分不开的。[14]
除了康有为、梁启超,当时积极传播西方文化,又与康梁持不同学术见解、不同文化观念,而且有很大影响的,首推严复。1895年春,正值甲午战败,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大谈惟有西学才能挽救中国。为了论证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严复将中学和西学置于同等地位进行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其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尽管严复做出“客观公正”的样子,但其褒贬扬抑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15]从论证方式方法看,这种选择性地抽取若干点进行比较,无疑是不科学和带有主观倾向性的,然而其说服力、针对性却极强,对破除妄自尊大的传统观念以及提倡西学确实有破旧立新作用。值得强调的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知识分子中间引起强烈的震动,特别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8字给人们以强烈的思想刺激,提醒人们若不奋发图强,中国将有亡国灭种的危机。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一场更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蓄势待发。就新文化运动而言,其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用西学反对中学并无本质差异,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要求和主张的彻底性和全面性,为谭、严、梁阶段所不可比拟。它以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激烈新姿态和新方式,带来了新的性质”。[16]在《青年杂志》发刊词中,陈独秀以中西文化对比的形式,抨击了各种传统观念,对青年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项期望要求,[17]由此拉开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新文化运动拥戴“德先生”、“赛先生”,高喊“民主”、“科学”口号,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给国人以精神洗礼。与此同时,一些外国著名学者来华讲学直接推动了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如胡适的老师约翰·杜威在中国多地讲学,为中国注入了实用主义哲学。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于1920 年10月来到中国后,在9个月的行程中足迹遍及中华南北,作了《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和《数理逻辑》等多场著名演讲,在当时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一件盛事。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促使五四作家将语言和思维进而民族精神、文化心理联系在一起,于是到了20年代表现为某种科学主义的追求,即要求或企图把西方的近代科学作为一种基本精神、基本态度、基本方法来改造中国人,并注入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在这样的背景下,1923年爆发了“科玄论战”。在论战中,张君劢等“玄学派”提倡“新宋学”,强调反求诸己、内心修养等等,展现了“现代新儒家”的方向路线;而相信“科学派”的青年人则开始走向马克思主义。此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逐渐取代了上代人所崇奉、信仰的进化论。[18]
四、阶级斗争和思想禁锢:新中国成立后西学遇冷
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19]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也多次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然而,因为极“左”路线的影响,“双百方针”和“古今中外”原则都没能很好地贯彻实行,西方思想文化一度遭到冷遇甚至退场。
由于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建国初期我国主要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非拉友好国家在文化各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我国引进了芭蕾舞、交响乐、歌剧、油画等许多西方古典艺术门类,培养了大批优秀文艺人才,大大丰富和繁荣了我国文化艺术的百花园;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文化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中国京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乐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一大批完全有别于旧社会戏班子的新型文艺院团;全国各地建设了大量的影剧院、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益文化设施,基本结束了旧中国文化事业积贫积弱的局面”。[20]这些成就不可谓不大,但主要还停留在歌舞表演等较浅的视听层面,真正的思想文化交流非常有限。
五、求知若渴和话语抢夺:改革开放后的西学升温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终于迎来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从而彻底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与西方国家资金、技术一并进来的还有资本主义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以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西方思想文化在掌握话语权的情况下澎湃而来、不可阻挡。
打破与西方思想文化交流的僵滞局面,首先需要译介书籍。据北京主要出版社的统计,1949年到1984年这35年中,每年平均出版社科新书约250种,其中翻译的只占一小部分。然而到了1985年,仅翻译出版社科著作就有399种,1986年为477种,1987年已经有600多种,1988年仅第三季度就翻译出版了600多种。[21]大量西方书籍的出版一方面极大满足了大学生求知若渴、寻找答案的心情,另一方面又使西方思想文化在大学生中极具影响力。
在众多西方文化思潮中,率先俘获大学生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对“自我选择”、“怀疑精神”的强调,契合了青年人对自我价值、人生道路的困惑和思考。继“萨特热”后,又出现了“弗洛伊德现象”和“尼采热”。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党内的不正之风也开始显现,有些大学生将这些不合理现象归结为一个“权”字,误认为在中国有权就有了一切,于是尼采的权力意志论与中国传统的“官本位”观念合流,形成了“尼采热”。据1988年针对京、津、穗、宁、长沙、郑州、呼和浩特、唐山等地1600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50%以上的学生读过尼采的书。北京某高校某系86级学生,60%的学生拥有一两本尼采的书,85%的学生读过尼采的书。[22]除了以上诸人的理论,马斯洛的“自我实现”、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也受到大学生的追捧。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学生思想极度活跃,以至于在后期走向膨胀和迷失。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互联网快速兴起和发展,特别是近几年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横空出世,以及智能手机上网的普及,使得西方思想文化输入中国更加方便、频繁,由此导致中国人的思想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多变多样。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值得关注的国内外十大思潮中,“新自由主义”得到9.2分,高居榜首,进入前十的还有“普世价值论”(7.5分)、“宪政民主”(5.6分)等西方文化思潮。[23]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中国越来越占据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以及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与竞争越来越深入、激烈,西方文化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交融交流交锋将成为常态。
回顾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历史境遇,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与国家的实力地位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明末清初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总体持较为开放、包容的态度,而在衰败、孱弱之际则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总而言之,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文化自信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强大,而强大的硬实力则是文化自信的支撑和保障。历史启示我们,无论何时都要对西方文化秉持积极、开放、包容的态度——我强固然无需过分紧张,我弱更要在碰撞中成长——这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自觉的体现。
注释:
①“西学中源”说的论证几乎都是采用简单比附的方式,中西文化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找出点上的相似相通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因此“西学中源”说的错谬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偏向,也源于论证方式的偏差。
参考文献:
[1][4][6]马勇.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M].东方出版中心,2008.30.42-43.28.
[2]田朝晖.“学霸”康熙[N].新华每日电讯,2014-06-13(13).
[3]刘治琳.中国与梵蒂冈之间的历史纠葛[EB/ OL].环球网,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 013-03/3702540.html.
[5][7][8][9][10][12][15]丁伟志,陈崧.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上卷)[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34-135.122.122-123.124-125.115.182-189.223-22 5.
[11]姜义华,张荣华(选注).康有为文选[C].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3-21.
[ 1 3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 M ] .北京出版社,1999.47.
[ 1 4 ]汪澍白.文化冲突中的抉择——中国近代人物的中西文化观[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190-192.
[16][1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48-63.
[17]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74-77.
[ 1 9 ]毛泽东选集(第3卷) [ M ] .人民出版社,1991.1083.
[20]蔡武.新中国六十年对外文化工作发展历程[N].中国文化报,2009-07-29(1).
[21][22]杨德广.西方思潮与当代中国大学生[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19.81.
[23]周素丽,潘丽莉,高骊.2014中外十大思潮调查评选——2010-2014社会思潮动向调查分析报告[J].人民论坛,2015(1上):14.
(责任编辑 丛文娟)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2015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当代大学生文化心态调查与分析”(15Z14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359(2016)01-0073-06
作者简介:王军,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邮政编码 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