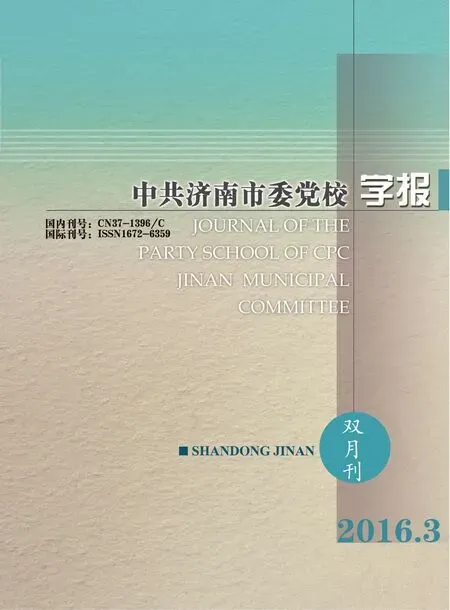身陷政治漩涡的中唐女性
——评电影《刺客聂隐娘》塑造的人物形象
刘 凤 李迎春
身陷政治漩涡的中唐女性
——评电影《刺客聂隐娘》塑造的人物形象
刘 凤 李迎春
电影《刺客聂隐娘》以个性化的叙述手法、独特的镜头语言重现了唐朝中叶波诡云谲的政治氛围。在时代激荡的政治漩涡中,以聂隐娘为代表的女性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历史的实践者。此部影片成功塑造了几个性格迥异、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引发观众关于人性、命运、政治与抗争的思考。
政治;中唐女性;人物形象
2015年,《刺客聂隐娘》在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斩获最佳导演奖。这部由台湾导演侯孝贤根据唐代传奇小说改编的电影,以其个性化的叙述手法、独特的镜头语言,向世界重现了8世纪中叶的唐朝所具有的恢弘、精致、华美以及波诡云谲的政治氛围。
安史之乱后,唐帝国从盛世巅峰猝然跌落。表面上仍然维持着大一统,但帝国内部藩镇兴起、割据一方,形成“国中之国”。藩镇与中央之间若即若离,彼此随时可能金戈铁马、剑拔弩张。在大小林立的数十个藩镇中,尤以河朔三镇拥兵自重,长期与朝廷分庭抗礼。“河朔宁,则天下宁;河朔得,则天下得”。在这种时空背景下,以聂隐娘为代表的一批女性被强大的政治漩涡所裹挟、激荡,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历史的实践者,以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影响甚至改变着历史洪流的走向。
影片围绕聂隐娘行刺表兄田季安这条故事主线,层层深入、抽丝剥茧展现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并由此塑造了一系列性格迥异、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在此,本文对聂隐娘、嘉诚公主、道姑、田元氏、胡姬等5个女性进行逐一点评,探析影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拿捏。
一、“剑术已成,道心未坚”的聂隐娘
一袭黑衣、手持匕首、表情冷漠、动作迅疾,或藏于树上,或隐于帘后,神秘莫测,典型的刺客形象。聂隐娘的出场,是以为师傅完成一次刺杀任务为起点的——“为我刺其首,无使知觉,如刺飞鸟般容易。”此时的聂隐娘,惟师命是从,不细问缘由,默默接过匕首,隐匿于斑驳陆离的树影间,待目标逼近,纵身一跃,手起刀落,干脆、决绝、不假思索。“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惟有树叶映衬着阳光随风作响。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武功绝伦、铁面无情的刺客,在第二次行刺时却“意外失手”。隐娘奉师命潜入大僚府内,藏于梁上,静待时机。而此时,大僚正与小儿嬉戏玩耍,好不欢愉。待大僚与小儿于榻侧酣睡,本是行刺良机,隐娘却迟疑未动手。师傅怒问缘由,隐娘回答:“见大僚小儿可爱,未忍下手。”一句简洁的话语为我们呈现了这个看似无情的刺客颇为感性的质地。或许,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去探析隐娘藏于梁上静观府内情形时所经历的心理变化。13年前,隐娘因故被道姑掳走,远走他乡、漂泊异地,这对于一个10岁的小女孩来说该承受了多么大的心理冲击!尽管岁月流逝,隐娘已长大成人,并被培养为一名杀人如刺飞鸟般的刺客,但在她的内心深处,依然有一块最柔软的部分,保持着那份被割裂的童真、割舍的亲情。见到大僚与小儿嬉戏,此情此景,又何尝不触动她内心柔软的质地,曾经失去父爱的她,怎忍心让悲剧再次重演?于是,失手已是意料之中。
山间道观,曲径通幽。“汝剑术已成,而道心未坚,今送汝回魏博,杀汝表兄田季安。”师傅再次给隐娘下达了指令。此次刺杀,于公于私,看似都合情合理。于私,田季安背信弃义,抛弃婚姻承诺;于公,田季安嗜好杀伐,暴虐成性,是朝廷稳定的隐患。然而,随着事情的步步深入,隐娘知道当年田季安悔婚是情非得已,而且田季安对隐娘父亲的救命之恩一直铭记在心。隐娘起初以为“杀一独夫贼子能救千百人”,拨开政治迷雾之后却发现,各派势力在魏博明争暗斗,“杀田季安,嗣子年幼,魏博必乱”。隐娘看到了这种政治大势,决定不杀。在和师傅诀别后,隐娘与磨镜少年、采药老者踏上了北上新罗之路。由此,隐娘终于结束刺客生涯,重获个人自由。
二、“青鸾舞镜,终宵奋舞而绝”的嘉诚公主
影片中,嘉诚公主是作为旁人的回忆而存在的。早在3年前,嘉诚公主大恸咯血而亡。作为朝廷与魏博之间政治联姻的牺牲品,嘉诚公主的一生是孤苦凄冷的,然而她却以决绝之心、柔弱之身守护着魏博与朝廷之间脆弱的和平,“不让魏博跨越河洛一步”。
嘉诚公主作为母亲,当然希望自己抚养长大的儿子田季安能与青梅竹马的窈七(即聂隐娘)结为伉俪,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不要在下一代身上重演。所以在田季安冠礼那年,将一对玉玦作为婚约信物分赐二人。然而,理想看上去总是很美,当洛州刺使元谊带万人来投奔时,为了让庶出的儿子在未来的继位斗争中增添砝码,嘉诚公主不得不棒打鸳鸯,“屈叛了阿窈”。这也成为嘉诚公主临死时无法释怀的一件事。
在嘉诚公主的身上,始终弥漫着悲情、抑郁的气氛。纵使有着异于常人的坚忍,也经受不住接连的人生变故——“四年前先皇崩,皇侄继位一年又崩”,终于大恸咯血,香消玉殒、珠碎玉断,“京师带来繁生得上百株的白牡丹”也随着枯萎。
片中,蕙质兰心的嘉诚公主以一段“青鸾舞镜”的场景而惊艳。她一身华服、独坐庭院,斜倚古琴,身后牡丹似雪,开得正旺。琴声时而急促、时而舒缓,纷乱繁杂,公主喟叹道“罽宾国王得一鸾,三年不鸣,夫人曰:‘尝闻鸾见类则鸣,何不悬镜照之。’王从其言。鸾见影悲鸣,终宵奋舞而绝……”这是公主人生的真实写照,从风华绝代的京师来到陌土,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
三、“剑道无亲,不与圣人同忧”的道姑
作为嘉诚公主的同胞妹妹,嘉信公主却反其道而行之,走上了一条“以暴易暴,以杀止杀”的道路。一身白衣,一把拂尘,表情肃然,寄居于深山道观中,游走于芸芸尘世间,高举“替天行道”之旗帜,施展杀伐决断之法度。她将窈七带走,隐入山间,妄图将窈七训练成“斩绝人伦之亲”的刺客,替她刺杀一切有碍于中央大一统局面的藩镇统领、大僚。
作为公主,生命的底色天生就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尤其是生逢乱世——“出生时,正值吐蕃兵掳掠京师,孝武先皇出奔陕州,双胞公主给送到五通观避难”。从小在道观长大,习道悟道,只不过她心中坚守的“道”是“杀一独夫可救千百人,则杀之”。她的这种“道”,是绝对的“道”,也是孤立的“道”。“此僚制毒弑父,杖杀胞兄”,在她看来,这就足以成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理由,必杀之而后快。同样,对暴虐的田季安也必须“斩绝人伦之亲”而杀之。她看不到也不考虑历史大幕之后掩藏的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她需要的是粗暴、简单、干脆的“以暴易暴、以杀止杀”。正是有了心底的这份执着,才有了她一而再再而三命隐娘行刺节度使、大僚等人。
与嘉诚公主一样,道姑本身也是一个极具悲情色彩的人物。姑且不说,她作为千金公主的身世与道姑的身份所形成的巨大差异,就她抚养、训练隐娘成杀手而言,也是以失败告终。师徒俩终于“道不同不相为谋”,恩断义绝。
四、心狠手辣、挟势弄权的田元氏
中国历史上,外戚干政的事例比比皆是。在《刺客聂隐娘》中,田元氏家族树大根深、力量雄厚,政治上党同伐异、铲除异己,企图坐拥天下。
作为几个孩子的母亲,田元氏很早就开始为其儿子登基扫除障碍。宫中眼线众多,且安排精通巫术的师傅坐镇,其他妃子如有身孕,必以纸人符咒巫术除之。阴谋揭穿后,她善于利用子女作为挡箭牌——当田季安怒冲冲闯入田元氏寝宫,将纸人摔向田元氏时,“坐拥孩子们的田元氏,白着脸并无惧色”。在她看来,凭着她为皇室传承的龙脉和自己雄厚的家族势力,纵使贵为藩主的田季安又能奈何!
实际上,作为政治联姻的产物,田季安与田元氏早已是貌合神离,夫妻情意荡然无存。在本片中,看不到两人亲昵的举动,有的只是相互猜忌、恫吓与争斗。衙前兵马使田兴被贬为临清镇将,田季安特命聂虞候亲自护送,且步入田元氏宫中特地说道“三年前活埋丘绛之事,不可再有”,这无疑是对田元氏的郑重警告。然而,田元氏却不肯罢手,反而变本加厉,命人迅疾追杀田兴,差点再次上演活埋事件。
片中,田元氏还具有另一重身份——作为顶尖杀手的精精儿,与聂隐娘在树林间的岚雾深处有着惊心动魄的激战,“一战,再战,三战,精精儿护卫田元家的意志是如死一般坚决”。这为这个谜一样神秘的女人增添了强悍、可怖的色彩。
五、心存善念、力求自保的胡姬
论地位,胡姬出身舞伎;论根基,她来自西域,无雄厚家族势力。在步步惊心的宫廷斗争中,她深知自己处于劣势,惟有谨小慎微才能求得生存。她以鸡血伪冒月事,企图骗过田元氏的耳目,掩藏已有身孕的事实,但她同时也对宠爱她的田季安刻意隐瞒,并未主动寻求保护。她的这份天真终于被无情地碾碎。田元氏的师傅空空儿施展符咒,“胡姬遭丈高人形扑来,罩住全身”,在生死攸关之际,幸得隐娘搭救,才保全性命。
胡姬内心保存着朴素的善恶观念,具有同理心。当田季安跟她讲述自己与窈七青梅竹马却被拆散、窈七被迫远走他乡的往事时,胡姬叹道:“替窈七不平!”此时胡姬定然感同身受,既为窈七不平,也为自己不平。身处政治夹缝、本来与世无争的她,却不得不时刻提防着明枪暗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作为一部个人色彩很明确的作品,侯孝贤执导的《刺客聂隐娘》处处显现着独特质地。他将人物的台词简约到极致,更多地通过镜头语言表现人物的特质、关系及故事情节的发展。与其说这是一部经过剪辑的“电影”,莫如说是一幅中唐女性的群体生活画卷,关于人性、命运、政治与抗争。
(责任编辑 丛文娟)
刘凤,江西省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迎春,中国电信南昌分公司工程师(邮政编码330000)
J905.2
A
1672-6359(2016)03-0095-03
——论女性主义视域下电影《刺客聂隐娘》的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