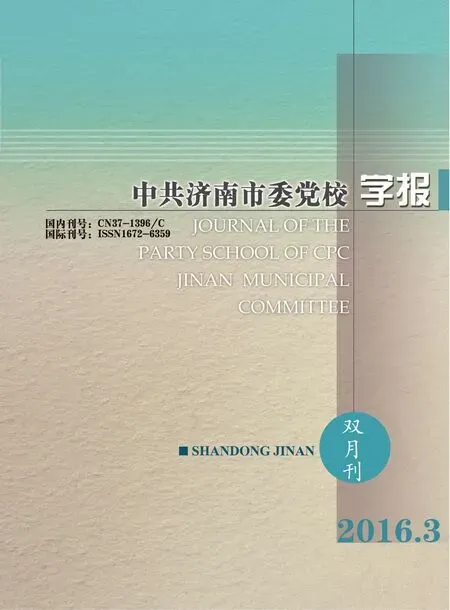基于1978—1984年中国共产党农村改革的思考
李 钰
基于1978—1984年中国共产党农村改革的思考
李 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正式吹响了号角。此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式迈出改革的第一步,而这个第一步恰是以农村为突破口,同时也带活了中国改革的大局。而今,伴随改革层次的深化和改革问题的复杂化,中国农村改革已进入瓶颈期,此时回顾1978—1984年农村改革历程,不在于获得细枝末节的指导,而在于继承锐意改革的精神、勇于破解改革难题的态度,汲取改革成功的经验和遭遇波折的教训,这不仅对于突破农村改革的瓶颈具有启示作用,而且对推进当下中国改革全局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历程;借鉴;启示
37年前,中国改革选取农村作为时代的弄潮先锋,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总闸门。经历6年积淀,1984年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至城市,掀开新篇章。37年中,改革的领域愈扩大、层次愈深化,改革所遇到的问题就愈复杂,前进的脚步也愈谨慎。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37年后的今天,当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着力破解农村改革的难题成为引领中国改革跋涉险滩、到达彼岸的关键。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我们也不可能将1978—1984年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生搬硬套于今日实践,因为时代在发展,改革在深化。今时今日,面对农村改革,我们已不可能就农业而农业,必须全方位统筹城乡发展、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1]因而今日面临的农村改革难题比起航阶段面临的问题更复杂、更棘手,但明晰历史、以史为鉴,可为当下农村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1978年党的农村改革起航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取得了诸多有益理论和实践成果,但由于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理论认识不成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走了许多弯路。在这期间,中国社会生产力长期遭受压制甚至饱受摧残,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缓慢,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难以充分体现。在农业领域,1978年我国粮食产量仅比1949年增长1.7倍,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5倍,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收入70多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高达67.7%。1978年我国总人口为9.6亿,其中农村人口为7.9亿,占全国总人口82.29%,由此可见农村改革不仅为中国发展的形势所迫,而且事关国家稳定和人民福祉,因而势在必行。[2]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吹响了农村改革的号角。[3]首先,《决定》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高速度发展是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条件”,并多次重申“真正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基础的位置上”,“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首先要考虑农业的负担能力”,这一认识完全不同于过去30年的发展思路;其次,《决定》着重通报了我国农业面临的严峻形势,不说假话、空话、套话,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几乎阔别了中国共产党20年;再次,《决定》以维护农民经济利益为原则,以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为切入点,对农民松绑,“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恢复按劳分配原则,反对不顾生产力水平拔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穷过渡”行为。
由于历史局限,《决定》依旧没能摆脱“左”的束缚,如继续宣传“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等口号,但瑕不掩瑜,《决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积极影响占据了主要方面:第一,对农业,主要思想即“重视农业,发展农业”;对农民,全力坚持“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这对扭转30年来“重工轻农”的思想和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二,《决定》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了改革,[4]进一步扩大生产大队、生产队自主权,对生产、分配领域进行调整,制止无偿调拨劳动力和绝对平均主义的行为,激活了农业生产积极因素。第三,《决定》敢于突破人民公社体制,在责任制领域开始松口,虽然文件明确指出“不许分田单干”,但承认 “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而且在“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可以包产到户,不属于上述地区的“不要包产到户”。这项突破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5]第四,对农业领域的发展进行了细致规划,有助于改善农业和农民的弱势地位,增强农业发展活力。
二、1978——1984年党的农村改革的重点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和确立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已完成了农村改革破冰的第一锤,并且就改革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形成了会议纪要。[6]
首先,纪要突出强调农业集体化的成就,明确表示“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随后,纪要指出,要“把改善经营管理,贯彻按劳分配,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当做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如此就把农民青睐的“生产责任制”提升到国家农业发展目标的政策高度。并且,纪要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地方干部和社员群众大胆实践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此外,纪要还指出“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并且高度评价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最后,会议纪要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又进行了一次突破,即按照人民意愿进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并且对包产到户的性质进行了明确规定,“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7]
总而言之,纪要体现的主要精神就是尊重农民、依靠农民、相信农民,在坚持集体经济的前提下,积极将农民的有益探索成果提升为政策方针,坚持“三不政策”,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准则,以巩固集体经济、促进农业生产为最终目的。
80年代农村改革没有采取行政裹挟的方式,而让群众自主选择,党和政府因势利导,因而包产到户首先在安徽、内蒙古、贵州等省区得到群众肯定后,继而在山东、河南、四川、广东等几个大省全面铺开。[8]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包干到户不是“平分集体财产,分田单干”,而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如此,1982年1号文件传达了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的长期性,以及这种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给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对消除农民的观望心态、抵制心态有很大帮助。[9]
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确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存在地位:“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文件还指出“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仍然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
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中央所肯定,截止1983年末,全国已有1.75亿农户实行了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在所有责任制形式中占比高达97.8%。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197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30476.50万吨,1984年增至40730.50万吨,增幅达33.6%。同时,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改善: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纯收入为133.6元,1984年增至355.3元,增幅达165.94%。
(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1978年前,农村存在的家庭副业、社队企业被说成“资本主义的尾巴”,并遭批判,但农民单纯靠农业很难致富,因而为扩大农民收入来源,增强农民再生产能力,农村改革起步之初就注重发展社队企业。
1978年《决定》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城市工厂要把一部分宜于在农村加工的产品或零部件,有计划地扩散给社队企业经营”。即国家和城市都要支持农村社队企业的发展,保障社队企业供销渠道畅通。
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规定》强调“公社工业的大发展”“是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重要途径”。随后,《规定》又对社队企业发展方针、经营范围、发展规划及城市和国家对社队企业的支持进行了详细说明。上述细致入微的构划进一步促进了社队企业的发展。
1980年,中共中央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社队企业、家庭副业繁荣农村经济的作用,进一步放宽了对社队企业的束缚,为其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在保证计划上调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农副产品的就地加工、产品精选和综合利用”,要逐步改变“‘全部劳力归田’的做法,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多种经营方面来”,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初步构想,对促进农村内生的工业化、全方位拉动农村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
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建立多部门的经济结构”作出重要批示:“发展多种多样的合作经济”,“发展合作商业”,“并给予必要扶持”,进一步放活了农村工商业。
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文件《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同意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报告》指出乡镇企业“是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新的重要来源”,并肯定了乡镇企业的生命力,指示加强对社队企业的整顿“以推进农业现代化”。自此,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迅速。
随着党和政府对乡镇企业发展的支持,中国相继出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离不开农民生活水平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反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又为农村注入了工业文明、科技因素。[10]从浅层看,乡镇企业聚集了农村闲置资金,充分利用农村资源,并成为农民收入的又一重要支柱;从深层看,乡镇企业由于体制灵活、见效快、收益高,因而吸引着大量农村劳动力脱离土地,进入第二、三产业,这不仅有助于改变农村单一的经济结构,而且成为农村工业化的原动力,为突破城乡二元体制和弥合城乡裂缝提供了契机。
三、1978—1984年党的农村改革的影响
1978—1984年作为农村改革的起航阶段为农村改革、甚至中国的全面改革开启了良好开端。改革起步阶段,最严峻的问题就是粮食问题,因而党和政府着力解决农业领域微观经营主体的问题,希望藉此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业生产能力和基础地位。上述改革定位既符合当时的局势要求,也能以“小突破口”带动农业改革的“大火车”。1978—1984年农村改革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如下:
第一,就全国范围而言,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1949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为208.90公斤,1978年上升为319公斤,1984年继续增长至392.84公斤,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人民温饱问题的解决不仅关乎生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而这项工作的完满解决为农村改革,乃至中国改革大局的推进都奠定了良好基础。[11]
第二,农业领域的经济结构由单一化转向综合发展。[12]1957年,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537.00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443.93亿元,占82.67%;林牧渔业占比极小,产业结构明显失衡。1984年,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农林牧渔各业的比例不仅有脱离极端化的趋势,而且总体经济效益也有了大提升:1984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214.13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占74.05%,林业总产值占5.03%,牧业总产值占18.27%,渔业总产值占2.65%。
第三,农村改革顺利推动了城市改革。由于农村改革扩大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统购统销政策逐步放宽也使得农产品流转空间扩大,促动了改革的市场化取向。[13]由于农业生产的稳中增长态势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城市企业有了更多生产资料来源,同时企业产品也有了逐步扩大的市场销路,从而增强企业活力成为城市改革水到渠成的话题。1984 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重心转移则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形成,因而追根溯源,1978—1984年农村改革功不可没。
第四,乡镇企业崛起使农村内部产生了工业化因素。乡镇企业在搞活农村经济、服务农民生活、密切城乡物资交流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乡镇企业也因此成为推动农村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助力器。
但也正因为1978—1984年农村改革是急形势之所急做出的先期探索,不可避免地缺少规划性和宏观性。有些问题是在农村改革后期逐步解决的,如市场化问题,这是城市改革带来的最显著变动,农村改革为了不落后于时代潮流、不阻碍改革发展大局,亦须进行市场化取向改革,关于这个问题,农村改革的后续阶段在某些程度上已经解决,但核心环节尚未被突破;有些问题则是经过长期实践显露出弊端,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在改革初期的确创造了巨大功绩,但家庭经营不适合大规模集约化生产,尤其在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已得到提升后,学者们陆续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继续存在提出质疑;还有些问题是至今尚未被破解的,如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这一问题反而伴随改革时间的持续和层次的深化而复杂化。可见,良好的开端并不代表改革进入坦途,面对未来的农村改革,我们任重道远。
四、1978——1984年党的农村改革的现实启示
37年倏然而过,“三农”问题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现在的改革局面是牵一发动全身,因而农村改革绝不会就农村而农村,这种各领域密切联系的关系网也使得改革步履必须谨小慎微。面对今日千头万绪的改革问题和日渐复杂的改革形势,或许我们可以从1978—1984年农村改革中获得一些启发:
首先,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被誉为“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先生在晚年谈及农村改革时常谈道,当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功劳不在于他,而在于千千万万奋斗在生产一线的农民,是他们用实践证明了农村改革的方向,而自己只不过是用政策的形式保护了农民群众创造的成果。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明确指出“按群众利益办事”,“尊重和保护社员群众的民主权利”。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农村改革遇到瓶颈,不如多倾听农民的声音,多看看农民的行动。当然,农村改革要坚持集体经济的原则,不可倒退回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但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引导、合作化的具体方式如何,还要遵从农民的意愿,在实践中进行检验、纠正。对于农村领域发生的一切人为的变革,尤其是来自上级领导机关的指令、政策,切不可不顾农民意愿强制推行,对于此类事情,让农民自己想清楚,自愿主动地执行是最为妥帖的实施办法。
其次,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农业在三大产业中属于弱势产业,农业虽事关国计民生,但其核心竞争力不敌工业和服务业,在产业发展序列上是基础地位但不居于引领地位;农民更是弱势群体,虽然农村改革启动以来国家对农民倾注了许多政策扶持,对农民生活进行补贴,但城乡二元结构没有破解,城乡差距仍在拉大,尤其我国工业化浪潮中出现的“农民工”群体进入城市,却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福利、社会保障待遇;农村由于承接城市转移的工业产业但没能得到城市的帮扶,造成环境污染、生活条件恶化等问题。“三农”问题是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如若不能很好地处理该问题,“三农”问题将成为中国发展木桶的短板,中国亦不可能完成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14]
再次,农村改革需要城市反哺。如果说1978年农村改革前,是农业、农村输血给工业、城市,那么伴随农村改革的深入,双方的角色应该对调,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如果就农业说农业,就农村说农村,不借助外力,农业、农民很难再获得质的发展,至少发展速度会慢许多。工业要为农业提供先进的机械设备和科学技术,支持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帮助提升农业的经济效益;城市应与农村建立良性互动机制,将资金、技术、人才、设备向农村有发展潜力的地区倾斜。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农村改革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37年前农村改革的具体措施或许已然不适用于今日,但1978—1984年农村改革起航阶段那种尊重农民、维护农民利益的精神,实事求是、直面困难的态度以及以推动农业发展为重的工作思路仍值得今日农村改革传承、借鉴。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韩俊. “十二五”时期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政策框架与基本思路[J].改革, 2010(5):5-20.
[2]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96-171.
[3]龚建文.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新农村建设——中国农村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J].江西社会科学,2008(5):229-238.
[4]党国英.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模式的转变——中国农村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J].社会科学战线,2008(2):9-24.
[5]乔榛.中国农村改革的制度变迁理论视角追溯[J].学习与探索,2008(6): 151-154.
[6]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M].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7]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宋洪远,赵长保,张海阳.深化中国农村改革的思考与建议[J].农业经济问题,2008(12):4-14.
[8]吴象.农村改革为什么从安徽开始?[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4(2):24-35.
[9]吴象.吴象:最主要是尊重农民的意愿[J].中国改革,2009(3):42-44.
[10]林毅夫.9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问题与展望[J].管理世界,1994(3): 139-144.
[11]张晓山.深化农村改革 促进农村发展——三大制约因素、一个基本认识、两类政策措施[J].中国农村经济,2003(1):4-12.
[12]陈锡文.当前的农村经济发展形势与任务[J].农业经济问题,2006(1):6-14.
[13]陈锡文.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形势和总体思路[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3): 6-10.
[14]王君,蔡锐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原著选编[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71-326.
(责任编辑 马树颜)
李钰,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邮政编码 250100)
F320.2
A
1672-6359(2016)03-005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