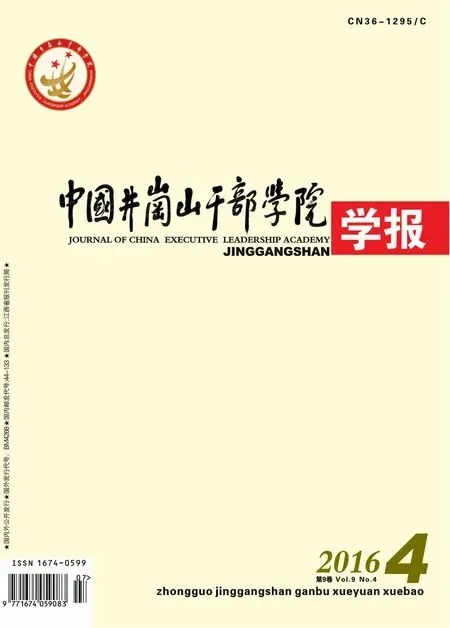论公民生态素养及其培育
□肖 祥 梁浩翰
(1.桂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2.纽约州立大学 奥尼昂塔学院,纽约 13820)
论公民生态素养及其培育
□肖祥1梁浩翰2
(1.桂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541004;2.纽约州立大学 奥尼昂塔学院,纽约13820)
生态素养是经过长期的教育和培养而形成的一种生态文化和生态美德修养或品质,其文化核心要素有生态道德认知、生态文化知识储备、生态公共理性修养。当前公众生态素养缺失主要表现为公民环保意识低下、生态知识匮乏、生态行为偏差,其原因主要是生态教育责任缺失、生态行为的法规约束乏力、社会生态价值导向尚未定型、社会生态文化淡薄。提升民众生态素养必须加强生态文化教育以塑造公民生态文化价值观;加强生态制度机制建设以强化生态素养的他律约束;加强生态行为实践以促进生态素养的形成与优化;加强社会生态文化建设以营造生态素养的外部环境。
生态素养;环境价值观;培育
贯彻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需要激发公民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性。尤其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确定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念之一,“绿色发展”必将更加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在此现实背景下,提升广大公民生态素养以培育公民环境价值观,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已然成为推进“人人有责”地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要求。
一、生态素养及其文化核心要素
素养是指文化和品德的修养,是一个人的环境、教育、经历等结合成的内在素质或品质,它表明内在道德品质和外在行为举止的有机统一。生态素养是现代文明素养的重要内容,它是建设生态文明必需的生态文化素质。在西方,“生态素养”是由环境素养的概念发展而成。美国学者Roth(1968)最早提出环境素养(Environmental Literacy)的概念。Hungerford(1976)认为环境素养包括认知的知识、认知的过程和情意三部分,后来他和Tomera构建了环境素养理论模式,认为环境素养由生态学概念、控制观、问题的知识、信念、价值观、态度和环境行动策略等八个要素组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1990年定为“环境素养年”,并提出环境素养应该成为全人类基本的功能性教育,以配合环境的需要并有助于可持续的发展。随着工业化不断发展,现代社会以环境恶化为代价实现着物质的丰饶,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全球性问题引发了学者们对整个生态的反思。美国学者David Worr和物理学家Fritjof Capra在上世纪90年最早提出和使用“生态素养”(Ecological Literacy)概念。David Worr 在反思现代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而共享太少的现状后指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重建一个完全不同的、能够最大限度保护我们星球利益的同时维护每一个人权利的后现代世界(a postmodern world),使我们的子孙后代得以生存。在西方,生态素养的核心内容包括生命系统的原则、尊重自然、系统思维、生态样式和可持续性转变、协作和公民身份等。
生态素养是一个系统性概念,从其目的而言,它旨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良性关系;从其构成而言,它既包括内在知识储备和道德素养提升,又包括外在价值导向和行为优化;从其形成而言,它是经过长期的教育、影响、修养而形成的一种内在品质;从其本质而言,它就是一种关于生态文化和生态道德的修养。概而言之,生态素养是以改善生态环境、协调人与自然生态关系为宗旨,经过长期的教育和培养而形成的一种生态文化和生态美德修养或品质。
生态素养的形成是个人长期磨炼的道德修养过程,其文化核心要素主要有:
一是生态道德认知。生态道德认知就是对生态现象和生态问题在思维中作出利益取舍和善恶评判,它是经过一系列道德思维、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而最终形成的。生态道德认知伴随着生态道德意识、生态道德规范和生态道德素质的不断提升而逐渐巩固,从而形成健康的生态保护、绿色消费和生态审美意识,自觉遵循保护生态环境的准则规范,更好地履行生态保护的道德义务与责任。生态素养是生态道德发展机制的成熟,它意味着形成了新的较高水平的认知结构,表明了有关生态问题的道德判断结构的形成并产生外显的生态道德行为。
二是生态文化知识储备。“在通往自我认识之路上,文化因素是第一个路标。”[1]P43生态文化知识储备就是通过学习获得关于生态与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发展规律的认识,并最终内化知识成为自己的思维体系。首先,生态文化知识储备促进道德心理结构的形成和完善,生态文化知识的获得不仅是一个“明是非”的过程,还是“辨善恶”的发展过程,从而形成正确的道德价值取向。其次,生态文化知识储备促进生态文化价值结构形成,在生态实践中唤醒和张扬人的价值意识,优化价值实现方式,形成恒常稳定的生态文化价值结构。但生态文化知识储备仅仅为生态素养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条件支撑,现实中“有知识无文化”、“有知识无修养”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生态素养的最终形成还需要进一步强化生态理性修养。
三是生态公共理性修养。公共理性是公民在处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所达成的最基本的共识和价值系统。公共理性目标是实现“公共善。”[2]P225生态公共理性修养一方面要用道德的自我约束校正感性偏差,让人反思自身行为,消除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消除主—客的二元对立。正如泰勒所说:“‘有道德’(to be moral)与‘有理性’(to be rational)乃属同一件事。”[3]P256二要矫正民众行为偏差,使社会民众在处置生态环境问题时不感情用事、不贪占妄为,从而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生态公共理性修养作为处理生态公共生活的一种价值观念,为实现生态和谐善治注入实践伦理精神,从而促使整个社会产生恒常的生态行为,其根本目的就是使社会每一个人成为有意识、有目的、有道德的生态关心者和保护者,即“环境公民”。黑格尔曾言:“只有作为有教养的理性,它才是自为的人。”[4]P13生态公共理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航标灯,因为“人类的未来不仅要求我们做我们能做的事,而且要求我们为自己应该做的事作出理性的解释。”[5]P194
二、生态素养缺失及其归因分析
生态素养是公民环境价值观的文化内核,也是其得以落实的关键。当前公众的生态素养缺失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公民环保意识低下。环保意识的强弱反映了公民素质的高低,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衡量标尺。[6]公众环保意识在环境保护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重要表现,如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把公众环保意识作为国民素质的重要衡量标准。[7]据相关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公众环保意识普遍薄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属于较低层次的参与,表现为公众参与环保的普遍性不足、制度缺失、效果不佳等。[8]尽管大多数民众的生态环境态度、生态参与、制止破坏环境行为、日常生活的生态行为表现(如节水、节电、垃圾分类)等方面显示了积极性,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表现是无知、无所谓、与己无关。
其二,公民生态知识匮乏。英国经济学家B·Ward和美国微生物学家R·Dubos在《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一书中指出:我们人类生存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水、空气和动植物组成的几百万年前就存在的自然界,另一个是人类用工具、机器、科技和梦想按照自己目标和方向建立起来的社会物质文明世界。但是,我们却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知之甚少。我们很多人不了解地球上的生物圈是一个大系统,生态系统进行着无时不刻的能量流动,人与自然进行着物质与能量的交换;也不了解生态系统自动调节平衡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就会导致生态危机,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是因为生态系统丧失平衡所导致的;不了解人类虽然处于“生态金字塔”的顶端,但如果没有金字塔基部的动植物支持,生命就难以维持,因此每一个物种的灭绝都是生物多样性的毁灭,最终危及人类本身;甚至不了解地球与生命、生命与水的密切关系。正是因为生态知识的匮乏,导致我们对自然灾害的根源认识不清、对动植物灭绝漠不关心、对生态破坏行为听之任之。
其三,公民生态行为偏差。环境保护最终要通过公众的环境行为来实现。但现实中生态行为偏差的现象比比皆是,如盗伐林木、乱扔垃圾、偷排废物或污染物、污染水源、私挖盗采、过度开发、猎杀鸟兽等等。中国现在面临着严峻的生态问题,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因为生态行为偏差造成的。如水污染问题,中国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淡水资源人均只有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上名列121位,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然而中国辽河、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珠江、长江七大水系的42%水质超过3类标准(不能做饮用水源),中国有36%的城市河段为劣5类水质,丧失使用功能。再如垃圾处理,中国工业固体废物年产生量达8.2亿吨,综合利用率约46%,城市生活垃圾年产生量为1.4亿吨,达到无害化处理要求的不到10%。再如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问题,我国荒漠化土地已占国土陆地总面积的27.3%,而且还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每年流失的土壤总量达50多亿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水土流失毁掉的耕地总量达4000万亩。
以上生态素养存在问题的原因当然是复杂多样的。从个体而言,价值观念、文化程度、职业、宗教信仰、收入水平,甚至年龄和性别都有可能成为其影响因素;从社会层面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制度政策、环境教育、大众传媒、环保工作力度等也会影响着生态素养的形成。因为个体因素的差异性大,而外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因素,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我们主要从外部因素分析当前影响生态素养形成的关键性原因。
一是教育责任缺失。生态道德认知和生态知识的获得是通过教育而实现的。但现实是我们给学生们传递的知识是“什么是有用的”、“什么能产生经济效益” 、“什么是切合当前社会需要的”;我们的学校和老师疏忽于向学生们传授如何维护生命系统的原则,如何尊重大自然,如何学会系统思维,如何实现生活的生态样式和可持续性转变,如何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参与社会并承担责任。David Worr指出:未能培育人们的生态素养这是教育不负责任的罪过。我们不仅未能教给学生们有关地球及其如何活动的基本知识,而且实际上我们传授的大量资料知识甚至完全是错误的。学生们接受的教育是生态学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生态教育是一个世界性的教育问题,上个世纪70-80年代欧美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逐渐意识到其重要性并采取行动;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奔忙,无暇顾及或者没有意识生态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如何让教育承担生态素养培育的责任,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努力,从教育理念、教育制度、课程选择、教材资料运用、教学方法实施、教育实践活动等方面具体落实。
二是生态行为的法规约束乏力。素养是一个由他律向自律转变的过程。要形成自律,必须有相应的法规约束。生态行为的法规约束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对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的惩罚。这些年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许多相应的法律法规,如大气污染防治法、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生态旅游法规、生态补偿法等等,但是缺乏对公民个人行为实施的具体办法和措施。由于法律的行为针对性不强、执法难度大导致的执法不严等现象经常发生,所以才会出现私挖盗采、乱砍滥伐、偷猎野生动物等等违法现象。2003年“非典”(SARS)疫情爆发敲响的警钟,这是对我们生态行为偏差的惩罚和警示。我们不应该等到自然界给予我们报复之后才醒悟,而应该通过制定强力的法规来约束。另一方面是维护公民的环境权益。美国是最早立法保护公民环境权的国家,1969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每个人有权享有健康的环境,同时也有责任推动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当前世界各国环境法都致力于加强国家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以及赋予公民参与环境管理权利。我国生态环境法规还存在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如我国环境法规多是有关对环境损害的处罚性规定,以“治”为主,缺少“防”的思想;而对公民环境程序权规定较少,缺乏对公民环境权的保护,如公民环境知情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监督权等。
三是社会生态价值导向尚未定型。从世界发展层面而言,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最强动力似乎为世界普遍认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更是将GDP作为发展的主导指标。世界各国贫富差距的拉大更加剧了生态利益的分化,从而更进一步恶化了全球生态系统。从国家发展层面而言,价值导向体现了国家的政治意志,推动着社会朝着某个方向发展。长期以来,中国以经济和生产力发展为价值导向,国家经济实力得到极大提升,但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破坏的负面影响。2012年,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体现了国家对于环境保护的强烈政治意志,将推动中国社会向生态文明社会迈进。从个人生活层面而言,生态价值导向将直接影响着个体行为的改变,实现向生态文明实践转化。当前我国公民社会生态价值导向的定型还有待时日,如浪费水电、乱扔垃圾、捕杀鸟兽、涸泽而渔等等行为随处可见。相比较而言,美国公众环保素质相对较高,在美国随处可见野鹅、野鸭、小鹿,却没人猎杀,这可窥一斑。但是美国公民生态价值导向的定型不是一蹴而就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也曾发生了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中的两起——多诺拉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污染事件,五、六十年代也曾因为滥施农药、化肥导致“寂静的春天”,西部大开发也使得自然精华丧失殆尽,但美国人醒悟快,绿色人士、绿色运动、绿色组织、国家领导等纷纷参与其中,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生态环境保护已经深入人心并取得丰硕成果。
其四,社会生态文化淡薄。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一场改造自然的工程,也是一场改造社会的工程,社会生态文化则是这场庞大社会工程的推动力。当前我国社会生态文化淡薄主要有三个根源:一是执政者建设生态文明的政治领导力和科学决策力有待提升,影响着社会生态文化的主导方向。尽管中央已经重视并努力提高,但有些地方党政领导的决策和执行力水平制约着地方产业布局、经济发展模式、环保措施等,并决定了地方社会生态文化发展水平。二是生态文明法规执行、管理落实、政策引导还需要加强,生态文化的软约束力具体化为社会生态实践还需不断强化。三是全社会生态文明的自觉行动能力不强,环保政绩观、荣誉观、权利观尚未得到普遍认同,生态文化对民众的思想意识影响没有普及深入。
三、新时期生态素养的培育路径
提升民众生态素养,是新时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公民环境价值观塑造的根本途径。
(一)生态文化教育:塑造公民生态文化价值观
加强生态文化教育旨在继承生态文化传统,普及生态环境科学知识,最终在广大民众中确立生态文化价值观,为培育生态素养注入价值动力。
其一,继承优秀生态文化传统,奠定现代生态文化价值观的文化基石
世界各国以及各宗教中都有非常多优秀的生态文化思想。在西方,基督教思想中蕴含的丰富生态文化观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基督教神学家和伦理学家正在努力应对诸如地球变暖、暴风雨增多、不平等、拥挤、暴力增多和生物种类减少等环境挑战。在这个关键时期,基督教生态学发挥着伦理学一样的作用,致力于维护地球的福祉。尤值一提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丰富生态文化思想观念是独树一帜的。儒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出发点尽管是人,但却强调人要遵循自然规律。《礼记·中庸》曰:“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意思就是说,人若能遵循天地自然规律则可以与天地和谐并立。《荀子·天论》亦曰:“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自然有其规律,人不能强加主观意志于自然,但人可以遵循自然规律而治。道家强调“道法自然”、“万物平等”、“和谐共生”等思想,对于当代生态建设具有积极的启示。道家认为修道之人,应当“慈心于物,恕己于人,仁逮昆虫……手不伤生……,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9]P114-115《庄子·马蹄篇》认为:“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生态思想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不违逆生态规律,不破坏生态平衡,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理念,对当今生态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启示。
其二,强化生态文化学科体系建设,普及生态环境科学知识
一要加强生态文化学科体系建设,为提升民众生态素养提供学科文化支撑。生态文化学科体系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生态伦理学及其指导。生态伦理学从责任担当和价值引导两个维度提升民众的生态素养。生态责任担当就是要求民众养成环境保护的生态行为,自觉宣扬和践行环境正义,自觉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作斗争。生态价值引导就是在民众中倡导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绿色消费的新风尚,将生活幸福与生态环境相结合,以价值导向引导行为实践。二是生态教育学及其实施。生态教育学旨在培养民众的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思维方式。生态教育应该针对不同的年龄阶段实施不同内容和要求的生态教育,如儿童期重点是培育生态意识;青年期重点是养成生态行为习惯;成人期重点是培育生态美德和生态社会责任等。三是生态科技及其运用。科技发展使得人类社会的进步获得持续动力。生态科技及其运用要贯彻科学发展观,即强调科技、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一致,强调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生活改善、人文提升的系统发展。四是生态艺术及其对生活美化。生态艺术及其对生活美化既包括艺术创作生态化、艺术审美生态化,还包括生态景观艺术化和美化,它是艺术审美和生态的双向互动。生态艺术不仅涵养民众的审美情趣,提升审美能力,实现审美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的有机融合。生态文化学科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上述四个重要方面之外,还包括生态文学、生态宗教思想研究、生态媒介、生态民俗学等等。
二要普及生态科学和环境科学知识。通过读书、讲座、报告、展览、参观学习等形式,使广大民众了解如“白色污染”的严重性、生物技术的负效应、野生动物保护的必要性、生态危机的危害性……等等生态科学和环境科学知识,自觉地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合理利用与节约资源的意识和行为渗透到日常工作生活之中,培养绿色生活习惯、消费观念,提高环境道德意识,推动全民注重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良好的社会风尚形成。生态文化价值观是生态素养的精神指导和动力。正确的生态文化价值观能有效约束人类行为,消除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一方面,形成以生态伦理、生态正义、生态良心、生态责任等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塑造适应新时期的绿色价值体系。另一方面,提升民众行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让广大民众自觉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旧思想,自觉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通过生态文化教育,使我们每一个人相信:“只有当人类的行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完整,才是正确的。”
(二)生态制度机制建设:强化生态素养的他律约束
生态制度机制为提升民众生态素养提供刚性的保障。建立和完善生态制度保障机制,以确保提升民众生态素养长效、顺利地形成。
其一,生态政策目标约束机制。生态政策从国家、社会和地方性范围为民众提供一种导向性的目标,并对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产生目标约束作用。美国环保政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环保措施上的多样性、创新性和灵活性,力求充分发挥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和民众的积极性;二是它基本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政策,即强调以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方法来实现对环境的保护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所以生态政策的目标约束毋宁说是一种导向激励措施,鼓励民众发挥主体能动性,积极投入生态环境保护。
其二,生态法制保障机制。生态法制主要通过强制性的他律,规范或惩戒生态违法行为,使企业、民众、个体的社会行为符合生态要求,进而引导民众逐步养成生态意识,实现对生态文化确认、引导和维护。美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生态环境破坏到寻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生态法制不断建设和完善的过程。美国联邦环境立法的开始以1872年《黄石国家公园法》为标志;1969年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出台,并成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美国生态法制保障机制有两个特点,一是生态立法历史悠久,二是操作性较强,有一系列保护荒野、保护森林、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与此相比,我国环境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但生态法制保障机制有待继续完善:一是立法指导思想有待从环境污染防治向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和建设改善转变;二是生态保护法律法规有待继续完善,如完善《环境保护法》基本法,设立专门的生态补偿、公民环境权保护法。
其三,生态制度规约机制。生态制度规约一是针对那些生态违规者、逃避者、破坏者给予道义谴责和行为处罚,通过抑恶的调控机制,使个体明白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并最终形成道德自觉;二是对于生态保护等善行进行褒扬,通过物质激励和精神鼓励使人愿意为善、乐于为善。生态制度规约机制的扬善抑恶实质上起着“他律”向“自律”转化的作用,促使人们养成生态意识和生态行为,自觉保护环境、遵守生态道德规范,最终提升生态素养。当前我国生态制度规约应改变重事后规范制裁和经济处罚而轻预防治理和积极建设的状况,增强对公民环境权保护意识和措施,进一步建立完善生态保护的奖励机制。
(三)生态行为实践:生态素养的形成与优化
一方面,生态行为实践是锤炼形成生态素养的必要方式,在不断的行为实践中才能铸就生态道德品质、养成德性;另一方面,人的行为实践又是生态素养的外显,反映着生态素养水平。
其一,生态实践活动。20世纪70年代生态行为实践问题受到欧美国家的重视。英国学者Lucas提出了环境教育著名的“卢卡斯模式 ”,英国环境教育界掀起了环境户外教育运动。美国知名儿童权益宣导人Richard Louv提出“大自然缺失症”(nature-deficit disorder)概念,并倡导“为了自身利益我们需要愈合孩童和大自然隔离的鸿沟,这不仅是出于审美和正义的需要,我们还藉此可以获得心灵、身体和精神的健康。”这引起各界响应并促使美国国会通过了“让儿童走向户外”法案,全球各地也积极推动户外“生态素养”运动。
实践活动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关键,只有在生态实践活动中,我们才能优化人的生态行为,调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概而言之,生态行为实践有两个基本的要求:一是和谐共生。一要约束自身行为,不做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事情,维护生态平衡;二要优化人际交往行为,不要为一己之私攫取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二是取用有节。即有限度地利用自然,实现可持续发展。优化生态行为实践,是生态素养不断修炼和提高的过程,“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才是人类通往未来的健康之路。
其二,生态保护参与。环境政策和环境保护规划实施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组织以及广大民众参与程度与支持力度。西方“绿色运动”之所以声势浩大、影响广泛,就在于每个公民积极的生态参与。1971年,加拿大工程师David Mc Taggart 发起成立国际性“绿色和平组织”,以非暴力抗议形式倡导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围绕“增长极限”、“公地悲剧”等问题的讨论,美国环保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绿党”在欧美国家纷纷诞生,以不同方法维护绿色环境。
当前,由于利益诉求、地域差别、民族传统异质性等原因,我国生态参与的社会机制并不健全。因此,发挥社会组织和民众的作用,使社会各方围绕环境与社会发展等问题展开积极交流与行动,实现广大民众对生态建设的积极参与,使生态参与成为民众生活的一种方式,是当前培育生态素养的重要任务。
(四)社会生态文化建设:生态素养的外部环境营造
社会生态文化建设为地方经济社会良性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生态文化建设无疑是对公众生态素养培育的重要路径。
一是实施生态文化建设工程。生态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生态文化建设工程实施,可以使民众生态素养的形成更有针对性、实效性、地域性。近几年,各省和经济示范区相继出台了具有地方特色生态文化建设规划方案,因地制宜提出了生态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实施策略,极大地推动了生态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具体而言:一要制定科学的生态文化建设规划,巩固现有的生态文化建设成果。从中央到省、市及各地方政府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生态文化建设规划,使生态文化建设规划既有宏观指导性,又有可行性和地方特色。二要开展生态文化建设活动,巩固生态文化建设成果。如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开展诸如“生态示范区文明创建活动”、“全民环境意识行动”、“生态文化村建设”、“大学生绿色行动”……等等。三要加强生态文化教育基地建设,普及生态文化知识。如选择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博物馆、纪念馆作为生态文化教育基地,加大建设投入和开展基地活动,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使生态环保意识深入人心。四要加强生态文化宣传,形成良好的生态文化舆论氛围。如通过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倡导绿色行为、弘扬低碳生活理念,进而实现生态文化价值观念深入人心、见诸行动。
二是大力发展生态文化产业。生态文化产业被誉为“朝阳产业”,它以生态文化产品为载体,向消费者传播生态、环保、健康、文明理念,同时整体性地提升民众生态文化素质。大力发展生态文化产业:一要整合地方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二要繁荣生态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如生态工艺绘画雕刻、生态歌舞艺术演出等,值得大力发展。三要开发和完善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推出生态文化旅游系列产品。四要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文化产业基地,如自然遗产基地、文化公园、生态长廊等,开展各种艺术展览、文化交流、旅游休闲、艺术品交易、就业培训等活动。作为一种新兴产业,生态文化产业将是根植于地方生态文化资源的沃土,成为符合现代产业发展趋势的可持续发展的“黄金产业”。
生态素养不仅标志着民众生态文化的修养水平,也标志着社会生态文明的建设水平。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提升民众生态素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主题。一个具有优良生态素养的民族,才能迈开小康社会建设的坚实步伐。
[1]〔美〕乔纳森·布朗.自我[M].陈浩莺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2]〔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M].北京:三联书店,1989.
[4]〔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6]洪大用.我国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7(2).
[7]吴上进,张蕾.公众环境意识和参与环境保护现状的调查报告[J].兰州学刊,2004(39).
[8]杨方.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状况调查[J].河海大学学报,2007(2).
[9]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责任编辑:朱文鸿)
On the Ecological Attainment of Citizens and Its Cultivation
XIAO Xiang1LIANG Hao-han2
(1.SchoolofMarxism,GuilinUniversityofTechnology,Guilin,Guangxi541004,China;2.StateUniversityofNewYorkatOneonta,NewYork,13820,U.S.A)
Ecological attainment is a kind of ecological culture and moral virtue or qualities formed through long term of education and learning,and its core elements include ecological morality cognition,reserve of ecological knowledge,and qualities in ecological public rationality.At present,the public’s lack of ecological attainment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low conscious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lack of ecological knowledge,and deviation in ecological behavior,and the reasons include the lack of ecological education responsibility,the lack of legal restraints on ecological behavior,the unshaped orientation of ecological value,and the weak ecological cultural atmosphere.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attainment of citizens,we must strengthen the ecological cultural education to shape citizens’ value on ecological culture,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to improve the external constraints of ecological attainment,strengthen the practice of ecological behavior to promote the forming and optimization of ecological attainment,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ulture to buil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ecological attainment.
ecological attainment;view on environmental value;cultivation
2016-05-28
肖祥(1970—),男,广西桂林人,博士,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伦理学原理。梁浩翰 (1961—),男,美籍华人,博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尼昂塔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
本文系2015年度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珠江—西江生态走廊建设中生态协同治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5BZX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广西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可持续生计与广西民族地区生态治理对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G02
A
1674-0599(2016)04-006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