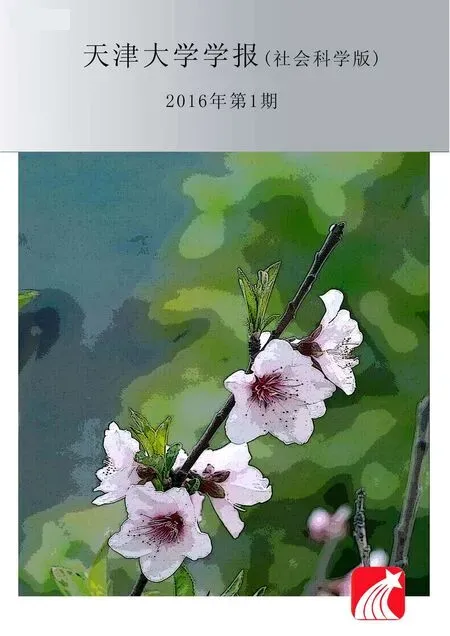20世纪美国要素主义课程实践探析
申心刚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天津 300074)
20世纪美国要素主义课程实践探析
申心刚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天津 300074)
摘要:要素主义是美国20世纪初出现的与进步主义教育相对立的教育流派。以巴格莱、科南特等为代表的要素主义,针对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知识观和课程观。他们认为,教育的唯一和最高目的是获取知识和发展智慧;而进步主义过多地关注儿童的兴趣,轻视学习的系统性,排斥系统的知识体系,导致基础教育质量下降,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危害。考察美国要素主义课程思想与实践,对我国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要素主义课程; 进步主义教育; 课程思想
世界各国课程改革的历史,始终没有离开“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基本命题。20世纪初,传统派教育思想在美国以新的面目出现,以要素主义为代表的“回到基础”的课程改革要求,在20世纪100年间周期性地复兴,成为课程史研究必须关注的问题。
一、 要素主义课程思想的渊源
要素主义课程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观。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建立,使城邦内邦员之间的社会关系,由纯自然的血缘关系蜕变为“自由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支撑这种关系存续的主体是被有意识塑造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城邦维护者。要塑造独立人的格,须先发展人的个性,教育是发展人性品质的应然途径——通过课程的学习,获得作为“自由人”应当具备的文化条件[1]5。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设计了一套管理层次与社会角色十分契合的国家体系。认为最理想的国家应以有知识、有智慧、有美德、崇正义的哲学家为国王,这种信念构成了柏拉图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并由此构建了理想的人才培养模式。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为智慧、力量和服从,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公正社会应培养三种人才的观点,即哲学家、军人和劳动者。教育应当培养哲学家的智慧(即理性),训练军人意志与劳动者的职业技能[1]63。
亚里斯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理论,他对个体自身的发展更为重视。他认为,课程安排的目的是使人的灵魂的三个部分(身体、情感、理智)都得到美满的发展。情感、理智的丰富与发展,须经过教育中介来完成——通过归纳与演绎的方法理解课程、获取知识[2]68。亚里士多德与早期智者派的课程观存在明显区别,比如,普罗泰戈拉等智者派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学会从事政治活动的本领”,通过课程的学习,使人学会处理“私人事务及公共事务的智慧”[3]132。
可以看出,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人文课程源流中,所张扬的是个人相对独立的发展;忽视人与“事务”的联系。虽然教育也培养普通劳动者,但这不是教育的主要目的,也不是教育的最高境界。这一论断将教育与训练置于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中,对后世产生了长久而重大的影响。
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课程思想与知识观被后人视为要素主义的滥觞,并成为英国传统课程实践的主要理论依据。这一课程思想后来通过英国殖民地,对印度次大陆、南部非洲以及印度洋、太平洋等地区的许多国家都产生了一定程度影响。
传承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教育精髓的要素主义,“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流行。它认为,真正的自由教育通过精心选择的学科得到最好的实施”[4]25。要素主义提倡“通才教育”的宗旨是培养能够触类旁通的“博学家”,而不是使学生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基于这一理念,整个20世纪,为英才及大众开设的“自由教育”课程,主要囿于学术性学科。英才教育的广泛存在,以及普通教育(即教育)与职业教育(即训练)相分离的事实,是要素主义在基础教育中保持中心地位的主要原因。
二、 美国20世纪早期逆流而上的要素主义
任何一个时代的课程发展史,都存在着相互交叉或呈网络状分布的多维线索,有主流思潮,也有逆主流而动的各种非主流学派。要素主义就是20世纪30年代逆进步主义潮流出现的许多教育思潮中影响最大的一派,它是传统主义教育思想20世纪初在美国的复兴。
研究美国的要素主义教育思潮,须先对其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作一了解。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经过30多年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步入20世纪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然而,在此发展过程中,美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和文化危机。一方面,国家经济实力大增,国力空前强盛;另一方面,出现了经济垄断和政治腐败,一些大财团和特权集团开始控制社会财富、干预政府运行。同时,贫富悬殊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社会矛盾非常复杂,国家面临许多新的问题。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劳工运动、平民主义运动等社会改良运动,对美国社会的黑暗面展开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最终形成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除旧布新运动——进步主义运动。进步主义运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新的认识方法和批判武器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场改革运动,它旨在改革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场运动的深远意义在于,它使社会各界人士认识到繁荣背后存在的隐患,只有除旧布新,社会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
进步主义运动作为一场文化重建运动,自然会在教育领域作出反应。因此,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是美国教育界对美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重大变革所引发的理论重构。以詹姆斯和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哲学,成为这一时期美国思想文化变革的主流。尤其是杜威,他是美国最有声望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
杜威彻底摈弃了柏拉图关于知识、社会和个人的看法,反对柏拉图主张的只有少数潜在的哲学王才有权获得真正知识和永恒理念的理论,拒斥柏拉图关于理念知识适合于培养社会领袖、职业技能只能用来培养匠人的观点。杜威认为,这种二元论和二分法降低了应用科学的地位,并对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自由教育与职业训练的对立进行了批判[5]101。杜威崇尚知识、经验、活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极力主张以知识和教育来改革社会。这种新的知识论对20世纪美国的课程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20世纪前半期主流课程思想——进步主义课程思想的理论依据。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超越了美国历史上所有的教育改革运动,它主要回答了什么类型的教育能够为年轻人参与社会做最好的准备这一必须解答的问题。在教学领域,反对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观念,在课程领域,反对以学科为中心的狭隘思维。它所倡导的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对美国20世纪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随着这场社会文化运动正在向前推进的时候,它的一些观念和做法遭到“保守”主义者的批评,它被认为是反智主义的。与公立学校运动一样,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也被批评为是白人—新教—社会中、上层的改革家试图把他们的价值观念强加给下层社会的运动。一些历史学家,如霍夫施塔特甚至说,这些改革者的动机不是为了提高他人的境遇,而是为他们自己谋得权利[6]233。所以,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尽管它如同教育发展中一束惊艳的奇葩,尽管有杜威、克伯屈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充当运动的主角,但它对课堂教学并没有产生持久的、预期的影响。它的真正影响是极大地推动了教育观念的更新,使人们对教育的理解进入到一个更宽的视域,使教育思想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1935年,德米阿什克维奇出版著作《教育哲学导论》,书中提及“要素主义”教育思想流派的概念,并列举出若干位这一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巴格莱、布里格斯、霍恩、坎德尔、门罗、塞拉尔、斯巴乌尔丁及斯特雷耶[7]147。德米阿什克维奇将进步教育协会的成员比作古希腊的诡辩家;而要素主义者正是反对这些诡辩家的苏格拉底学派。诡辩家鼓吹的是“改革的快乐主义学说”;而要素主义者则相反;强调人对行动的道德责任,重视永恒的道德责任[8]。1934年,著名教育家巴格莱出版了《教育与新人》一书,从要素主义教育理论产生的基础、课程理论、教师的作用与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要素主义教育的基本内涵[9]25-30。1938年,巴格莱在《要素主义者促进美国教育的纲领》中对进步主义教育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进步主义过多地关注儿童的兴趣,而忽视了基本技能的训练。进步主义教育完全取消学业成绩的严格标准,轻视学习的系统性训练,排斥具有系统知识体系的学科,抛弃学校的权威与纪律,等等。因此,进步主义教育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导致基础教育质量下降、学校教育迷失方向、传统的教育理论精华日渐式微[10]156-157。巴格莱将美国的教育与英国、德国等国家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比较,认为美国的教育软弱无能、不严谨、华而不实,不能充分地使年轻人有效参与社会。教育家的目标是服务社会,而不是试图改造社会、把学校当成社会工程的机构。一个有文化的公民,必须拥有一定的基本技能和知识,这些技能和知识,具有无可置疑的价值和永久性。它们不仅应成为理性认识的基础,而且也是共同思考与判断的基础[6]303。所以,美国应当规制有组织、有秩序的课程和教学过程。通过系统的和组织严密的教材对学生进行理智训练,以培养学生的概念化思维能力。虽然儿童的兴趣应当重视,但向他们传授持久的技能、艺术和科学知识更为重要,这是传承文明的基点。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处于中心地位,通过严格的学术标准和纪律要求,鼓励学生刻苦、勤奋,追求优良的学术成绩[11]541。这样,才能使每一代人拥有足以代表人类遗产最宝贵要素的各种观念、意义、谅解和理想的共同核心,才能体现有效民主所要求的文化共同性[10]158。所以,这些最宝贵的文化要素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数量知识。这些知识,在人类最初的生存与交往中就是必不可少的,它贯穿人类文明发展的全部历史。每个文明社会,都建立在这些内容的基础之上,一旦丧失这些要素,文明将不可避免地崩塌。
(2)间接经验。人们从直接经验之外获取的关于世界的知识,是公认的普及教育的要素之一,这一点并非偶然,在学校教育中很早就有关于人类历史的课程内容。
(3)调查研究、发明和创造力方面内容。这些知识反映了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成果。
(4)健康教育。在初等学校中,健康教育是基本的工作。
(5)自然科学。是推动和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人类取得的每一项科技进步,都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6)人文艺术及工艺劳作。这是培养人的人文精神的必要方法。
以上各项体现在课程中的“共同要素”,可以理解为人类共同的思想、共同的理解、共同的准则,以及共同的精神。从教育目标理解,它包含了基本技能的训练和学习习惯的养成、理想或情感化的准则、人生态度、道德修养等[12]95。
可以看出,要素主义教育思想最基本的观点,即主张把人类文化的“共同要素”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或学校课程的标准。在筛选课程内容时,要以坚持社会福利和社会进步作为基本准则。强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永恒不变的、青年人必须学习的文化与知识要素,并坚决地认为,传统教育的基本内容、原则、方法等仍然是现代教育必不可少并须发扬的要素。要素主义者的这些批评与建议,当时便得到了一些教育评论家的响应。
三、 美国20世纪中期科学主义推动下的要素主义
科学主义是西方最广泛的一种哲学思潮,由孔德、斯宾塞等人开创,后得到不断扩展。尽管科学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各异,但他们都崇尚科学,重视科学知识教育,试图用自然科学的观点解释人的问题。二战后,为了加强教育对科技人才的培养,美国政府启用了一批曾参加过世界大战的科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参与教育改革,这些人才也是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要素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
面对战后各种各样教育改革的思潮,科南特认为,美国的教育改革必须保持自己的特点,即保持公立教育的民主性质。因此,首先要发展和改进民主制的公立学校,加强面向全体学生的普通教育。这一观点,挽救了当时受到要素主义教育家中激进派攻击的综合中学。同时,他又特别强调指出,美国要在科技竞争中取胜,必须最大可能地利用和挖掘天才儿童和青年所拥有的丰富的智慧资源,以培养足够数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所以,在中学阶段应该对学生进行能力分组,为有天赋的学生攻读高深课程创造条件[5]111。
里科弗是反对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激进派代表,他主张用欧洲的传统教育思想指导美国的教育改革。他认为,美国教育的缺陷是忽视“优秀智力”和“心智训练”,主张借鉴欧洲的经验来改造美国的教育,使儿童获得一定的学术教育,为国家培养大量的通晓数学、物理、化学和天文学等学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13]363。
1955年,贝斯特也在他所著的《学习的回归》一书中强调,学校的唯一任务是训练心智,学校课程应严格限定在基本的学术性学科(即英语、数学、历史和现代外语)范围内。他反对综合课程,认为一切“非学术性”的学科都是不必要的,都是课程的虚饰。他在反对职业的、实用性课程的同时,还主张通过标准化测验对学生进行能力分组,认为能否继续接受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教育,不是一般性权利,而是因其成绩优秀、学习勤奋获得的一种特权[13]361。
1958年,美国《国防教育法》的颁布,进一步促进和扩大了要素主义课程思想的传播与实施,确立了加强数学、科学和外语三门基础学科教学的课改新方向。在以科南特为代表的一批改革家的影响下,美国教育协会政策委员会于1961年通过了《美国教育的中心目标》,要求把智力训练作为中学的基本职能。该文件认为,学校教育的时间是有限的,不可能完成所有的目标,为此,学校应该突出其中心任务,即训练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理解问题和进行推理的能力。这个文件直接指导了美国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学的课程改革,代表了基础教育改革的“学术化”方向。
20世纪60年代的课程研究,以布鲁纳的结构主义为指导,将改革推向高潮。但由于过分追求课程内容的高难度和现代化,而忽视大多数学生的能力条件,忽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忽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偏离了基础教育的要求,造成了教育目标混乱、学生学力下降、家长不满、疑虑和批判与日俱增等结果,加剧了战后教育质量下降的趋势。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教育界要求重新强调课程的基础性,即重视传统课程、学校纪律、学术标准等在基础教育中的价值。1976年,在美国基础教育委员会的倡导和推动下,“回到基础”的改革呼声席卷全美。此次改革并无专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由一般的家长、教会人员以及实业家、政治家等自发发起的。它再次倡导“学术化”的教育取向,要求恢复基础知识教育、教师的主导作用、严格的纪律、严谨的教学方法、适宜的考试制度等,这些意见和建议得到学校的积极回应。20世纪70年代,要素主义再次成为课改的主导思想。
四、 美国20世纪末受保守主义支持的要素主义
面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德国和前苏联等国家在国际市场中形成的竞争态势,20世纪80年代初刚刚组建的里根政府,在全球新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及时确立了通过教育改革、确保美国霸权地位的发展战略。
(一) 基于保守主义立场的课程改革
里根政府重新确立了共和党的保守主义价值观。1981年,美国教育部成立了由18人组成的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1983—1988年,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前任主席贝内特担任里根内阁会议的教育部长,作为新传统派永恒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又恰逢美国教育预算的缩减时期,他提出的应将初等学校的课程集中于基础技能科目、将中等学校的课程集中于基本的学术性学科的主张,奠定了20世纪末美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调,并扩大了传统派教育理论对中小学课程改革的影响。
1983年,在美国召开的2 000人参加的全国教育质量大会上,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提交了《国家处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调查报告,提出了学业优异的改革目标,确立了包括英语、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计算机科学在内的 “五项新基础课程”。1991年,布什总统在其签发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报告中,重申了统一核心课程的要求。1993年克林顿政府发表了《2000目标:美国教育法》,在五项基础课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外国语和艺术两门学科。这7门基础课程,便成为由国家确立的核心课程基本体系。
(二) 要素主义的“新基础”
20世纪的100年间,基础教育中基本技能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初(1918年)的基本技能主要指读、写、算;20世纪中后期(1976年),其范围拓展到人际关系、跨文化的洞察力、掌握相关资料、使用计算机、应对复杂事项、进行预算等多项技能;20世纪末(1999),它的范围更加广泛,包括对信息进行理性的解释或评定、进行批判性的判断、熟悉现代生活及理性的逻辑规则、了解人类的思维,增进理解和宽容等。
1983年《危机》报告发布以来,各州纷纷增加必修课和基础课程的比例,大多数州都制定了新标准,包括必修课程、毕业要求和新的表现标准等。
20世纪80年代,“新基础”一词被广泛使用。《危机》报告要求,所有的学术性学科都必须“充实”内容,增加计算机基础课程。这一时期的各类教育改革文件,都提倡文化基础、科学基础、计算机基础以及不同学科的基础。新的基础学科教学强调,用发现、探究、归纳、推理的学习方法,取代单纯的教师讲、学生练的做法;通过制作影片、手工制作课件等,代替单一的教科书;通过对学习过程的重视,取代过去仅仅关注结果的做法,学生不仅要知道是什么,更要知道为什么。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各州的学校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比如,有的学校开设了培养思维方法、训练思维能力、形成创造性思维品质的思维技法课、创造技法课和创造活动课,突出了学生的积极参与和对创造能力的培养。
总之,20世纪80年代后的教育改革仍然以课程改革为重点,统一核心课程和提高教学标准是改革的重要手段,是继1958年教学现代化改革以来,美国课程改革的又一次大的举措。与上次相同的是,两次改革都强调基础学科的重要性,突出核心课程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所不同的是,前一次改革强调教学方法的改革,重视技术手段在教学中的应用,而后一次改革吸收了现代派教育的精华,更突出人的因素,重视教师和学生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并以学生个人的发展和对社会的贡献作为教育的最终目的。
五、 保守与进步并存
美国近一百年基础教育改革的历史,实际上是一场论争迭起的课程改革史。100年来,错综复杂的教育万象往往使人难以直击教学的基本问题;流派纷呈的教育思潮,奉上了乱花迷眼般的概念和理由。然而,“由于没有把课程看作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每个科目被孤立地看待,特定时期的特定兴趣与要求,决定了某些科目的增加或被置于优先地位。对科目多样化的逆反应,要求恢复基础”[13]365是比较冷静与适宜的选择方案。
要素主义与传统派其他教育思潮一样,能够在国家教育预算缩减时期得以复兴,确有其兴盛的理由。要素主义的起起落落,尽管原因各异,但始终没有离开其所坚持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基本立场。纵观20世纪美国的教育发展史,从1958年《国防教育法》强调的“新三艺”,到60年代布鲁纳追求教学内容的高难度和现代化——重视理论知识的课程体系,再到1993年克林顿政府确定的7门核心课程,虽然改革方案不尽相同,改革过程中的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但保留了柏拉图教育理念基因的要素主义,凭借其野火烧不尽的生命张力与海纳百川般的包容性,为瞬息万变的教育变革贡献着令人瞩目的斐然成就。
探究要素主义课程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实践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识当下美国课程改革的实质性问题,它对我国的课程改革也有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1][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人主义传统[M].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2]吴式颖.外国教育史教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3]北京大学哲学系.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7.
[4]Brian Holmes, Martin Mclean.TheCurriculum:AComparativePerspective[M]. London: Unwind Hyman Ltd, 1989.
[5][英]霍尔姆斯,麦克莱恩.比较课程论[M].张文军,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6][美]迪安·韦布.美国教育史[M].陈露茜,等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7]Michael Demiashkevich.AnIntroductiontothePhilosophyofEducation[M].New York:American Book Company, 1935.
[8]金传宝.美国教育史上被遗忘的传统:巴克莱和要素主义的创建[J].教育史研究,2009(6):68.
[9][美]巴格莱.教育与新人[M].袁桂林,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10] [美]巴格莱.要素主义者的纲领[C]//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11] 腾大春.美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12] 单丁.课程流派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13] [美]丹尼尔·坦纳,劳雷尔·坦纳.学校课程史[M].崔允漷,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American Essentialism Curriculum Practice in the 20th Century
Shen Xingang
(Editorial of Office Journal,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In the early of 20th century, the Essentialism, whose representatives were William Bagley and James Bryant Conant, appeared as the antithesis of progressive education. It was against progressivism, whose representative was John Dewey putting forward a different view of knowledge and Curriculum. They believed that the only and ultimate goal of education is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develop wisdom. The progressive focused too much on the interest of the child, ignored the systematic training of learning, not pay attention to systematic knowledge, which lead to decline in the quality of basic education and brought harms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o study American Essentialism Curriculum thought and practice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oday’s Chinese education reform.
Keywords:essentialism curriculum; progressive education; curriculum thoughts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339(2016)01-064-05
通讯作者:申心刚,tjshen2006@126.coml.
作者简介:申心刚(1963— ),男,副编审.
基金项目:天津市“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HE1003);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基金资助项目(DOA120325);天津市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基金资助项目(125z026).
收稿日期:2015-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