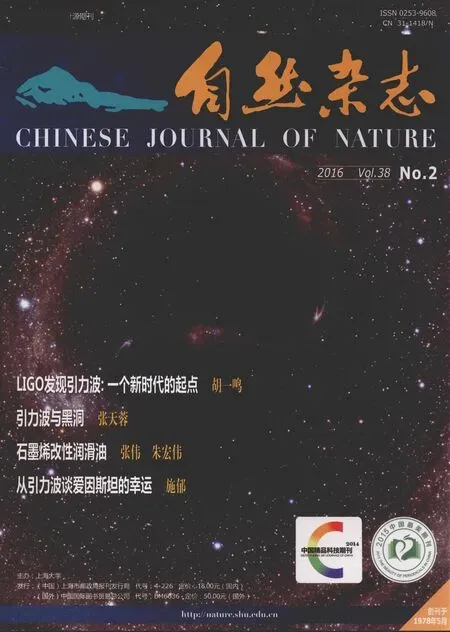DNA发现之前的基因
——遗传学家是如何揭示生命结构单元之基础的
马修·科布
DNA发现之前的基因
——遗传学家是如何揭示生命结构单元之基础的
马修·科布†
编者按原文载于《Discover》杂志2015年9月刊,摘选自马修·科布(Matthew Cobb)的著作《生命最大的秘密:角逐遗传密码真相的故事》(Life's Greatest Secret: The Race to Crack the Genetic Code),该书于2015年7月由Basic Books出版。本文由张钫、史晓雷翻译。
三一学院地处都柏林的中心,它那灰色的三层新古典主义建筑环绕在草坪和运动场周围。校园的最东头是另一栋灰色建筑,落成于1905年,则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那是菲尔兹杰拉德大楼,或者依据其门楣上刻的字叫“物理实验楼”。这栋楼的最顶层是一个演讲厅,1943年2月第一个周五的傍晚,400余人聚集在这里,坐在漆过的木质长凳上。
据《时代》杂志报道,有幸坐在这里的人主要有内阁大臣、外交官、学者以及社会名流,还有当时爱尔兰的总理埃蒙·德·瓦莱拉(Éamon de Valera)。他们聚集在这里是要聆听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埃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做的一场题为“生命是什么”的有趣演讲。对此感兴趣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很多人被拒之门外,在接下来的周一又安排了一场同样的演讲。
薛定谔是为逃离纳粹而来到都柏林的——在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前,他一直在奥地利格拉兹大学工作。尽管薛定谔以希特勒的反对者而闻名,但他对纳粹的侵占曾发表一封言辞并不激烈的声明,希望能够留下来。然而,这一策略并未奏效,他不得不匆匆逃离祖国,连诺贝尔奖章也未能携带。对物理学很感兴趣的德·瓦莱拉为薛定谔在都柏林新成立的高等研究院提供了一个职位。就这样,在爱尔兰这位量子力学大师的岁月才未被蹉跎。
连续三个周五,56岁的薛定谔前往菲尔兹杰拉德大楼的演讲厅进行演讲,他探讨了量子物理学与生物学最新发现之间的关系。
遗传性与物理学
他处理的问题之一是遗传的本质。与之前其他人一样,薛定谔为这一现象所震撼:在普通细胞分裂(有丝分裂,有机体生长的方式)和生殖细胞生成(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都能够精确地复制。你的身体能够长到现在这般大小,其间经历了数万亿次的有丝分裂,并且在整个复制与倍增的过程中,遗传密码显然也得到了精确的复制。从而,基因能准确无误地传递给下一代。薛定谔用大家所熟悉的哈布斯堡家族的特征向听众进行了解释——哈布斯堡家族所有人都有着突出的长下巴——这可以上溯几百年的历史,而没有明显的变化。
对生物学家来说,基因这种看起来恒久不变的特性不过是一个既成的事实。然而,对这些物理学家而言,这便产生了问题。
薛定谔计算出每个基因仅由1 000个原子构成。那样的话,基因就应该不停地闪烁和变化,因为物理学和化学的基本定律都是统计性的;尽管原子整体上总是趋于一致的运动,但是单个原子可以按背离这些定律的方式运动。对于我们遇到的大多数物体而言,这无关紧要。像桌子、石块或者奶牛等都由极大量的原子组成,因此它们不会以不可预测的方式运行。桌子就是桌子,它不会自发地变成石块或者奶牛。
薛定谔认为,若基因仅有数百个原子组成,它们就会显现出极不稳定的运动,也就是说它们不会在几代之间保持恒定的特征。但是实验表明这种变化非常罕见,并且即使突变发生时,它也能够精确地遗传下去。
薛定谔用如下的术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总结:
“在活的有机体内,有许多极小的原子团,小到不足以显示精确的统计学定律……而它们在极有秩序和极有规律的事件中确实起着主导作用。它们控制着有机体在发育过程中获得的、可观察的大尺度性状,决定了有机体发挥功能的重要特征。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显示了十分确定而严格的生物学定律。”
这个挑战是要去解释在仅由极少量的原子构成,且多数原子运动并不规律的情况下,基因是如何有规则地运作并产生正常有机体的。为了解决物理学定律与生物学事实之间的明显矛盾,薛定谔转向了当时已有的、最复杂的遗传理论——这是由梯莫菲也夫·列索夫斯基(Nikolay Timofeeff Ressovsky)、卡尔·齐默尔(Karl Zimmer)和马克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三人提出的。
三人论文
1926年,苏联遗传学家列索夫斯基与美国遗传学家荷曼·缪勒(Hermann Muller)合作,发现基因暴露于X射线可产生突变。不久,列索夫斯基开始与放射物理学家齐默尔和年轻的德国量子物理学家德尔布吕克展开一项合作。
三人团队决定针对基因采用“靶向学说”——这是研究射线效应的一个核心概念。他们用X射线轰击细胞,随着射线频率和强度的变化,观察不同突变发生的频率。这样,他们认为应该能够推测出基因(靶标)的物理大小,并且通过测定其对射线的敏感度,可以揭示出基因的构成。
1935年,他们合作的成果便是一本合著的德文出版物——《关于基因突变和基因结构的本质》,其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三人论文”。
三人团队得出结论,基因是分子般大小的不可分的物理化学单位。他们还提出,突变与分子中化学键的改变有关。尽管他们已尽最大努力,然而基因的本质及其确切的大小,仍然无从得知。
薛定谔在都柏林向听众讲述遗传的本质时,他不得不给出一个解释,就是基因到底包含什么。然而即使在当时最为前沿的理论——“三人论文”,也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因此,薛定谔仅用逻辑来支持他的假设,认为染色体“包含了个体未来发育和成熟个体机能的全部模式的密码本”。这是首次有人明确提出基因可能含有密码,或者更简单地说,基因就是密码。
将他的观点转化成合乎逻辑的结论,薛定谔认为受精卵的“密码本”应该可以阅读,从而可以知道 “在适宜的条件下,这个受精卵是发育成一只黑公鸡还是一只芦花鸡,是长成一只苍蝇还是一棵玉米,一株杜鹃花,一只甲虫,一只老鼠或一个女人”。
薛定谔的思想的确标新立异,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是对这两种早期思想的回响:有机体是如何发育的,以及未来有机体的行为隐含在受精卵中这一古老设想。他提出的问题是,未来的有机体在受精卵中是如何呈现的,以及通过何种途径使得这种形式成为生物实体。他认为这两者其实是一个问题:染色体结构在“隐含”信息成为有机体的过程中起了作用。它们就像是法律条文与执行权力的统一体一样,或者用另一个比喻,就像是建筑师的图纸和建筑工人的技艺。
用密码说话
为了解释他所假设的密码本是怎样工作的——由于关乎“有机体所有未来的发育”,它不得不异常复杂——薛定谔借助于一些简单的数学来说明一个有机体内形式多样的不同分子是如何编码的。
薛定谔指出,如果每个生物分子由1到25个字母组成的一个单词决定,并且该单词由5个不同的字母组成,那么就会有372 529 029 841 191 405种可能的不同组合——这远远超出了任何有机体中目前所知的分子类型的数量。在展示了一个简单密码的潜在力量后,薛定谔总结到:“微型密码应该对应于一个高度复杂而精准的发育蓝图,并且可能以某种方式包含了使密码起作用的程序,这一点已经不再难以想象了。”
尽管这是首次公开指出基因包含了像密码一样的东西,但是早在1892年,一位名叫弗里兹·米歇尔(Fritz Miescher)的科学家就提出一种有点类似的观点。米歇尔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指出,有机体分子的不同形式足够满足“遗传性用于表达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就像所有的文字语言能用24~30个字母表达一样。”米歇尔的观点相当有远见。特别要提及的是,他还是DNA或者当时称之为核素的发现者。然而米歇尔从来都不认为核素是编制这些字母的物质,此外他的观点在80年后才公之于众。由此可见,其模糊的字母、单词的比喻从来没有像薛定谔的密码本的概念一样清晰表述。
薛定谔随后开始研究基因的分子由什么构成。他认为这是一种他称之为一维非周期性的晶体——一种非重复固体,缺乏与密码本存在相关的重复。在一个有机体中,这种非重复为有机体内形成那么多不同分子提供了必须的特异变化。尽管缪勒、美国物理学家伦纳德·特罗兰德(Leonard Troland)和苏联遗传学家尼古拉·科尔佐夫(Nikolai Koltsov)早在20多年前就提出基因可能像晶体一样生长,但是薛定谔的观点显然更为精确。他对基因结构的观点集中在密码本的非重复特性,而不是在染色体复制与晶体对其结构自我复制能力之间的简单对比。
伟大的思想,零星的关注
薛定谔的演讲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仅仅徘徊在都柏林的空气中,短暂地萦绕在那些用心聆听者的脑海里。对这些演讲唯一的一次国际报道出现在4月份的《时代》杂志上,其中并未涉及薛定谔所讲的任何细节,因此他的任何思想也没传到外界。唯一的详细报道是在《爱尔兰日报》(The Irish Press)上,报道将他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概括,包括密码本和非周期性晶体两点。鲜有其他报纸再对事件给予应有的关注。当1944年1月薛定谔在科克再一次进行同一版本演讲时,当地的报纸《克里人报》则将他的演讲与“利斯托尔生猪交易”(据报道,有126头猪需要出售)给了同等的版面。
薛定谔觉得公众可能会对他的观点感兴趣,因此演讲一结束,就立刻将其整理成文,并最终在1944年12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冠有薛定谔的大名,一个引人入胜的题目和一家享誉全球的出版社,并且适逢二战即将结束,所有这些意味着它将得到广泛传阅,并且不断再版。尽管《生命是什么》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然而它是薛定谔涉足生物学的收尾之作。此后他再也没有就此问题公开发表文字,甚至在1953年发现遗传密码存在之后,他也如此。
该书随即引起了巨大反响,从大众媒体和科学期刊上热情洋溢的评论即可看出。在该书刚一出版的四年里,就出现了60多篇评论,尽管很少有作者注意到如今看来极有远见的观点——非周期性晶体和密码本。此外,这本书还被翻译成了德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和日文。
在顶级的科学周刊《自然》杂志上有两篇延伸评论,一篇是遗传学家霍尔丹(J. B. S. Haldane)所写,另一篇是植物细胞学家艾琳·曼顿(Irene Manton)所写。霍尔丹直奔问题的核心,从中提炼出非周期性晶体和密码本的新思想,并与科尔佐夫的工作联系起来。曼顿也注意到薛定谔使用的“密码本”这一术语,然而她将其理解为“遗传物质的总和”,而不是关于基因结构和功能的一个特殊假设。《纽约时报》的评论确切地指出了其核心观点:“基因和染色体包含着一种薛定谔称之为‘密码本’的东西,它能够决定执行过程中的秩序。由于我们至今无法解读密码本,因此事实上我们对生长、生命一无所知。”
相反,一些科学家后来回忆说这本书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太多印象。20世纪8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化学家鲍林(Linus Pauling)就表示,他在读过《生命是什么》后很“失望”,并声称“我一直认为薛定谔对我们理解生命没做出什么贡献。”
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马克斯·佩鲁茨(Max Perutz),这样评价薛定谔:“书中正确的东西均不是原创,而多数原创的东西,即使在其写作的年代,也是不正确的。”1969年,遗传学家沃丁顿(C. H. Waddington)批评薛定谔的非周期性晶体的概念是“极其荒谬的表述。”
除了这些回顾性的批评外,在这本书刚一出来,就有一些异议的声音。尽管德尔布吕克在那篇“三人论文”之后受到过薛定谔的公开支持,但他在一篇评论中还是对其提出了批评。
他表示薛定谔的非周期性晶体的术语掩盖的比揭示的还要多:
“给予基因如此惊人的名字而不是现在称之的‘复杂分子’……这些论述并无新意,却占据了该书的大半部分,生物学读者更倾向于略过这些部分。”
这显然是极不公平的,事实上,薛定谔的假说非常精确,并不仅仅是创造一个新的术语。德尔布吕克勉强认为,这本书“如果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关注的话,将会产生启发性的影响”。
在另一个评论中,缪勒也说他期待这本书能够为“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遗传基础之间日益增长的友好关系”产生促进作用。缪勒对薛定谔没有引用他的工作愤愤不平,他指出自己在1921年提出过基因复制和晶体生长之间的类比关系(然而缪勒没有提及他的想法源于特罗兰德)。他还否认薛定谔对有序和负熵的讨论存在新意,认为它们对“普通的生物学家都非常熟悉”。无论是德尔布吕克还是缪勒,都没有对密码本的概念做出评论。
鼓舞人心
尽管他们总体上持怀疑态度,但德尔布吕克和缪勒在这点上完全正确:薛定谔的书的确激励了年轻一代的科学家。因揭示DNA结构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三人——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都声称《生命是什么》在他们通向双螺旋之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威尔金斯还在加利福尼亚从事原子弹研究工作时,就从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了一份《生命是什么》的复印本。当被广岛和长崎的恐怖深深战栗后,威尔金斯被薛定谔的著作深深吸引,并决定放弃物理学而成为一位生物物理学家。克里克回忆1946年当他读到薛定谔的书时,觉得“伟大的事业在向其召唤。”沃森读到《生命是什么》的时候,还是一位大学生,结果他将研究兴趣从鸟类生物学转移到了遗传学。
尽管《生命是什么》的一些思想极富远见,而且毫无疑问激发了一些在20世纪科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然而数十年努力解决遗传密码问题中涉及的实验和理论与薛定谔的演讲并没有直接联系,历史学家及当时的参与者对薛定谔贡献的重要性有所分歧。
三人论文中提出的突变观点,薛定谔大加赞赏,但这并没有对后续的研究产生影响;而他认为通过对遗传物质的研究将会发现新的物理学定律,则是完全错误的。即使在今天看来有预见性的密码本理论,也并没有对生物学家发现基因产生直接作用。后来在遗传密码发现过程中所产生的论文,没有一篇引用过《生命是什么》,即使是读过此书的那些科学家。
事实上,薛定谔“密码本”的概念并没有我们今天使用的“遗传密码”含义丰富。薛定谔并不认为基因的每个部分和精确的生化过程之间有所关联,而这正是遗传密码所指。而且他也并没有提出密码本确切包含什么,仅是给出一个蓝图的模糊建议。
如果问今天任何一个生物学家遗传密码包含什么,他们都会用一个词来作答:信息。薛定谔并没有使用这个强有力的比喻。这在他的语汇和思考中是完全缺席的,而这其中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这个词当时还没有今天我们所赋予的抽象的、广泛的含义。
“信息”当时即将闯入科学,不过在薛定谔演讲时还没有发生。没有遗传密码的概念,薛定谔的洞察力仅仅是时代洪流的一部分,一种对即将到来之事物的线索,而非塑造后续思想的突破。
(2015年9月17日收稿)■
(编辑:段艳芳)
Ge nes before DNA: How geneticists brought the foundation of life's building blocks to light
Matthew COBB
10.3969/j.issn.0253-9608.2016.02.011
†Matthew Cobb,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动物行为学及生物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