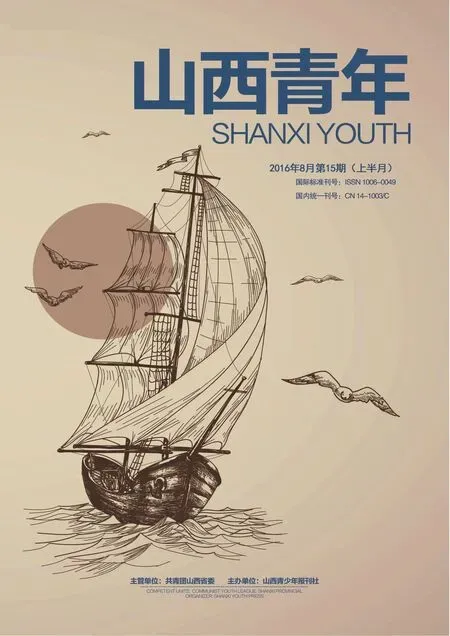薛蟠在《红楼梦》中的结构意义
张 楠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薛蟠在《红楼梦》中的结构意义
张楠*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81
薛蟠这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在《红楼梦》中属于次要角色,但在全书的整体结构中却是一块不可或缺的砖瓦:他是重要角色现身的引线,是映衬复杂人格的旁线,是预示小说结局的暗线。
红楼梦;薛蟠;结构意义
《红楼梦》展现了高超的结构布局,创造了“伏脉千里,击尾首应”的网状叙事结构——全书浑然一体,诸多部分又可独立成章,“这有点像黄金的性质,具有可切割性”[1]。这种“联结与游离”相伴的“黄金性”,可从薛蟠的结构性安排——从次要角色“升格”为具有结构意义的抓手——中窥见一斑。薛蟠并非贾府直系亲属,却在前前后后共30回中屡屡出现,足可看出作者对这一人物的重视。且看薛蟠的初次登场:
“黛玉虽不知原委,探春等却晓得是议论金陵城中居住的薛家姨母之子——表兄薛蟠——倚财仗势打死人命,现在应天府案下审理”(第三回)[2]。
之后则借原告之口介绍道:
“这拐子便又悄悄的卖与薛家,被我们知道了,去找拿卖主,夺取丫头。无奈薛家原系金陵一霸,倚财仗势,众豪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仆已皆逃走,无影无踪,只剩了几个局外之人。”(第四回)
短短几句,便将薛家的势力及“呆霸王”之“霸”体现出来。作者通过薛蟠仅有的几次出场,即完成了对其“纨绔”一面及善的一面的塑造,又通过其它场合的侧面叙述及动态描写使读者对这个“问题少年”的傲慢霸道印象不断加深。薛蟠的“不得不出场”,展现了该人物在全书整体结构上的穿针引线作用。
一、“抛砖引玉”,呼唤重要角色现身的前奏
其一,薛蟠的出场引出了一个《红楼梦》中至关重要的重量级人物——薛宝钗:
“这薛公子学名薛蟠,字表文起,今年方十有五岁,性情奢侈,言语傲慢。虽也上过学,不过略识几字,终日惟有斗鸡走马,游山玩水而已。虽是皇商,一应经济世事,全然不知,不过赖祖父之旧情分,户部挂虚名,支领钱粮,其馀事体,自有伙计老家人等措办。……还有一女,比薛蟠小两岁,乳名宝钗,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第四回)
脂评说,“其意实欲出宝钗,不得不做此穿插”。
其二,柳湘莲的性格刻画也是和薛蟠联系在一起的:
柳湘莲与宝玉说完话后本欲先走,却“刚至大门前,早遇见薛蟠在那里乱嚷乱叫说:‘谁放了小柳儿走了!’”,听过此话,便“火星乱迸,恨不得一拳打死”(第四十七回)。
作者本可直接“放”走湘莲,却偏偏“让”他听到薛蟠的这番话。通过“呆霸王调情遭苦打”,和下文柳湘莲出手相救路遇强盗的薛蟠并且拒绝接受谢礼,来刻画柳湘莲的冷面却正气、强烈自尊却又率性豪气的个性。柳湘莲“一冷入空门”后,作者以薛蟠四处寻找及痛哭作为柳的煞尾,而未“让”私交甚好的宝玉为其谢幕“送行”,足见薛蟠之于柳湘莲这个人物的重要性。
其三,借薛蟠大婚,又引出一位个性鲜明的重要人物——夏金桂。她和薛蟠都是被宠大的,但其嚣张跋扈却比薛蟠更甚——“爱自己尊若菩萨,窥他人秽如粪土;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呆傻如薛蟠,亦知行为需要分场合和对象——调情柳湘莲是“错听了旁人的话”将湘莲错当成伶人;而夏金桂却不仅用下三滥的手段陷害香菱,闹出事又公然和薛姨妈“隔着窗子拌嘴”,气的薛姨妈“身战气咽”,毫无大家闺秀之范。夏金桂的“妒妇”脾性虽和王熙凤颇有相似之处,但两人的教养不可同日而语。首先金桂排除异己的手段明显逊于凤姐,漏洞百出、易惹怀疑,在夫家和婆婆闹;其次金桂自己耐不住寂寞,趁薛蟠不在,竟使尽解数勾引薛蝌。写年轻女子,唯独夏金桂用贬斥笔调,或是借此重塑宝玉对女性的看法和对人生的参悟?
二、草蛇灰线,映衬复杂人格的暗笔
前八十回虽是曹雪芹一人主笔,叙述聚焦却并非定式,且多有隐晦曲折之笔,蕴含着深长的意味,“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动作,都在告诉对方某些事情”。借助于文本错综复杂的编织,薛蟠的一些看似呆傻的行为看似无用,却像毛衣的边线,在整体结构中饱含意蕴。
第二十五回,宝玉和凤姐在园子里疯了似的寻死觅活,闹得天翻地覆,在众人忙乱、烦难、气氛紧张之际,薛蟠并非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却“更比诸人忙到十分去”:
“又恐薛姨妈被人挤倒,又恐薛宝钗被人瞧见,又恐香菱被人臊皮,——知道贾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功夫的,因此忙的不堪。忽一眼瞥见了林黛玉风流婉转,已酥倒在那里。”薛蟠的行为虽与此场合的核心——宝玉和凤姐——无甚相干,却也是有理有据。脂评说:“写呆兄忙,是躲烦碎文字法”,“是愈觉忙中之愈忙”[2]。“写贾珍等一笔”[2],是交待“忙”的原因;写薛蟠看到黛玉后“已酥倒在那里”,暗示了两人代表着两个世界的巨大鸿沟,这种“同时代实为超时空交叉时空并存的想象设计”,展现了两人的共时性和不共容性:林是超脱世外、遗世独立的高洁人格的象征,是薛这个典型的市井俗人穷尽一生也无法达到的人格境界,寄托着作者的精神指向。薛蟠的这一眼,顶多是“惊鸿一瞥的绝望”,“在人格独立的黛玉面前,薛蟠是彻底失语的”。
第二十八回,薛蟠扮演了非他莫属的称职的“丑角”嫖客形象。作者对薛蟠并非一味贬斥,而是展现了该角色的复杂人格,正所谓“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总是在平衡当中有一种搭配”。如果说宝玉的诗和曲都体现了纯粹的“情”,而蒋玉菡则诗“情”曲“欲”,那么薛蟠仅作一诗则尽显“欲”望,且漏洞百出:前两句“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窜出个大马猴”,毫无诗意可言,意象的选取亦俗不可耐,在他的生活里没有艺术,没有美,十足的俗人一个。但作者并未将薛蟠永久地放在下流的层面,而让其吟出“太韵”之句“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将薛蟠从“丑角”中解救出来,写出了薛蟠身上存在的人性闪光,使得低俗与高雅相互交融,体现了作者对薛蟠的肯定,让薛蟠成就了一个微妙的颠覆,用他的下里巴人,嘲笑了知识分子引以为豪的阳春白雪。诗的最后一句又回归到了粗俗,点出了薛蟠的核心性格——只拥有直接的欲望,终究不能冲破既定的牢笼。再看当蒋玉菡行完了令后,“薛蟠又跳了起来,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该罚,该罚!这席上又没有宝贝,你怎么念起宝贝来?’”众人疑惑之际,“薛蟠道:‘袭人可不是宝贝是什么!你们不信,只问他。’说毕,指着宝玉。”“实心人”薛蟠演出这似是无厘头的闹剧,令人不明所以,但最后袭人果真嫁给了蒋玉菡,隐然有作者看似无意、实则有心的暗笔——袭人的判词是“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
三、以小见大,应扣世家没落的写意
薛蟠以人命官司出场,又以人命官司收尾,薛家衰败的在所难免,就体现在这两次人命官司的不同了结上,也在更大背景下与《红楼梦》四大家族兴衰的相照应。第一次薛姨妈只是花了几个钱,又通过贾雨村,便草草作结。但第二次却一波三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薛蟠的命运也随之起起伏伏,本来已用银子买通获释,却碰到了刑部驳审,“依旧定了个死罪,监着守候秋天大审”,幸而又获皇帝大赦。第二场官司的起落不定,从侧面说明了薛家的衰败。薛姨妈对宝钗的一席话更是直接的点出了薛家的衰落:
你还不知道,京里的官商名字已经退了,两个当铺已经给了人家,银子早拿来使完了。还有一个当铺,管事的逃了,亏空了好几千两银子,也夹在里头打官司。你二哥哥天天在外头要账,料着京里的帐已经去了几万银子,只好拿南边公分里银子并住房折变才够。前两天还听见一个荒信,说是南边的公当铺也因为折了本儿收了。若是这么着,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的了。作为皇商的薛家,最不缺的应该就是钱了,当年的门子就曾对贾雨村教导说“薛家有的是钱”。但现在,薛家的万贯家财只剩“南边的公当铺”,衰败之势不言而喻。
这第二起案件,自八十五回薛姨妈得知薛蟠在外殴人至死始,至最后一回此案才了结,实际就相当于在后四十回的主线之外又辅设了一条以薛蟠的案件为主题的副线,而这条副线不仅几乎贯穿了续作的始终,而且铺陈广阔连绵,覆盖了大量篇幅,足以见高鹗对此的重视。或许续作者是希望用这次事件修正薛蟠教育中的一些偏差,“让”薛蟠从不知世事艰难最终走出薛姨妈为他编织的“想要即可得”的幻境,意识到金钱并非万能和世事之艰辛。于是我们听到了他的誓言,“若是再犯前病,必定犯杀犯剐”。至此,薛家或许还有振兴的希望,也或许没有,但薛蟠的悲剧性却是要伴随终生的。
贾政作为薛蟠的亲戚和荣国府主要当家人,在薛蟠的两次官司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这正是四大家族官官相护的体现。因此,当贾政偶看一本刑部文件,得知薛蟠之案愈加严重之时,知道此事“牵连着自己,好不放心”。薛家的没落、贾政的徇私,亦在为贾府被抄家做着准备。如此,《红楼梦》观念上的宿命论与结构上的预示性达到了“心照不宣”的应扣。
四、结论
《红楼梦》的网状叙事结构纵横交织,一些看似不重要的部分,却有着“蝴蝶效应”般的催化力量。尽管薛蟠对主线故事的合理发展并不产生直接的影响,但若抹去其存在,不仅会使故事单调了许多,也失去了描绘当时真实的生活场面、丰富和发展其他人物性格、显示人物之间联系的重要条件。
[1]王蒙.王蒙活说红楼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2]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张楠(1995-),女,河南汝州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本科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J826
A
1006-0049-(2016)15-012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