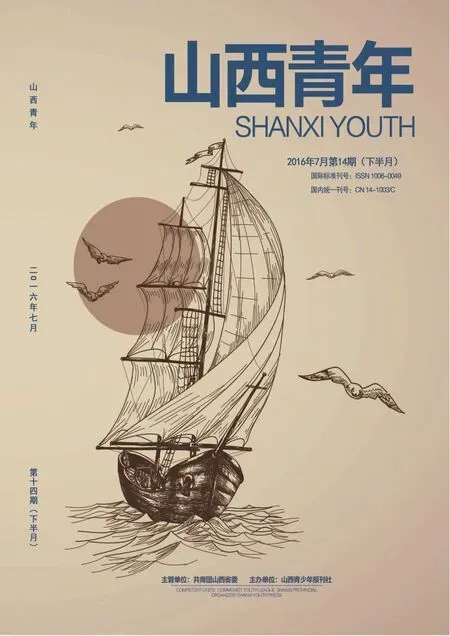“朝隐”与郭象的圣王思想
赵亚明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上海 200433
“朝隐”与郭象的圣王思想
赵亚明*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上海200433
摘要:本文试图探讨“朝隐”思想与郭象“圣王”思想的联系,由于时局发展和玄学思潮的影响,两晋之际社会上产生了调和“自然”与“名教”,论证“朝隐”合理性的需要;而郭象顺应这一时代潮流,发明了一套用来论证“内圣”与“外王”相统一的政治思想。可以说,郭象是中国历史上“朝隐”思想的集大成者。
关键词:隐逸;朝隐;圣王;自然;名教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隐逸的传统,历朝历代都不乏归隐田园、回归自然、发璞归真的高隐之士,他们高举生命的本真价值,希望过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渴求全性葆真,不以物事累形伤生,因而选择隐居人迹罕至的荒野山林。提到“隐逸”一词人们首先想的一般都是这种画面,然而在魏晋之际由于玄学思潮的影响或者时局社会环境的险恶,魏晋士人在隐居山林的传统隐逸方式之外,发展出另外一种在当时颇为流行的隐居方式——朝隐,其形式就是“身居魏阙,心存林泉”、“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或“身处朱门而情游江海,形入紫闼而意在青云。”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东方朔可谓“朝隐”做法最早也最典型的代表,但见他“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史记·滑稽列传》)因此司马迁认为东方朔乃“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扬雄《法言·渊骞》中“或问,柳下惠非朝隐者与?”和《后汉书·张衡传》中“庶前训之可钻,聊朝隐乎柱史”都用到了“朝隐”一词。
如上所言,魏晋士人“朝隐”的原因或是由于时局的险恶而不得不由隐入仕,或是由于社会盛行玄学思潮而故作隐逸的高姿态以名利双收。具体说来就是:魏晋之际有一批名士不得不出仕以为全身之道,否则司马氏政权就要惩治杀害他们。在西晋立朝前后,司马氏为扩大政权的统治基础,积极争取社会名流的支持,对于能拉拢过来的名士则予以优待;而对于衷心忠于魏氏的名士则大肆打压迫害,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杀王凌,灭李丰、夏侯玄,除母丘俭,诛诸葛诞,杀嵇康、吕安,因此《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中有“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说法。可见,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对于部分名士而言可谓极其险恶,《世说新语·言语》篇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即可反映当时名士处境之险恶:“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在严刑峻法的政治高压下,不少名士不得不屈服于司马氏的淫威,参与到司马氏政权中以求全身保家,当时的名士比如阮籍、向秀、山涛等人即先后表示对司马氏政权的认同,《晋书》卷四十九《向秀传》记载:“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阮籍等人都是不得不出仕,他们心存畏祸避世之念,曲从而朝隐,居官而不理政事,莅其位而韬光养晦,以求守志远害。因此,对部分魏晋时期士人而言,朝隐是他们面对严酷的政治现实所作的一种无奈选择,但是他们在朝堂之上依然能够保持正直、清高的人格,依然能恪守自己的人格理想追求,有所为有所不为,仍旧能够在朝堂之中活出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尊严来,因而他们仍算是“隐逸”之士,没有侮辱“隐逸”一词。
然而出于动机和目的的“朝隐”则应另当别论。魏晋之世崇尚玄学,人们率以隐逸为高尚之举,为博取此好名声,士人都对隐逸之举心向往之,但是在实践上却不能忍受隐居生活的艰苦;王瑶先生认为,隐逸虽然可使士人获得一个好名声,“但一个‘心迹双寂寞’的真正隐士的枯槁憔悴生活,却不是生活在富贵奢侈圈子里的一般名士们和门阀子弟们所能忍受的。”①曹魏中期的王昶《家诫》中的这段话——“山林之士,夷叔之伦,甘长饥于首阳,安赴火于锦山,虽可以激贪厉俗,然圣人不可为,吾亦不愿也。”——也反映出魏晋士人虽然很羡慕老庄那种超脱、自然的境界,贪慕高隐的好名声,也时有潇洒脱俗、放荡不羁的飘逸行为,但是实际上他们很不乐意到山野乡林中过艰苦的隐士生活,不能彻底的超脱世外,不能不在乎生活的舒适享受,于名利物欲无所挂念,从而出现了南宋鸿儒朱熹所总结的“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②的怪异状况。余嘉锡先生对魏晋士人的这种心理有段鞭辟入里的分析:“魏晋士大夫虽遗弃世事,高唱无为,而又贪恋禄位,不能决然舍去。遂至进退失据,无以自处。良以时重世族,身仕乱朝,欲当官而行,则生命可忧;欲高蹈远行,则门户靡讬。于是务为自全之策。居其位而不事其事,以为合于老、庄清净玄虚之道。”③所以,对这些人来说,最好的双全之法就是“朝隐”,“朝隐”既可以凭借做官过上富足的生活,又可拥有一个好名声,而且也可以生活的优游闲适,实现名利之并收、身心之“两全”。但是这种形式的“朝隐”实质上彻底违背了“隐逸”的初衷。
陈寅恪先生认为,“魏末主张自然之名士经过利诱威迫之后,其佯狂放荡,违反名教,以图免祸,如阮籍、阮咸、刘伶之徒尚可自解及见谅于世人,盖犹不改其主张自然之初衷也。至若山、王辈其早岁本崇尚自然,栖隐不仕,后忽变节,立人之朝,跻位宰执,其内惭与否虽非所知,而此等才智之士势必不能不利用一已有之旧说或发明一种新说以辩护其宗旨反覆出处变易之弱点,若由此说,则其人可兼尊显之达官与清高之名士于一身,而无所惭忌,既享朝瑞之富贵,仍存林下之风流,自古名利并收之实例,此其最著者也。故自然与名教相同之说所以成为清谈之核心者,原有其政治上实际适用之功效,而清谈之误国正在庙堂执政负有最大责任之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虚,不屑综理世务之故,否则林泉隐逸清谈玄理,乃其分内应有之事,纵无益于国计民生,亦必不致使‘神州陆沉,百年废墟’也。”④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山、王等变节才智之士和我们上边所说的不堪忍受隐士生活之苦的士人势必发明一种学问为自己诡辩,此学问可以论证“其人可兼尊显之达官与清高之名士于一身”,从而心安理得的实现名利双收,这一学问现在看来就是郭象《庄子注》里所阐发的圣王思想。
在上述出于个人目的和动机的考虑之外,当时的社会也迫切需要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在当时玄风影响之下,士人纷纷以清远为高,超俗遁世者为众望所归,做官穷于细务者则为时论所鄙;勤于职务的被视为俗吏,为官不理政务者反被誉为高雅,如《晋书》卷三十五《裴頠传》所言:“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这样虚诞的世风肯定直接影响了实际政务的运作,使得行政效率低下,连元康贵“无”派代表人物乐广都觉得这种情况很过分,在《晋书》卷四十三《乐广传》中,他规劝放达名士说:“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此外,“三语掾”的故事也为我们所熟知,《晋书》卷四十九《阮瞻传》记载:“(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将毋同”的意思就是“差不多”。从乐广“名教内自有乐地”的说法和“三语掾”的故事中,我们得知在郭象之前社会上已经有有调和“名教”与“自然”的想法和需要了。汤用彤先生就认为“夫论自然名教相同,乃晋代之通说;圣王合一,乃我国道德政治原则。”⑤
此外,郭象本人热衷政事,《晋书》卷五十《郭象传》说郭象:“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后辟司徒掾,稍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晋书》卷六十一《苟晞传》也称“主簿郭象等操弄天权,刑赏由己。”。《世说新语·赏誉》中说:“郭象字子玄,自黄门郎为太傅主簿,任事用势,倾动一府。”汤一介先生据此认为:“郭象虽为玄学清谈大师,但他不但热心追求名誉和权势,而且运用其权势作威作福。魏晋名士口谈‘玄远’,自诩‘放达’,然往往是名利场中人,其言行不一若是,实为当时之世风。”⑥就是在这样的世风之下,就是这么一个热心政事的人,最终接受了“圣人常游外以弘内”、“其人可兼尊显之达官与清高之名士于一身”的“朝隐”之道,并为论证其合理性而积极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不足为奇的。
庄子所认可的最高理想人格是“离人群”“超世俗”的“神人”“至人”等等;郭象反对庄子的看法,他说:“若谓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得称无为者,此庄、老之谈所以见弃于当涂。当涂者自必于有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逍遥游》注)他认为理想的“圣人”应该是能够“游外者依内,离人者合俗”的“圣王”,他即是“内圣”,又是“外王”。
郭象注《庄子》的目的是要使人“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前者代表郭象对社会问题的总看法,或者说是解决‘自然’和‘名教’关系的总命题;后者代表他对整个宇宙的总看法,或者说是解决了‘无’和‘有’关系的根本思想。”⑦在“自然”与“名教”关系问题上,郭象认为“外王”与“内圣”根本就是一回事,“名教”与“自然”之间也全无矛盾。他说:“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然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绋(扰乱)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不知至至者之不亏哉。”(《逍遥游》注)这就是说圣人不管置身何地,无论“戴黄屋,佩玉玺”,“在庙堂之上”,还是“历山川,同民事”,只要精神上能够超脱淡然、清高绝俗,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为什么“圣人”能够如此?郭象说:“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故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这是说“游外”与“游内”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最能“游外”者也最能“冥内”,最能通达“自然”的人必定是最熟悉“名教”的人,作为“游外之致”者的圣人必定也是“游内之致”者。因为圣人是“常游外以弘内”的,是能够“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的,所以不能看到圣人处理政事,与人群同处,就认为他会被俗人俗事所累;也不能认为顺物之性与之变化,就认为他不能“坐忘而自得”;应该看到,圣人的“神气”(精神境界),并不会因为这些事受到影响,他是能“应物而无累于物”的。
如此一来,郭象通过对庄子的全新阐释,将原本只存在于精神世界的逍遥隐逸落实到了现实的人世间:“入群”即是“遗世”,“应物”即是“坐忘”,“名教”即是“自然”,“外王”即是“内圣”,“入世”即是“出世”。郭象的圣王政治思想为魏晋之际流行的朝隐之风提供了形而上的理论依据,也使得魏晋以来的“朝隐”之风愈演愈烈,这导致的结果则是让更多的达官士人“无所惭忌,既享朝瑞之富贵,仍存林下之风流”,“名利并收”,使得“庙堂执政负有最大责任之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虚,不屑综理世务之故”,从而国家也越来越衰弱。
[注释]
①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02.
②王瑶.《中古文学史论》.206.
③王瑶.《中古文学史论》.80.
④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87,188.
⑤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著.—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2:107.
⑥汤一介.《郭象与庄子哲学》(增订本)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118.
⑦汤一介.《郭象与庄子哲学》(增订本).第135页.
*作者简介:赵亚明(1992-),男,汉族,河南安阳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研管二大队学员16队,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049-(2016)14-0077-02
——王弼名教思想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