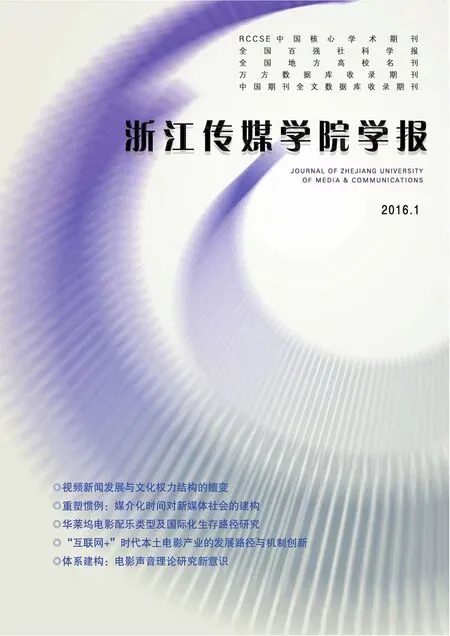真实性话语与现代性焦虑——从《子夜》谈当代中国小说经典的形成机制
俞春放
真实性话语与现代性焦虑
——从《子夜》谈当代中国小说经典的形成机制
俞春放
摘要:茅盾小说《子夜》在几十年的文学传播中经历了经典化到去经典化的历程,阅读者对其评价在不同时代迥然有别。由此出发去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意义,就会发现不同的判断背后却有着相同的话语体系,即关于现代小说的真实性话语及掩藏其中的现代性焦虑,而这一话语体系又深刻地影响到了20世纪中国小说经典的形成机制。
关键词:《子夜》;真实性话语;现代性焦虑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茅盾绝对算得上是一个传奇性人物。这种传奇性不是体现在他作为一个男性而具有女性的细腻,或者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而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出的贡献。在我们看来,更有意思的是不同时期对茅盾评价的迥然有别,而这又主要体现在对茅盾长篇小说《子夜》的评价上。
茅盾一贯以一个经典作家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在中国现代文学家排行榜上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占据“鲁郭茅”三甲之一。成就这一经典地位的主要就是其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子夜》。这部小说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是1933年一部“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扛鼎之作。下面这些说法我们早就耳熟能详:冯雪峰说《子夜》“一方面是普罗革命文学里的一部重要著作,另一方面就是‘五四’后的前进的、社会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之产物与发展”。瞿秋白则肯定道:“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鲁迅给曹靖华的信中,就有过对于《子夜》的经典评价:“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寄上),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及的。”[1]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在“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之下,对茅盾及《子夜》评价的另一种说法也是一时之热。如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中认为《子夜》是一部抽象观念加材料堆砌而成的社会文献,作品对社会生活的大规模描写,完全是服从于作家的先行主题的。这种配合现实政治斗争、指向性很强的描写,根本谈不上反映现实的真实性,是笨重而使人生畏、可读性较差、缺乏艺术魅力的“高级社会文件”。缺乏主体性体验,缺乏时空的超越意识,过于急功近利,没有深刻的哲理内涵作为恒久启示,缺乏对人性、生命和宇宙意识的透视。王晓明则在《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论茅盾的小说创作》中指出茅盾创作中有滑坡现象。《蚀》三部曲是在对往事的情感记忆中获取灵感,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风姿;《子夜》、《林家铺子》等则每每是从判断时事的抽象例题出发去进行构思,拥有明确的社会政治主题。认为茅盾是随时代潮流而变化。他从最初提倡“为人生”文学起就有强烈的功利欲求,此后十几年政治热情不减,到30年代大爆发,以致掩盖、压抑了自身艺术素质的充分发挥。持非议的自然不止蓝、王二人,事实上在90年代出版的《二十世纪大师文库》中,茅盾已经被排除在20世纪众多文学经典作家之外。
在此,我们无意再去讨论《子夜》的艺术性问题,让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对《子夜》评价迥然有别的背后,却有着相同的话语体系,即关于现代小说的真实性话语及掩藏其中的现代性焦虑。我们的意图便在于从《子夜》出发,探索这一话语体系如何影响到20世纪中国小说经典的形成机制。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真实性话语
从商务印书馆时代,茅盾就开始了对国外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以“为人生”的文学作为标记,反对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创作大多以现实人生为一般问题,形成所谓的“问题小说”。作为12个发起人之一、文学研究会的首席批评家、改革后的《小说月报》的首任主编,茅盾虽然强调对于为艺术的艺术和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但在他自己的文学主张上却为新文学的特征作了明确规定:“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2]这种主张背后是文学创作上的理性实用原则,与50年代茅盾在《文艺报》上发表《关于文学研究会》时所总结的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遥相呼应。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以及与之相应的在艺术形态上的典型化主张。
《子夜》毫无疑问是这种创作模式的代表。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子夜》作为焦点备受关注自是不争的事实,在此无需多加辨析。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将其定位为“社会剖析派”,从形态上确立了其经典地位。[3]在我们看来,这种经典性来源于两个方面,即时代主题的书写及与之相应的现实主义形态。
茅盾在谈到怎样写成《子夜》的原因时,首先就点明了其时代性:“1930 年春世界经济恐慌波及到上海。中国民族资本家, 在外资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威胁下,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更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增加工作时间,减低工资,大批开除工人。引起了强烈的工人的反抗。”[4]而事实是当时的学术界正在展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因素下,他准备用小说的形式来写出三个方面:“(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 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 为要自保, 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 (三)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4](17)三块内容背后其实是同一个话题,即中国到何处去或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道路问题。撇开我们已经略觉不习惯的意识形态术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的是,支撑起对时代主题书写的是经典现实主义话语,它不追究存在之思,而是以历史书记官的身份,力图去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小说以吴老太爷进城拉开全书的序幕,在吴老太爷的丧事上以例证性动作引出小说绝大部分主要人物,之后进入小说的主体部分即“对抗”部分,围绕公债市场的斗争、裕华工人的罢工及双桥镇农民反对恶霸地主的斗争三条线索写吴荪甫(民族资产阶级代表)、赵伯韬(买办资产阶级代表)对抗,最后以吴荪甫的全面失败告终。这种书写形态带着些史诗式的气概,力图用社会透视的结构来包容复杂的矛盾、丰富的生活及众多的人物,所谓展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这种特点既是茅盾成为经典作家、《子夜》成为经典小说的缘由所在,同时也是后来出现另一个声音的根本原因。在我们看来,两者观念尽管大相径庭,其心理结构却是一致的,即作为意识形态的真实性话语。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指出,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各个门类彼此呼应,协同推动一个巨大的观念体系缓缓运转,这一情况在20世纪中国文学写作中显得更为直接。
中国的文人历来有文学写作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情结,就小说而言,就是被赋予一种史传性质,而史传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解构历史”文本。历史被叙述为一种话语,《史记》就是典型的代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有趣的现象,即写作过程成为混杂了家国叙事与个体体验的话语建构。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指出:“以小说比附史书,引‘史传’入小说,有助于提高小说的地位,再加上历代文人罕有不熟读经史的,作小说借鉴‘史传’笔法,读小说借用‘史传’眼光,似乎也是顺理成章。” 因此,陈平原接下来说道:“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经,以广阔的社会画面为纬,如此构思长篇小说,‘新小说’家颇为自觉。”[5]中国现代小说尽管是来自于西方的文体,但毫无疑问在接受过程中已经进行了充分的中国化。首创“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提出“新民”、“新国”的理念,强化小说的社会话语实践功能,从根本上来讲与这种“史传”精神的内核是相通的。文学的使命感又一次被强化,小说被定性为观照和改造现实的器具。“新文化运动”以来,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提出“写实文学”、“国民文学”、“社会文学”的概念,周氏兄弟更是理论和创作双重推进,强化了文学的“为人生”功能。无论是周作人从“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角度加以阐述,还是鲁迅以他“写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在创作上的推动,无不呈现出西方现实主义小说思潮中国化后的鲜明特征。然而这是个启蒙的时代,20世纪文学研究至此终是不免充满感慨,认为之后救亡取代了启蒙,以至文学的政治功能被相当程度地延展。我们姑且把两者间的价值之争放在一边来面对一个基本的事实:从作为启蒙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甚至可以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个现实主义小说从话语建构到知识实践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对“平民”的关怀开始(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对平民文学、人的文学的阐述),历经对国民性的探索(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到最后将文艺定义为广泛的人民事业去反映人民的现实生活和历史愿望。
其话语建构越到后来越呈现出以唯物主义为哲学依托的倾向,“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这类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论或者其他类似的如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都成为人民耳熟能详的对小说创作和评论起指导作用的标杆。而在其知识实践上,我们看到,从50年代至80年代,现代小说艺术的探索尚未出现,歌功颂德的“非文学”自然不在我们讨论之列,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只剩下“干预文学”。小说成为小说家们揭示、分析政治问题或社会重大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的文本。无论是建国之初王蒙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这一类揭示“进城”后存在或产生的问题的小说,还是新时期之初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甚至“题材热”时期农村题材、城市题材、工业题材等各类题材,均是在小说中提出或制造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然后加以分析揭示,背后的终极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从本质上讲,这种“干预小说”和茅盾的“社会剖析小说”是相一脉相承的。不再将《子夜》神化之后,人们更多看到的是茅盾的困境。他对小说史诗般的构造成全了他却也给人留下了言说的空间。五四时代的激情开始被理性分析所取代,时代的功利性要求加上本身的政治身份使得他对社会问题作了简单化的解答,而与之相应的就是在人物形象的处理上偏重于表面的复杂性,给吴荪甫安排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其矛盾,但这一切却无法掩盖人物形象作为审美对象的苍白。
然而我们还是无意于对茅盾的小说作更多的价值判断,我们始终认为这种判断事实上也是一种解构历史的叙述文本。我们回过头来讲,从社会剖析小说到干预小说,包括到题材热时期各种题材的小说,因其强调注意社会问题、提倡干预生活,再加上主流意识形态积极倡导唯物主义,必然形成纠缠于现实主义叙事法则的美学形态,真实性问题也随之变成一种超验的元语言,对于文学的言说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了对真实的言说。换句话说,现实主义叙事法则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真实性话语,在上述多重要素的综合作用之下,带上了强烈的主流意识形态性,成为对小说所有话题都能加以言说的超级能指。何西来在发表于1982年第1期《新文学论丛》上的《现实主义——新时期文学的主潮》一文就认为文艺必须真实,不真实的文学艺术是没有价值的,是人民所不需要的。同是80年代,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却认为中国闭塞太久,“文化大革命”以后人们对西方文学的了解还停留在19世纪,具体的一个表现就是对现实主义近乎看成真理。温儒敏对这一现象的总结是:“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现实主义’这个词用得太滥了;如果有哪一部作品被扣上‘反现实主义’这顶帽子,差不多也就等于被判处了艺术生命的死刑。”[6]由此反推,《子夜》的经典性问题事实上跟现实主义叙事法则及相应的真实性话语密切相关。其所以成为经典,固然由于人们对于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主义及真实性的首肯,而最终另一声音的出现也可以理解为对于作为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美学形态疏离以及对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真实性话语的怀疑。事实上我们看到,先锋小说的出现从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了经典现实主义的叙事法则及其关于真实性的界定,开始将叙述本身作为小说第一要素(马原),强调全新的经验世界(格非)及作者在小说中的最终退场(余华)等等,形成一种众声喧哗的局面。如果说先锋小说以提供新的经验及经验方式为小说创作打开了现实主义之外的另一扇门的话,那么紧随其后的新写实小说则进一步改写了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集体记忆——小说固然已经不再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真实”也已走出“本质的真实”而趋向于对碎片化的表层的认同,而新生代的崛起以及70后写作带来的物欲世界的私人化体验则彻底使小说写作向内转,从对于外部世界普适性问题的描述转为对于个体内心的探秘。
上述对文学史的回顾使我们看明白一点:90年代初对《子夜》经典性的质疑主要倒不在于对《子夜》本身的质疑,其结构性“缺陷”以及人物的“概念化”处理不至于是一个需要等上几十年才能让人看清的问题。《子夜》只是一个个案,背后的实质是20世纪中国小说经典机制的变迁。这种变迁一变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诉求,二变于小说观念上的内化。换句话说,《子夜》经典性的确立一直与现实主义及其“真实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化密切相关,最初的质疑来源于80年代重拾启蒙后在文学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去主流意识形态化本身也是一种鲜明的意识形态,而最后的颠覆则在于进入90年代后文学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观念变化至斯,重新定义经典及重排文学史座次就变得自然起来了。
颠覆经典或可看作是一时的快感。90年代后,文学写作迅速从面向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进入消费时代的个人化写作,看上去像是对一个过去的时代的戏谑与解构,然而在我们看来,其心理结构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现代性焦虑。这种焦虑感从近代文学以来便已存在,至今仍在延续,成为判定文学经典的一个心理基础。
二、心理积淀中的现代性焦虑
现代性焦虑已经是一个老话题,但我们今天来回顾20世纪以来中国小说的经典问题时仍然觉得这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杰姆逊在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已故同事和友人罗伯特·艾略特而举行的第三次纪念会上的演讲稿《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认为对民族——国家的强烈而又独特的体认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政治无意识”。他指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他们执著地希望回归到自己的民族环境之中。他们反复提到自己国家的名称,注意到‘我们’这一集合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不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如何能够比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做得更好、我们具备自己独有的特性,总之,我们把问题提到了‘人民’的高度上。”[7]事实上杰姆逊所指认的“政治无意识”正是一种现代性焦虑。这种焦虑贯穿于20世纪以来的文学写作,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元叙事。“五四”新文化运动伊始,对外国文学创作与理论的译介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口甘露,而80年代重拾启蒙时又将目光转向了西方20世纪以来的文化思潮,把西方整整一个世纪所走的路,用两到三年走了一遍。有意思的是,“五四”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意在构造一种新的关于民族——国家的书写,如鲁迅的小说成为一种“民话寓言”,在“写出沉默的国人的灵魂”过程中,从呐喊到彷徨,而最终以讽刺戏谑表达对现实深层的绝望,绝望背后其实就是一种现代性的焦虑。到80年代这种焦虑尚未消减,依然是努力构建家国话语,韩少功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8]与其说是一种底气倒不如说是发自内心的不安。文学史提到寻根小说时认为寻根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创作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是文化意识的形成,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单一的政治视野;二是打破了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的单一格局。这自然是极有道理的说法,却也并非就能掩盖了“寻根”时期及此前此后急于在世界之林中对主体身份加以确证的深层心理结构,说白了就是一种怕游离于世界之外的现代性焦虑。
这种焦虑感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历史记忆。清末国势式微,历史告诉我们西方列强用坚炮利船敲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落后就要挨打”这种观念至今仍被人不假思索地接受并为此而伤感,在西方面前,主体建构过程中的压迫感转化为对现代化的焦虑。
这成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一种独特传统。家国的主体身份在焦虑中得以认同,对焦虑的书写则成为一种执著的文学实践。当世界经济新秩序将古老中国强制性地纳入其体系中时,家国生存意识强化为一种现代性焦虑,并最终成为一种文学元话语。以新时期文学为例,我们随手择取的小说中都能读出这种意味。如工业题材的经典之作《乔厂长上任记》开篇就以主人公乔光朴发言记录的形式来营造一种紧迫感,为整个小说定下了基调。乔光朴说:“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先讲时间。如果说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那么咱们这个给国家提供机电设备的厂子,自身的现代化必须在八到十年内完成……再看数字。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二百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这说明什么?要求我们干什么? ”[9]在这里,不同国家的两家企业被贴上国家身份,个体情感被强化为家国意识,在放大了时间和数字的差异之后,现代性焦虑成为该小说书写的真正命题。而路遥的《人生》却以一种退守的姿态来表达这种焦虑。小说展示的是关于人生的选择,正如同名电影剧本上所写:“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10]主人公高加林的选择就是“事业上的”和“个人生活上的”,在路遥看来,他走岔了道。所以生活给了高加林鲜活的教训,而小说中担任“导师”功能的德顺爷爷则在高加林沮丧地回到乡下时,语重心长地跟他讲了这番话:“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是不,不会有!只要咱们爱劳动,一切都还会好起来的。”[11]而高加林之所以最后被安排了这一命运,只是因为在他的内心中有一种不安定的因素,正如他的女同学,同时又是爱着他、与他有更多共同语言的黄亚萍赠给他的小诗所说:“我愿你是生着翅膀的大雁/自由地去爱每一片蓝天/哪一块土地更适合你生存/你就应该把那里当作你的家园……”[11](61)高加林代表的更具现代性的追求在预先占领了道德制高点的乡土情结面前自然受到了毫无疑问的批判,但这似乎并不能看作是对现代性的质疑——尽管这种质疑在当时的小说中大量存在,比如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以感伤的笔调去写葛川江边行将消失的乡村文化形态——在历史语境中质疑是脆弱而可疑的,我们毋宁说这更像是一种应对现代性焦虑的策略。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子夜》似乎与比它晚了几十年的《人生》有某种相通之处。两者都是关乎现代性的选择,都在道德制高点上将主人公预先置于终将失败的悲剧命运,而在潜文本里主人公又反身成为某种具有开拓性的“英雄”。这种复杂的潜文本正好契合了作者的焦虑感。
创作《子夜》的上世纪30年代初既是茅盾创作上的转型期,也是社会背景的一个转型期。1927-1937年是中国“红色的30年代”,就文学创作而言,这是作家直接投身社会革命、以文学创作介入社会变革的十年。这十年风云际会,民众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暴涨,为左翼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基础。本身就作为早期中共党员的茅盾从更具个人化写作特色的历史叙述(作为知识分子心灵史的《蚀》三部曲)中抽身出来,进入社会剖析性叙事,自然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了。
《子夜》创作之际,正是中国思想理论界展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之时。因其身份原因,茅盾的写作带着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寄希望于通过自己的小说创作,以人物命运来回答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这必然使他的写作带上了民族、国家、阶级等富有内涵的词汇。而这些词汇在表达理性分析社会性质问题的政治使命的同时,实际上更多地体现了杰姆逊所说的“政治无意识”:一种情感上的家国身份认同,外化为一种对现代化世界的复杂感受。
这种复杂感受首先表现在对现代都市的迷恋。茅盾最初的构想是通过描绘30年代中国社会的全景图来完成他的政治化写作,但成书后明显偏重于都市生活,双桥镇的农民运动远不及上海大亨们的斗法来得精彩。说是“成书太仓促”也罢,说是对农村生活的熟悉程度远不及对都市生活也好,其实都只是一种表面的因素,从本质上来讲其实是发自内心的对都市的迷恋。小说开端场面的描写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摸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这时候——这天堂般五月的傍晚,有三辆一九三○年式的雪铁笼汽车像闪电一般驶过了外白渡桥,向西转弯,一直沿北苏州路去了。”[12]这段文字中有种来自内心的喜悦感,开场第一句话定下情感基调,然后用一连串的细节来强化:苏州河和黄浦江的水、苏州河上的船只、外滩公园的音乐、外白渡桥的钢架、电车与电车线间的火花、霓虹电管广告及1930年式的雪铁笼汽车。从潜意识里来讲,《子夜》中写到的一些次要人物,佩瑶、佩珊、博文等等的日常生活,与卫慧的《上海宝贝》中天天的生活方式:“在床上看书、看影碟、抽烟、思考生与死、灵与肉的问题、打声讯电话、玩电脑游戏或者睡觉,剩下来的时间用来画画、陪我散步、吃饭、购物、逛书店和音像店、坐咖啡馆、去银行,需要钱的时候他去邮局用漂亮的蓝色信封给妈妈寄信。”[13]在精神内核上是何其相似。
对现代世界的复杂感受还表现在人物塑造的复杂性。小说以民族企业家吴荪甫的悲剧命运为结构性线索展开叙事。命运的悲剧性常常来自于一种不可抗力,并且这种不可抗力常常会带上存在之思,如俄狄浦斯的悲剧。吴荪甫的悲剧也是来自于一种不可抗力,但这种不可抗力来自于一种先验的判断,即茅盾所认为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途是非常黯淡的。基于这样的一个前置判断,吴荪甫的个人遭际便被纳入公共空间,他的败局便等同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失败,他的困境便成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困境。可是吴荪甫本人却是一个迷人的人物形象,茅盾在字里行间也不吝欣赏之情,完全是塑造了一个现代型人格。这个人物从德国学成归来,有西方现代科学的背景;这个人物有事业心,他的事业不是光想着自己赚多少钱,而是有一个家国梦想,所以他对大舅子杜竹斋有些不以为然,而在大谈三民主义的政客唐云山面前却“只有吴荪甫的眼睛里却闪出了兴奋的光彩”(《子夜》第3章)。茅盾借林佩瑶赞美吴荪甫是“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子夜》第3章)。他描写吴荪甫的语调充满着激情:“荪甫的野心是大的。他又富于冒险的精神,硬干的胆力;他喜欢和同他一样的人共事,他看见有些好好的企业放在没见识,没手段,没胆量的庸才手里,弄成半死不活,他是恨得什么似的。对于这种半死不活的所谓企业家,荪甫常常打算毫无怜悯地将他们打倒,把企业拿到他的铁腕里来。”(《子夜》第3章)正如前面说到大量感性的细节透露了茅盾对都市的迷恋,在吴荪甫这个人物形象上面,我们也注意到了他用大量感性细节透射出来的主人公的个人魅力。
将理性的框架与感性细节的把握融在一起,自然有茅盾的天资在起作用,但其实也说明了作者对于现代化的感悟与理解。光怪陆离、眼花缭乱的洋场世界是他对现代性的直接感知,《太上感应篇》固然救不了的吴老太爷,“一代枭雄”吴荪甫也最终落个悲剧命运,“民族”的“传统文化”固然已经落为一种“糟粕”,“民族”的实业家也逃不了现代世界里在“西方”面前的溃不成军。于是寻找一个乌托邦世界便成为自然的事。正如王晓明在《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中所认为的那样,在当时茅盾的心目中,写文学论文和从事政治活动本就是互相联系的事情,都同样能够满足他改造社会的内心热忱。茅盾的政治身份使他在小说中为现代性困境寻找这么一个答案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认为现代化的实现就是要在回应现代观念和制度的挑战、现代性因素充分积累的基础上,生活方式由农业为主转向工业为主,社会文明结构得以重组后才能得以实现。而对我们来说,现代性的焦虑来自于中西方冲突中的焦虑:一方面由于西方的侵入而使本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破坏,另一方面来自西方的“现代性”又成为一种无以抵抗的诱惑。于是就造成了一种有趣的现代性叙事:在反西方中向西方靠拢,在反现代性中深受现代性诱惑。
《子夜》正是如此。现代性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生活方式也已经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连冯云卿这种靠一亩亩骗取农民土地而发家的乡下地主都进入到了上海公债市场。西方的入侵不仅使中国农村完全溃败,而且也让中国民族资本陷入绝望,而正是在这种“反西方”、“反现代性”的情绪中,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现代性的社会经济结构才成为迫切的需要。
现代性焦虑作为“元叙事”贯穿了现当代中国小说创作,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评判小说经典性的一个标杆。新时期以来,经过短暂的“伤痕”与“反思”,无论是社会建设还是文学写作,都进入一个“现代化”时期。此一时期各种题材的小说,能引起广泛关注的,无一不是如《子夜》一样,用以提示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的,其基本话题就是“中国如何进入现代化”及“现代化的中国向何处去”。这种情况下,《子夜》作为经典的一个标本稳居文学史中的地位是可以被理解的,即便是后来被非议的结构性缺陷与人物的概念化,此时也并不是主要问题。事实上此时人们更多的是以“开阔的社会视野和贴近时代脉动的描写,揭示了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来看待《子夜》。同样,对人物的理解也着重在人物本身的鲜活性——不可否认的是,像吴荪甫这个角色,除了最后强奸女佣的行为可能让一些人觉得意外,其他方面来看,这个人物都是鲜活的,后来的所谓概念化,主要还是硬塞给了他一个悲剧的结局,而不是按人物性格来推进叙事的展开。而80年代前后各种题材的创作,在“真实性”与现实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背景之下,基本上走的就是这条道路,现代意识与现代物质文明冲击之下农村的改革开放问题、城市的工业改革问题等诸如此类,现在来看,很多都是在对现代性的复杂感情之下概念化地处理社会现实问题及结构人物故事,而这放到当时的语境中去,却其实是一种经典化的书写。笔者一直认为贾平凹的《废都》是他写得最好的小说,这部小说完全是一部“失控”的小说,作者对现代性的焦虑已经无以复加,焦虑已经成了写作本身,原本那种现实主义规范下的经典化写作则处处显露出其局限性。
《子夜》的非经典化及小说经典概念的变迁在80年代才刚刚开始,后面起码还有两大因素在等着:一是在走出二元结构后的精英意识;二是文化市场上大量消费者被唤醒。前者主要发生在80年代初中期,写作开始走出形态上的现实主义独尊,在内容上也不再关注具体的社会问题,开始把精力放在小说艺术可能性的探讨与人的存在的本质之思。新的叙事形态消解了《子夜》及此类小说的经典性,同时似乎也消解了现代性焦虑。但事实只是消解了前者,而后者却得到了强化。外来的概念被津津乐道(如马原的那个本质上从博尔赫斯那里搬过来的叙事圈套),一些国外著名作家作品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更是如雷贯耳。诸如《追忆逝水年华》、《尤利西斯》、《万有引力之虹》、《芬尼根的守灵夜》、《百年孤独》等作品及博尔赫斯、卡夫卡等作家,对国内诸多作家及文学爱好者来说,作品不一定看过,但提到作家作品的名字时必须朗朗上口。创作者与阅读者都期待着一次决裂,理论界不失时机地宣称“写什么”的时代已经过去,“怎么写”的时代正在来临,一批代表着新的美学趣味的小说应运而生。显然,强化的就是那种急于融入世界现代小说之林的焦虑感,或者说是一种建立在文化抵抗上的家国认同。如果说这种决裂与认同主要还是在精神层面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后,文化市场上大量消费者被唤醒则主要在于物质层面,问题意识已经成为一个大而无当的话题,个体在这个物质化的世界中的体验才是最主要的。
因此,可以说现代性焦虑一直是现当代中国小说写作中绕不过的话题,但是焦虑本身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是不同的,这也影响到了中国小说经典的形成机制。
三、结语
时至今日,就茅盾谈茅盾似乎真的已无大的必要,这也差不多成了某种共识。2009 年,《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王保生曾结合该杂志近几年来稿的情况指出:“‘鲁郭茅巴老曹’六大经典作家中,关于茅盾研究的来稿是最少的。”[14]话虽如此,但茅盾的经典意义是不可否认的,他对中国20世纪以来的小说贡献不仅体现在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积极倡导,还体现在他身体力行的创作实践中。他的《子夜》往往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这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话题。
就我们而言,《子夜》在文学史地位上的变化及20世纪以来小说经典机制的变迁,与其说是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回归自身的文学性、审美性,倒不如说是一种话语的变迁。话语的核心是一直困扰国人的现代性焦虑,这种焦虑至今大有继续不断延展之势。正是因为这种焦虑感的存在,才可能使小说的真实性及现实主义带上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形成一种以时代精神为内在规定、以现实主义为美学形态的经典标准体系。也正是这种焦虑感的存在,才会在重拾启蒙时,强调文学创作上的去意识形态化,强调对艺术表现广度和深度上的可能性掘进,形成一种全新的包括去意识形态化之后的现实主义在内的经典标准体系;而也正是这种焦虑感,在走出了意识形态化与反意识形态化这对政治话语后,在一个非政治的、无中心的消费社会,逐渐形成着新的叙事话语。
历经一个多世纪时间的洗礼,现代小说已经发生了长足的变化。再去纠缠一部八十几年前的小说的艺术性或者来指责当下这个消费时代去经典化心态对小说艺术的不敬都没有太多意义。现代化困境构成了我们庞大的语境,这个问题还将长期存在,可能只有当我们不再意识到这个问题时,才是困境消解之时。
参考文献:
[1]刘勇,张弛.茅盾及现代文学的经典意义[N].文艺报,2011-07-15.
[2]沈雁冰.新文学平议之评议[A].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48.
[3]严家炎.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75.
[4]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J].读写天地,2002(3):17.
[5]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22,229.
[6]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7]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30.
[8]韩少功.文学的根[A].林建法,王景涛.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82.
[9]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EB/OL].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3139535/,2011-10-27.
[10]路遥.人生电影剧本[A].路遥文集(1、2合卷本)[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477.
[11]路遥.路遥中短篇小说.随笔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90.
[12]茅盾.子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
[13]卫慧.上海宝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3.
[14]陈迪强,钱振纲.“茅盾与时代思潮”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5).
〔责任编辑:高辛凡〕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6)01-0109-08
作者简介:俞春放,男,讲师。(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