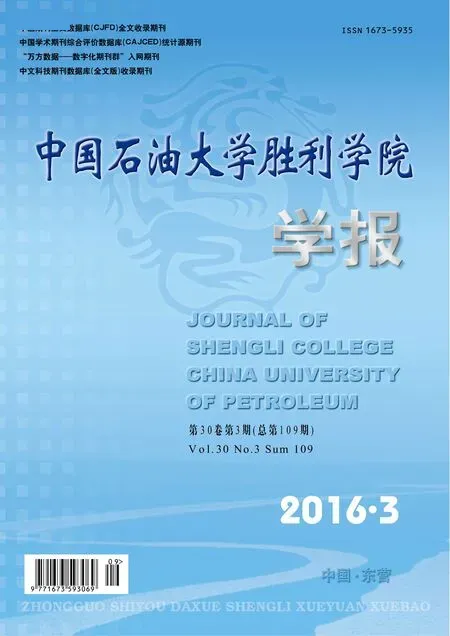从“影视到小说”的当代影视文学现象
刘 玥
(山东大学 文学和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3)
从“影视到小说”的当代影视文学现象
刘 玥
(山东大学 文学和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3)
小说改编成影视剧之外,先有影视剧再出现同人小说也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新现象。文学的广阔性与无限性相较影视的固定性、有限性,有较多的发挥空间,可以阐述被影视弱化、舍弃、隐藏的内容,同时,影视直接地表现为读者进行文学阅读提供了基础。从影视发展到文学创作,也契合了文学创作商品化的趋势,在把握读者趋向,吸引读者群体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由于影视文学作者写作能力参差有别,对影视文学文学性的讨论此起彼伏,成为最有争议的部分。
影视文学;文学商品化;文字符号;视觉艺术;再阅读;文学性
影视与文学分别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自身区别于彼此的特性为二者的交互融合提供了诸多的可能,在当代比较普遍地表现为将小说改编成为影视剧。影视剧将文学作品形象性地进行了再次演绎,扩大了文学的受众群体,也为影视剧提供了大量潜在观众。值得注意的是,从文学到影视的转化并不是单向的,仍然存在一种先有影视作品继而出现相应文学作品的现象,例如刘震云的《手机》、薛晓路的《北京遇上西雅图》、于正的《宫锁沉香》等等。“从先有小说再有影视,到先有影视再有小说,看似一个简单的反转,却是一种崭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生命,不但预示着文学旺盛不衰的活力、生机和创造力,也预示着文学的希望、未来和前途。”[1]
一、影视文学出现的重要动因:商品化
当代文学包括影视文学在内,所面临的情况是它们不再被要求承担一定的实际功用,反而随着文学出版流通的商品化,成为一种流通于市场的消费品。文学作者不再拥有冯骥才所说的“信使般的使者”的崇高责任感,却成为本雅明口中“现代城市的拾垃圾者”。为顺应文化消费的需求,文学生产必须去满足公众的审美趣味,同时也被商业规则所支配[2]。虽然文学的独立的主体性一直在被强调,文学应该有其自身的评价标准,不应过于功利,但是在商品化与世俗化日渐浓厚的背景下,一个作家写作时要体现特立独行的立意、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可是不考虑生存问题、温饱问题也是不切实际的,那么他就应该在可达性与可行性之间寻求一个平衡,而非仍旧独行其是。虽然说文学之外的因素应该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刻意地规避,但在当下的文学生产流通环境下,文学的商品化程度也不失为衡量文学作品质量的一大标准,尽管这一标准并不绝对或者并不拥有完全的权威性。影视先于文学出版,能够提前洞察大众的审美趣味,尽可能迎合读者的阅读喜好与阅读期待,获得最大的市场效益。同时,一部成功的影视作品也会为影视文学带来大量的潜在读者,被影视作品培育出的忠实的爱好者,当面对由此部影视作品改编成的小说时,出资购买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另外,影视接受可以视为影视文学接受的一部分,读者出于阅读方便、高效的考量,也会愿意选择影视文学。由此观之,影视文学的出现存在着极大的商品化目的。
二、影视与文学的沟通
影视文学作为影视向文学转变的成果,保留并融合了影视与文学的双重属性,展现出其与其他文学形式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形象、叙事与接收三个方面。
(一)影视形象对文学形象的固定
文学以语言文字符号刻画形象、表情达意,作用、形成于人的想象,属于语言的艺术。而影视用以描绘世界的手段往往是直观的画面、形象等符号,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是视觉的艺术。文学形象不能通过人体感官进行直接接受,需要读者充分发挥想象,即便同一部文学作品中的同一形象也往往以不同的面貌存在于不同读者的脑海中。相对而言,影视要求通过图像来逼真地临摹出世间的人生百态,也就是说,文学形象是灵活变动的,影视形象却是固定的。影视的影像跳过了文学阅读到读者头脑中形成形象的感知过程,直接进行图像的观看,向观众灌输影视生产者的见地,这就构成了影视的“暴力与独裁”,影视接受以及形象形成过程中读者的交互反馈作用是不被允许的[3]。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常常使读者认为不尽如人意,文学形象形成于读者的头脑,是依靠文学描写而存在的特定的却又不成形的个体,这个个体在文学作品中的“留白”部分使读者自己有很大的自主权。影视则是强硬地将“留白”补足,再贴近于想象的现实再现依然会存在龃龉,形成现实与想象的落差。影视小说创作作为小说改编成为影视作品的逆向活动,由于固定化的影视形象是先入为主的,读者对随后进行的文学阅读便会将已经固定了的形象带入文学叙事中,先前接受的影视形象可以说成为统领文学想象的导向,成为文本阅读中文学想象与文学形象塑造的一部分。
(二)文学对影视形象、叙事的丰富
美学理论认为文学语言具有间接性和广阔性,文学阅读中作者与读者以文本为中介进行并不发生面对面相互作用的活动[4]。相比之下,影视表现也就固定得多。文学叙事表现是网状结构,由于文学表达借助表意的文字,文字的表达又是灵活的,一段文学表达可以同时交代广阔的时间、空间背景;影视只能以时间为脉络以进行的方式将情节展开,更多强调的是单调的纵向发展。这里并不否认影视中对于倒叙、插叙等打破叙事顺序的手段的运用,但相比于文学,其运用则僵化得多,一些人物关系、前因后果只能随着故事的发展借助不同的手法加以补充说明,令接受者不能理解的部分,只能针对即时出现的铺陈空白进行补足,颇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意味。文学与影视发生关联都会出现情节脱节的现象,不同的是将文学作品改编成为影视作品是进行削减,这依然可以用文学语言的间接性、广阔性与影视传达的进行性来解释,同一个叙事长度,文学可以用可多可少的文字进行表达,读者也可以自由控制阅读时间,但诉诸影视只能在限定的时长内叙述出来,所以于影视表现不甚重要或者表现有难度、不得力的情节就会被舍弃,更有甚者影视作品只保留了原作的人物及关系,而情节与主题却南辕北辙。除此之外,影视直接以描绘客观生活的方式来推动情节进展,这也就要求影视表现要符合日常逻辑与大众审美,不能惊世骇俗、离经叛道,那些能在文学中出于补偿动机不为日常逻辑所接受、在日常中难以实现的情节就要被删减;影视小说则是进行增添,例如,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的同名小说不但讲述了电影中拜金第三者为生子远赴美国,在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下患难见真情的故事,而且也对文佳佳父亲患病无钱医治的身世、她在日常交际中的心理与行为进行了细致的刻画描写,使人物形象十分丰满,一个赚钱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做人情妇却又没有完全被声色犬马物质世界所规驯的女性形象呼之欲出,使其在短时间内个性由重钱到重情的转变不至于突兀,令读者觉得无可厚非。小说在叙事过程中也穿插介绍了在当今社会存有的婚外情、出国生子现象以及做出这个选择的人员构成,也间接涉及同性恋家庭伦理问题、中国大陆独生子女形式与二胎现状以及国外非法月子中心的经营状况,小说在反映现实的功用、广度、深度上要远远优于电影。
(三)文学再阅读
所谓再阅读,即对已经被阅读了的作品,在已得到的意旨基础上再一次进行的阅读[5]。文学作品的写作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活动,文本本身就是开放、未完成的,出于文本的这个特点,一部文学作品由作家定稿再经由媒介传播,最终由读者阅读,创作过程才算最终完成,作品的意义才算真正地发挥出来。所有对文学文本的解读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与初次阅读读者对作者的写作习惯、情节架构需要熟悉相比,再阅读在一种轻车熟路的状态中更能深入挖掘文本文字之外的其他意义。通过对影视的观看,观众对整个故事架构有了初步的了解,可将其纳入对文学文本的初次阅读的形式之一,而且影视以其直接性,对情节传输的明了易懂、简洁快速的特点为传统阅读所不具备,大大缩短了文学阐释的时间长度,有利于文学文本意义的不断涌现与翻新。以《手机》为例,电影《手机》以严守一邀请费墨因录制自己的《有一说一》特别节目来到一个度假村的情节展开,与之同行的除了严守一的女友沈雪和费墨的妻子李燕外,还有与之有着不明关系的另外两位女性。在度假村的生活中,严守一和费墨被美女环绕却又忍受着被四个女人不断地猜疑、纠葛,前一刻重情重义的严守一后一秒就又恢复成了“花花公子”的真实面貌,人前被人倾慕、为人师表的费墨却是妻子口中的“衣冠禽兽”。电影《手机》无非是讲述了一个关于谎言的荒诞故事,小说却将电影中的一部分扩充为三部分,这使得小说《手机》中人物关系更加复杂,加之刘震云多用反讽,表现手法较为含蓄,对读者来说解读小说文本网状结构所承载的巨大的信息量是有难度的,电影《手机》以角色的行动、对话直观地将情节得以展现,并用不同的演员面孔对人物形象外观进行标示,读者才能在对故事梗概、人物关系有了清楚认知的基础上回到文本后做出快速且合宜的深层意义挖掘。带着对故事脉络的把握阅读刘震云的小说《手机》,会发现在围绕着手机展开的暗流涌动的故事之下隐含着社会上关于家庭与情感的道德问题,尽管严守一所谓的个人隐私有悖于社会道德,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仍然在隐私范围之内,严守一要守住隐私,而沈雪却想方设法的窥探隐私,正是因为这种对抗,才出现了一幕幕婚恋悲剧,最终导致了谎言的产生,作者的立足点是日常生活中的“说话”,主人公严守一是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以“说话”为生,如名所示,有一说一,他的节目以说真话见长,但在平日生活中,他不由自主地开始说谎,与自己主持的节目《有一说一》相对照就显得极为讽刺。最后严守一甚至对说话产生了恐惧,从而令手机变成了定时炸弹,变成了“手雷”。
三、影视文学面对的争议:作家能力
影视文学面对的最大争议应该在于其究竟算不算是优秀的文学,甚至说,它们能否算作文学。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探讨了作者的文学创作素质对作品质量的影响,刘勰关于“才、气、学、习”[6]1010的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作者的性情决定文学作品的风格与面貌,文学作品的形成过程中,作家起到了主导的作用,文学也就是人学[7]73,作家的创作素质对文学文本质量的影响是直接的,作者创作素质差异也就导致了作者的创作能力、水准、定位的差异性,“才有庸俊”[6]1011,才气有层次和程度上的差别,文学作者应该才华超众,并且具有创新精神,才会有独到的手法和眼光。《手机》的作者刘震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鲁迅文学院攻读研究生,中国作协会员,在《手机》之前就发表了《新兵连》《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等优秀的文学作品;《北京遇上西雅图》作者薛晓路,同为同名电影的导演、编剧,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中国作协会员;《闯关东》作者高满堂,国家一级编剧,编剧作品有《温州一家人》《红白喜事》等著名电视剧;《宫锁沉香》作者于正,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著名编剧、制片人;《小爸爸》作者文章,著名演员。由此可见,影视文学作者的写作能力是难以判别的,按刘勰所论,“才”与“气”皆取决于天性禀赋,后天的社会、舆论、文化、道德的浸染、教育则对“学”和“习”产生深刻的影响,先天赋性与后天所得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构成文学创作影响因素的方面。可见,形成作者的创作能力要素的原因不外乎先天所得与后天习得,也就是个人原因与社会原因,概括来说即内因与外因。作者创作素质的形成是综合构成的作用,与生俱来的写作天分确实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而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培养起来的写作能力的效力仍不容忽视[7]74。诚然良好的文学天赋对优秀文学作品的形成的作用是直接而且深刻的,但不以文学写作为职业,或者未受到特殊文学写作训练的影视文学作者,不禁会令人对其写作能力提出质疑,那么他们经手创作的影视文字作品究竟能不能具备足够的文学性而被纳入文学这一范畴是值得商榷的。
语言文字是具有张力和弹性的,好的作家,无论是否创作影视文学,都是在语言上见长,在语言上取胜的。以编剧于正为例,自2011年以来,于正平均每年要完成两部电视剧编剧,三至五部电视剧制片工作,在相对短促的时间内应对如此大的工作量,就不得不选择创作上更为简便、更为格式化的影视创作手法来进行小说文本写作,这类文本格式布局是固定化的、大同小异的,只要将其中的人物、关系、背景、情节稍作改变即可成文。以导演的角度来看,恰恰是具体直接的描述容易被影视实现,而文学性较强的表达手段会增加影视还原的难度[8]。这种作用也会反向发生在又影视到文学的转变中,受影视画面的影响,大多数影视小说虽然注重了情节的设置与可看性,注重了人物的刻画和塑造,增添了画面感和视觉冲击力,但确实忽略了文学的审美特性,特别是忽略了语言的质感和叙事的美感,大部分影视小说的语言干瘪、粗糙,充满直白的镜头化叙述,损害了文学的艺术品相。文学的表现手法诸如场景描写、环境烘托、人物心理活动刻画等交替有机地综合使用,文学才能呈现富有层次的美感,在情节表达上,只有这样才能在一条时间轴上同时叙述多个时间、空间层次上发生的因果联系,而这也容易处于非职业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之外。总的来说,语言缺乏张力与美感,叙述手段较为单一,不够丰富,是影视小说普遍存在的问题。影视文学,如果将其划归为文学,就应该保持文学特有的审美特性、人类精神活动反映以及兼具外在实用功利的价值,对影视文学的界定和评价不应因为影视的影响而放松标准。
在新媒体时代,影视与文学相互连缀的现象将更为普遍,而这用互动在影视与文学各具特色的情况下将焕发无尽的活力。只要准确把握影视与文学各自的艺术特点,在不失特色的基础上加以融合,这种影视与文学共生共荣的局面,将越来越多地被作家和出版家及影视工作者所接受和追随,共同促进文学与影视行业的繁盛,文学将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影视创作的影响、启迪,使当代文学发展呈现新面貌。
[1] 彭学明.影视小说:中国文学的新生儿[J].小说评论,2010(5):29-34.
[2] 欧阳俊杰,万燚.论当下中国文学的世俗化与商品化[J].语文学刊,2012(11):23- 61.
[3] 罗磊.网络小说影视剧改编现象之反思[J].创作与评论,2012(6):98-99.
[4] 狄其骢,王汶成,凌晨光.文艺学通论[A].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41- 42.
[5] 子安宣邦.阅读古典及再阅读[J].现代思想,2005(6):11.
[6]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A].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 张利群.中国古代作者创作素质构成论研究——刘勰的“才、气、学、习”说新解[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8] 马俐欣.大数据背景下的影视文学创作——以“于正”现象为例[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5(1):42- 45.
[责任编辑] 李志强
2016-06-23
刘 玥(1994—),女,山东烟台人,山东大学文学和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研究。
10.3969/j.issn.1673-5935.2016.03.016
J90-05
A
1673-5935(2016)03- 0049- 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