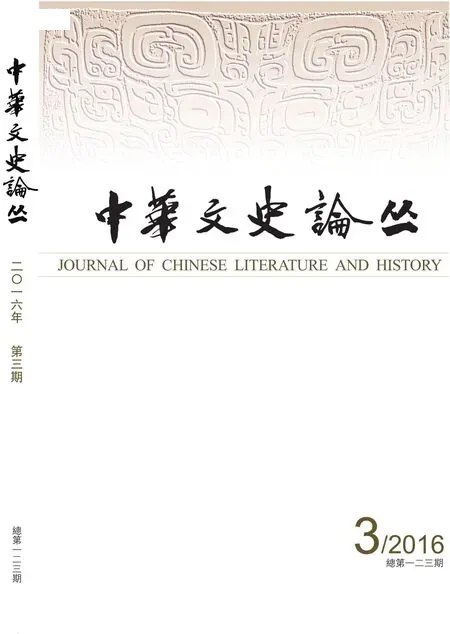唐嶺南節度使馬總爲禪宗六祖慧能豎碑事
孫昌武
唐嶺南節度使馬總爲禪宗六祖慧能豎碑事
孫昌武
元和十年,嶺南節度使馬總奏請朝廷褒揚禪宗六祖慧能,詔賜“大鑒禪師”師號、“靈照之塔”塔號,請時任柳州刺史的柳宗元撰寫《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柳文沒有對禪宗宗義加以闡發,而是一方面基於“統合儒釋”立場,强調慧能禅宗思想“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的教化作用与意义,另一方面大力表揚馬總的功績。按一般歷史記述,中晚唐時期禪宗洪州一派形勢大盛,籠蓋諸宗。而《大鑒禪師碑》則揭示了當時嶺南地方統治者支持禪宗“統合儒釋”、“以教輔政”的發展態勢。柳宗元的碑文作爲禪宗史和文化史的重要文獻,對於全面認識中晚唐禪宗乃至佛教的整體狀況具有重要價值。
關鍵詞: 天台宗義洪州門風統合儒釋以教輔政
禪宗六祖慧能圓寂後有三位文人書寫碑文,這三位都是唐代文壇一時領袖人物。這在中國佛教史上是空前絕後的事。第一篇《能禪師碑》是王維寫的,應寫於天寶初。王維是虔誠的佛教信徒,又是慧能弟子神會的朋友,他的碑文具有很高文獻價值是不言而喻的。大約七十年後,馬總擔任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於元和十年(815)奏請朝廷褒揚慧能,朝廷下詔賜給慧能“大鑒禪師”師號、“靈照之塔”塔號。馬總請柳州刺史柳宗元寫一篇新的碑文,即《柳河東集》裏的《大鑒禪師碑》。元和十三年,有曹溪和尚道琳率領門徒專程前往連州(今屬廣東),請貶在那裏的刺史劉禹錫另寫一篇碑文,俗稱“第二碑”。
按一般説法,慧能圓寂於先天二年(713),到馬總奏請朝廷加以表彰已經過了一百多年。在百年之後,朝廷、使府做出如此隆重的舉動,當然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事件,再聯繫前此二十年的貞元十二年(796),“敕皇太子集諸禪師楷定禪門宗旨,遂立神會禪師爲第七祖,內神龍寺敕置碑記見在;又御製七祖贊文,見行於世”,*宗密《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三之下,《續藏經》第9册,頁532下。這兩件事應當有內在關聯,意義就更值得重視。
既然已經有王維所寫著名碑文,爲什麼馬總又請遠在柳州的柳宗元另寫一篇?柳宗元寫了,爲什麼曹溪僧人又專程到連州找劉禹錫再寫一篇?這中間的緣由值得研究。
一 馬總其人
馬總(?—823),《舊唐書》卷一五七、《新唐書》卷一六三有傳。*馬總,《舊唐書》本傳作馬摠,《新唐書》本傳作馬揔,今依《通鑑》。他少孤貧,性剛直,不妄交遊。貞元十五年,姚南仲任鄭滑節度使、鄭州刺史,辟爲從事。南仲是地方官員,與朝廷派遣的監軍宦官薛盈珍不叶,被誣奏不法,免官。馬總受到牽連,貶泉州别駕。後薛盈珍入掌樞密,福建觀察使、福州刺史柳冕迎合他的旨意,打算殺掉馬總,經從事穆贊審理,幫助馬總脱罪免死。後量移恩王傅。元和初,遷虔州刺史;五年六月,升任安南都護、本管經略使;八年七月,爲桂管觀察使;十二月,爲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後入朝,十二年七月,以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淮西行營諸軍宣慰副使,參與平定淮西吴元濟之役,輔佐統帥裴度有功,先是擔任蔡州留後,晉升蔡州刺史、彰義軍節度使;次年五月轉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使。十四年,遷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入爲戶部尚書。長慶三年(823)八月卒。*《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462;卷一五七《馬總傳》,頁4151— 4152。《新唐書》卷一六三《馬總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5033—5034。
馬總性篤學,雖吏事倥偬,仍勤於著述。重要作品今存《意林》五卷,成書於貞元初,是唐代惟一一部諸子著作選集。這部書是根據庾仲容所編《子鈔》增損而成的。庾仲容,南北朝梁朝人,取周、秦以後諸子雜記凡一百零七家,摘錄要語,輯爲三十卷,名曰《子鈔》。宋高似孫《子略》稱仲容《子鈔》,每家或取數句,或一二百句。馬總認爲《子鈔》摘錄繁簡失當,遵循《子鈔》原目,加以增删,成書較《子鈔》選錄精嚴。《意林》有貞元二年(786)撫州刺史戴叔倫所作的序,稱贊説“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闕,下以佐屬文之緒。有疏通廣博、潔淨符信之要,無僻放拘刻、激蔽邪蕩之患”。*《文獻通考》卷二一四《經籍四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750。《四庫全書總目》評價説:“馬總《意林》,一遵庾目,多者十餘句,少者一二言,比《子鈔》更爲取之嚴,錄之精。今觀所采諸子,今多不傳者,惟賴此僅存其概。其傳於今者,如老、莊、管、列諸家,亦多與今本不同。”*《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三《子部·雜家類》,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1060。值得注意的是,漢、魏以降歷代朝廷皆尊儒術,子書除《老》、《莊》外,幾近堙沒。到中唐時期,先秦子學得到重視,是學術史上的一大變化,馬總編撰《意林》是先行者,表明他學問淵博,確有卓見。後來清乾隆有《御題意林三絶句》贊揚説:“集錄裁成庾潁川,《意林》三軸用兹傳。漫嫌撮要失備載,嘗鼎一臠知味全。”“都護安南政不頗,用儒術致政平和。奇書五卷銅柱二,無忝祖爲馬伏波。”“六經萬古示綱常,諸子何妨取所長。節度豈徒事占畢,要知制事有良方。”*《意林》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872册,頁197下。詩裏連帶評價了馬總治理嶺南的政績。
馬總受命出掌南海大鎮廣府,和當時國家總體形勢有關。南北朝以來,江南包括嶺南逐漸得到開發。經過“安史之亂”,函陝凋敝,東都尤甚。代宗朝負責管理財政的劉晏曾移書宰相元載,指出“東都凋破,百戶無一存”,“起宜陽、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見戶纔千餘”。*《新唐書》卷一四九《劉晏傳》,頁4794。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除戰亂喪亡,還由於中原居民大量流移,主要是往江南,“自至德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二》,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552。“賢士大夫以三江五湖爲家”。*穆員《鮑防碑》,《全唐文》卷七八三,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3年,頁8190上。這些地方社會安定,經濟開發已有相當基礎,遂又成爲朝廷財賦仰賴之地。朝廷多派儒臣能吏擔任鎮帥、州守,多能注重發展農耕,興修水利,招徠商賈,安撫流亡。據《通鑑》,元和二年(809),李吉甫編撰《元和國計簿》,統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賦税倚辦其中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資治通鑑》卷二三七,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7647。這大約是天下方鎮、州府總數的六分之一;納税戶一百四十四萬,大約集中全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這是按唐後期開成四年(839)戶口數最高年份近四百九十九萬六千戶計算的。嶺南處在這個經濟繁榮地區的南方邊緣,而廣州又是面向南海的大港,兼得通商、漁鹽之利,必然受到朝廷重視。*中唐社會危機的重要根源和表現在藩鎮割據。各地藩鎮大體可分爲四種類型: 一是中原地區拱衛朝廷的;二是西北邊疆抵禦回紇、吐蕃的;三是以“河北三鎮”爲代表的實行割據、謀求獨立的;而作爲朝廷財賦來源的江南方鎮算作第四類,時有“天下方鎮,東南最寧”之説。第四類方鎮對於保障朝廷安定起着關鍵作用。
就廣州(南海郡)具體情況説,“安史之亂”以後,朝廷多遴選政能文才傑出的重臣鎮守。歷史上知名的就有徐浩(大曆二年至三年)、李勉(大曆三年至七年)、路嗣恭(大曆八年至十二年)、杜佑(興元元年至貞元三年)、楊於陵(元和三年至五年)、鄭權(長慶三年至四年)、崔龜從(會昌四年至五年)、蕭仿(大中十三年至咸通元年)、韋宙(咸通二年至九年)、鄭愚(咸通十二年至乾符元年)等。至於後來創建南漢的劉隱,也在天復元年(901)至天祐四年(907)擔任過嶺南節度使。當時唐朝已分崩離析,他也就自專獨立了。馬總即是朝廷選拔的治理嶺南的一位幹材。*附帶説明,廣義的嶺南包括今廣西即桂管觀察使所轄地區,朝廷任命爲桂管觀察使、桂州刺史的同樣多是能臣,如裴行立(元和十二年至十五年)、李翱(大和五年至七年)、鄭亞(大中元年至二年)等。《新唐書》本傳上説,“元和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廉清不撓,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新唐書》卷一六三《馬總傳》,頁5033。
馬總治理嶺南的具體業績,歷史上記載的,有在漢建武十九年(43)馬援於象林縣南界(今越南中部)所立作爲漢領地標誌的銅柱之處,復以銅一千五百斤鑄二柱,刻書以頌唐德。這在當時藩鎮割據日趨嚴重形勢下,體現他維護國家統一的立場。至於一般政績,如上引《新唐書》等文獻記載多加肯定。後來他隨同裴度出征淮西蔡州,時韓愈擔任行軍司馬,寫詩贈給他,有句頌揚説“紅旗照海壓南荒”,*《贈刑部馬侍郎》,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一〇,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頁456。也是指他治理嶺南的功績。後來他以軍功被命爲天平軍節度使,元稹草擬制書説:“踐歷他官,所至皆理。處馭南海,仁聲甚遥。”*《加馬總檢校刑部尚書仍前天平軍節度使制》,《元稹集》卷四三,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474。長慶三年(823),韓愈任京兆尹,依例上疏舉人自代,推舉的就是馬總,也説“略更方鎮,皆有功能”。*《舉馬總自代狀》,《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633。他死後,韓愈祭文又説:“於泉於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番禺,去其螟蠧,蠻越大蘇。”*《祭馬僕射文》,《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五,頁329。可見他治理嶺南確是成效顯著、名聲遠被的。
馬總蒞任後請求朝廷加封慧能謚號、推尊佛教,乃是治理嶺南的具體舉措。
二 馬總和柳宗元
柳宗元因爲“永貞革新”被貶謫,先是到永州(今屬湖南),擔任一個閑職司馬,還是“員外”編制,實同繫囚。元和十年(815)初一度被徵召入京,又被加貶爲更邊遠的柳州任刺史。柳州屬桂管觀察使統轄,屬嶺南道,這樣,柳宗元就成爲馬總的部屬。實際兩人早有交誼,而且是相當深厚的道義之交。
柳宗元父親的族兄弟柳并,字柏存,官至御史,早年與馬總一同受業蕭穎士門下。這樣,馬總與柳氏乃是世交。馬總撰《意林》,柳并在戴叔倫之後另作一序,稱贊説“聖賢則糟粕靡遺,流略則精華盡在,可謂妙矣……予懿馬氏之作,文約趣深,誠可謂懷袖百家,掌握千卷,之子用心也,遠乎哉!旌其可美,述於篇首,俾傳好事”。*柳并《意林序》,《全唐文》卷三七二,頁3780下。該文作於貞元三年(787)。後來柳宗元熱衷於子學研究,考辨《列子》、《文子》、《鬼谷子》、《晏子春秋》和《鶡冠子》等子書,在諸子研究中取得重大學術成就,開拓子學研究的新局面,顯然受到馬總的影響。馬總當然了解柳宗元在這方面的成就,兩人學術上乃是同道。
馬總和柳宗元間接的關係,前面説到貞元十五年馬總作爲姚南仲部屬被貶泉州,險遭被殺之禍,是穆贊解救了他。穆贊和柳宗元的父親柳鎮交好,爲官以剛正著稱。柳宗元在《先君石表陰先友記》裏稱贊他“强毅仁孝”。*《柳河東集》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87。他兄弟四人,與柳宗元一家關係殊非泛泛。穆贊曾牽涉到的一個案件,《先友記》裏曾提到。事情發生在貞元五年,陝虢觀察使盧岳病死,盧妾裴氏有子,盧妻分配遺產不給裴氏子,裴氏上告朝廷,穆贊以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身份審理此案。他的上司御史中丞盧佋偏袒盧氏,脅迫穆贊給裴氏定罪,穆贊不允,盧佋就誣陷他接受賄賂,把他逮捕下獄。盧佋是姦相竇參的黨羽,權重勢大。穆贊的弟弟穆賞赴闕上訴,朝廷依例命御史臺、刑部、大理寺三司推按。其時柳宗元的父親柳鎮是殿中侍御史,代表御史臺參與審判,平反了這起寃案。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柳鎮和穆贊的爲人品格、政治態度是一致的。上一節説到穆贊和馬總的關係,當初鄭滑節度使姚南仲及其部屬馬總被宦官薛盈珍誣陷,薛盈珍派遣一個叫程務盈的小吏帶着誣奏姚南仲文書晉京,恰值姚部下一位牙將曹文洽奏事去長安,追趕他到長安城南長樂驛,把他殺了,然後自殺。就這件事,還有另一件同爲義士的韋道安事,柳宗元作《曹文洽韋道安傳》,已佚,文集裏存目;又作《韋道安詩》,今存。*《柳河東集》卷一七,頁313;《全唐詩》卷三五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6年,頁873中。由此可見柳宗元對馬總及其早年被陷害的不幸遭遇早有了解並極表同情。
這樣,柳宗元的父輩柳鎮、柳并,穆氏兄弟,馬總和柳宗元本人,這些人長期密切交往,相互支持。這是些才華、人品、學問都相當傑出的士大夫,又都不畏權勢,剛正不阿,富於革新精神。他們相互激厲,引爲同道。當柳宗元貶到嶺南道的柳州擔任刺史,成了馬總的部屬,對於雙方必然都是值得欣慰的事。
三 寫慧能碑文,爲什麼請柳宗元?
這樣,馬總與柳宗元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適逢朝廷敕謚慧能師號這件大事,馬總以鎮帥身份鄭重請托柳宗元書寫一篇碑文,也是因爲他對柳宗元器重並對柳宗元好佛有所了解,贊同柳宗元的佛教觀點。
如前所述,慧能圓寂,本來有著名文人、號稱“詩佛”的王維撰寫碑文,而且這篇文字還是受慧能大弟子神會請托作的。按常識推斷,其內容應當是得到神會首肯,甚或資料是神會親自提供的。馬總爲什麼還要請柳宗元另寫一篇碑文?當然是加謚立碑所需要,也是希望柳宗元寫出一篇更具現實意義的文章。
柳宗元自稱“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柳河東集》卷二五,頁423。説這句話在他四十歲前後。他又説“余知釋氏之道且久”。*《永州龍興寺西軒記》,《柳河東集》卷二八,頁464。他本是一位勤於理論探討的思想家,從思想理論角度對佛法有相當深入的了解。他活動的年代正是禪宗南宗洪州宗一派大盛的時候,而他研習有得的主要是天台宗。*關於柳宗元接受天台宗宗義,參閱拙著《柳宗元評傳》第七章《尊崇佛教“統合儒釋”》,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320—368;《柳宗元與佛教》,《文學遺產》2015年第3期,頁73—81。洪州宗進一步發揮慧能的“頓悟”、“見性”思想,提出“平常心是道”、“即心即佛”,因而主張“道不要修”、“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賈晉華《馬祖語錄校注》,《古典禪研究——中唐至五代禪宗發展新探》附錄一,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32—338。這樣弭平了“清淨心”與“平常心”的界線,實則是把平常的“人性”等同於“佛性”,否定了修持的意義。洪州宗思想的價值與意義這裏不論,其在實踐中慢教輕戒,走向極端,導致呵佛駡祖、毁經滅教,從而也就破壞了宗教信仰的基礎;在社會層面,則動搖了中國佛教傳統上以教輔政、教化民衆的作用。柳宗元又是具有鮮明革新意識的政治家,立身行事主張“有益於世”。*《覃季子墓銘》,《柳河東集》卷一一,頁180。他心儀天台止觀,天台“觀心”之道要求降服結習,斷除惑念,愛養心識,啓發“智慧”,與洪州宗“道不要修”的觀念相對立,也是從有益於世用的角度考慮的。
柳宗元對洪州宗思想有相當深入的了解。貞元元年(784)他十二歲的時候,父親柳鎮到洪州擔任洪州觀察使李兼的幕僚,正值洪州宗創始人馬祖道一在那裏開法。其時李兼部屬多有馬祖道一的支持者,包括後來柳宗元的岳父楊憑、文壇上的前輩權德輿等。馬祖弟子分散四方,聲勢大振,成爲南宗禪的主流。柳宗元在永州也接觸過洪州學人。
而柳宗元和韓愈革正文體,倡導“古文”,重要先行者之一梁肅是柳宗元父親柳鎮的朋友,柳宗元作《先友記》,稱贊他“最能爲文”。*《柳河東集》卷一二,頁188。梁肅信仰天台宗,柳宗元熱衷天台當受他的影響。梁肅明確反對洪州禪慢教輕戒、無修無證的門風。他説:
今之人正信者鮮。啓禪關者,或以無佛無法、何罪何善之化以之。中人以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之類,以爲斯言至矣,且不逆耳。私欲不廢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焦爛,而莫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衆魔外道,爲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天台)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天下爲不侔矣。*《天台法門議》,《全唐文》卷五一七,頁5256上。
柳宗元對洪州流宕忘反的門風同樣加以批評,在《送琛上人南遊序》裏説:
今之言禪者,有流蕩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脱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送琛上人南遊序》,《柳河東集》卷二五,頁428。
柳宗元以理性態度批評洪州禪狂放不拘的門風、流宕忘反的趨勢,强調修行中體、用一致,顯然又更重視“用”的方面。
當馬總出任江西、嶺南要職的時候,正值韓愈等人大力興儒反佛。同時柳宗元和韓愈就佛教信仰及其思想價值、社會作用進行激烈辯論,情形廣泛傳播士林。柳宗元對於佛教的看法,包括他對禪宗的批評,馬總當是有所了解並贊同的。加上兩個人的交誼、柳宗元的文名,當朝廷頒下慧能賜號,需要建碑紀德的時候,對於馬總來説,柳宗元就成爲不二的人選。
四 柳碑寫了什麼?
柳宗元所寫碑文全稱是《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欲了解這篇作品的內容,先來看看他的另外兩篇作品。
《柳州復大雲寺記》是集中體現柳宗元佛教思想的文字,開頭一段説: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惟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河東集》卷二八,頁465。
這是説,柳州當地人蒙昧無知,相信巫術,鬧得戶口減少,田園凋蔽,而佛教神道設教,且所説法神秘又强大,容易被人接受,乃是教化的一術。這説的是佛教的社會作用。

王維所作《能禪師碑》所述慧能思想主旨是:
……於是大興法雨,普灑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成,於初發心,以爲教首。至於定無所入,慧無所依,大身過於十方,本覺超於三世。根、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即凡成聖。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王右丞集箋注》卷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447。這裏所説慧能所教的“忍”,不是一般的容忍、忍耐,是“無生”、“無我”,是對“般若空”的領悟。以下所作解釋,就是《壇經》裏説的“我此法門從上以來,頓漸皆立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的意思。*郭鵬《壇經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31—32。一經比較就清楚,王維碑是傳達慧能南宗禪本來旨意的。而柳宗元碑所述則對慧能思想作了新的解説,或者用現在流行的語彙,作了新的“詮釋”。因爲表彰慧能經馬總奏請朝廷,所以碑文大幅引用馬總的話,實際是表達柳宗元自己的看法:
自有生物,則好鬥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誖乖淫流,莫克返於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黄、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説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柳河東集》卷六,頁91。這裏第一句是柳宗元社會發展觀的概括,即主張人類社會發展是由內部矛盾鬥爭形成的客觀的“勢”推動的,孔子的思想(儒家)也是基於這樣的形勢產生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思想史的看法,不像韓愈那樣認爲佛法破壞了儒道,而主張“楊、墨、黄、老”百家雜説使儒術“分裂”,而佛教“合所謂生而靜者”,起到挽救儒道危機、使之恢復本源的作用。韓愈主張儒學復古,大力辟佛,柳宗元和他爭論,一再提出“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送僧浩初序》,《柳河東集》卷二五,頁425。對於佛説可以“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衺,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柳河東集》卷二五,頁419。認爲“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柳河東集》卷二五,頁422。這就是所謂“統合儒釋”思想。
正是基於這樣的主張,他對慧能禪法的闡釋是:
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柳河東集》卷六,頁92。這裏前一句講的是佛法的“無爲”、“空”;後一句講的是儒家的性善,最後歸結到《易經》的“人生而靜”。佛法講“性淨”,是無善無惡的超然境界;儒家講“性靜”,是先天的道德屬性。柳宗元就這樣把慧能的禪“統合”到儒家倫理上來。所以他在碑文裏又頌揚馬總的政績:“受旂纛節戟,來蒞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噩,允克光於有仁。昭列大鍳,莫如公宜。”後面銘辭又頌揚慧能説:“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厖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於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苖。中一外融,有粹孔昭。”*《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柳河東集》卷六,頁93。這就把馬總的治績和慧能的禪聯繫起來了。
就這樣,柳宗元站在“統合儒釋”的立場來重新解釋慧能的思想,結合馬總治理南海的業績,强調它的教化作用與意義。從另外的角度看,也是有意扭轉洪州門風的偏頗。這是當時洪州禪大盛局面下對於禪、對於佛教發展的另一種主張。
馬總請求朝廷給慧能賜號表彰,是治理地方的行政舉措;柳宗元寫慧能碑文,則是强調佛教的教化功能,歸結到表揚馬總。
四 劉禹錫的“第二碑”
劉禹錫是柳宗元的好友。在柳宗元去世前,兩個人命運大體相同: 一起參與“永貞革新”;同是被貶謫的“八司馬”一員,柳貶永州,劉貶朗州;後來同被召入京,又同被加貶遠州,柳到柳州,劉到連州。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朝廷賜號慧能的詔書下達到廣州,立碑完成在第二年。三年後,曹溪有和尚道琳率門徒來到連州,請劉禹錫再作一通慧能碑文。其故安在?不清楚。推測可能是因爲柳宗元的碑對於慧能本人用筆墨不多,主要是表揚了馬總,令慧能的門人感覺意猶未盡。
劉禹錫和柳宗元不只是好友,思想觀點也大體一致。比如在當時、對後世影響重大的關於“天”、“人”關係的辯論,兩個人都反對有意志、能主宰的“天命”之“天”,主張人如果掌握自然規律則可以勝“天”。劉禹錫更提出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頗具辯證觀念的看法。*《天論中》,瞿蜕園《劉禹錫集箋證》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143。同樣,對於佛教兩人也有同好。劉禹錫在連州,和僧人密切交往。法名見於劉氏作品的僧人,就有文約、中巽、道准、圓皎、貞燦、圓靜、文外、惠榮、名肅、存政、道琳、文約、浩初、儇師等。其中有些人來往於劉、柳兩人之間,如方及、浩初,實際起到二人交往紐帶的作用。柳宗元寫慧能碑的事,劉禹錫當然知道,也會讀過這篇作品。
所以,劉禹錫關於朝廷褒揚慧能一事的意義,看法和柳宗元全同,他的第二碑説: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大鑒,實廣州牧馬總以疏聞,由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夷孔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爲前碑……*《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劉禹錫集箋證》卷四,頁108。這裏的“不隔異教”,就是肯定“統合儒釋”;“同歸善善”,就是柳碑所謂“始以性善,終以性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銘文中的這一節:
……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差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爲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劉禹錫集箋證》卷四,頁106。
這一段意在批評南宗禪分化爲不同派系的紛爭,也包含不滿洪州禪的意思,立意則在恢復慧能禪的本來旨意。當然,這種旨意也是基於他個人的理解。
五 馬總立碑一事與唐代嶺南佛教
馬總奏請朝廷表彰慧能,豎碑表德,是中唐嶺南佛教的具體事件,也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
前面説過,“安史之亂”以後,中原居民大量遷徙江南,包括嶺南,有力地推動了這一地域的開發。官僚士大夫階層來到這些地區,對於文化發展發揮了積極推動作用。這些人大體可分爲四類: 一類是朝廷命官,如馬總,是鎮守一方的大員,其觀念、行爲對於所統治地區造成直接影響,如馬總尊崇、褒揚慧能;一類是貶謫的朝官,如柳、劉,還有人們熟知的貶潮州的韓愈,其中有些是罪犯待遇,同樣能發揮不同的作用;第三類是州、鎮辟署的幕僚,史稱“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爲重”,*洪邁《容齋續筆》卷一《唐藩鎮幕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223。這種情形中晚唐更爲普遍,“諸使辟吏,各自精求,務於得人,將重府望”。*《舊唐書》卷一三八《趙憬傳》,頁3778。戴偉華《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一書根據文獻著錄總結唐代文士入幕情形,列表加以統計: 安史亂前,入幕者計一百七十四人次,其後肅宗至德宗年間入幕者驟增,計一千零一十二人次,而入幕者多數在江南,其中嶺南東道九十人次,西道二十四人次;*《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84—85。第四類是避難舉家南遷者,例如晚唐的清海節度使(即嶺南節度使)劉隱和劉巖,割據廣州,後來建南漢,“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辟地,多遊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裔之徒,隱皆招禮之……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漢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810。這四類人不論來到嶺南主觀動機如何,對推動嶺南經濟、文化發展大都發揮了相當巨大、顯著的作用。
佛教本是傳播文化的載體,對於嶺南這樣的經濟後進地區,佛教更能夠發揮獨特的作用。“安史之亂”以後,隨着經濟重心南移,當地佛教也得到長足發展。代宗時期廢黜租庸調制,實行“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的兩税法,*《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頁2093。土地開墾、兼并合法化,當時興盛的禪宗農禪制度,得以迅速地擴張勢力。據《新唐書》,開元年間造僧尼簿籍,統計人數是十二萬六千一百人。*《新唐書》卷四八《百官志》,頁1252。而元和年間李吉甫在奏章裏説:
自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軍士可計者,已八十餘萬。其餘去爲商販,度爲僧道,雜入色役,不歸農桑者,又十有五六。是天下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唐會要》卷六九《州府及縣加減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452。
這裏沒有具體説到僧尼數字,但可見數量迅速增加的形勢。以柳宗元所在柳州爲例,天寶年間領縣五,戶數二千二百三十二,口數一萬一千五百五十;元和年間領縣不變,戶數一千二百八十七,口數缺。*梁方仲編著《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93—108。當時的統計當然會有隱漏,但當地人口稀少是可以肯定的。而據柳宗元《柳州復大雲寺記》,柳州本來有四座佛寺,三座在柳江北,大雲寺在柳江南,江北六百戶人家,江南三百戶。就是説,九百戶人就有四座寺廟。柳宗元説永州原有大雲寺,已經失火燒毁近百年了,故“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柳州復大雲寺記》,《柳河東集》卷二八,頁465。從這個例子可以知道,當時嶺南佛教傳播的廣泛程度及其在當地發展的地位。
柳宗元又認爲: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柳河東集》卷七,頁105—106。
根據他的“統合儒釋”觀念,儒育人以仁義,佛教人以定慧,二者對於教化都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嶺南這種荒僻地區,發揮佛教“以教輔政”的功能就更具現實意義;又當地少數民族雜居,如桂管各州,黄洞蠻叛復不常,成爲地方動亂的根源,佛教信仰又能夠起到調節民族關係的作用。這也是柳宗元恢復大雲寺的初衷。
講唐代佛教史,特别是中晚唐一段的記述,大半篇幅主要講禪宗。這也確實是禪宗極盛,在社會上、在思想界發揮重大作用的時期。但禪宗是所謂“適合中國士大夫口味的佛教”。*范文瀾《中國佛教通史簡編(修訂本)》第3編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頁601。它創造出極其豐富有價值的思想、文化成果,不過其重大影響主要在官僚士大夫階層。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太虛法師講《改善人心的大乘漸教》,仍然實事求是地説:“在以前中國之知識界,皆讀孔、孟之書,而無知識的愚夫愚婦等,則崇信神道;佛教於此,亦分兩種施設: 在知識界方面,施與簡捷超妙的禪宗;其不讀書之多數人,則施與神道設教之教化。”*《太虛大師全書》第17册,善導寺佛經流通處出版,1980年,頁7—8。對於唐代嶺南地區民衆來説,“神道設教”的方便教化顯然更爲適宜和必要。《大鑒禪師碑》正反映了這樣的觀念和態度。
總起來説,這篇《大鑒禪師碑》反映了嶺南禪宗和佛教發展的實態及其整體趨勢: 對於中晚唐各地方鎮的統治者來説,借助佛教來教化民衆、維護統治秩序更爲重要,因此禪宗也好,佛教整體也好,要回歸到與政治密切結合、“以教輔政”的道路,在思想層面則要發揚“統合儒釋”的傳統,致力於勸人向善的道德建設。這也預示當時佛教包括禪宗的發展必然走上“禪教一致”的道路。
這樣,了解馬總推尊祖師慧能的本意和柳宗元、劉禹錫兩篇慧能碑寫作的立意所在,不僅可以更全面地認識中晚唐佛教的發展態勢,對於全面認識中國佛教發展的歷史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作者係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