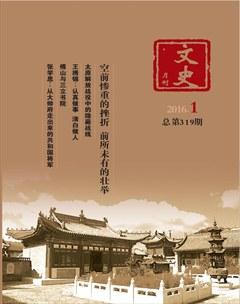远古遗踪(连载)
王益人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来头,而探寻人类文明的起源,就绕不开山西这一方厚土。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人类文明的摇篮,山西蕴育了光耀千秋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2015年8月16日会见世界华文媒体高层访问团时,首次提出山西古文化的“三个一”(即一座都城、一堆圣火、一缕曙光)。“一座都城”临汾襄汾陶寺遗址,使尧文化走出传说成为信史,树起了5000年中华文明的伟大丰碑;“一堆圣火”运城芮城西侯度文化遗址的火烧骨,把我国范围内发现的人类用火历史前推了100万年;“一缕曙光” 运城垣曲的“世纪曙猿”化石,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多万年。
本文详细讲述了西侯度遗址的发现历程,并带我们领略目前我国境内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风采,更让我们了解人类文明的圣火,是怎样从黄河岸边开始燃起……
西侯度,位于山西省西南角芮城县风陵渡镇以北约7公里,地处黄河左岸丘陵地带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首次发现的早于100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西侯度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1962年,我国著名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王建率领考古队对此进行了发掘。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侯度遗址发现于早更新世(第四纪更新世的第一个时期)初期之泥河湾期(华北山区地文期中的一个堆积期)地层中,令当时大多数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诧异和难以接受,其命运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自发现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同时由于遗址系河流相(由陆上河流或其它径流作用沉积的一套沉积物或沉积岩形成的沉积相)埋藏环境,出土石制品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磨蚀,学术界由此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和争议。
为了解开这一困扰学术界几十年的谜团,作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我,于2005年4月间,率领一支科研队伍,再次对这处山西省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50余天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很大突破。根据发掘所獲资料综合分析,西侯度石制品虽然受到河流搬运埋藏的影响,但人类行为及其特征毋庸置疑。
人类最早的脚踏地
人类起源是一个既神秘又十分有趣的问题。100多年前,随着西方学术思潮的冲击,“女娲”“三皇五帝”等传统的中华始祖形象,被“由猿到人”的进化论所取代。1929年,史前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教授在周口店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在震惊世界的同时,也使得中国人口口相授了几千年的“历史故事”变成了神话传说。考古学成了揭开人们心中“谜团”最直接的手段,博物馆成了大众学习和接受新知识的最好去处。今天,“人之由来”早已成为最基本的常识,但这个常识的取得却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走得十分艰难曲折。
西侯度遗址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首次发现的属于早更新世初期的人类文化遗存。在其被发现之前,大家熟知的人类最早祖先仍是“北京猿人”(中国猿人)。因此,在当时要想挑战这个“纪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半个世纪前,北京二道桥一个普通的四合院——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里,王建仔细观察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现的石器和人类遗骨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北京猿人”不是最早的人类,在他之前一定有更加原始的人类存在。这一说法得到了我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的肯定。1957年,贾兰坡、王建在《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以下简称《脚踏地》)一文中提出:“中国猿人不是最早的,在他之前的泥河湾期的地层中应有人类及其文化存在。”文章对中国猿人的用火遗迹、石器打制技术、猿人体质进化特征等几方面作了综合分析后认为:中国猿人已经能够控制、管理和使用火,能够用三种方法打制石片,打制的石器已有了相当的分化和分工。“北京猿人”的体质特征虽然尚保留有猿的性质,但已经进化成了能够直立并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人。因此,在与“北京猿人”时代相接的泥河湾期的地层中,还应有更为原始的人类及其文化存在。这篇文章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为了证明他们的理论推断,贾兰坡、王建等人努力在泥河湾期的地层中寻找人类的遗骸和遗物。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山西省西南部,投向了孕育华夏文明的黄河中游地区,这里有着与泥河湾同属早更新世的“三门期”(华北山区地文期中的一个堆积期,时代为更新世早期,与泥河湾期相当)地层。
1957年,考古工作者在三门峡水库调查中,在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镇西北约7公里的匼河村一带发现了几处旧石器地点。1959、1960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又两次对这一地区进行调查和发掘,发现旧石器地点16处。在此期间,考古学家们来到东距匼河3.5公里的西侯度进行地质考察,在村后的“人疙瘩岭”下部地层中发现一件距今100多万年前的早更新世轴鹿角化石和三块具有人工破碎痕迹的石块,这一发现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深切关注。因为这不但证明了此前他们提出的泥河湾期的地层中有更早人类的理论,也使学术界必须直接面对周口店“北京猿人”是不是最早的人类这一疑问。
1959年12月20日,《文汇报》上的一篇《山西风陵渡一带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报道了匼河发现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1961年1月10日《光明日报》的《芮城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再次报道了这一发现。1961年8月,贾兰坡、王择义、王建公布了他们的初步研究成果:在《山西芮城匼河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中,从地层、动物化石及石器等方面综合研究,认为匼河遗址的地质时代属于更新世中期最初阶段,即与周口店“北京猿人”化石产地下部堆积(约第10层以下)或周口店第13地点的时代相当。并认为当时的人使用的工具比“北京猿人”的还要原始。同时还提到了在西侯度的早更新世初期地层中,发现了“几块极有可能是人工打击的石块”。这些发现对“北京猿人”的人类始祖地位提出极大的挑战,在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界引起了一场长达一年多,关于“北京猿人”是不是“最早人类”问题的大讨论。
在考古学上,发现才是硬道理。理论探索是一方面,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来才能算数。西侯度是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还要看他的发掘和研究。
1961至1962年,西侯度遗址的发掘工作在此起彼伏的争论声中进行了两个年度的发掘,获得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烧骨和带有切痕的鹿角。尽管发现的石制品上的人工痕迹由于河流搬运埋藏而变得不很清晰,烧骨和带有切割的鹿角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发现它们的意义仍十分重大。首先,它是中国大陆上的第一个被发现的属于早更新世初期的古文化遗址,将中国人类演化的历史提前了100多万年。其次,在考古学上,西侯度遗址的发现解除了长期以来“北京猿人是人类最早祖先”的陈旧观念。之后发现的元谋人、蓝田人以及泥河湾的东谷坨、小长梁等人类遗址或地点,不断地充实着中国早期人类演化的足迹,使得西侯度不再孤单,并一次次地为《脚踏地》的理论做出注解。事实证明,西侯度遗址的发现不但证明了《脚踏地》中的理论推断,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双重突破,也使得中国古人类和旧石器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80万年的人类文化
西侯度遗址所在的西侯度村,地处中条山西南端向黄河倾斜的丘陵地带,高出黄河河面约170余米。由于新构造运动的抬升和水土流失的共同作用,附近包括新第三纪和第四纪在内的厚度达140米的土状堆积,被切割冲刷成数条东西向的涧沟和梁峁。因此这里的第四纪地层发育齐全,出露良好,是观察研究第四纪地质的理想地点。 在西侯度村后的土山“人疙瘩”北坡一个叫 “后山根”的地方,出露有一套厚度约18米的早更新世砂砾层。1960年发现的三块具有破碎痕迹的砾石就是在这里发现的。从村西的一条蜿蜒小路可以到达一个叫“后地口”的地方。1961、1962年由王建等人组成的发掘队在这里进行了两次发掘,以后山根为主,在后地口也作了试掘。这两个地方的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器的性质是相同的,因此,通称为西侯度文化遗址。
“人疙瘩”海拔约563米,其顶部为一套7—10米厚的晚更新世灰黄色粉砂土(即马兰黄土);之下为厚约50米的含有13条古土壤层的中更新世“红色土”;再下为厚度约18米的早更新世砂砾层。西侯度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集中分布在其中下部平均1米厚的灰白色、锈黄色交错砂层中。根据古地磁测定为距今180万年;下伏的60 余米的上新世夹有砾岩和砂砾石层棕红色钙砂质粘土。
西侯度遗址中发现的石制品类型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等。石核可分为巨型石核、漏斗状石核、两极石核等。其中最大的一件石片石核重8.3公斤,最小的一件漏斗状石核仅33克。石片分为锤击石片、碰砧石片和砸击石片三类。由这些石核和石片分析,当时的人类已经掌握了用锤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生产石片。砍斫器可分为单面砍斫器、双面砍斫器和有使用痕迹的砍斫器;也可按单边和多边来分,其中一件多边砍斫器用大石片制成,周边4个刃口正反两个方向交替打制。刮削器可分为直刃、圆刃和凹刃三类。其中一件用紫色石英岩石片修制的边刃刮削器十分典型。三棱大尖状器只有一件,器尖对称,呈三棱状,它是以一块三棱状砾石经过简单打制加工而成的。这件标本虽系脱层采集品,但是由于附近未发现其它文化层,所以可断定它与发掘所得的石制品同出于一层。三棱大尖状器是我国旧石器时代的一种传统性工具,在黄河中下游晋、陕、豫三省交接的三角地带的匼河、蓝田公王岭和三门峡以及汾河流域、丁村等遗址中都有发现。西侯度遗址三棱大尖状器的发现,可以将这一传统上溯到100多万年前。
西侯度遗址中与打制石器同层出土的动物化石除鲤、鳖和驼鸟外,还有刺猬、山西轴鹿、晋南麋鹿、古中国野牛、山西披毛犀等22种哺乳动物。其中绝灭属占47%,绝灭种100%,被称之为西侯度动物群,是华北地区最早的早更新世动物群之一。这一动物群的成员绝大部分属于草原动物,同时也有适于丛林和森林生活的动物。从这些动物的特征和生活习性来看,当时西侯度附近应为疏林草原环境,反映出这里的气候比现在还要干燥凉爽一些。
西侯度遗址文化层中还发现了一些颜色呈黑、灰、灰绿色的化石标本。他们大部分为哺乳动物的肋骨、鹿角和马牙。经研究者观察和化验,确认这些不同颜色的骨角牙为烧骨。这些烧骨有可能是人类用火的证据,但也不能排除是森林野火烧死的动物遗骸的可能。另外,我们还发现了带有人工切痕的鹿角。
质疑与讨论
1978年由贾兰坡、王建合著的《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以下简称《西侯度》),对西侯度遗址发现的石器、动物化石和烧骨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确立了西侯度文化。
然而,西侯度文化的时代毕竟距离我们太遥远了,而且由于发掘所获材料的数量有限,加之石制品上的打击痕迹也因水流搬运埋藏而变得不太清楚。因此,西侯度发现以后,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石制品的人工性质和以“烧骨”为中心的用火遗存的讨论。
一是石器之谜。100多万年前到底有没有人类存在,他们打制的石器到底是什么样子?在当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西侯度遗址发现以后,我国学术界进行了十分激烈的争论。以贾兰坡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西侯度遗址发现的石器,无法用自然动力造成来解释,其人工性质可以肯定;但另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西侯度地点出土的、被辨方鉴定为石器的标本上有严重的水流冲磨和碰撞的痕迹,颇似欧洲的‘曙石器’,难以排除是由河流碰撞造成的可能性,应进一步做工作,不宜断然肯定。”
即便是5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学者认为:“西侯度的石制品有明显的水流碰撞和磨蚀痕迹……西侯度出土‘石制品’的人工性质存疑……有必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的评估。”也有学者认为:“西侯度遗址的发现意义重大,西侯度石制品磨蚀严重,有一部分仍然可能受到怀疑。石制品遭受水流的碰撞和磨蝕,只要还显示人工痕迹,石制品的性质就没有改变”。
1982年贾兰坡与王建再度合作,他们根据西侯度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的性质、特点,进一步提出《上新世地层中应有最早的人类遗骸及文化遗存》。文中指出,西侯度遗址的石制品虽然出现在180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其打制技术比较原始古拙,但从石器生产的全过程来看,仍有其进步的一面,石器的主人能选择具有一定硬度和韧性的石英岩、脉石英和基性喷发岩作为原料,并用多种打击方法打制石片、修理石器。石器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已有了一定的类型和功能区分。说明这些石制品是经历了漫长历史洗礼的产物,预示着中国土地上最早的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还应当到比它更早的上新世地层中去寻找。
二是用火之谜。西侯度遗址文化层中发现的那些颜色呈黑、灰、灰绿色的化石标本,大部分为哺乳动物的肋骨、鹿角和马牙。经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化验确认这些不同颜色的骨、角、牙为烧骨。研究者认为这些烧骨有可能是人类用火的直据,也不能排除是森林野火烧死的动物遗骸的可能。贾兰坡曾经这样描述:“这种不同颜色的骨并非矿物所染,因为从新的破碴来看,色调一直达到骨的内部。我们在北京人遗址里看到过成千上万块烧骨,颜色也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把骨头都烧裂了;在西侯度遗址中发现的马牙有的也裂开了碎纹。一句话,把西侯度的烧骨放在北京人的烧骨中,恐怕谁也看不出它们之间的区别。”
火是人类从自然环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动力,它使得人类有了一定的支配自然的能力,给人类带来了光明,亦可驱赶毒蛇猛兽,并且对早期人类体质的进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总之,火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明创造。那么,如何认定早期人类用火的问题,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世界上更新世早期人类用火的考古材料也有不少,但可靠的、能够站的住脚的并不多。肯尼亚特卡那湖(Lake Turkana)东岸的Okote Tuff 地点发现的怀疑是“能人(Homo ergaster)”使用的火塘遗迹(160万年)和 Chesowanja 等地发现的红烧土遗迹。但它们都被怀疑可能是自然草原森林大火造成的。在我国,早更新世的用火遗存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包括西侯度遗址的烧骨(180万年)和元谋人遗址含碳层(170万年),它们都因露天遗址难以排除有关的遗迹或者遗物与人类用火的必然性而遭到质疑。目前,人类能够管理和控制性地用火的证据大都来自中更新世以来的遗址,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金牛山人遗址、陕西洛南花石浪龙牙洞遗址等,这些都属于洞穴埋藏环境。除此而外,蓝田、匼河、周口店第15地点、本溪庙后山、盘县大洞等许多遗址中都有用火遗迹的报道,但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疑问。有学者认为用火遗迹都发现在有人类活动的地层中,而且自然野火也不会很容易就在任何有人类活动的地点发生。
由于西侯度遗址文化层属于河流相埋藏环境,因此烧骨的认定十分困难。困难之处不在于能不能肯定其烧骨的性质,而是这些烧骨的来源和埋藏之前有没有人类的作用。所以,我们认为西侯度遗址中烧骨存在质疑是很正常的。即便本次抢救性发掘中再次发现了烧骨,也不能肯定它就一定与人类的活动有关。不过,西侯度遗址前后相隔40多年的发掘均发现烧骨,并且与石制品同出在一个文化层中,这不得不使我們感觉到蹊跷。接下来需要我们证明的就是这些烧骨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尽管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
从1957年《脚踏地》的发表到现在,已经过去50多年了。在考古学上,西侯度遗址的发现解除了长期以来“北京猿人是人类最早祖先”的陈旧观念。之后发现的元谋人、蓝田人以及泥河湾的东谷坨、小长梁等人类遗址或地点不断地充实着中国早期人类演化的足迹。西侯度遗址这个东亚地区早期人类的脚踏地,也被许多新的考古发现所超越。如今在非洲已经发现300万年前的原始人类遗存。在我国除西侯度以外,发现了多处与之时代相当早更新世初期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而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考古发现从早更新世初期到一万年前的晚更新世结束,有数十处之多。泥河湾已经从当初的猜想变成了中国北方地区第四纪地质和旧石器考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