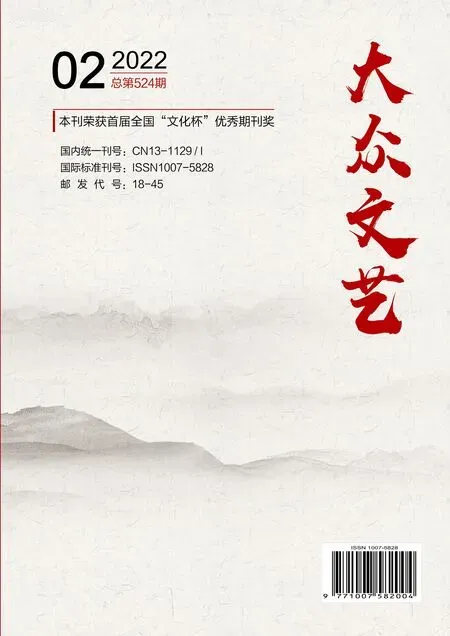我的人体画之说
张 京 (常熟理工学院 215500)
我的人体画之说
张 京 (常熟理工学院 215500)
摘要:人体绘画作为美术生必修课程,因其艺术性和人文性,有着其独特的魅力。本文是笔者结合自身学习与实践的经验,就自己对人体画的认识,联想以及个人创作的等各个方面,对人体素描绘画课程的总结。
关键词:人体;艺术;我
人体这古老的图形散发着永恒的美丽,那流失已久的古朴,自然性灵的轻盈,从人类童年的生活中走失,自希腊人之后,人与自然越来越远,与自己的身体失去了亲缘,所谓的“理性”“道德”“文明”,将健康单纯的人体审美压抑得几乎殆尽,使人无法单纯、坦然地面对自身身体的存在,人体焕发的美丽被衣物紧紧遮蔽。
但当人体走近我们朴实的艺术创作,它会带来怎样的感动,回归,纷杂的情感又将如何流溢于这古老的造物呢?
一、源于希腊的美丽
希腊的蔚蓝天空下,希腊人展露他们的身体。将自己融在自然的光辉里,按照神的模样美化、欣赏自我。人类童年的天真,使他们与神同形同性,并讴歌这神的赐予,陶醉在至纯梦境里,创造出高贵肃穆的文明。
在艺术里,这些愉悦的因素可能是他们冲突内心制造的慰藉幻象。
艺术还残存着古希腊时期的纯朴天真,对美的执着追求 ,对自我的至纯至真欣赏,只可惜,人已久久不再凝望自己,失掉了纯洁的眸子,已失去了对自我的情致。希腊人用健全的眼光欣赏裸露的人体美;现代人以裸体为羞耻,又用异样诧异的眼光看待人体;希腊人懂得单纯朴素的伟大,现代人的灵魂却像一座复杂的迷宫,热衷浮夸;希腊人懂得孕育沉默,故有伟大的创作。
现代文明的发展强迫人被灌输理性、道德残忍地剥夺了原始自然的好奇与灵性。自然的禀赋一出现便被忽视,或告诫,斥为不该,哪怕仅有的童年的天真也得不到保护与肯定,却被硬生生拽入与之相反的,充斥着应该,允许,程式的空间里去。这些被强迫接受的力量,使得来源于人类童稚时期的无邪与美没有被正确地认识和保留,好奇的想法没有得到应证。人离最初的自身越走越远,生活与童真的趣味越发彻底脱离了,所谓文明的生活也越发抵制这原始的审美。于是,将人最初天真所承认的美丽逼入艺术的象牙塔。只有在这个象牙塔里,它才是安全的。
然而,现代的世界里充斥的丑陋与无知,强行地干扰着艺术,尤其使人体艺术依旧遭到与它毫不相干的误读。
90后实验艺术家王嫣芸:“我坦然地看着你,你敢看着我吗?”这个女孩子面对大众的质疑,赤裸着端坐在镜头与记者面前。这是艺术对公众公然的对峙和声讨,直指现代人面对裸体,心理的弊端和单一的指向,虽然具有冲动的性质,但这种出自本能的、艺术性质的,虽然带着个人表达话语的冲动,对于公众具有一定的威慑。但公众对此会若有所思还是更加轻蔑地嘲笑,是极其复杂与沉重的问题。人类已经积重难返了,只有心灵澄澈,富有自然灵性的人才能捉住过往的人性之美。
好在艺术家回到与自然大化融为一体的童年,捉住了那永远缠绕在画家的心底笔下的人体,生出无限的生命与鬼魅。
人体,隐抑未露的美丽,只有流落到艺术,才能安身立命了。
二、无尽生命的颂歌
被人丢弃的原始美丽与情怀被赶入艺术的象牙塔,而艺术在被众人忽视的天地里打破禁忌,汲取一切营养,恣意酣畅地生长,萌动着精彩倔强的生命力。
人体是人最初所有情感的来源与流露的载体,是生命力量最神秘,最原始的图腾。人类的情感、情绪,或深或浅,都通过身体来表现。奔放健康,流淌着血液的红润,枯槁憔悴的面容,欢快的舞蹈,痴迷的眼神,抑郁的深思,一切自然生命力的兴衰,都直接作用于身体,并因身体而流露呈现,产生互动与交流的可能。身体呈现了生命运动的状态。
艺术化的人体艺术了生命的状态并赋予他们深深的关怀与美感。画家凝视着这些个生存与毁灭的轻盈或悲壮,企图发掘,再创造些美丽或动人的画面,一笔笔地描摹出这世间所有善恶悲喜。或醉心于这画里的世界,或冷冷地跳脱出来,生出一丝留恋无望的悲哀。
如果肉体荡然无存,灵魂便游弋不定无所居了。
众人舍弃了艺术,画家躲到艺术的角落里,满怀爱与热烈,将它化为深沉、隐晦的视觉语言。默默无言的形式,透着宁静的力量与对美的坚守。
这残存的人类天真、清高的同时,拦不住外溢的热情,它担负着唤醒人类童年的使命,它终究要带着画家深沉的爱找寻赐予它生命的熔炉,它赤裸裸地站在人的面前,它要闯入,重新回到人的身体里去,回到人的生命里去,去唤醒麻木的知觉,看到遗失的亲缘,重拾自身,回到最初的大化里。虽然,回到自然的大化里,固然是个美梦罢了。可至少使人拥有欣赏的能力,实现的憧憬和对不曾拥有的过去的惦念与幻想。如此,也至少是诗意了的。
艺术的方式是将人性的,动人的东西放大与强调,要我们去发现与关注,呈现了洋溢于人体的精神与情态,可贵而美丽。若不歌颂人自身,艺术要做什么呢?自然固然伟岸,但它属于我们无知的宇宙表面。在人类的年限里,它不死不休,静静地看着人的兴衰。我们无从真正亲近。只有面对人自身,才能在局限的赤裸里,真正感受到人脆弱渺小与可贵稀有。
人体的艺术,感慨这生死,歌颂不息生命的力量。是生命的辉煌颂歌。
三、现实相生的画面
我画面上的人体是模特与画者的契合。写生,作画的过程是两者相互的走近,相互影响,二者相生,绝不孤立。
美好对象展现在面前时,我就会沉醉在对对象的欣赏中,仔细打量暂忘自身,这是一种短暂的审美的快感。此时,我常常会不自觉,本能地描摹还原模特人体本身的美。虽然所看到所描绘的恍惚光影和曲折,成为可扑捉的美并非一致,而每一个体都是短暂且独一无二的。好景佳人难留,光景却恍若隔世。归根结底,皆因时间的无限和自然造化的偶然。我心底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却仍想在这可怜的局限里捉住些什么。我在作画过程中通常有“留住美”的潜意识和“模仿自然造化”的原始冲动。一番看穿还醉其中,梦醒痴恋旧时悲音。
我通常还会被另一种美所吸引,想去描绘一种感觉,捕捉一种韵味,蜷缩或舒展,便想要造出这番感觉来。而只有稍稍脱离了模特完整形象才可以形成一种有意味的、模糊的、抽象的潜在意象,就好像去了肉,剩下了骨和灵,人体可能变成了纯粹美的形式,虽还未可道明却已经呈现纸上。
那是一种感觉,是将感觉植入到画面里去:“侧面女人体,自上而下,是一条细长的、下垂、流动的线条,想要抽象地表现这种柔和,连贯。”目光落点的轨迹与人的联觉构成了感受的来源。
有时候,模特的一些造型会引起我的感动与思考,既在描摹模特,也是在描摹自己。某种东西在我自身的思维情感里酝酿已久,主体个人早已生成的思维因客体的吸引而跳脱出来,成为一种表达的倾向。
我在画一个男性人体时,找到了一种入画的因素。它使人虔诚地拥有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几乎是条件反射却自然地进入客体的思维里。抓住瞬间里最最动人的东西:难得的躺姿,模特头偏向一边睡着了。画这幅画时,正好能看到模特头拉着脖子偏过去,头偶尔微微转动。我看到一个疲惫的人,在一天单调的劳累中偶得小憩,忘记了他正在做的事,沉重又浅浅地睡着。我想表现他的疲惫与沉睡。同时,我在想,他真的熟睡了么?因为左腿的姿势需要着力,不可能完全地放松。梦是最深的个人防线。即使我们面对的是裸露睡着的人,也决不可能窥探到哪怕一点点的真相,它的灵魂独立于任何混乱的场景,为自我留下尊严和孤高不屑的圣地。
当如此,我的内心是充满了爱意与神圣的,感他人之所感,绘人性之共,不仅仅生成了一幅画面,更生成了高于画面的情感与精神。
四、我是画,画是我
绘画使我心灵的片角不断完整,通过借鉴和实践寻找语言表达内心的过程。在人体画中,把我的思想填充到笔下的人体里去,让人体成为最直接,最自然符合的语言,成为我自己,来歌颂、深思和哀悼。它们飘忽、轻逸、若即若离,犹如克里姆特的人体素描,不加刻意的修饰却各具韵味神姿,而我,迷恋于这种飘忽不定。
我曾做过一个与天鹅久失重逢又走失的梦,凄美又无奈:梦中的天鹅从黛青色的天边而来,脖子颀长而柔软,它有一双芭蕾舞演员的绷直的、高贵的脚。我无比清醒地知道,在我的梦里,那双脚,那只天鹅意味着什么。自此以后,那双绷紧着的脚成为了我人体画里最执着的语言:用它来执着于表达对失去美好的悼念与怀想,挣扎着即将失去的心的高贵。
当我看到莫迪里阿尼的“天鹅脖”与那种投于画面之外的眼神时,便深深爱上了它。空灵而茫然,不屑中带着淡漠的凝神,仿佛思考着另一个时空里的故事。自此之后,在我的人体画里,常会描绘脖子与肩部的动态来表现某种依恋,某种情感。
有些执着会一直伴你入梦,有些坠落尘埃的故事又在梦里闪现。而当你梦醒时,你会为此留恋,为你自己感动。入梦方见心里挚爱坚守之深。在梦和醉里,恍惚看见了自我真理的片角。当爱融在梦幻的童真里时,梦显得莽撞和天真的可爱,好比夏加尔那永远萦绕着乡愁与爱的梦幻,既然让我看到了离心如此近的梦境,那何不造出一个幻境来?用笔来留住梦的执着?
所以,梦境、自我、芭蕾舞者的脚、依恋、淡漠、失去,是我人体画永远迷恋执着的主题。
我的人体画是对人类失落自身的找寻,对人性的归依。通过对人体画的欣赏,人具有了更多的包容性,对何为人有了更多的感慨。
每个人都是未完整的自身的一部分,生来寻找他的临零散失落的胞体。只不过有人生性敏感多思,有人未曾留意。
每一段人生,每个人体都是艺术品。人们常常忘了,当我们退而远观时,他们都是一张可供欣赏的画。可它们却被湮没在忙忙碌碌之中。而人体,它让人看到真实的自己,使人窥探到他成为人类的原由,使他愈来愈成为人。当你看到它时,你发现了你不曾有过的情感,不曾有过的虔诚情怀,会勾起了你对遥远自身的遐想,也是对人类的遐想。缺失的人得以瞥见完整。
画中的人体都是潜在的自我。当我们审视它们,我们看见了自己。画中吸引你的某种美丽,不是个人的,而是上苍对全人类的赐予而散落人间了。我将它们找到并还给我们。
当你画一个人体,看一个人体,你不该问这是谁。你该感叹:“这是我!这是一个人。而我,可能就是他。”
参考文献:
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