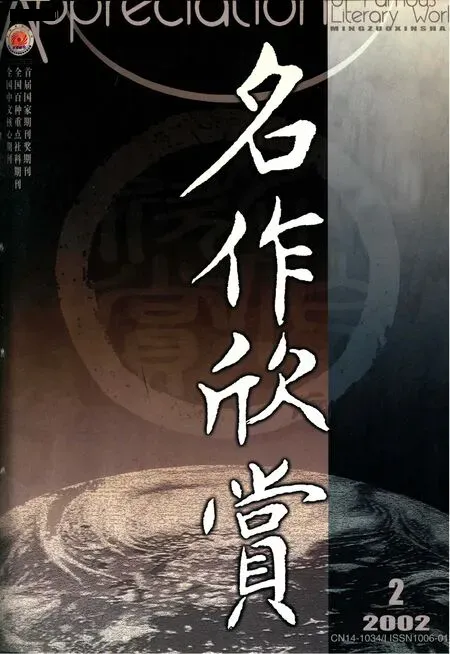黄宗羲亲情诗“三美”论析
⊙范杞燕[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黄宗羲亲情诗“三美”论析
⊙范杞燕[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宁波315211]
摘要:黄宗羲是清末明初的著名学者,他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亲情诗。其亲情诗具有丰富的美感,主要包括意蕴美、朴素美、感伤美。本文通过论析其亲情诗的美感,走进黄宗羲真实的情感世界,从而更真切更全面地了解黄宗羲。
关键词:黄宗羲亲情亲情诗
黄宗羲(1610—1695)是清代浙派诗的鼻祖,有《南雷诗历》传世。亲情诗在《南雷诗历》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在“天崩地解”的历史时期,黄宗羲参与了反阉党、抗清等重大历史事件,表现出铮铮铁骨。另一方面,黄宗羲在亲情中总会表现出他的万般柔情。在《南雷诗历》中,亲情诗有近五十首,是我国古代亲情诗的珍贵遗产。笔者细细品味之,觉其有“三美”,以下试加论析。
一、意蕴美
黄宗羲的亲情诗,是指他在一生中创作的以表现其和亲人之间情感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诗作,这些亲情诗无一不体现了意蕴美,主要包括他的家书,他对父母长辈的孺慕之情、对远游儿女的思念以及对早逝子孙的悲悼。在这些诗中,黄宗羲展现了自己的丰沛情感,反映出他内心的起伏波动,我们在品味意蕴美的同时也看到了这个铁汉柔情的一面。
(一)山高水长家书传
对于羁旅在外的游子来说,家书总是牵动着他们的情感,给他们带来慰藉和希望。在《南雷诗历》中,有一些是黄宗羲的家书,他以短诗的形式寄予家人,辞温意柔,充满了对家庭的深情。
《天台家书》是《南雷诗历》中出现的第一首家书,创作于崇祯十三四年(1640—1641),诗云:
山城古寺岁将除,犹问乡人度岭无?
欲归欲留未成计,惆怅寒窗难下书。
年关将近,诗人客居于天台山城的古寺中,心情十分矛盾。时间逼近除夕,该回乡的人早就回乡了,挨到这个时候回乡的肯定是越来越少。可是诗人并不死心,总是追问乡人中还有没有人越岭还乡的,如果有,一定要帮自己捎带上家书。可真正等到写家书时,诗人又踌躇不决:自己该与乡人一起归家呢?还是留在他乡过年呢?留下来,在家书中又该如何向家人交代呢?诗人铺纸伸笔之际,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两难之间,那就权以诗歌当作家书了。山城古寺,本就给人幽深寂冷的感觉,加之“寒窗”意象,既写出了岁暮腊月之寒,又写出了内心的凄冷孤寒。这种孤寒是来自于对母亲、妻子和儿女的思念,来自于孤身漂泊的惆怅。诗人内心的盘旋纠结,真可谓是欲解不去。
黄宗羲还有《泊河口家书》二首,都是诗人顺治十七年(1660)赴庐山途中经过江西铅山河口时所作,其一云:
三尺孤蓬乱石滩,已随鸥鹭泊更残。
闻得乡音惊坐起,渔灯分火写平安。
首句是写诗人乘坐的小舟在“乱石滩”中穿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在天色昏暗的河流中,随风飘荡着一叶孤舟,岸边的鸥鹭静静栖息,万籁俱寂……下联笔锋一转,这种深夜的安静被忽然打破,诗人突然听到邻舟中传出熟悉的乡音,情绪顿时激涨起来,躺在船中的身体一下子坐了起来。接下来,诗人过去与乡人亲切攀谈,然而此等细节全都被诗人略去,最后直接托出特写镜头:他傍着渔灯急急地写下家书报平安。“闻”“惊”“坐”这三个动词传神地刻画出诗人的行动细节,这一连串动作,将连日行舟无人可报平安的苦闷一下子全发泄出来了。这两句诗分别化用了元稹《闻乐天授江洲司马》中的“垂死病中惊坐起”和吴文英《莺啼序·春晚感怀》中的“渔灯分影春江宿”。诗人通过对前人诗句的艺术加工,使思家的情感得以爆发奔突,一静一动、一悲一喜,也唯有故乡的牵绊才能让诗人的情绪有如此大的波动。
以上几首家书诗语淡情深,以家常之事论家常之情,却有着打动人心的魅力。山高水长,总有那么一封家书传递着割舍不断的亲情。
(二)真挚的孺慕之情
黄宗羲还有一些诗是写对父母双亲以及长辈的孺慕之情,主要有《归途杂忆》四首、《金陵哭外舅叶六桐先生》《叔父孝廉季真》《西瓜初熟饷诸叔父》等。
《归途杂忆》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充分体现了黄宗羲对母亲的真挚感情。此组诗都是在母亲病逝后,诗人为谢吊至海宁、杭州等地时沿途创作的。其一云:
出门长自请归期,才到归期即望儿。
今日更无人倚闾,萧萧唯有白杨知。
前两句写的是诗人母亲在世时的情况。诗人经常出门远游,每次出门母亲总会询问归期,刚到约定的日子,母亲便会早早地翘首以盼。这一句仿佛让人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依立门旁,翘首远望,在等待儿子的归来,形象真切、生动。①“今日更无人倚闾”是出自《国策·齐策》,王孙贾之母对儿曰:“汝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倚门”“倚闾”都是亲情诗中常引的事典,用来形容双亲盼子归的殷切心情。如王维《送友人南归》:“悬知倚门望,遥识老莱衣。”诗人写“无人倚闾”是暗示那个盼儿心切的慈母已魂归黄泉,自己失去了母爱。忆往昔,家中总有母亲在等待着诗人;想如今,诗人却走在谢吊的途中。今昔对比,徒增一份无可奈何的伤感,诗人将这份哀伤诉诸路边的白杨,唯有萧萧白杨知晓他此刻的心情。
叔父黄季真在黄宗羲的心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在为其写的墓志铭中说道:“维吾叔父,仁心独秀。琐碎虫鱼,旁通医祝。牛筐诗瓢,件离惯朽。不名一家,不资师授。场屋风气,逐影而徒。”②诗人与叔父离别才三月,竟惊闻叔父逝世的噩耗。他的挽诗诉说叔父临死前还在灯下用蝇头小楷抄写诗人所作的《子刘子行状》,让诗人如何不动容;叔父在修黄氏家谱时的慎重小心,似乎还历历在目。诗人还来不及向叔父好好尽孝,“药不亲尝含不试”竟成了毕生的遗恨。全诗读之,唯觉凄情哀切,缠绕笔端。
黄宗羲在表现自己的孺慕之情时,往往融入岁月蹉跎之感,似要将此生的艰难都倾倒而出,使浓郁的哀伤久久不散……
(三)对远游儿女的思念
子女永远是父母心头最牵挂的人,作为父亲的黄宗羲也将他对子女的爱与殷殷期待写进了诗中。黄诗中经常提到“第四女”,即诗人特别钟爱的女儿徽音。事实上,徽音只是黄宗羲的养女,因她酷爱作诗,黄宗羲收其为女,父女间颇为亲近。《南雷诗历》中有关徽音的诗有数十首,可见黄宗羲对女儿的爱怜之心。如《寄新茶与第四女》云:
新茶自瀑岭,因汝喜宵吟。
月下松风急,小斋暮雨深。
勾线灯落蕊,更尽鸟移林。
竹光犹明灭,谁人知此心。
诗人采摘完新茶,想到爱茶而又经常喜欢通宵吟诗的四女,便立即为爱女寄去刚采制的新茶,还赋诗相赠。诗人选用了“松风”“暮雨”“移鸟”等这些雨夜中的意象,将山村景物亲切自然地呈现在女儿面前。月下的松风、小斋的暮雨都是女儿最熟悉的生活环境,情在景中,不仅能表达诗人对女儿的关怀,也解了女儿对家的思念。诗人又别有深意地在句末点明,此情此景只有亲人才能体会“此心”。属于父女间的浓浓默契和亲情自是不言而喻。我们可以想象,当女儿收到浸润着满满父爱的新茶与新诗时,一定会怀着无比欣喜的心情,或许还会通宵品茗作新诗相和吧!
《岁暮望两儿归》是写诗人对儿子的思念,其一云:
老去虽眠食,艰难欲仗儿。
如何腊月雨,不见夜航维?
落叶惊孱犬,风灯罢钓丝。
几回开户视,空做一番疑。
“两儿”是指诗人的次子正宜和季子百家。全诗紧扣一个“望”字,流露出父子间的深厚感情。诗人自觉年岁渐老,倍感生活起居的艰难,希望仰仗在外的儿子们。寒冬腊月下着雨,为何不见雨中归来的航船?一个反问将诗人的思子之情进一步升华。颈联写叶落之声惊了孱犬、风灯惊扰了鱼儿来突显夜间的寂静。如此安静的夜晚,若是儿子回来,诗人必定会知晓。然而思子心切的诗人并不放过一丝丝微小的声响,几回开户查看是否是儿子回来了。这一细致入微的描写将一个老父孤寂思子的心情表达得尤为生动感人。
(四)对早逝子孙的悲悼
《南雷诗历》中悼亡诗占很大的比重,其中提到早夭的有幼子阿寿,孙女阿迎、阿好,儿媳等,在艰难困苦的重压下,家中人一个接一个地去世,给黄宗羲以莫大的打击,他只有写诗来寄托哀思。
阿寿是黄宗羲的第四子,他对阿寿尤为疼爱。阿寿的夭折对他打击极大,极度悲痛的他连续作了二十多首诗来怀念阿寿,如《至化安山送寿儿葬》《梦寿儿》《忆化安山》《初度梦儿》《上寿儿墓》《思寿儿》。且看其《至化安山送寿儿葬》:
五年吾闭户,赖汝得殷勤。
朔雪遮新土,荒山出小坟。
天昏吾自去,月暗汝谁群。
临老无多泪,溪流总不分。
这首诗写于阿寿死后诗人送其至化安山黄氏禁茔安葬。阿寿在世的五年正好是诗人隐居的时候,阿寿的殷勤陪伴给诗人带来了欢乐,让他暂时忘却抗清失败之事。诗人在《亡儿阿寿圹志》中说:“五年以来,予衰索无复四方之事,食与儿同盘,寝与儿连床,出与儿携手,间一游城市,未暮而返,儿已迎门笑语矣。”诗人想到爱子将一个人寂寞地长留于此,教人怎不伤心。然而诗人自觉垂老已无泪可流,他将自己的欲哭无泪怪罪到溪流头上。诗人怪溪流无情,只管自己汩汩地流淌,却不肯分些予人权当哀子之泪。溪流之深,更能衬托诗人丧子之痛,也给全诗留下了潺潺不断的哀思。
阿寿死后,黄宗羲的孙女也相继离世,《孙女迎儿墓上生石楠一株高丈余远望如花》是写他对孙女阿迎的怀念。阿迎是诗人次子正谊之女,也是他十分钟爱的孙女。阿迎牙牙学语时,诗人曾写过《书贻孙女迎》来表达他对这个小孙女的怜惜。自阿迎后,他的另一个孙女阿好也不幸夭亡,《哭女孙阿好》云:
廿载伤心自寿迎,那堪阿好又凋零。
明知早慧同槿艳,且得明眸慰暮龄。
锄却幽兰留泪眼,空移红影射窗棂。
剡中十亩埋荒地,树树松来作怨声。
诗人忆起阿好出生时异常聪慧,他隐隐担忧这个孙女会有和木槿花相同的命运,经历太多生死的诗人自我安慰“且得明眸慰暮龄”。不幸的是,阿好果然如朝生夕陨的木槿花也过早地夭亡了。人夭室空,如空谷幽兰般美丽的阿好如今也长埋于剡中了。此时诗人又想到早于阿好离世的阿寿、阿迎,他们都安葬在此,山林间飒飒作响的松涛之声宛若他们共同发出的悲怨之鸣。
黄宗羲悼念儿孙的诗都写得文情并茂,体现出他对儿孙怜爱之深、追忆之甚、悲悼之痛。
二、朴素美
黄宗羲一生充满豪壮之气,他的诗歌大体上有着强烈的时代风雷之声,有沉郁冷峻的史诗风格。而黄宗羲的亲情诗却是别具一格的存在。在这些叙写亲情的诗歌中,没有了时代疾风暴雨的阳刚之气,更多的是一种婉转柔情,不仅体现出意蕴美,还呈现出朴素美和感伤美。
朴素美作为一种风格,历来受到诗人们的推崇。所谓朴素美是指以朴实的形式自然地表达出作者的思想情感,并由此生成一种耐人寻味的审美艺术境界,让人获得充分的美感享受。艺术的朴素美,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诱人的绚丽,但富有内涵和具有较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③朴素美主要表现为语言的质朴、表达手法的朴实以及思想情感的纯朴。可见朴素美是把这些美的形式与所要表达的内容完美结合,使作品色淡味浓,于朴素之处见作者的巧思。
《南雷诗历》中的亲情诗体现了朴素美,黄宗羲将自己的幽思缓缓道来,辞温意柔、体贴入微,朴素平淡之语却能勾起不平静的思绪。《天台家书》中诗人简笔勾勒了山城古寺、故乡之人,最后说到“难下书”,短短几句就表达出对家人的深情。又如《泊河口家书》,诗人并没有大笔墨地直接叙说自己思家的愁绪,而是通过“惊坐起”这个简单的动作,直接将思家的情绪渲染得淋漓尽致。《岁暮望两儿归》中诗人紧扣一个“望”字,却能写出老父思子的寂寞心境。诗人甚至还使用了口语化的诗句,如“出路芝儿归也未,童心阿祝近如何”“五年吾闭户,赖汝得殷勤”“我亦归程应计日,担头书册好分肩”……这些句子如同信口聊天般,却能在平易之中更加贴切生活,更容易打动人心。李东阳在《麓堂诗话》里说道:“质而不俚,是诗家之难事。”显然黄宗羲成功地用朴素之言写出了真挚之情,又不显俚俗。
黄宗羲在亲情诗中还用极精练质朴的手法写景、状物、叙事。“秋深昏晓异温凉,静坐南窗白日长”,寥寥几笔把诗人独坐深秋的形象勾勒了出来;再如“月下松风急,小斋暮雨深。勾线灯落蕊,更尽鸟移林”,写出了雨夜黄家续钞堂书斋内外的景物,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昏暗的月光、松间的凉风、潇潇的暮雨、明灭的灯火、林中的鸟儿……其他如“春雨迷台路,秋声滞燕矶”“三尺孤蓬乱石滩,已随鸥鹭泊更残”“准拟千山一夜明,其如丛桂湿三更”等,这些句子没有浓墨重彩的细致雕琢,语言朴实明畅,却是黄宗羲亲情诗的独特之处。
黄宗羲的亲情诗虽见朴素却不乏文采,初一读来如寻常口语;细细读之,不失为工整的对偶。如“衣染霜花从柏叶,饼怜月影画婵娟”“蓬底漏痕争坐位,孤城涛势逼匡林”……黄宗羲还喜好用典,亲情诗中也有不少用典之作。但其在亲情诗中的用典却是极为贴切易懂的,即使是不懂典故之人也能明白他的诗中之意,这才是用典的绝妙境界。黄宗羲在《归途杂忆》中用“倚闾”指代母亲盼儿归,用“负米锄瓜”指代奉养父母之事;在《叔父孝廉季真》中用“马尾”喻叔父的慎重细心……这些对仗、用典以及其他表现手法并没有使他的亲情诗晦涩冷峭;相反,使他的诗歌于朴素中多了一分不凡之色。
黄宗羲说:“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只有贯注自己真性情的诗歌才会产生巨大的精神感染力。情到深处自无华,黄宗羲就是这样用朴素平常的语句抒发浓郁的亲情,自然地流露出一个普通人所具有的世俗情感。他是如此真实亲切,触及了人们的内心深处,既让我们品味人间的真情,也从中获取了一份朴素平易的美感享受。
三、感伤美
所谓感伤是指感慨而伤怀之意,感伤美是文学艺术中重要的审美基调。我国的文学作品历来就带有这种哀怨忧伤的色彩,如《诗经》《楚辞》等,后世甚至出现了以悲为美的文学思潮,可以说感伤美是随文学创作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艺术风格。感伤美的形成与我国传统的文化积淀、各个朝代的历史背景以及创作文人的个人境遇和人生价值观有关。正是由于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幽思导致了文人在审美基调上对感伤的崇尚,从而创造出具有感伤韵味的作品。
黄宗羲的亲情诗大多具有感伤美的情调,主要表现为好用冷色调的字、选取冷色调的意象;在情景交融中含蓄地道出哀思;采用虚实交错、吞吐回还的表现手法。
冷色调的字词和意象更容易给人以压抑的感觉,如《金陵哭外舅叶六桐先生》:“流水秦淮咽,黄花篱落衰。”本来秦淮流水和篱边黄花都是与人无涉的客观存在,只是诗人将内心的愁苦伤怀投射到了它们身上,且“咽”“衰”这些冷字的使用加重了深夜哭舅的晦暗的画面感。又如《忆化安山》:“招魂何自不归家,火冷春深草欲遮。”“冷”“深”“遮”三个冷色调的字连用,无疑更是突显出诗人对儿子的哀思之情。此外,黄宗羲在意象的选取上也颇为用心,如《泊河口家书》:“三尺孤篷乱石滩,已随鸥鹭泊更残。”此诗中的意象有“孤篷”“鸥鹭”“乱石滩”等,这些意象的组合共同抒发了诗人独自漂泊于外的孤寂感,显出一丝淡淡的感伤。
黄宗羲的亲情诗还往往通过写景塑造一个既凄清又优美的境界,隐露出种种感伤情怀的“韵外之味”。在他悲悼儿子时这样写道:“青青乱笋穿坟出,汨汨溪流傍晚哗。”既有墓地凄冷的静感,又有溪流喧哗的动感,静与动、荒凉与欢快的融合毫无冲突,让人感受到凄美中蕴含的忧伤。又如在《第四女来两月别去旋寄二诗次韵》中的环境描写:明月是“空悬”在当头的,仿佛失去了皎洁的月光,只剩下一轮模糊清冷的月影;昨夜的西风是“高急”的,似要把深秋的寒冷吹进诗人的心里;落叶是无情的,偏偏要堆满江上的小楼,拨动起诗人本就敏感的情思。明月、西风、落叶,也同样塑造了一个凄凉中带着忧伤的美丽的诗境。
黄宗羲的亲情诗中多带有缠绵悱恻的感伤情调,这与他虚实交错、今昔对比的表现手法是分不开的。他在《归途杂忆》中表达对母亲的感情时采用了梦的笔法:“一旦于今成梦幻,可知多少不如人。”他自认为母亲在世时,没有好好地尽孝,让母亲为他担忧,这种深深的内疚,让他在无数次午夜梦回时想起母亲。诗人在《初度梦儿》中写道:“今日娇儿来拜我,梦中萧索五更天。”现实中诗人再无法拥抱自己的爱子,于是只能寄托梦幻再续父子深情。在现实与虚幻的强烈落差中,我们自可品味其中的感伤。诗人还通过叙写昔年之事与今日之惨况对比,在巨大的反差对比中营造哀婉意味。如“昔日嫂曾梳短发,今来儿不怯啼鹃”“去年记得娇儿在,一日相呼有百回”“今日更无人倚闾,萧萧唯有白杨知”……
感伤美在黄宗羲的亲情诗中令其情将尽而其意无穷,置身于这样凄美的诗境中,我们被他的亲情触动,为他的感伤而感伤,与他一同发出思亲的悲鸣。
我们对黄宗羲的传统定位是刚直的遗民诗人,一位处于时代狂流中的不屈志士,然而他的亲情诗却让我们触及他内心柔软温情的一角。黄宗羲的亲情诗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与真实写照,因此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形象,是对他完整人格的补充,从而使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一个有血有肉、情系家人的黄宗羲。这也是黄宗羲亲情诗的魅力与价值所在。
①②宁波师范学院黄宗羲研究室:《黄宗羲诗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页,第72页。
③王绍辉:《朴素美:艺术创作的高层境界》,《中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清)黄宗羲著.戚焕埙,闻初旭整理.黄梨洲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徐定宝.黄宗羲年谱[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3]吴光.天下为主——黄宗羲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4](清)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2003.
[5](宋)吴文英.增订注释吴文英词.[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6](明)李东阳.麓堂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
作者:范杞燕,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2014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编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