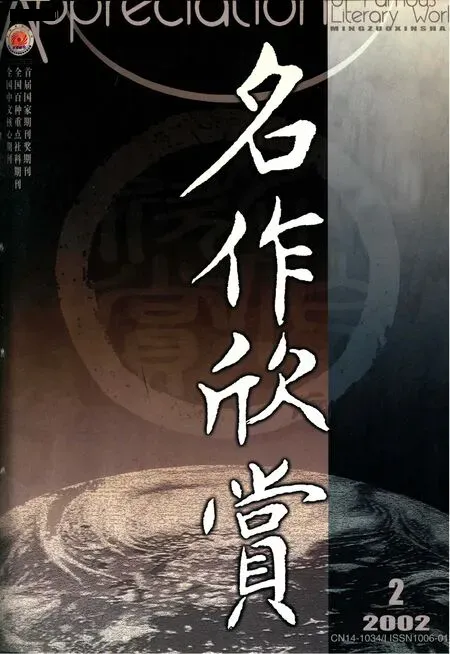楚调雅怨与李白的乐府拟古
⊙陶 冉[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89]
楚调雅怨与李白的乐府拟古
⊙陶冉[首都师范大学,北京100089]
摘要:《乐府诗集》收录的李白乐府古题中相和歌辞拟作倾向十分明显,而且相和歌辞楚调曲比重尤为突出。楚调在汉初“上有所好”下成为汉乐府典型曲调之一,经贵族文人群吟唱而形成独特的女性化雅怨本事模式,也由此与汉魏六朝歌吟抒怀的文士气质相通。同具有骚雅情结的李白在“将复古道”的拟乐府中对楚调有所倾重也就并非偶然,并为其注入了极具个性的生命力。
关键词:乐府楚调雅怨李白
一、楚调雅怨的形成与嬗变。《乐府诗集》相和歌辞楚调曲,主要是王僧虔《技录》中《白头吟行》《泰山吟行》《梁甫吟行》《东武琵琶吟行》《怨诗行》①几种及衍生新题,收录歌诗却有131首之多,由此可见赵宋前文人对楚调的青睐。李白的乐府诗数相和歌辞与杂曲歌辞最多,而33首相和歌辞中楚调曲的拟作密度最大,共拟7个曲名,9首作品。这不仅在他本人乐府古题拟作上比重突出,与其他文人代拟楚调相比也不容忽视。
楚调曲以“怨”为主导内蕴,这从《白头吟》《怨歌行》及后世衍生的《长门怨》《婕妤怨》《长信怨》《玉阶怨》等曲名上即能看出。而且,楚调的怨情模式与其他乐府曲调明显不同:它虽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但主导的本事模式却既非源自民间下层的生活甘苦或普通男女的爱情,也非生死之思,战争丧乱或济世关怀;所抒之情既非平民对黑暗腐败或压迫离乱的控诉悲歌,也不似其他古辞那么朴实铺白、直露激切。相比之下,楚调之怨,往往会在婉曲悠长的诉说中,敷以典雅的意象和语词抒发一腔怨情,因而具有雅怨的气质。而这种曲调特质与西汉贵族宫廷的推崇和流变是分不开的。
从“高祖好楚声”、武帝“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②起,楚调就已与西汉贵族的文艺生活趣味相合。本身即楚人的刘氏皇族将楚调从《安世房中歌》《郊祀歌》的雅乐,唱到《大风歌》《秋风辞》、刘友《幽歌》、刘细君《悲愁歌》等个人怨嗟,楚调也演变成与秦声并列的汉乐府基础声调,在汉乐府中“时代最早,地位最高,力量也最大”③。即使之后胡声充溢,乐府渐以中原北派之声为主并独立成体系而与楚声鲜涉,楚调仍是汉代歌诗最有代表性的三类歌调之一④,并促成以悲为美的审美形态,渗入其他古题的本事情韵中。邱琼荪先生即指出清商曲辞源于楚调⑤,而《远别离》《昭君怨》《楚妃叹》等未被郭茂倩划入楚调的曲名也都荡涤着楚声楚调的余波。西汉贵族的楚调推崇不仅带给乐府楚调伤时嗟世,忠诤罹忧,知音难觅,美人迟暮,思君不见等悲怨基调,更为其形成一套具有鲜明女性雅怨色彩的本事模式奠定基础。从楚调曲古辞上看,其本事往往都溯至西汉,《白头吟》传为卓文君自绝而作,《怨歌行》《长信怨》《婕妤怨》明显指向班婕妤,《长门怨》《阿娇怨》亦系阿娇失宠之事,这些本事都集于失宠弃妇之身,也就使楚调具有了弃妇之怨的女性色彩。同时这些弃妇身份非普通民间女性可比,皆为宫廷贵族或上层名流之属,围绕她们展开的叙事,便自然在语词上多了柔顺和叠音叠韵的运用,团扇纨素、汉宫夜色等意象也淡化了浅俗而典雅渐增。雅怨的内蕴在琴瑟琵琶、笙笛竹节的丝竹相和而非金石之声中吟叹回环,更显要眇绵长。
男女之情、妃嫔宠弃和与君臣际遇心理的相类使这些失宠贵妇之怨能够为失意文士代言,而本事人物的贵族身份又使抒情有了近似于“怨诽而不乱”的变雅基调。孙月峰评《怨歌行》“含一怨字,正以不露为佳”⑥。这种委婉与敦厚正是其他乐府弃妇诗鲜少具备的,也就更为文士所取。当然,楚调曲雅怨的本事模式虽与西汉贵族的推崇运用关系密切,但真正被建构起来,还是文人纷纷拟作的结果。正因楚调蕴含的雅怨情韵与汉魏六朝文人的情感暗合,才会使这些西汉贵族女性本事被优先选取,广为流传,诸如周公、卞和一类本事在传播上则渐渐黯淡。曲名本事和古辞虽然屈指可数,楚调乐府却被后世文人相继代拟,从而确立起这种起自西汉贵族宫廷,成形于文人拟托女性以抒雅怨的本事模式。
楚调乐府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嬗变。最初的汉魏乐府基本停留于本事层面的缘情叙事,如《白头吟》等本辞和曹植的《怨歌行》,同时透露出议论的倾向。到晋宋时,楚调在陆机、鲍照等人手中明显文人化,不拘于本事叙述而征引旁典,比如鲍照《白头吟》“申黜褒女进,班去赵姬升。周王日沦惑,汉帝益嗟称”。且议论兼抒情的比重增加,已呈现出更重心境及环境描摹的倾向,抒发的情感也渐褪女性色彩而更有文士不平的意味。齐梁以后文人在此基础上更能把握本事内蕴而绕过事典本身,用声情状物将雅怨运用于生死感怀等更多题材上。并且楚调原初的宫廷声色更与齐梁宫怨诗产生气质的呼应,于是宫怨承载起楚调的情感,辞藻和情思也明显盖过对叙事的遵循。文人才思的介入赋予了楚调雅怨向绮丽方向运笔的可能,最终使其超越对贵族女性本身的依撑,而达到《宫怨》《杂怨》《玉阶怨》之类不明字面对象所指,而具有普遍性体验的雅怨境界。楚调本事因其雅怨特质而为后世文人所趋,而其逐渐流于绮靡声色,既是诗坛整体追求所致,也有本身潜质的基础。所以经过文人的运用和提炼,最终传承更多的往往是本事中的情愫而人物事件却逐渐模糊。情感的深发,绮靡化的状物描摹,叙事的隐去,在陆机、谢灵运、张正见等人的作品中即可看出。
楚调曲的风貌演变使其拥有了与各期文学相应的气貌,但留下的弊病也不乏批评,原本汉魏楚调的平畅妥帖被声色雕琢取代,含而不露的淳厚志兴被单一的抒情渲染淫溢。周紫芝在《古今诸家乐府序》中称:“后人之作,其不与古乐府题意相协者十八九……独恨其历世既久,事失本真,至其弊也,则变为淫言,流为亵语,大抵以艳丽之词更相祖述……无复有补于世教。”⑦直到唐朝,诗人拟楚仍多是继承齐梁声情描摹的手法,虽未过度渲染,可也是殿阁玉窗,凄草宫树的玲珑意态,于状物描摹中写婉曲哀怨,即使提及长门长信等事也只是一笔略过。与此同时,时风更是逐渐导向“即事名篇,无所依傍”的新题乐府创作,于是兴复古乐府的任务便由李白主动负起。他对古乐府的归循和新创也可从楚调曲的拟作上作一观。
二、李白“拟楚”的复归与自树。李白对楚调曲拟作的重视前文已从量的层面有所说明。济世抱负、仕途遭遇的愤懑在他激扬胸怀中难以掩平,雅怨的楚调正好为他提供了深厚的吐露依傍,加上“将复古道”之志和“我本楚狂人”的慕楚情结,李白在拟古中对楚调的看重与前人相比更具有浓厚的个性气息和时代独特性。
李白的楚调复古并非完全因循汉魏乐府的本事模式和语言技法,也未彻底绕过六朝文人的繁丽绮情。一味地复古和模仿只会是对原有范式的固步重复,所以,李白在复古方面深有一套既融汇前人创作精华,又凝聚其本人离奇惝恍、纵横变幻的技法,从而在本事选择、语言体式的取弃中恰如其分地再现汉魏乐府的本事与志兴。
综合来看李白九首楚调曲乐府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在本事敷演上倾注更多之作,如《白头吟》《怨歌行》。《白头吟》前后两首同异相间,“语意多同,或谓初本云”⑧。《乐府解题》曰“皆自伤清直芬馥,而遭铄金玷玉之谤”⑨。不管这两首诗创作的具体语境如何,从前后明显的加工痕迹都可见李白对该调拟作的看重。观历代拟作,至晋乐时《白头吟》的比兴之语便有所增加,鲍照和张正见又列出周幽褒姒、婕妤飞燕、冯敬通、王嫱、崔亭伯,使人典丰富细碎许多,且叙述者的弃妇形象淡化,文士不遇之意渐浓,“惆怅”“幽忧”等连绵词使古题乐府有了六朝色彩。与鲍照、张正见多引他人事典相比,李白则紧密围绕卓文君进行叙事,本事贯穿全篇,同时也夹叙夹论,怨情自见。
全诗的叙述层次演进分明,开篇锦水鸳鸯起兴以比夫妻忠贞,之后换七言体完整叙述事件本末,千金长门赋一事的捕捉加入,在原有本事模式上更化用无痕地增加了诗歌容量和故事完整性。东流难西归等比兴回应开头作结后,转为五言发论,以汉乐府常用的菟丝女萝与人心对比,发叹规劝,并在最后如楚歌“乱曰”一般以七言戒之。全诗章法皆承汉魏乐府,语言表述也与六朝文风不同,李白很大程度地复归了汉乐府本辞的朴实叙事之风,在流畅的对比中自然地流露感情和评论。全诗五七言交叠错落,七言楚歌古已有之,句式在保留之中亦有新变。在内容上,此诗为李白早期出蜀时感于卓文君之事而作,秉承“缘事而发”的基础,将故事尽求完整地演绎出来,并在借用其他典故的同时不冲淡本事,这主要得力于他采用菟丝女萝、龙须席、琥珀枕、青陵台一类物典来暗喻,而非直接罗列人事进行说理,故而能在比兴中主次分明。而且,诗的叙述视角也在君妾相称的自白和客观介入中灵活转换,将代言感叹和敦厚规劝回环道出,雅怨回荡。可以说李白对《白头吟》代言体式的沿用和事中显情的回归,以及叙论结合的继承正体现了他对汉乐府古风与楚调旧声的归复,而结尾发论劝诫之语在思想上较本辞又更进一层,也拉开观照的距离和层次。在承用五言诗传统的同时又将叙事的娓娓道来和议论的洋洋洒洒通过富有流动性的七言抒写而出,声情流畅。《怨歌行》是一首借古题写时事之作,诗题自注云:“长安见内人出嫁,友人令予代为《怨歌行》”⑩,却仍依循班婕妤之事,开篇从“十五入汉宫”交代写起,与傅玄“十五入君门”倒也相合,不过傅诗更宕开笔墨渲染心境寂寥,引入“涂山”“采葛”之典,“纤弦感促柱”等句也显繁丽声涩。李白则与本事联系更密,脱去赘琐的景物描绘和典故穿插,抒情增加但叙事不减,表现出事态发展的过程性,叙述视角虽偏于侧面道来,但仍留有与诗中人物重合发声之感。对《怨歌行》的本事,李白选择班婕妤一说而非卞和之事,也不从曹植一派直言君臣,这在体现他对汉乐府本事叙事坚守的同时,也可见其对楚调雅怨的倾斜。
第二类楚调曲是《东武吟》《梁甫吟》一类恣肆豪迈,翻新出奇之作。《东武吟》和《梁甫吟》曲调古老久远,古辞已失,《技录》皆言“今不歌”,相传本为挽歌或哀时之嗟,前人拟作也更多苍寥深沉的气势,这类曲调是楚调中别具风格的一支。左思《齐都赋》注云:“《东武》《泰山》,皆齐之土风”,或许可以假设,这种源头久远的齐地土风是经汉代楚声普及的加工后渐变为楚调歌诗的,而其本身留有的北地贞刚也能为后人继承,李白便将其发挥到极致。
李白《梁甫吟》与相传诸葛亮之辞意同体异,以三五七言歌行之风将见谗罹忧的愤懑与求索明主的渴望回环跌宕地表现而出。太白诗风的飘逸洒脱、“窈冥惝恍”也在这类楚调作品中彰显融合。朱乾《乐府正义》称《梁甫吟》初为“哀时”之作,后为葬歌,李白上溯本源,将其重新归入有德之士见谗小人的哀时本怨中。从开篇“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到“我欲攀龙见明主……以额扣关阍者怒”,或“婉转曲折,若断若连”,或直言抒怀,掷词如雷,雄奇意象复沓铺排,情节转承大开大阖;吕望、郦食其、二桃三士等典故,三五七言整散交织和屡次换韵营造出节奏顿挫、铺张扬厉的风貌,既将“君不照鉴我之精诚,我亦无容以国事为忧”⑪的满腔怨闷倾泻酣畅,也在汉魏六朝五言诗的沉郁内敛外将楚调怨声发出自家气派。《东武吟》作于天宝三载夏离开翰林院之时,同样铺叙纵横,虽伤时变,却不失笑傲不羁,与鲍照之作同情不同气。凭借飘逸不羁的性情将“愠于群小,乃放还山”⑫的沉郁凝滞挥洒成或诡谲奇幻、或要眇空灵的气韵,这是李白对楚调怨诗拟作中自树立的新境界。
最后一类是近似齐梁诗风之作,即《长门怨》《长信怨》和《玉阶怨》。这几首曲调创自齐梁后,已是当时文人出自声情追求,对楚调本事自度的新声。李白并未拘于齐梁的框框。两首《长门怨》遵循阿娇本事,虽也只通过“金屋”和“长门”这两个意象点明对象,以侧面渲染路线来写怨情,不过都改以七言绝句体式,加上语言洗去雕琢,也就在声律上更加流动自然。《玉阶怨》祖班婕妤“华殿尘兮玉阶苔”之意,谢之作已经达到化去本事具体情节和对象而从横截面上纤巧地炼出哀怨的境界。李白更是把宫人伫立秋宵,却下回头的低回百转、欲说还休演绎得幽微空灵,精确捕捉复杂微妙的心理变化过程,而且未着一字,却将谢诗末尾的“思君何极”炼为“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的深婉玲珑。且短短四句落笔即点曲名,真正将玉阶白露融入诗境,字句也比谢诗“流萤飞复息”之类更为到位而不露斧凿。
三、结论。西汉宫廷贵族的弃妇事典在楚调之声中流传,逐渐形成怨而不伤的雅怨情调,并与后世文士的心境契合,借以代言,这既促进了楚调雅怨本事模式的确立和完善,也使其在世情时序下走入淡化本事叙述,流于绮靡声情,消去天然朴质而转向事典雕琢的窠臼。李白在特定时期对楚调的看重和拟作,为其注入了深厚强劲的活力。总之,与前人相比,他在重拾叙事笔法中对本事背景尽求完整流畅的归循和强调;无论旧事或时事,都明确继承汉魏古乐府的言志讽兴精神;内容到思想上把楚调女性化雅怨的哀婉缠绵演绎到位,即使是齐梁宫怨型楚调也剔除了六朝文气,以天然流畅笔势,使哀怨绵长而不直露过烈。叙述方式上也未舍女子代言体,只是会时而在深挚回环的自述中穿插客观叙述作交代补充,使诗中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委婉地寄寓文人伤怨。体制上多袭汉魏五言,字句畅达自然,同时也熟练运用三五七言等句式增强叙述的流动性,情势突转鲜明。所以,李白对楚调乐府的拟作既出自对汉魏乐府归复的追求,也包含了对历代文人拟作的研习和改进,并以自身的感怀志意和艺术表现力运笔其间,从而创作出既有传统汉魏乐府特色,又熔铸着太白才情的楚调乐府诗来。
①⑨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99页,第600页。
②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43—1045页。
③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32页。
④赵敏利:《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23页。
⑤邱琼荪:《楚调钩沉》,中华书局《文史》1983年10月第21辑,第168页。
⑥黄节:《汉魏乐府风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4页。
⑧⑩⑪王琦:《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4页,第283页,第173页。
作者:陶冉,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专业方向:汉语言文学。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