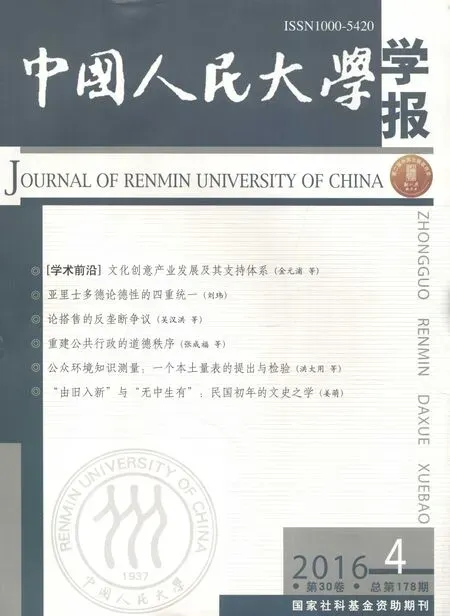论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的形成
刘小燕
论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的形成
刘小燕
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的形成,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考察:一是直接和间接形成的距离;二是政府与公众彼此地位不平等和信息不对称形成的距离;三是政府行为形成的距离和解释政府行为形成的距离。三个维度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交叉,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政府与公众距离的远近。政府及媒体组织、其他组织或个人的解释水平的高低也会对距离产生影响,这就要求不同的主体选择合理的解释水平来协调政府与公众的沟通距离。
政治传播;政府与公众;距离;心理距离;政治信任
有关政府与公众间的距离及二者间距离的形成、拉近等问题,是各国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政治传播学应当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重点解析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的形成过程。
一、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状态及形成
政府与公众间的距离在形成之前是一种距离状态,静态的距离状态串起来形成动态的过程,即政府与公众距离形成的过程。为论述上的方便,在讨论政府与境外公众间的距离时,其中的境外公众,既包括其政府,也包括其民众。当一方政府为行为主体时,另一方政府即为公众。某种意义上,在政府传播中,政府与政府可以视做互为主体,互为公众。
(一)距离状态与距离形成
在分析政府与公众间距离形成之前,先展示一下政府与公众间的距离状态。它可以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理解:就静态而言,是指一种距离状态;就动态而言,是指一种距离的形成。串起每一阶段的静态,则形成整个过程的动态。
静态: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距离状态,从无关到有关到关系密切(或关系恶化),即从无关联(谈不上距离)到有距离(距离远或距离近)。其间,会经过一系列的变化过程。当政府与公众彼此没有意识到对方存在时,双方关系处于无接触状态。此时,双方完全无关联,谈不上彼此间有无距离。尤其是在双方直接的行为互动和话语沟通之前,彼此对于对方尚处于旁观者立场,既无契约关系,又无伦理关系;既没有相互的利益缠绕,又没有彼此的情感卷入。如果一方开始注意到对方,或双方彼此产生了相互注意,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相互作用便随之开始,一方开始形成对另一方的初步印象,或彼此都获得了关于对方的印象。
动态: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距离,随着彼此间的信息沟通互动、利益诉求与回应(还包括国与国间的利益交换),使彼此间的关系亲疏(距离远近),处于不断变动之中。
对于一国政府而言,公众(无论国内公众还是国际公众)是无法选择的,政府一旦建立,意味着公众关系也就确立。从双方开始沟通互动(或直接或间接)的那一刻起,彼此就产生了直接接触或间接联系。这便是双方利益关系和情感关系发展的原点,也是彼此距离形成的起始点。
随着彼此的信息沟通、互动(及诉求呼应、利益交换)的深入和扩展,政府与公众间共同的愿望和利益、共同的心理领域、价值偏好、意识形态等也逐渐展现,它们与情感融合的程度相适应。
这里的利益需要从广义上理解,它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利益,也包括广义上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和战略意义上的利益,以及精神(或情感)意义上的利益。从利益、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情感无接触到深度重叠,意味着政府与公众间的距离从无到有。接触越浅,相互交集越少,距离越远;利益、价值观和情感相互交集越多,或重叠越深,双方距离越近。
我们将政府与公众间的距离状态或距离的形成,除了“无接触”状态(彼此间无任何关联,谈不上有无距离)外,分为四种距离状态:表面接触、轻度交集、中度交集和深度交集。表面接触体现的是,政府与公众间,无论是经济诉求、利益取向,还是价值观、意识形态、情感,均处于甚少接触状态,彼此的利益共同点甚微,所发现的共同心理领域极小。相反,矛盾或冲突远远大于理解和认同。这时,双方的利益距离和心理距离很远。轻度交集体现的是,政府与公众间,或者利益,或者价值观、意识形态或者情感,彼此的利益交集面较少,所发现的共同心理领域较小,双方的心理世界仅有小部分重合,也仅仅在这一范围内,双方的情感是融洽的,是可以有利益交换的。此时,双方的利益距离和心理距离较远。中度交集体现的是,政府与公众间,或者利益,或者价值观、意识形态或者情感,彼此已发现有较大的利益共同点及较大的共同心理领域,双方的心理世界也有较大的交集或重合,彼此的情感融合范围、妥协让步的空间相应较大。这时,双方的利益距离和心理距离较近。深度交集体现的是,政府与公众间,或者利益,或者价值观、意识形态或者情感,同大于异,彼此发现的共同心理领域大于相异的心理领域,彼此的心理世界高度(但不是完全)交集或重合,情感融合的范围也覆盖更广泛。不仅在利益上紧密相关,在理念认同上也逐步契合,你将对方看成是亲密伙伴,对方也将你看成是亲密伙伴。这时,双方的利益距离和心理距离很近。彼此距离远近,能否休戚与共,理念上的认同有时会超越经济诉求,意识形态一致往往超越利益取向。
不过,通常情况下,政府与公众间,只有少数情况或特殊情况、只有少数行为主体间方能达到深度交集状态,多数行为主体间大都处于较浅或轻度、中度水平。心理学告诉我们,人际关系双方心理世界完全重合的情况是不存在的。“无论人们的关系多么密切,情感多么融洽,也无论人们主观上怎样感受彼此之间的完全拥有,关系的卷入者都不可能在心理上取得完全一致。”[1](P288)政府与公众间的关系,是基于人与人的关系(但它又比人与人的关系复杂得多、宽泛得多),自然也具有人际关系心理距离的某些特征。同样,政府与公众之间,无论在利益、价值观、意识形态还是情感方面,不存在彼此完全重合的情形。无论政府与公众的距离多么近,联系多么密切,情感上多么理解,但是,政府与公众是两个世界,处于两个方面理解的基点。即,政府与公众是两种诉求的基点、两种情感的基点、两种价值取向的基点、两种意识形态的基点、两种利益的基点。政府与公众间只存在利益、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情感等在多大程度上相一致的问题,而不存在完全相一致的情况。
(二)距离形成的三个维度
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的形成,可以从三个维度考察:第一个维度:直接和间接形成的距离;第二个维度:政府与公众彼此地位不平等和信息(知识)不对称形成的距离;第三个维度:政府行为形成的距离和解释政府行为形成的距离。这三个维度中又有相互交叉的因素。比如,作为第三方的“解释政府行为”的解释说明,造成政府与公众间的距离即为间接形成的距离(或拉近或离间)。
第一个维度:直接和间接形成的距离。
直接距离:政府与公众直接互动[政府(官员)与公众的面对面互动、新媒体背景下拟态环境里直接互动](无中间环节)所形成的距离。
例如,2012年10月22日,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湾塘等村数百名村民,以该市一化工企业(PX项目)距离村庄太近为由,到区政府集体上访,并围堵了城区一交通路口,造成群体性事件。直到10月28日傍晚,一则简短信息的发出才标志着宁波反PX群体事件落下帷幕:“宁波市经与项目投资方研究决定:(1)坚决不上PX项目;(2)炼化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停止推进,再做科学论证。”有学者认为,具危险性的发展项目之所以激起民意强烈反弹,是因为民众不满官员只考虑政绩和升迁,危险和隐患却留在当地和百姓。《新京报》也发表社评,指出官方与民众沟通不足,才让宁波反PX事件闹大。对如此敏感、公众极度关注的项目,在立项之初就应用数据向公众解释说明,以免事件走向“民众受伤害,项目要下马”的双输结局。[2]民众通过上访而与政府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属于政府与公众的直接互动,由最初沟通对话的不充分到最后互相达成协议,才实现了政府与公众距离由远至近的调整。
间接距离:政府与公众之间间接互动(如通过大众传媒或NGO等中间组织)所形成的距离。对其中间环节应有更宽泛的理解,比如,一国(政府)与另一国(政府、公众)距离的间接形成,除了大众传媒(或广告)、智库或NGO等发挥作用外,还有第三国居中协调、调停(或居间的离间、挑拨),如代表政府的A与代表公众的B通过第三环节C间接互动。像广告作为“第三方”起作用的事件如,2008年7月,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由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AI)委托TBWA法国分公司制作的、利用奥运元素蓄意“辱华”系列广告,旨在配合西方国家杯葛北京奥运会。这组广告包括三个独立内容,分别以游泳、射箭和举重等奥运项目为背景,着力渲染中国囚犯被虐待。“大赦国际”授意“TBWA巴黎”随意甚至是恶意“诠释”中国,实质是在羞辱中国和奥运会精神。这组辱华广告很快在互联网上引发中国人民及海外华人的愤慨与谴责。事件最终以TBWA全球总裁凯斯·史密斯发出声明,向中国人民诚恳道歉收场。但该广告的制作与扩散,在当时无疑激化了中国与西方的紧张关系,扩大了中国与西方的距离和彼此不信任。
第二个维度:政府与公众彼此地位不平等和信息(知识)不对称形成的距离。
一是彼此地位不平等形成的距离。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理论*权力距离,是指社会成员对于组织中社会阶层以及权力、物资分配不均造成的不平等现象的接受或容忍程度。权力距离有大小之分,其大小用指数PDI(Power Distance Index)来表示。可以根据上级决策的方式(民主还是专制)、上下级发生冲突时下级的恐惧心理等因素来确定权力距离指数的概念。它是荷兰组织行为人类学和国际管理研究专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于20世纪末提出来的四个“文化维度”(Cultural Dimensions)之一,其他三个维度包括: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度与女性度。告诉我们,权力距离有大小之分,权力距离影响着社会成员之间(或者说权力占有者与权力非占有者之间)的沟通和互动行为。
高权力距离的社会强调对权威的服从和尊敬。在高权力距离文化环境下,权力是分等级的。某些群体比如贵族或者执政党或官员比普通民众拥有更多的权力。在高权力距离国家中,等级顺序严格,把他人视为对权力的潜在威胁,基于对他人的不信任,非权力合作难以达成。不同群体间的等级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掌权者享有特权,权力所有者和不占有权力者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无权力者与有权力者(或下级对上级)有相当的依赖性,或偏爱这种依赖,或抵制这种依赖(情感距离较大),不占有权力者(下级)不太可能与权力所有者(上级)直接讨论问题,更不会去反驳权力所有者(上级)。在高权力距离的环境下,权力所有者和不占有权力者(上下级)认为彼此之间天生就不平等,形成了等级制度的基础,组织机构的权力通常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权力所有者和不占有权力者(上下级)之间的联系是前者主动、后者被动,二者的差距巨大,上层人物享受特权较多。换言之,政府与公众间冲突较大,彼此间距离也较大。
而在低权力距离国家中,每个人应有同等的权力,等级是为了便利而设立的,有权与无权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和谐。等级差别被减少到最低程度,有权力地位的人应该尽量造成比他们实际上所拥有的权力要小的印象。处于不同权力地位的人相互信任,很少感到威胁。不占有权力者对权力所有者(下级对上级)的依赖性较小(情感距离较小),权力所有者和不占有权力者(上下级)之间更多地用协商方式,不占有权力者(下级)也容易与权力拥有者(上级)探讨并反驳权力拥有者(上级)的意见。在低权力距离的环境下,权力所有者和不占有权力者(上下级)认为彼此平等。换言之,政府与公众间冲突较少,彼此间距离也较小。
二是信息(知识)不对称形成的距离。信息不对称指交易中的各方拥有的信息不同。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中,一些成员拥有其他成员无法拥有的信息,由此造成信息的不对称。在这些活动中,社会成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和掌握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较充分者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者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不对称信息可能导致逆向选择*逆向选择,一般指交易的一方如果能够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使自己受益而对方受损时,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便难以顺利地做出买卖决策,于是交易难以顺利实现。。这一交易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在政府与公众间也有充分体现。本文在此论述的形成彼此距离之因素,既包括信息占有多少的不同,也包括知识拥有多寡的不同。信息(知识)不对称影响着彼此[信息(知识)充分拥有者与信息(知识)贫瘠拥有者]之间的沟通和互动行为。不言而喻,信息(知识)充分拥有者,沟通注意水平*沟通注意水平所评价的是沟通者投入沟通、对沟通过程起相互支持作用、使其自然持续的注意水平。参见章志光主编:《社会心理学》,30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亦高;信息(知识)贫瘠拥有者,沟通注意水平亦低。一般来说,沟通注意水平高的沟通者,不仅注意自己所发出的信息的指向性、准确性和对方的可接受性,而且对于对方的反馈过程也保持高度关注。因而,信息(知识)充分拥有者一方,能够较好地根据反馈调节自己的沟通过程,对双方的沟通形成良好的配合与支持,使沟通始终保持较好的互动状态和双方对应性,使彼此互动得以顺利延续。显然,此时,政府与公众间的心理距离也较近。相反,沟通注意水平低的沟通者,注意力往往会分散,发出的信息通常不能很好地与自己的沟通意图相对应,尤其是不能很好地注意对方的反馈和给予对方的沟通以充分的反馈支持。因此,信息(知识)贫瘠拥有者与信息(知识)充分拥有者的沟通很难进入状态,也往往缺乏应有的对应性,沟通过程很难顺利、自然地得以继续。此时,政府与公众间的心理距离也较远。
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尤其前者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组织,但彼此间沟通互动的具体执行者是作为个体的人(如前者有代表政府的政府公务员,后者或是独立的个体人,或是代表某一组织的个体人)。诚然,具体到某一情况下某一方面,代表政府的个体人未必就比代表公众的个体人拥有更多的信息(知识),如经验较少的公务员与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相比。总之,如果沟通双方难以保持较好的互动状态和双方(信息或知识上的)对应性和适应性,彼此形成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光电设备日渐趋于小型化、精密化和高性能化,使其成为可折叠的便于携带的产品.因此,对透明导电薄膜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进而对薄膜制备工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尽管AgNWs薄膜具有许多突出的优点,但是如何在高透光率下获得低的片电阻仍然是一个挑战,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AgNWs网络的电导性明显取决于AgNWs之间的连接.以传统方法制备的AgNWs网络存在较大的接触电阻和接触稳定性问题,不利于电子设备的精细化应用.为了降低片材电阻,研究人员提出了几种有效的AgNWs焊接方法,包括激光束焊接[17]、化学焊接[18]、电阻焊接[19]及冷焊[20]等.
第三个维度:政府行为形成的距离和解释政府行为形成的距离。
1.政府行为形成的距离
广义上的“政府行为”,包括政府施政行为和政府本体状态,它是政府传播的客观基础。政府整体素质的高低、行政能力的强弱、职能履行情况的好坏,以及政府的廉洁与否等,决定着政府绩效的好坏,决定着政府传播效果的优劣,亦检验着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的远近。
政府与公众间的距离,体现着政府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公众所认同和接受。如政府要履行自己的职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就要有所作为,而且,政府是掌管国家事务、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公共机器,其行为必然要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和评判。所以,政府履行职能(或者说公共行政)的过程,便是政府与公众间距离形成的过程;社会公众监督、评判政府行政行为的过程,也是政府与公众间距离形成的过程。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的职能和角色不断调整和转变,政府与公众间的距离也随之有远有近,处于动态变化中。
就国内而言,在政府所履行职能的施政过程中,尤其是在处理那些关系国计民生、关系民众切身利益问题的过程中,隐藏或不时显现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引发社会失衡、失业、失序、失信和动乱的潜在因素,都是社会公众评价政府时最为关注的问题。如果政府调控和治理不力,一旦这些因素被“累积”和“激活”,就可能成为破坏社会发展中人与人关系和谐的直接障碍,引致社会不稳定,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均没有尊严和安全感。这时政府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就是一个失职的、无能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公众间的距离不言而喻。
关于政府行为(既包括内政,又包括外交)形成与国外(或境外)公众的距离,因所涉事务和公众成分极其繁杂,也相对复杂,在此不赘述。
2.解释政府行为形成的距离
本文所说的“解释”,特指对政府(国家)行为的解释,包括政府自己(及政府的支持者、拥护者)对政府行为的解释,以及大众媒体和新媒体、他人(如智库、政客、专家学者等)、他国等对政府行为的解释。
解释政府行为,就性质而言,有政府自己的解释和他人的解释,既包括基于政府自身立场(或者较亲近政府立场)对政府行为的解释,也包括与政府立场相悖者(或者是对政府的某些理念、行为不认同者)对政府行为的解释,还包括“第三者”较为客观公允的解释。这三者的解释各有不同,其间的相互逻辑关系较为复杂。关键要看解释者“如何解释”、“在什么情况下解释”、“解释成什么”,还要看公众对政府是否具有既有立场(印象)或公众自身的接受取向如何。
基于政府立场的解释,就是政府政要及官员、智囊团、媒体、公共关系部门等,借助国内外大众传播媒体,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将政府(国家)适当的行为,传播(解释)给适当的公众,从而对培养公众对政府的亲和力、拉近政府与公众间的距离,起到积极作用。一般来说,政府均有一套成熟的公共关系体制,时刻保持着对媒体(乃至舆论领袖)的影响力,以便赢得媒体和舆论对政府的支持,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强化政府在公众中的黏合力。的确,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解释”政府(国家)的适当行为,也包括“解释”政府及时纠正、挽回自己的“不适当”甚至恶劣行为。应当承认,作为主体的政府,对其行为的解释或形象传播,具有唯美主义的行为特征,即追求的是基于政府好的行为,将政府美的一面抑或追求讨好公众的一面呈现给公众。诚然,出于某种需要(维护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政府自己的“解释”——且不说他人的“解释”——和政府的“行为”有时是相互脱节的。显然,没有政府真实行为支撑的“解释”是没有生命力的,没有心灵靠近的表面上“靠近”的距离或亲和力是靠不住的。
解释政府行为,从解释主体来说,应当既包括大众传播媒介对政府行为的解释,以及人际传播、公众传播等对政府行为的解释,又包括政府智囊团(智囊团是政府治国、施政的设计师,又是解释政府执政理念和施政行为、说明政府本体状态的参谋)、媒体、公关部门等专门机构作为话语传播者的解释。而后者对政府行为解释的运作和结果,最终还要通过传播媒介(传统媒体、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呈现给社会公众。
传播媒介对政府行为的“解释”,就是告知社会民众,政府“要做什么”、“正在做什么”、“做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以及政府为何做“某事”、做了“某事”的后果和意义如何。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解释”(无论是正能量的还是负能量的),是对“政府行为”的“扩音”和“放大”,即广告天下,意在尽人皆知,无人不晓。社交媒体、互联网、电视、广播、报刊等传播媒介都是政府行为的解释者。尤其是对于政府行为导致或与政府关联甚深的重大突发事件,不管是政府全心全意履职、善后,还是渎职、懈怠、不作为;无论是基于政府立场(或呈现真相、真诚面对公众,或刻意掩盖、回避负面事实,或顾左右而言他、推卸责任)的解释,还是逆于政府立场(或直击真相,或刻意抹黑、渲染,甚至借题发挥)的解释,或相对客观的第三者的解释,一经切身利益相关者、耳闻目睹者的人际传播、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其他国际媒体的传播,以及情绪受刺激后的公众传播,造成海内外尽人皆知,尽人皆议。这时,政府行为的解释者,除上述“解释”主体(媒体、智库、政客、专家学者)外,不但增加了“自媒体记者”,也增加了普通公众等有兴趣“解释”(议论甚至指责、批判)政府行为的解释者。此时,信息极其混杂,公众良莠难辨,政府基本上处于“被放在架子上烤”的境地,大部分公众做“壁上观”。就此,政府与公众间的距离令人忧虑。
二、“解释水平”影响公众“距离感”
政府及媒体组织、其他组织或个人的解释水平也会对政府与公众的距离产生影响。
(一)“解释水平”与“距离感”
“解释水平”的内涵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解释水平”是对事物的抽象认知,且认知水平有高有低。第二,“解释水平”分为“高解释水平”与“低解释水平”两类。“高解释水平”是指解释主体运用抽象的、核心的、主要的、连贯的话语方式来反映、解读与自身距离遥远的解释客体;相反,“低解释水平”则强调解释主体运用具体的、表面的、次要的、细碎的话语方式来反映、解读与自身距离较近的解释客体。第三,“解释水平理论”的应用体现为:解释个体对他人、对事物的态度差异及态度转变;解释个体对他人印象的产生;解释个体对他人的偏好以及支持程度上的差异。[3]
解释主体与解释客体之间的距离包括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与假设性,且这四类距离均隶属于心理距离的范畴。一般来讲,当事件与民众在时间、空间上更为贴近,或是与民众的关联度、相似度很高,或是事件发生的概率很大时,解释方式应是具体且注重细节的。相反,当事件与民众在时间、空间上相距遥远,或是与民众的关联度、相似度很低,或是事件发生的概率不大时,宏观且抽象的表述方式是较为合理的。事实上,“心理距离”在本文的语境内是一个中性的词汇,民众与事件之间存在心理距离是一种客观存在,而“距离感”则是体现解释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心理距离无法在根本上消除,但距离感是可控的,是可以消除的,而这恰恰需要科学的解释水平。因此,解释水平的高低,高解释水平与低解释水平是否被合理运用是影响政府与公众距离感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解释主体要有效控制公众的距离感,换句话说,应致力于在公众之间凝聚共识,既可以是对价值理念、制度伦理的共识,也可以是对某一具体的社会事件的共同认知,有助于维护社会的总体稳定。
政府传播的重要维度之一就是解释政府行为,而解释政府行为的主体是多元的,既包括政府自身以及政府所拥有的媒体,也包括其他大众媒体,相关人士(如政客、学者、智库)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等。解释政府行为水平的高低自然会影响公众对政府的距离感,而不同解释主体,鉴于其各自立场以及同具体事件的心理距离的远近,其解释水平是异质的且始终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可以说,高解释水平与低解释水平只是解释水平的手段,若要降低公众的距离感,根据具体情况合理运用这两个手段才是关键。
(二)政府及其媒体的解释水平对“距离”的影响
政府对自身行为进行解释是政府行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政府解释自身行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政府要对重大决策、未来目标以及长远规划进行解释,实际上,这是政府对自身施政纲领、方针、政策以及实现途径的宣示。一般而言,这些内容并不会迅速转化为现实,而是需要政府长时间的努力,且不一定会全部实现。另外,这些内容多半涉及的是国家层面,是从全体民众的角度进行考虑的,但与每位民众的具体需求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根据解释水平理论,政府需要采用高解释水平的方法,即抽象、宏观、连贯、突出核心与重点。比如,在汇报政府工作的会议上,政府代言人应该把自己的理念、目标与实现途径表述清楚,从而激发参与者的认知、态度直至情感上的共鸣,动员他们支持、配合政府工作的开展。所以,在上述情境中,经常使用口号这种特殊的话语表达方式。这是因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载体之一的口号,其内容言简意赅且富有力量,通过“询唤”作用对公众个体进行刺激、教化与暗示,把每一个无组织的、松散的公众个体建构为主动的、有强烈意志的主体,并使其产生对口号所蕴含意识形态的接受与认同,在理念上形成紧密联系,进而影响自身的思想与行动。
第二,围绕具体的现实问题,政府应当采取低解释水平的方式。现实问题往往千头万绪,与公众在时间、空间上有着明显的接近性,且问题发生甚至进一步衍变的概率也非常高,换句话说,现实问题与公众的切身利益有着紧密联系,现实问题相较于宏观的政策、目标而言,对公众的生产生活各个方面都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自然,也易受公众的关注。具体来讲,当前广受公众关注的关于“快车”、“专车”性质的讨论,前不久有关延迟退休的讨论等现实议题,事关广大公众的现实生活,倘若政府依然采用抽象、宏观或是“喊口号”的方式进行回应与解读,可以想见解释效果必然不佳。因为,公众面对这类具体的问题时需要的是具体的答案,先不论公众是否满意,至少是要让公众感觉“听得懂”的有“干货”的答案。所以说,面对具体问题时,政府在解释自身行为上应着重表明政府所做的具体工作(尤其要突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策略),以及日后打算。
距离的远近使关于事物及其背景信息的可得性和可靠性发生变化,距离越远,事物及其背景的具体信息越不可靠甚至不易得,而当距离靠近时,具体信息才变得详细、清晰、可靠。对于这一猜测,最直观的类比是当人们从远处看一大片不同种类的树时,它是森林,而当距离越来越近时,一棵棵活生生的树会变得越来越清晰。[4]诚如,距离远的信息不可靠甚至不易得,政府则抓住其精髓,在宏观上予以解释,而距离近的信息可靠且清晰,政府应当展示其细节,以打消公众疑虑,凝聚共识,赢得信任。实际上,政府合理运用解释水平理论的目的不是要缩短同公众之间的距离(因为有的距离是无法弥合的),而是要缩减同公众之间的“距离感”。假设政府总是用公众听不懂的语言来解释其行为,那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公众从“听不懂”的状态转变为“不愿听”的状态,形成固化的刻板印象,彼此之间的距离感越来越强,甚至会出现疏离感。也可以说,政府的这种解释行为是一种“政府角色的错位”,而其解释方式是一种新的“八股”。政府解释自身行为的根本目的是要赢得公众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包括利益认同、制度认同和价值认同等方面内容,其逻辑顺序是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政治认同的逻辑起点在于公民的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为公民政治认同提供了价值基础,是政治认同的关键,而价值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核心。[5]实现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也意味着政府解释水平要达到相应的层次与水平,归根结底,要求政府以合理的解释水平来缩减同公众之间的距离感,毕竟政府同公众之间的距离感小了,政治认同才有实现的基础,总的来看,距离感大小同政治认同高低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具体到中国,公众的整体文化素质虽然相对以往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囿于人口基数大,且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的公民文化素质在总体上还是参差不齐的。另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全面调整、改革的阶段,诸多社会矛盾易发多发。由此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应重视低水平解释的应用,这不仅符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而且也是对中国政府过去在解释政府行为上的回应。的确,中国政府以往采用了过多高水平解释,使得政府同民众之间出现了一定的疏离,而用具体且充满细节的解释正好可以对此进行中和。典型的案例如乌坎事件,该事件得以成功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能够虚心听取村民就土地使用、民主选举等有关实际问题的诉求,并在充分调研后给予村民细致、具体且合乎实际的答复,给村民吃了一颗“定心丸”,而不是一味地“说空话”、“放空炮”。当然,需要强调的是,高水平解释与低水平解释并无好坏优劣之分,二者的使用应结合具体情况,而不是厚此薄彼,偏向一方。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当前应注重低水平解释的应用也是综合了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的考虑。
就政府所拥有的媒体而言,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其作为政府工具的地位,自然,这类媒体解释政府行为的目的与政府解释自身行为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其对解释水平理论的运用应与政府保持一致。作为政府的“工具”,媒体应通过对政府行为的合理解释拉近政府同公众之间的心理距离,而不是“帮倒忙”。具体到中国,主要是指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媒体,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传播党的路线、方针和国家的政策、主张。当然,完成这一使命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并不是只有全文刊登领导者讲话、发表社论或是评论员文章之类。官方媒体以往较多地使用高水平解释,不仅语言上略显生硬,而且往往“不接地气”,不能很好地联系公众。若要拉近政府同公众之间的距离,促进政府同公众达成共识,官方媒体就应该调整解释水平,尤其是要向低水平解释倾斜,多讲动听的故事,多说公众听得懂的语言,让新闻报道有血有肉,务求直观、具体、生动、全面、深入。实际上,之前开展的“三贴近”、“走转改”活动就较好地践行了低解释水平的要求,也的确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各种媒体应以此为基点,灵活运用解释水平理论。
(三)其他组织或个人解释水平对“距离”的影响
无论是其他大众媒体,亦或是政客、学者、智库,乃至其他国家政府机构,在解释一国政府行为时都处在“第三方”的位置。首先,这一位置并不改变解释水平理论的应用原则,即政府行为同第三方的心理距离相近时,第三方会采用低水平解释;反之,政府行为同第三方的心理距离遥远时,第三方会采用高水平解释。其次,第三方采用低水平解释或高水平解释,本身也并无好坏优劣之分,采用何种解释关键还是要看同具体事件的适应性。最后,除了考虑心理距离,第三方采用何种解释水平往往蕴含着一定的目的。一般意义上,第三方的解释水平往往有两层目的:一是要捍卫事件的真相,二是借此表明自己的立场。政府及宣传媒体在解释政府行为时,很容易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因此可能(不管是主观刻意还是无意)造成部分失实。当然,第三方的解释行为也并不一定是真实可靠的,因为其行为背后是各种利益在驱动。
总的来讲,第三方对于政府行为的解释是必要的。一方面,第三方可以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对政府行为施加影响,监督、促进其不断改进,间接地辅助政府加强同公众之间的联系,缩短二者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第三方对于政府行为的解释也有助于其自身缩短同公众之间的距离,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增强自身的话语权。无论如何,第三方合理运用解释水平理论对于增强公众对其信赖程度是有帮助的。这样,公众同第三方之间的心理距离会越来越近,公众渐渐会对第三方产生一定黏性。这里,也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政府及传播媒体如何处理好同第三方之间的关系。假设在公允的条件下,政府及传播媒体若能同第三方在解释行为方面协调一致,自然会进一步缩短同公众之间的距离,增强彼此互信,反之亦然。需要补充的是,鉴于存在意识形态冲突或是根本利益矛盾,有些第三方不可能从客观公正的角度去解释政府行为,比如,日本政府因为《南京大屠杀档案》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扬言要减少甚至拒绝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缴纳会费。因此,判断政府行为合理合法与否的标准不单单是第三方的解释,公众也应对包括政府及其传播媒体、第三方在内的所有解释主体的解释行为都进行客观判断与评价,做到既不可轻信,也不能矫枉过正。
综上,本文从三个维度考察了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的形成,三个维度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交叉,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政府与公众距离的远近。政府及媒体组织、其他组织或个人的解释水平的高低,均会对距离产生影响,不同的主体要选择合理的解释水平来协调政府与公众的沟通距离。此外,政府及其传播媒体也应试图与第三方在解释行为方面协调一致,从而缩短同公众之间的距离,增强彼此互信。
[1] 章志光:《社会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2] 沈泽玮:《宁波民众反PX成警民冲突》,载《新京报》,2012-10-28。
[3] 黄俊、李晔、张宏伟:《解释水平理论的应用及发展》,载《心理科学进展》,2015(1)。
[4] Dhar,R.& E.Y.Kim.“Seeing the Forest or the Trees:Implications of Construal Level Theory for Consumer Choice”.JournalofConsumerPsychology,2007(2);Trope,Y.& N.Liberman.“Temporal Construal”.PsychologicalReview,2013(3);Wakslak,C.J.,Trope,Y.,Liberman,N.& R.Alony.“Seeing the Forest When Entry is Unlikely:Probability and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Events”.JournalofExperimentalPsychology:General,2006(4).
[5] 孔德永:《动态理解政治认同与政治稳定》,载《思想理论教育》,2014(9)。
(责任编辑 林 间)
Formation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ublic
LIU Xiao-y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The formation of the distanc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ublic is a process of which the static states are united and changed into the dynamic state,which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the distance stage form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the distance state formed by the inequity status and asymmetry inform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ublic,the distance state formed by the governmental behaviors and the explanations on these behaviors.These three distance states are different from and mixed with each other,and the distanc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ublic changed with one of them.In addition,the explanation ability of government,media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or individuals exert impacts on the distance relation,which needs to be adjusted with suitable explanation by proper subjec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government and public;distance relation;psychological distance;politics trust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府话语权与国际规则之关系研究”(14BXW022)
刘小燕: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