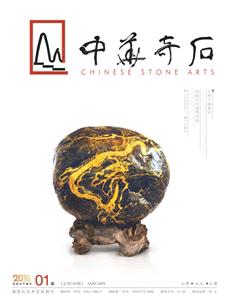毕减索大象无形

顾默修,影像艺术家,旅法多年,目前工作生活于上海,业余爱好收藏。
毕减索者,盖毕加索创作后期由繁而简,由绚烂而至平淡之意。人生由做加法,而至做减法,赏石亦是如此。
很多石友反映,当初之所以会爱上玩石头,就是因为某次机缘巧合,被一块巧夺天工,活灵活现的石头给吸引了。在刚入门玩石头的阶段,最爱就是象形石。不论什么样的石头放在眼前,总能从它身上看出个形状,老虎、狮子、小鸟、小金鱼,要不就是花纹图案像字形或者人形,百看不厌,其乐无穷。人们对此津津乐道,既可以获得同好的称赞,也能够获得切实的收益。几乎所有的石友手上都还保存着一两块当初入门时心爱的象形石。
慢慢地,玩石头的时间久了,随着鉴赏能力与审美能力的提高,渐渐觉得这些象形的石头虽然有趣,但在味道上总有一些缺憾和不足,有些人物、动物类的象形石,在肖似方面,已近完美,但总觉得越是近于某种固定的对应形象,距离隽永研美的意味越是遥远,这种缺憾和不足,到底是什么呢,却又说不清,道不明。这种浅切直白的内心感受与认知,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艺术审美实践中的核心问题——形。
要在具体的赏石实践中讲清楚“形”这个问题,先要弄清楚“形”这个概念下几个相互关联又各自区分的向度:
一、形态
这个层面包含形状、色彩、纹理、图案、质地、尺寸等因素。
很多人都知道北宋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的几句: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有些石友就把“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两句与“不求形似,但求神似”的观点等同起来,这是对这两句诗的一种误读。苏轼是说不能仅仅以形似来论高下,但并没有否认形似的重要性。
据苏轼《怪石供》与《后怪石供》记载,在1082年前后,当苏轼在齐安江边游玩的时候,他被江水里美丽的石头所吸引,就用饼向江里游泳的小孩子做交换,那段时间他总共收集了二百九十八块这样的石头,其中有一块小石头看起来像一只老虎,有活灵活现的嘴巴、鼻子和眼睛。这块虎石被苏轼当作群石之首,他将两百五十个这样的石头放在一个古铜盆里,最后把这些石头送给了庐山佛印和尚。可见,苏东坡这样的大文人,也玩过动物类的象形石,并将小石头放在承具,也就是铜盆中以建构微型景观。
因此,一块石头,即便是象形的,也须以其自身的大小、高低、长短、曲直,来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形状,给人以虚实、隐显、聚散、起伏、纵横、顿挫等不同的内心感受与审美认知。从而引发情绪上的触动,或崇高悲壮,或温柔缠绵;或心如止水入禅定,或人面桃花沐春风,最终达到心理上的审美愉悦。
二、形式
上述话题,恰恰与西方艺术理论中所谓的“有意味的形式”暗合。这就牵涉到第二个向度,形式。
Form(形式)一词,纯是西文的,“形式”这两个汉字,是对它的翻译。我们中国人是不讲“形式”的,但不代表我们没有“形式”的概念,我们在形神论中用“形”来表达类似的观念,虽然这两者不可以直接化约对等,在艺术与美的问题上,西方讲求“有意味的形式”。因此,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形态上的美感问题,而是关乎心理认知的美学问题。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并不是简单机械的形式排列与组合,而是经过诗人审美认知处理和筛选过的一组有意味的形式。这样的一组名词,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意象,以及这种意向的关系和组合,我们视之为有意味的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就是一切艺术的共同本质。
在具体每块不同的石头中,线条、色彩、纹理及其自身空间存在,以特定的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的组合关系,此时石头的各部分、各素质之间的这种特定方式排列、组合起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那么它便主宰着这块石头的“作品属性”,并最终唤起面对这块石头时的受众的内心审美情感。
三、形神
形神论是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占有统摄性的理论。
前面说到苏轼的“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意思是说,如果画画只能画得像,那就跟儿童的水平差不多;如果做诗只能停留在字面的意思上,那一定不是一个好的诗人。儿童由于受到自身生活阅历与知识经验的限定,看画只能看到像与不像的层面上,而认识不到“形”更深一层的美学内涵。
赏心者为上,悦目者为下。中国传统艺术追求的不是停留在形的描摹上,而是必须上升到作者的思想志趣与哲学理念,也即是神。以神统形,以形写神。正如顾恺之所说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就是说,给人物作画的关键在眼晴里。中国艺术有这样一个原则,就是不似似之。如果太相似,就显得庸常而刻板,完全不相似则脱离现实本身。这一原则的最高标准,在于似不似之间,既不具象,又不抽象,徘徊于若有若无之际。
运用这一原则的关键,涉及到赏石实践的具体品鉴活动。也就是说,如何鉴赏一块石头,并不在于这块石头的像与不像,而在于如何对待“形”的态度上。形为神寄,神由形出,以神统形,以形御神,形神结合,这才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地。画已尽,而意不止;笔虽止,而势不穷。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厘清了这几个向度的问题,最后让我们回到象形,也就是形似这个问题上来。
这个问题看似容易掌握,形似不似,就是像不像的问题,像什么,就有看点,值钱;不像什么,就没有看点,不值钱。事情如果就这么简单,有些石友也就不会有上述困惑了。我们不妨把目光放长远一些,对于像不像的问题,不要仅仅把像不像的对象放在那些具体固定的动物和人物身上。
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Schafer)根据中国古代文人的趣味偏好将其所赏玩的石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薛爱华称作巴洛克趣味式的,其对象是那些“貌似自然”(pseudonatural)的石头,第二类薛爱华称作原始主义趣味式的,这类石头往往呈现出具有貌似人工的轮廓外形和花纹。根据薛爱华的观察,更受欢迎的,是那些巴洛克趣味式的石头。
中国人对石头的欣赏,暗含着一种轻视人工秩序的哲学趣味和美学判断。在这种判断下,自然无为,是为高;人工机巧,则等而下之。这里的人工,不是指人为的去加工,而是指一种貌似人工的外在形态,太过酷肖的石头,则机巧太重,有违天心。在中国人眼中,石头身上体现了自然的秩序,自然反映了天心,它讲求的是无为和顺应。而人的秩序依赖知识与经验,对理性孜孜以求,自然的秩序则是无拘无束,水到渠成。对石头的欣赏,就是以顺应为美,以无为为上,摆脱知识的束缚,拾趣于理性之外。中国人喜爱石头,不是寄情于一个外在的物,而是要通过一块石头,观照自然,体味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