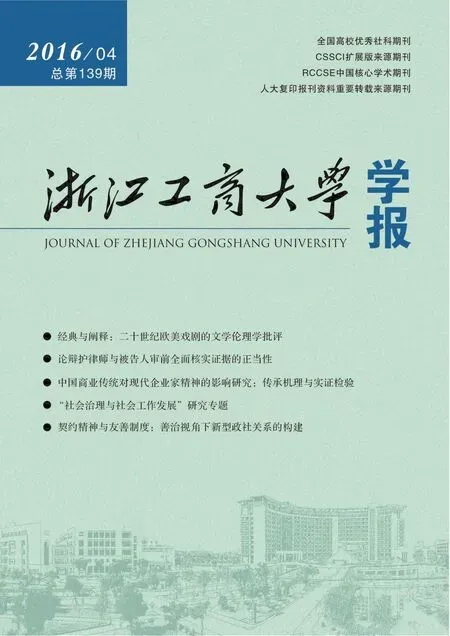论品特剧作《情人》中的自由意志与“幽会游戏”
刘红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外语学院,武汉 430073)
论品特剧作《情人》中的自由意志与“幽会游戏”
刘红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外语学院,武汉 430073)
哈罗德·品特于1963年创作的剧作《情人》是一部关于婚姻伦理反思的作品。理查德和萨拉夫妻间假扮情人的“幽会游戏”是这部作品中的主要戏剧情节,是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殊伦理语境下人们所持有的两性/婚姻观最为生动、客观地写真。通过“幽会游戏”这一“戏中戏”的表现手段,品特极力展示导致“情人现象”发生的本质原因,即人的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共存的两面性本质。两人试图逾越婚姻的欲望成为危及他们婚姻关系的闯入者。游戏中,两人完全被兽性因子所主导,意志冲突中自由意志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透过“幽会游戏”的表面,可以看到游戏下面掩藏的本质就是如何进行伦理选择。与此同时,剧作家也指出“婚外情”对于健康家庭和婚姻生活带来的危害性。
文学伦理学批评;《情人》;幽会游戏;伦理环境;自然意志
“品特式的”(Pinteresque)是一个用来概括英国当代戏剧家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1930—2008)戏剧创作所具有的独特形态的词汇。其作品主题的多元性以及艺术表现手段的丰富性相辅相成,构成了“品特式的”独特戏剧艺术,使得他的戏剧创作能够独立于当代英国“主流”戏剧,拥有很高的辨识度。在他的作品中,直观的艺术呈现远甚于主观的道德说教,体现出文学的教诲功能以及作家强烈的责任意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品特戏剧创作中的题材主要是取自于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婚姻不忠的社会现象,对于这一现象的关注体现出他对于当时因受“性解放”运动影响而出现的异于传统婚姻及性伦理的思考。
1963年创作的《情人》(TheLover)是品特第一部这类题材的作品。从这部戏的剧名里,人们似乎能够轻易且精准地获悉作品关于“婚外情”的伦理主题。但是,随着剧情的逐步推进,观众们开始体会到“情人”一词的歧义和复杂性。整部戏里,除了理查德和萨拉夫妻之外,舞台上并没有看到由第三个演员扮演的“情人”出现,剧中所谓的“情人”原来只是这对夫妻在家中“幽会游戏”中各自扮演的“角色”。如此的情节设计大大出乎观众预料,也因此剧评家迈克尔·比林顿曾评论说:“《情人》是很令人费解的一出戏”[1]。对此,还有些观众因无法理解这对夫妻违背常规的行为,感叹像是经历了一次强烈的“道德冲击”[2]。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这对夫妻会在自己的家里假扮情人幽会?这场“幽会游戏”背后又蕴含着哪些深层次的意义呢?由于“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3],因此,我们可以从伦理视角出发,梳理辨析这部作品创作的伦理环境,阐释“幽会游戏”中人物身上所表现出的斯芬克斯因子共存本质,从而找到合理的解释。
一、“荒诞”或“真实”的“幽会游戏”?
《情人》这部剧作有其“荒诞”的一面,但更有其“真实”的一面。剧中有关萨拉与理查德夫妻二人取悦于扮演幽会中各自“情人”的剧情与真实生活相去甚远,无疑是荒诞的。然而如果从作品创作与接受的伦理环境来看,这部戏中的“幽会游戏”更像是20世纪“放纵的60年代”人们所持有的两性/婚姻观最为生动、客观地艺术呈现。
《情人》这部戏的荒诞离奇从开场时男女主角的一段对白就初见端倪。理查德和萨拉是住在英国温莎市郊的一对结婚已有十年的夫妇。萨拉是一位家庭主妇,理查德在伦敦上班,每天早出晚归往返于市区办公室和郊外居所。幕开启时,观众们可以看到舞台上萨拉身着鲜艳得体的衣裙,正在客厅里清扫烟灰缸。理查德走到门前,拿起柜子上的公文包准备外出上班。临出门时,他面带着微笑与萨拉亲吻道别。这一场景是住在英国郊区再普通不过的中产家庭的日常生活场景。此处,品特设计的这个非常典型的家居场景,使得剧作里的人物可以被锁定在一个观众熟知的社会语境中,也能够让观众们很快产生身临“真实生活”的感觉。
但是,当观众听到夫妻两人的第一段对话之后,眼前原本熟悉的日常生活场景变得有些异样:
理查德:(和颜悦色地)你的情人今天来吗?
萨拉:嗯……
理查德:几点到?
萨拉:三点。
理查德:你们打算一起出去……,还是待在家里?
萨拉:啊……打算就待在家里。
理查德:我还以为你们要去看那个展览呢。
萨拉:我是想去看看那个展览,可……可又一想,还是和他待在家里好。
理查德:噢。好了,我该上班去了。(他走向门厅,戴上礼帽。)他会待很长时间吗?
萨拉:嗯……
理查德:大约……到六点,差不多了吧。
萨拉:差不多。
理查德:下午玩的开心。
萨拉:会的。
理查德:再见。
萨拉:再见。
(理查德打开房门,走了。萨拉继续打扫房间。)*本文中的《情人》引文均出自Harold Pinter:Plays Two. London: Faber and Faber,1991.中文译文均参考哈洛德·品特著,秦亚青,金莉译:《情人》,载《外国文学》1986年第10期,下不另注。[4][5]
这对夫妇一天的生活竟是如此开始的!这样的开场白显然出乎观众的预料,所造成的悬念为之后的故事情节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观众的好奇心被有效地调动起来,迫切地想要知道后面还会有怎么样的好戏。晚上,理查德下班准时在六点回到家中。晚饭之前,夫妇两人坐在客厅里,边喝着酒边聊着天。此时,理查德再次问到萨拉下午与情人约会的情形。当他问萨拉在幽会的时候,是否想过当时他正在办公室累死累活地工作着,萨拉却反击说那种场面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我知道你没在办公室,我知道你和情妇幽会去了”[5]。
从剧中理查德和萨拉夫妇这对夫妻的对话中,观众发现他们两人不仅都有婚外不轨行为,而且心知肚明对方的不忠诚行为却仍能坦然面对,放任另一半出轨的行为,甚至把它当作笑料,互相调侃。对于妻子在自己外出上班的时间居然要在自己的家中与情人幽会,理查德非但没有表示出任何吃惊或愤怒,而且还显得非常大度,“和颜悦色”地予以接受并祝福。在许多观众和批评家看来,这样的故事情节是如此地荒诞,难以置信。
的确,从传统道德的角度看,“婚外情”无疑是不道德的行为,因此,偷情通奸之类的事情本该是偷偷摸摸的行为,是无法摊在桌面上公开谈论的,更何况是夫妻之间。难道这是一个不正经的人家?如何理解这段开场对白呢?
二、“幽会游戏”与“性解放”的伦理环境
理查德与萨拉之间“坦诚”面对对方“婚外情”的情节设计看似荒诞不经,令人费解,事实上,却以戏剧艺术的形式生动地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的特殊伦理环境,即在“性革命”运动中许多人对两性/婚姻伦理关系的新看法。
“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3]作为一种能够直观反映人类不同时期社会文化现象的艺术形式,戏剧作品创作和接受的特定伦理环境及其伦理道德观念的考量是至关重要的。
“性革命”一词出自于西方“性革命”运动的理论奠基人威廉·赖希于1945年出版的英译本《性革命——走向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一书。书中赖希提出的“生活幸福的核心是性欲的幸福”“男女两性基于性吸引力的感情结合”等命题和看法成为20世纪60年代“性革命”思潮的理论基础。
赖希整个“性革命”理论就是论证人类满足自然的需求的重要性,呼吁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享受自己的欢乐,并进一步把这种人的自然需求归结为主要是性的需求,认为人只有通过性行为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6]268,因此,人们应当坦诚地对待它,维护自己的性权利。继而,他提出若想真正实现性需求,人们将会面临许多障碍,其中,当今的婚姻制度就是第一个障碍。他认为“婚姻就是一种性关系,不论有无结婚证书”[6]285,批评现有的婚姻制度充满了强制性。与此同时,他又提出应该正确看待婚外性生活的问题,认为“当一对夫妇被禁锢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之中,当他们根本无法在自己的配偶那里获取真正的性快乐之时,唯一的出路就是或明或暗地在婚外寻找新的性伙伴,即在新的‘红颜知己’那里获得性快感”[6]287。
《情人》中无处不在的“情人现象”以及理查德和萨拉夫妻间“幽会游戏”的戏剧情节设计,正是赖希有关“婚姻制度”和“婚外情”观点的艺术再现。结婚十多年之后,理查德和萨拉的婚姻已经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但也发现在婚姻之内他们已经再无法轻易从对方那里获得真正的性快乐,于是决定选择过一种“双重生活模式”。特别之处在于,他们没有去在婚姻之外寻找新的性伙伴,而是选择在家中扮演各自的情人幽会,营造了一个充满性诱惑的情景,以此重寻久违的激情欢愉。就如剧中乐此不疲于幽会的萨拉所感叹,“一切都是如此美妙、舒坦”[5]。婚姻之中找不到的性快乐,萨拉却在假扮婚外情人的游戏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值得关注的是,在赖希的专著中,他特别强调,不能把人们的“婚外情”与强奸、嫖娼等混为一谈,竭力反对在性问题上的随意性,反对“将婚姻变成交易,将两性变为杯水”,反对性混乱和性犯罪[6]284。但是,在“放纵的60年代”里,赖希为实现性需求所提出的各种措施却是被一些人肆意曲解的基础上加以接受的,把赖希关于实现性需求的设计歪曲成一种“杯水主义”“纵欲主义”。社会上风行的“新情爱规则”对性的定义首先是功能性的、情欲的和心理的,性的表达无须束缚也不必有所顾忌,只要不伤及他人即可;每个人,无论妇女还是男人,都是自由的,都可以做其认为是好的事情,而且不会受到社会的责难,对性行为不再有什么责任的要求,在床上,只要情人们你情我愿,就不会有什么不妥。
身处这一特殊时代之中,品特敏锐地观察到了社会上这种“纵欲主义”倾向的危险性。在《情人》一剧中,他通过理查德之口表达出来。当萨拉调侃说他在上班时间其实也是去和情妇幽会时,理查德马上辩解道,“什么情妇?……我哪有情妇,我和一个妓女混得挺熟,可我哪里有情妇啊,妓女和情妇可是有天壤之别的”[5]。在他看来,妓女只代表着及时行乐,“不值一提。上车下车空里随叫随到的东西,根本没啥深交,……妓女聪颖不聪颖有什么关系,充其量不过是个妓女,是那么种东西,要么叫你满足,要么叫你不痛快,……今天或许叫人满足。明天么……?谁也保不准”[5],她们仅仅意味着纯粹的性行为、“性欲”发泄。由此可见,当我们将《情人》这部戏剧创作和接受时的特殊伦理语境作为理解作品的重要前提时,也就不难理解这部作品所谓“荒诞”的情节的真实性了。
三、“幽会游戏”与自由意志
在《情人》这部戏中,理查德和萨拉夫妇过着富足的、精致的中产生活,但其生活模式是被精准地“设定”好,夫妇二人之间由于缺少正面的亲密交流和沟通,每天早晚的迎送吻别也早已变得“程式化”和“礼节式”,没有任何新鲜感。为了消解婚后生活的单调乏味,他们决定选择在自己家中假扮情人幽会,试图改变这一婚姻现状。他们这种“双重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一种伦理选择。选择之后,他们各自原有的伦理身份以及伦理关系均发生了变化,由丈夫/妻子身份转变成“情人”身份,普通的夫妻关系也转换成了特殊的情人关系。
理查德和萨拉夫妇在“幽会游戏”中的“角色跳转”扮演过程则体现出人的两面性本质,即“斯芬克斯因子”共存本质。“斯芬克斯因子是用来解释人在经过伦理选择之后仍然善恶并存的术语”[7],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两部分构成。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婚外“情人现象”的产生“主要来自于个体的道德自律与情感失控之间的冲突。道德自律是人性因子中理性意志发挥作用的体现,而情感失控则是兽性因子中自由意志没有得到抑制或约束的结果”[8]。剧中理查德和萨拉主要被兽性因子所主导,意志冲突中他们的自由意志起到关键性作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这种强烈的自由意志主要通过游戏过程中“换装”“击打非洲鼓”以及“角色跳转”等戏剧策略得以充分表现的。
萨拉是一个“双面人”,既是一个日常生活里的“贤惠妻子”又是一个“幽会游戏”中的“放荡情妇”。在伦理层面上,她的两面性则是“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共存的典型例子。萨拉身上的两面性首先从她在两个不同场合中的“衣着装扮”的细节中体现出来。身为理查德的妻子,萨拉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一切均是按照为妻之道的伦理规范行事,表现出其理性的一面。每天清早,穿着“一身色彩鲜明而又优雅合体的衣服”的萨拉会在丈夫出门之前,就已经开始忙着收拾整理家。傍晚时分,她又会提前准备好晚餐,等待着丈夫下班回家一起享用。因此,萨拉是理查德眼里一位完美的妻子形象,高雅端庄,勤快贤惠,衣着优雅合体,就如理查德曾夸赞她说的,“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你很美……和你在一起,我感到骄傲。……有你这样一个妻子,挎着我的胳膊从大街上走过,我这脸上多光彩。看着你的举止言笑,行走,弯腰,坐着不动,听着你自如地应用时髦的词汇,欣赏着你巧妙娴熟地调遣最新最地道的语句,感受着别人因此而对我产生的妒忌,体会着他们对你好心好意的殷勤和心怀叵测的阿谀,回味着你拒人千里之外的庄重典雅,知道你是我的爱妻,真叫我心里充满了美滋滋的满足”[5]。
然而,当丈夫出门上班之后,萨拉立刻换上一件胸口开得很低的黑色紧身衣,脚蹬一双高跟鞋,性感迷人。在与情人幽会时,我们看到萨拉的装扮瞬间发生了变化,身份也由稳重得体的家庭主妇摇身变成放荡不羁的情妇,衣着暴露,举止妖艳放荡,其行为举止更多地是被她身上的自由意志所控制。
在“幽会游戏”这段虚拟的婚外情境中,舞台道具“非洲鼓”有着深刻的伦理寓意,象征着萨拉和理查德夫妇试图挣脱道德婚姻束缚的强烈愿望,彰显出两人最原始的、本能冲动的欲望。“幽会游戏”中,由理查德装扮的情人麦克斯进门后,萨拉最初并没有表示出任何欢迎或亲热的举动,而是冷漠地转身坐回到沙发上,翘起二郎腿。麦克斯则慢慢地走向沙发,试图靠近萨拉。萨拉再次躲闪开,起身移坐到左前方一把矮椅子上。见此情形,麦克斯没有再坚持,而是朝门厅的柜子走去,从柜子里拿回一面锥形的非洲鼓放在沙发上,自己则站在沙发前。坐在沙发上的萨拉仍然没有任何回应,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然而,当麦克斯拿起这面“非洲鼓”敲打时,萨拉立刻像是换了一个人,开始变得异常地兴奋主动起来。观众可以看见:
萨拉的食指划过鼓面,朝理查德的手移过去。她猛地在他手背上抓了一把,又把手抽回。接着,她用五个手指交替击鼓,一面敲,一面朝理查德的手移过去。萨拉的手停下来,食指插在理查德的手指缝里摸弄着鼓面。理查德两腿绷紧,手使劲抓住萨拉的手。萨拉想把手挣脱,两人的手指搅在一起,在鼓面上弄出很响的声音。[5]64
这段描述人物细节动作的舞台提示语,非常形象地将萨拉和理查德体内兽性因子中原始欲望表现出来。“非洲鼓”急促的敲击声预示着萨拉和麦克斯两人体内压抑许久的原始欲望试图摆脱社会文明束缚的冲动。由于日常的婚姻生活平淡无奇,因此在虚拟的婚外情境中,两人内心的激情欲望迸发出来,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随着鼓声节奏逐渐加快,舞台上萨拉与麦克斯两人进入游戏状态,开始多次角色变换的游戏。两人的角色在“施虐”与“受虐”“顺从”与“控制”之间不断地发生着转化,频繁的“角色跳转”使得两人强烈的原始欲望更加彻底地得以释放,自由意志进一步得到彰显。
麦克斯先假扮成一个陌生人试图勾引并以强暴为威胁,而萨拉反抗说自己正在等丈夫。此时,萨拉宣称自己已婚的身份状态显示出这场游戏违反社会常规的特性,也更具刺激性。随后,麦克斯又装扮成公园管理人员,玩起了“英雄救美”游戏,将萨拉从那个无赖手上解脱,并把她带进一个安全的小屋。之后,他们重新坐回到沙发上开始新的游戏。麦克斯又变回到强势形象,逼近萨拉。萨拉试图离开退出游戏,但是麦克斯却威胁说,“你走不了。小屋上了锁,这里就咱俩,你可算是中了圈套了”[5]65;萨拉慌乱无助地喊道,“中了圈套?我是有夫之妇,你不能这样对待我”[5]65,这一刻,麦克斯变得冷酷无情。戏中的这些变化确实很古怪,很难让人理解,但是两人却都忘乎所以,尽情投入其中。
这出充满着“性幻想”的“角色跳转”游戏,在两人“躲藏在茶桌下”的情节中到达高潮。此时,舞台上,长时间的沉默。这段情节没有一句台词,只有一大段舞台提示语。当麦克斯逼近萨拉时,“萨拉急忙走到桌子后面,背靠着墙站着”;麦克斯“走到桌子另一边,一手提着裤子,弯下腰,从桌底下朝她爬过去。他消失在天鹅绒桌布底下。沉默,她盯着桌子底下。从观众席上看不见她的腿。他的手摸上了萨拉的大腿。萨拉四下张望,面呈痛苦状,她咬紧牙关,喘着粗气,慢慢沉到桌子底下,直到完全消失”[5]65。这一大段舞台提示语却强烈暗示出两人已经发生的行为上出轨。
游戏中的“角色跳转”让观众经历了一次“沉浸式”的体验。尽管舞台上演戏的演员没有变化,但是“幽会游戏”中急速的角色跳转变化,使得萨拉和理查德两人真实身份变得的模糊不清。舞台下的观众不得不在“萨拉”“理查德”“麦克斯”“道拉瑞斯”“玛丽”等不断变换的名字中努力辨识真真假假的角色。观众开场时如临“真实生活”的幻觉很快被打破。在此过程中,他们渐渐察觉,舞台上发生的一切并不是真实生活情景,只是一出戏。由此,剧作家得以成功地引导观众从虚构的戏剧情景中抽离出来,进而对剧中“婚外情”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判断,从中深刻体察到游戏婚姻危险性的道德警示。
四、结 语
每一个作家的创作都离不开他/她所生活的时代,他们个人的经历与体验对于其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情人》这部作品既是品特对于自身生活的审视和反思,更是他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特殊伦理语境下社会变迁的积极回应。创作《情人》的前一年,即1962年,品特与BBC女记者琼·贝克威尔开始有了婚外情。贝克威尔曾在她的自传《床的中心》中讲述了他们这段长达7年的恋情。她回忆道:“60年代的生活氛围宽松、自在,是一个适宜发生一些风流韵事的年代”,但是他们决定“对彼此的另一半隐瞒这一切。只要两人不彼此伤害或不危及彼此的婚姻,一切都好办”[9]。由此可见,作品中呈现的婚外“情人现象”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流行风尚,许多人对此抱以“无关道德”的评断。
在《情人》一剧中,理查德与萨拉夫妇被禁锢在淡而无味的婚姻之中,当他们根本无法在现实婚姻中从自己的配偶那里获取真正的性快乐之时,选择在家中假扮情人幽会,希望在充满“性幻想”的游戏中寻找新的性伙伴,以期能够彻底释放他们的原始欲望。透过“幽会游戏”的表面,可以看到游戏下面掩藏的本质就是如何进行伦理选择。品特在《情人》中并没有对婚外出轨行为做出“对”或“错”的道德判断,而是在创作中通过“幽会游戏”“戏中戏”的表现手段极力展示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本质原因,即人的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共存的两面性本质。全剧并没有出现实质上的越轨行为,两人试图逾越婚姻的欲望成为危及他们婚姻关系的闯入者。游戏中,两人完全被兽性因子所主导,意志冲突中自由意志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正是“由于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以及所体现的对立统一原则决定了伦理选择的永恒价值,文学经典才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10]。健康的婚姻必须具备理性需求和价值取向。“婚外情”势必会危及健康的家庭和婚姻生活,一旦听凭原始欲望的肆意,必将导致在理性基础之上建立起的各种道德规范被摧毁。正是因为兽性因子的存在,所以才需要人性因子的理性和职责对其控制,从而使得健康婚姻价值取向的伦理意识得以存续。
进入2l世纪后,“情人现象”在高速发展的中国也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这种所谓流行的社会风尚对已有的家庭和婚姻伦理秩序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和破坏性,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之认真地反省、深思。时至今日,《情人》这部深受中国观众欢迎的戏剧作品仍能起到道德警示作用。
[1]BILLINGTON MICHAEL.Harold Pinter[M].London: Faber and Faber,2007:143.
[2]TAYLOR-BATTY MARK.The Theatre of Harold Pinter[M].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2014:70.
[3]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2-22.
[4]PINTER HAROLD.Harold Pinter: Plays Two[M].London: Faber and Faber,1991.
[5]哈洛德·品特.情人[J].秦亚青,金莉,译.外国文学,1986(10):59-70.
[6]威廉·赖希.性革命——走向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M].陈学明,李国海,乔长森,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7]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76.
[8]刘红卫.自由意志、理性意志与激情之爱——《背叛》中“婚外情”的伦理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13(6):26-33.
[9]BAKEWELL JOAN. I was Pinter’s Other Woman[N].Mail Online,2010-01-16.
[10]吴笛.追寻斯芬克斯因子的理想平衡——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J].外国文学研究,2014(4):19-23.
(责任编辑杨文欢)
An Ethical Interpretation of Free Will and Game-Playing in Harold Pinter’sTheLover
LIU Hong-wei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Wuhan430073,China)
Harold Pinter’sTheLover(1963) arouses reflections on the marital ethics. As the main plot of the play, the game-playing between Richard and Sarah in their house demonstrates literally the social and ethical transformation during 1960s—1970s. By using the artistic technique of role-switching, Pinter intends to decode the fact that Man is an existence of Sphinx factor, composing human and animal factors, which causes the extramarital love. During the erotic game, the couple is controlled by the animal factors, and their free will overcomes the moral obligation within the ethical conflict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essence of game-playing is how to make the ethical choice. At the same time, the negative effects from the extramarital love is also emphasize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TheLover; game-playing; ethical situation; free will
2016-03-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13&ZD12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英国20世纪戏剧研究”(09BWW011)
刘红卫,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英国现当代戏剧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
I106
A
1009-1505(2016)04-00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