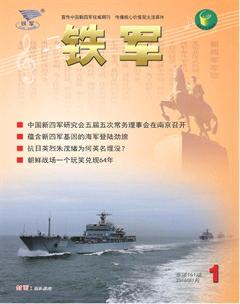相依为命 激情感怀
朱素

我和晓峰,从战争中走来,至今已有70个春秋。我们结为夫妻,也已63个年头,是老夫老妻老战友了。
70年间的风雨坎坷中,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相依为命。年轻时,我们在战场上团结奋战,一致对敌,直到胜利。我曾写过《初踏战争岁月的医务战线》,记述上世纪4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的烽火岁月,我俩在一条战壕里战斗,在一口锅里吃饭,相依为命。我们从江北到江南,从江苏到福建,年老后为家庭、为生存奋斗,同样是相依为命。我当年在部队医院传染科工作,那时住农村,谈不上防病隔离,别说是人,连驻地群众家的狗都患了肺结核病。加之工作任务重,生活条件差,1962年,潜伏在我身上的肺结核爆发了——开放性、传染性,我必须立即住院、必须严密隔离……当时我们是四口之家,两个孩子都才三四岁。怎么办?晓峰凭着军人气概毅然送我入院。我在遥远的闽清传染病院一住就是两年多,在此期间从未回家一次,直到疾病根除出院。每个星期天,他都带着孩子到医院探视一次,饭不敢吃、水不敢喝。在晓峰的“相依”精神下,公务事、家庭事,一切都划上了圆满句号。
相依为命是一种美德,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正能量。我今特用《相依为命 激情感怀》为题,书写最近发生的令我不能忘却的记忆:
去年7月,一个周六的中午,孩子特意趋车带我们到江滨渔村避暑、品尝海鲜。晓峰还有个期待——要到这个渔村再读范仲淹的《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一进这家海鲜楼,海潮带着江风,满楼宾客都兴高采烈,唯独我冷得不行。下午一到家,我就倒下了,起不了床,吃不下饭。起初,我俩都不以为然,孩子按计划回了北京。周日上午晓峰外出回家后,见我全身木木的,两眼呆呆的,两腿一动也不动,立即要车送我到机关医院急诊。我当时40度高烧,被诊断为深度肺炎、陈旧性结核,转入“重症监护室”,晓峰接到了我的《病危通知书》。
如果我在那天无人相依或不送医院急诊,就十分危险了。直到现在,晓峰一想到此,就要掉泪,既是掉惊险泪——无依没命,太险!也掉高兴泪——有依得救,高兴!除此之外,当然也还有老年危机感的泪!
这次住院时晓峰天天来看我,有时他被允许进病房了,我却因高烧而不认识他。后来,只要我“不认识”他了,他都会掉泪!俗话说军人流血不流泪,这种“流泪”意味着什么?我知道,这自然是“相依为命”的悲情、深情和激情啊!
后来我转入正常病科,环境改善了,还请了护理工,但近一个月时间,晓峰和孩子还是天天来探视我,天天给我送吃的,以致病友和护工似乎都对我这个家庭有一种钦佩和赞誉。自我这次病后,晓峰对我的关爱更加无微不至——上下楼梯要扶着,横跨马路要牵着,风扇空调开关都要管控着,特别怕我再吹风受凉。
我们都是近90高龄的抗日老兵了,之所以能度过这些风雨坎坷,与实践说了多年的“夕阳人生”格言很有关系。这就是:不老的希望,辩证的思维。理解社会、善待夫妻、以和为贵、相依为命、运动延年、笑对人生。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责任编辑 魏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