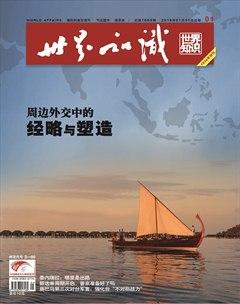突尼斯:脆弱的宁静
殷之光
2015年11月24日,北非国家突尼斯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一名宗教极端分子伪装成安全人员,混入一辆运送总统府安全卫队士兵的车辆,随即引爆炸弹。事件造成至少13名卫队人员死亡,17人受伤。突尼斯总统埃塞卜西随后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突尼斯的宁静瞬间被打破。而就在此前的10月9日,“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刚刚得到西方世界的赞许——荣获201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在诺贝尔和平奖的官方新闻稿中,“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被认为在突尼斯民主转型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市民社会的作用,并在推动突尼斯世俗政党召唤党与伊斯兰复兴运动进行谈判的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乐观的西方观察家看来,这个由突尼斯总工会牵头发起,集合了突尼斯工业贸易及手工业联盟、突尼斯人权联盟以及突尼斯律师公会的组织,重新点燃了人们对阿拉伯民主转型的期望。
更加理性的“革命”

2015年12月17日,一些突尼斯民众纪念“茉莉花革命”爆发五周年。
“全国对话”的出现与这两年的突尼斯政局息息相关。2013年7月25日,突尼斯反对派、左翼政党联盟人民阵线的重要成员之一、纳赛尔的信徒、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穆罕默德·布拉米在自家门口,被两名骑着摩托车的蒙面枪手射杀在自己妻儿面前。在此前五个月,人民阵线的另一名重要成员肖克里·贝莱德也遭暗杀身亡。据称,在遭到暗杀的前几天,肖克里·贝莱德在参加一场活动时曾遭到极端势力的围攻。这两场针对左翼政党领袖的暗杀事件,将突尼斯政局推到崩溃的边缘。人民阵线的支持者认为当时的议会第一大党伊斯兰复兴运动是暗杀事件的幕后凶手,因而冲击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在突尼斯多地的办公室。
而就在7月份的暗杀事件发生之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主席、约旦前副首相马尔旺·马沙尔还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表示,“突尼斯模式”是埃及乃至整个中东效仿的对象。的确,与其他发生政治动荡的阿拉伯国家相比,突尼斯的情况似乎要理性得多。突尼斯既没有像利比亚那样将前领导人暴尸街头,也没有像埃及那样出现借革命之名泄宗教、种族之恨的情况,更没有像叙利亚那样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相反,突尼斯“革命”很快就走上了议会政党斗争的道路。2011年3月,在推翻本·阿里政权两个月之后,突尼斯便进行了民意调查。刚刚合法化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获得了29%的支持率,超过了其他世俗政党。在当年10月的制宪会议选举中,伊斯兰复兴运动不出所料获得了217席中的89席。虽然伊斯兰复兴运动与穆斯林兄弟会、哈马斯等组织有着密切联系,但是,以温和面目示人的他们向突尼斯和世界保证,他们不是“伊斯兰主义政党”,而仅仅是遵循《古兰经》原则的伊斯兰政党。而且,伊斯兰复兴运动似乎很熟悉西方的政治话语,将自己的政治理论与基督教民主相比,同时强调会以土耳其的模式来处理政教关系。
但是,外界观察家却对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真正意图表示怀疑。特别是在这两场政治暗杀事件之后,舆论普遍认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正在用恐怖手段来实践其政治目的。这种猜忌给温和派的伊斯兰复兴运动造成了重大打击。很快,突尼斯制宪会议中的60名反对党成员集体辞职,并要求成立由非党派人士领导的新政府。加上旅游、外贸、纺织等支柱经济领域增长乏力,突尼斯陷入了政治和经济双重危机之中。“全国对话”便在这种局面下出现在突尼斯的政治舞台上。
诺贝尔奖的背后
牵头发起“全国对话”的突尼斯总工会,一直与突尼斯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比如总工会的前任领导人之一塔依比·巴库切就在现任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世俗政党与伊斯兰政治势力博弈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全国对话”之所以能成功促成当时执政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反对党对话,还与埃及政局变动息息相关。一开始,以召唤党为代表的反对党提出,对话的条件是执政党政府集体辞职;“全国对话”则提议,执政党政府在对话之后的三周后解散;伊斯兰复兴运动则表示,只有在立宪大会完成工作并提名了总理候选人之后才会下台。而随着2013年7月埃及总统穆尔西下台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遭到残酷围剿,伊斯兰复兴运动也开始对自身命运产生了担忧。实际上,自从上世纪90年代遭到本·阿里政权打压并被宣布非法之后,突尼斯的伊斯兰政治势力便一直处在举步维艰的境地。直至2011年推翻本·阿里、解除党禁,复兴运动才重新恢复活力。历史记忆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现实遭遇,使得复兴运动最终决定妥协,接受了“全国对话”的条件,与召唤党进行谈判,以解决突尼斯的政治和经济危机。2014年1月,突尼斯完成政府改组并通过新宪法,标志着其民主进程进入新的阶段。2014年6月,突尼斯各政治派别通过全国对话大会,确定了新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日期。2014年11月,突尼斯完成议会选举。其中,召唤党获得217席中的86席,取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值得注意的是,与2011年选举后产生的复兴运动政府不同,此次选举后产生的召唤党政府似乎受到更多的照顾。作为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政府的每一个举措和决策都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甚至质疑,很多人担忧伊斯兰复兴运动随时会将突尼斯拖入伊斯兰化的“不归之路”。对于大多数突尼斯中上阶层来说,情感与政治认同上与世俗政党更加接近。从历史上看,突尼斯国父布尔吉巴本身就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毕业于巴黎大学,青睐西方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在突尼斯独立之初,布尔吉巴便明确了彻底去除伊斯兰传统陋习的社会改革目标。正是这种态度,使得突尼斯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西方学者视作中东地区民主政治的最大希望。突尼斯政治的精英主义倾向非常明显,而其精英也大多受到过良好且系统的西式教育。因此,多数突尼斯人对世俗的召唤党政府宽容得多。尽管在召唤党获得的86个席位中,接近半数成员都曾在本·阿里时代的宪政民主联盟中有过高层职位,而且同商业大资本、媒体以及警察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这些均未受到过多质疑。换句话说,被民众推翻的本·阿里政权的既得利益阶层,在“革命”后重新成为突尼斯民主转型的标杆和希望。
2015年9月30日,就在诺贝尔奖要给突尼斯民主转型加持褒扬之前,突尼斯总理哈比比·易思德到访美国。易思德是一个从美国拿了经济学学位的政治精英,他表示“突尼斯还面临着许多挑战,还需要在多个领域内进行改革”。相比当初采用新自由主义模式迅速刺激国内经济发展的本·阿里政府,今天的突尼斯虽然获得了西方世界的褒扬,但是由于对国家缺乏真正的管理能力,缺少必要的施政计划,因而迟迟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不见起色,这也着实让那些不遗余力为其搭台的人感到无奈。而且,与埃及一样,今天的突尼斯政府也在不断试图加强对国家的管控。2015年上半年发生两场针对西方游客的恐怖袭击之后,召唤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除了提高安全部门权限、增加警力之外,突尼斯还决定在与利比亚接壤的边境上建造隔离墙。而就在“全国对话”获得诺贝尔奖三天后,突尼斯舍阿奈比地区又发生了一起针对安全部队的武装袭击。而在2015年5月,“伊斯兰国”组织警告全球穆斯林,自6月3日起不要乘坐突尼斯航空的班机。据统计,目前约有2500至3000名突尼斯人加入了“伊斯兰国”,突尼斯已经成为“伊斯兰国”海外“圣战”分子的最大来源国。这使得人们不免怀疑,现任政府在国家治理上究竟有多大能力。与此同时,突尼斯议会选举采用了欧洲流行的比例代表制。这种选举方式看起来兼容并包,各行各业各色人等均有人“代表”,但也导致议会内小党林立,严重碎片化。表面上和平的议会政治,实际上掩盖了突尼斯缺少政治共识的事实。甚至在党派内部,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斗争也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行政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突尼斯是外界观察西亚北非国家政治局势的窗口,也是我们反思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实例。
(作者为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埃克塞特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