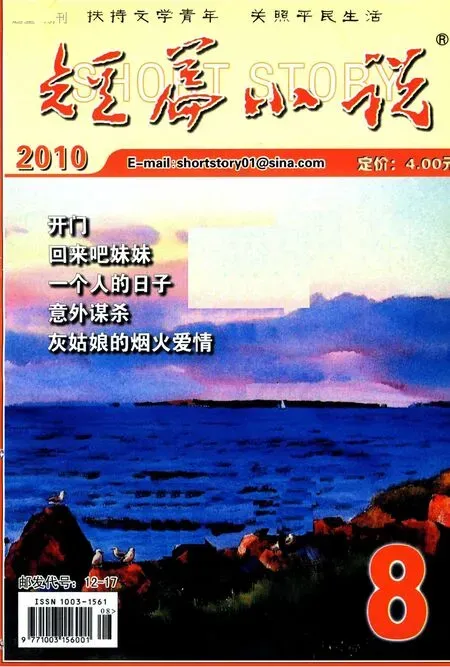面朝黄土
◎陈柳金
面朝黄土
◎陈柳金
一
爹已收拾好了东西,连牙刷手帕这样的小物件也没落下。唯独那把剑,还挂在墙上,爹也许没打算把它带走。我坐在音响室,默不作声。剑是属于远方的,而爹的心在老家,爹和剑只是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发生了一次武林侠士般的邂逅。当江湖已远,爹是要回归山林的。而剑,便只有插回剑鞘,做沉睡的铁。
对于我这个城管,生发这样的感慨未免显得矫情。但我是一个喜欢音乐的城管,经典乐曲就像吗啡融进了血液,我的大脑神经常常会怪异地收缩和扩张。有时会缩成一朵蒲公英,有时又会膨胀成一把大降落伞。这种非正常的收放之间,我觉得自己超凡脱俗,每天踩着一朵音乐的祥云。但玩这种发烧音响注定是烧钱的,唐小栩三天两头和我吵闹,吃饭时碗都摔了好几个。爹实在受不了,说,我来的时候好好的,就一个月时间,这个家便成了窝里斗!爹嚯地站了起来,挥出那只舞剑的手,我明天一早回老家!无论怎么挽留,爹都吃了秤砣铁了心。
楼下已响起了音乐声,有人喊起了爹的名字。爹换了衣服,迟重地取下剑挎在肩上,真的像一个老侠士。我在唐小栩的骂骂咧咧中回到音响室。电容刚修好,用了八百元,那个师傅一开价就是一千,我磨破嘴皮才砍下两百。那种沙沙声果然消失了,又恢复到原来的音质。
唐小栩就是那时出现在门口的,如母狮子怒目圆睁,又烧钱了,把家底都砸进去吧,这个月没米下锅了,全家都把嘴封住!
我说,又不是拿钱去赌博,嚷什么嚷!
唐小栩的声音提高了八度,比赌博还烧钱,都砸了五六十万了,一套破音响值得吗?每个月还要做房奴、车奴……
我拧大音量,凭空跃起的音响气浪把唐小栩逼得后退了两步。她涨红了脸,一定很恼火,终究没有冲进来。所有的战事都是在饭桌上解决的,这是唐小栩一贯的策略。果不其然,吃饭的时候她便施展了高调训人的才华。
此刻,我不想听音响。想象着爹在楼下打太极剑的心情,一定是沉重、愤慨的。他跟那群大爷大妈刚混熟,总算找到了能唠嗑的人,而明天一早就要回老家去。这不是他的本意,但他骨子里有一种“一口唾沫一颗钉”的硬气。爹此时一定跟着大爷大妈们腾挪有姿,呼啸生风,剑光和红缨在空中穿梭绕行,打出武当太极的气韵。
窗外忽然响起 “嗞——嗞——嗞”的鸣声,很凌厉,很瘆人,耳膜都震得嗡嗡响。我坐立不安,异常烦躁,额上沁出了汗滴。这蝉鸣,一下子把五月的白天抻长了,把黑夜压短了。我极不适应这种时空的调整,脑神经又在无节制地收放。但我在唐小栩生气的时候,忍着不敢开音响,生怕激起她更烈的怒火,冲进来把音响砸了。便踱出客厅,儿子拿着一个盒子,发出“嗞——嗞——”的鸣叫,说,爸,我捕了几只蝉!我爱理不理,蝉有什么好玩的,吵死了,像你妈!儿子嘻嘻地笑了,我告诉妈,你说她坏话!我一把拉过臭小子,恶狠狠地说,敢说我揍扁你!儿子看着陌生的我,我看着淘气的儿子,时间一下子凝固了。
就在这时,门重重地敲响。儿子伸手拉开,爹被那位徐姨扶了进来,当初爹学剑还是她教的呢。爹双手紧捂住肚子,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着,汗水沿着脸颊往下淌。儿子盒里的蝉不合时宜地鸣叫起来。
徐姨急匆匆地说,快,你爹犯病了!
我赶紧把爹扶坐在沙发上,爹,我送你去医院!
爹决绝地说,不,不去,这是蛇疹,我知道怎么治!
爹接着说了两个字,蚯蚓……
徐姨嘘了口气,对对,蚯蚓管用,他就信这个!
我说,我这就去找!
爹吃力地说了一句,几年前我亲眼看见村里的赤脚医生用这种土方法治好了村里人的蛇疹,敷五六天就好了,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爹的性格犟得很,谁也拿他没辙。你用牛绳拉,他用千斤顶顶住。
掀开爹的上衣,腹部露出一片血红的疱疹,活生生一块鸡血石。
我焦躁地穿上鞋。儿子跑过来抱着我的大腿,我一推搡,闹什么闹,去找你妈!走出门,回头朝屋里看了一下,这个铁石心肠的唐小栩还是没有出现。
徐姨从后面追上来说,多找点,要快,越快越好!下楼时与慌乱成一团的大爷大妈的目光对上了,我顾不得跟他们说什么,径直去管理中心借了把短柄铁铲,便开着车消失在苍茫的夜色里。
二
我说过,我是城管。城管除了管流动摊贩,还管泥头车,当然,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职能。泥头车按规定晚间上路,我便通常上晚班。主要是盯紧那些土头土脑的车,只要泥土抛撒出来污染路面,就要逮住处罚。看了看表,八点,十点要上班,只剩下两个钟的时间。我四处游荡了一圈后,竟然发现这个城市裸露的肌肤少得可怜,混凝土把地面封得严严实实,他妈的全是坚硬的龟壳。哪怕费老半天劲找到一处泥土,一铲子下去,却是乱石,铁铲被磕破了嘴,在月光下流淌着白色的血液。
真见鬼!我恨恨地骂道。正要挪步逃离,手机响了。对方好像刚做完一件不可告人的事,话语间的气流有点接不上——……十点啊……接一下我……到那个……啊……香树丽舍工地!前面几个音节好像一根折断的苇秆,从电流里浮浮沉沉地漂过来,只有最后那个音节才是完整的,所有的铺垫似乎都为了奔着“香树丽舍工地”而去。我支吾了一声,硬邦邦地磕了电话,仿若铁铲磕到石块的声音,硬冷,决绝。
我必须去找,哪怕挖地三尺也得找到。这老头子,简直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他决定了的事,航空母舰都拉不回来。我还能怎么着,只得硬着头皮找。但十点就要上晚班了,我祈愿剩下的一个多钟头里会有奇迹发生。
好不容易又找到了一处泥土,一铲子下去,却是一堆生活垃圾,臭哄哄的气味扑鼻而来。马上闪到路边,尖厉的喇叭声吓了一大跳,一辆稀头巴脑的货车从身边冲了过去,扬起大片灰尘。我嘴里直骂,心却被一束强光照亮了。看了看表,九点!把铁铲扔到车尾箱,赶到单位换了制服,开出执法车,火急火燎地直奔香树丽舍。
停好车,站在工地门前的拐弯处,心里虔诚地默念着。过了十分钟,果真出现了一辆泥头车,车灯射出的两道光柱在城市缭乱的灯火里惊惶地晃动,仿佛拉着一车的不明物品。
不知道是路面颠簸,还是泥土装得太满,路上已经撒了一大片细碎的土末。穿着笔挺制服的身影,恰好在这当儿出现了。我拧亮警用手电筒,强光如孙悟空的金箍棒,在司机脸上划拉了几下。是一个光头,样子很像动画片《熊出没》里的光头强。我想起儿子说的话,爸爸是熊大,一到晚上就跟熊二去抓光头强。光头司机马上像一只泄气的充气球,一踩刹车,排气管嗤嗤地排出一长串气,听起来很是无奈。我索性拉开车门爬了上去,跟“光头强”坐在驾驶室里。就在这时,“嗞”一声响,很刺耳,我看了看光头强,光头强也看了看我。
他说,城管大哥,行行好,放俺一马,俺改天请你吃宵夜!
我说,少废话,把车开到前面空地上!
光头强只得往前开,嘎一声停在那僻静处。我一手握手电,一手握铁铲,这两件武器让光头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在他耳边低语了两句,光头强马上像打足了气的充气球,简直是从地面飘上了装满泥土的车厢,用铁铲在土堆里卖力地下了第一铲、第二铲、第三铲……
手电的光亮照着搅动的泥土,很遗憾,我想要的东西没有出现。看了看表,九点三十分,时间迫在眉睫。我扳住车厢的挡泥板,一用劲爬了上去,夺过铁铲一阵疯挖,带出的泥土散发着一股迷人的芳香。我已没有时间去顾及这种久违的气味,下了一铲,又下了一铲……
亮光里,出现了一条甩动的蚯蚓,我感觉到脸上的皱纹瞬间舒展开,绽放成一朵带着泥土香的花。“嗞——嗞——嗞”,居然又响起那声音,以为是蚯蚓的叫声,马上否定了,像蝉鸣。光头强也愣了一下,我已管不了那么多,继续深挖一铲,又一条蚯蚓蹦了出来。接连下铲,都没有落空,这蚯蚓像是约好了似地要在这个时刻破土而出。光头强手里的塑料袋已经装了近十条蚯蚓,甩得袋子噼里啪啦响。
我从车厢上跳了下来,说,你走吧,回头把路面冲洗干净,要快!
光头强如蒙大赦,连摸带滚爬上驾驶室。车已开出去了,忽然停下来,光头强探出车窗,扭转头说,城管大哥,改天请你吃宵夜,喝冰啤!
就在这时,手机又响了,那个声音似乎有了点精气神,却显出几分不耐烦,怎么还没来,黄花菜都等凉了!
我说,这就来,急什么呢,又不是去收复钓鱼岛!
对方的声音明显大了,像你这作风,不被钓鱼岛收复才怪呢!
风风火火地往小区赶。“嗞——”,那种像蝉鸣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要不是手机响的时候掏出一只知了,我真的怀疑是不是蚯蚓的哀号声。我用肩膀和耳朵夹住手机,头顺势歪着。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摁下窗玻璃,一扬手,那只挣扎的知了便消失在这诡异的夜色里。肯定是儿子那个淘气包干的,回去好好收拾那臭小子。
是唐小栩的声音,死哪去了,这么久还没找到,爹痛得要命!
她的这声责怨反而使我温暖,我说,叫爹忍忍,快到家了!
停好车,塑料袋里的蚯蚓也许睡着了,只轻晃了一下。我提着一袋子的梦回到家,爹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很绵软,像一条巨大的蚯蚓,乏力地扭动着腰肢。那把剑歪放在沙发上,发出微弱的光。昏暗的灯光把爹脸上狰狞的表情映衬得更加恐怖,还听到几声长长的哀叹。
唐小栩不知在厨房里鼓捣什么,能闻到一股香味儿。
三
爹,总算找到了!我摁亮大灯,爹的眼极不适应,好一阵才睁开,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悦,这束光被我捕捉到了,像萤火虫,很轻微,也很晶莹。爹用尽全身力气撑坐着,所有沉睡的骨头又苏醒过来,恢复了力量,把他疲弱的肉身支撑起。爹站立着,简直是夺过我手里的塑料袋,一肚子怨气地说,在城里找一条蚯蚓比上天还难!要是老家,在门前的土坷垃里就能扒拉出来。都说这城市要啥有啥,都是骗人的鬼话,连一条蚯蚓都找不到,连一条蚯蚓都找不到,哎……
我第一次看爹自个给自个治病。爹忍着疼痛在大碗里倒进白糖,把洗干净的蚯蚓悉数放进去,蚯蚓慢慢分泌出白黄色黏液。爹用筷子使劲搅拌,蚯蚓成了糊状糖浆,拿棉签蘸了涂在腹部的疱疹上,用纱布盖住。爹长长地嘘出一口气,说,什么都有解药,鲜地龙是蛇疹的解药,八脚蜘蛛是小儿惊风的解药。什么一级医师三甲医院,都不如我这地龙管用。要是到医院,又是抽血又是扫CT又是打吊针又是吃西药,把人折腾得半死不活,等病治好了,人也瘦下去一圈。医生都是宰人不眨眼的杀猪佬,最好离远一点!
唐小栩从厨房端出一碗绿豆红糖汤,说,爹,趁热喝,这汤解毒!
爹深深地喝了一口。唐小栩从沙发上拿起那把剑,挂在爹房间的白墙上。我看到它发出悦意的光泽,好像生活终于以另一种方式挽留了它的主人,它差点沉寂的命运得到了转机。
过了一阵,爹腹部的疼痛果真减缓很多,似乎那鸡血石一样红的疱疹也黯淡了一些,真是神奇。我不得不信服民间流传的秘方,竟然为爹的犟劲感到些许自豪。我很想拧开音响来庆祝这场惊险的成功,但儿子已睡着了,唐小栩心里的那把火刚刚熄灭,我怎能不知好歹地点燃?
放心地去上晚班,顺路接了那个打过两次电话的同事,与他一起去了香树丽舍。他说,奇怪了,明明有市民投诉这个工地泥头车污染路面的,竟然没看到。
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一早,家里涌进了一大群穿太极服的大爷大妈。他们提着水果、营养品,甚至有些提着泥块,说,在城里蚯蚓真难找,一大早跑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找到,最后在一个建筑工地才挖到了几块有蚯蚓的泥巴!那位徐姨是最后一个进来的,手里提着蚯蚓,说,这城里连泥土都很难见到,蚯蚓简直比冬虫夏草还难找,我是叫儿子开车跑到离家十公里的河堤上挖到的!
爹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待他们离开后,给我下达了一道命令——去运几包泥土回来,我要养蚯蚓!我知道爹的性格,说一不二,他想办的事哪怕上刀山下火海都要办成。说实话,我打心里高兴,这一病,把爹留了下来。其实爹回去,也是孤零零一个人,娘几年前走了,走的时候劝说爹,你这犟驴跟我犟了一辈子,我走后你跟谁犟去?把这毛病改了,好好跟孩子过日子!爹说,我哪也不去,吃饭留着你的碗,喝酒留着你的杯,睡觉留着你的枕!
我在三百公里外的城市工作,总是放心不下爹,跟他做了几年的思想工作愣是做不通,一个月前几乎是把他挟持到东莞的。他住了几天就嚷着要回去,说地里的黄瓜豌豆莴苣苦瓜番茄洋葱甘蓝胡萝卜要晒干了,还有池塘里那些草鱼也饿几天了。我骗他说,这城里也有一大片地,改天带你去种点瓜果蔬菜,说不定比家里种的还好呢!爹有了盼头,又住了几天,实在闲得慌,便一个人走上街去。
我是在听帕格尼尼时接到的电话。
对方说是东城城管分局的,你爹破坏绿化带,按规定要罚款!
我一听头都大了,连忙赶去。
爹坐在那两个城管面前,显然是在做调查笔录。他们费劲地听着爹诘屈聱牙的普通话,我大体弄明白了爹的“犯罪”过程——爹听儿子说在这城里有大块地可以种菜,等了好几天儿子都没空,爹闲不住,便一个人上街去找,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哪有空地的影子。爹看到那个斜坡种着杂花闲草怪可惜的,便买了锄头一阵猛挖,想着把土平整好了栽上瓜苗菜秧……
俩城管似乎觉得爹是一个史前动物,用一种怪异的目光盯着他。当我亮出自己的城管身份时,他们说,没办法,钱是要罚的,已经立案了!
我拿了罚款通知单,经过银行时顺便把一千元罚款打到指定账户上。爹坐在车后座,我从后视镜瞥见他紧绷的脸,好像蒙受了奇耻大辱。他压根没想到在城里种菜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他以仇视的目光看着窗外的城市。
爹嗫嚅着说,要是在老家,怎么要赔这冤枉钱!这城市,没一点人情味!
我怕爹又要嚷着回去,脑子里蹦出个想法,说,爹,一点小钱,咱不跟城里人计较。你晚上去练太极剑,这运动对身体好!
爹固执地说,我不去,我一个种地的人练剑干吗?
路过体育器材店时,我还是买了太极服和太极剑,把爹放在车尾箱的那把锄头悄悄扔了。佩着红缨的太极剑仿若在城市的高楼之间任意挥舞,将带着农村味的锄头打到了臭水沟里。
楼下一到晚上便有大爷大妈练太极剑、打太极扇、跳广场舞。当我强拉着爹下楼去时,一位叫徐姨的大妈接纳了他,一招一式不厌其烦地反复教他。没几日,爹居然打得有模有款,呼呼生风。没想到爹在这方面还挺有天赋。
加上孙子跟他玩得来,整天缠着他,他的心也就踏实了点。唯一让爹不开心的就是我和唐小栩之间的抵牾,总是三天打雷两天霹雳地闹。后来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爹竟然也跟唐小栩站到了同一条战壕里,用那只持剑的手指着我说,你这是哪根筋搭错了,破喇叭值那么多钱吗,你把我几辈子的钱都搭进去了。要是你娘没走,还不被你活活气死!
他一说到娘,我的心就疼,脑神经一收一放,太阳穴隐隐作痛。而只有音乐,才能为心灵疗伤。我沉浸在经典音乐强大的艺术气场里,一个人如痴如醉地听巴赫、帕格尼尼、门德尔松,脚踩祥云周游于世界音乐殿堂里。实话跟你说吧,我把这套音响当作红颜知己。那些土豪舍得几百万上千万为情人买豪宅买地皮买名车买股票买基金买和田玉买翡翠项链,我扔个几十万买套音响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的眼神像柔软的手指从音响器材上轻轻掠过,如弹奏一支钢琴曲——单端845功放,六角形天朗 AUTOGRAPH音箱,“莲12”CD机。一条喇叭线的价格,足以在市区买下二十平米。我听的巴赫,比如意大利协奏曲和半音阶幻想曲与赋格,是1976年录音的飞利浦西德银圈PDO#03版 CD,从广州专业高端音响店淘回来的,一个CD上千元。那种音质自然非同凡响,能辨听出音色的细微变化,立体感和穿透力很强。
而这正是被唐小栩责怪的原因,她总是骂我中音乐的毒太深,这辈子恐怕都没有解药了。再这样不知收敛,两个人只有重新选择。唐小栩一次比一次说得凶,都推到了悬崖之上,再往前一步,感情便粉身碎骨。
四
爹坐在客厅用蚯蚓糖浆涂抹腹部疱疹,有些地方已结了痂,痛已完全消失。爹的命令不能不执行,没有办法,我只得又找到光头强,跟他要了两大袋泥土。
爹的蛇疹已痊愈了,吃完晚饭照例到楼下跟那群大爷大妈练太极剑。他养在大花盆里的蚯蚓居然活了,一有空就在阳台松土。好像盆里种着灵芝仙草,而爹是修炼经年的世外高人。他捏起一条蚯蚓,蹲在一旁的孙子忙跳开,吓得哇哇大叫,爷爷怎么养怪物?爷爷怎么养怪物?爹说,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这是蚯蚓,中药名叫地龙,作用大着呢。身上不长胆,怕个毬!
爹几乎不叫我给他买东西,这次却背着唐小栩要我买智能手机,我很快买了回来,爹叫我帮他开通微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剑友们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就我一个人没微信。我费了好大劲才教会爹,他进了那个群,很快就有十几个人加他为好友。爹发的第一张图片是阳台花盆里的蚯蚓。马上有个叫“乡下徐娘”的人点了个赞,还发了评论:城市阳台新风景,不养花草养蚯蚓!这些字爹都认识,连说,造孽啊造孽啊,城市再大也离不开土地,没有蚯蚓的城市是笑话!我背着爹把他说的话回复了过去。
那天傍晚,蝉一如既往地嘶鸣。似乎蝉是一个镇流器,一到夏天便经受不起用电高峰期的重荷,嘣地坏了,成天发出“嗞——嗞——嗞”的鸣声。爹的手机几乎不响,这次却意外地响了起来。爹不小心按了免提键,对方焦灼地说,我是徐芬,刚才不小心被开水烫伤了,快挖几条蚯蚓,我上次听你说蚯蚓加白糖能治疗水火烫伤!爹赶紧从大花盆里挖了蚯蚓,用塑料袋装了跑出门去。我愣愣地站在阳台,挖出的新土弥漫着一阵钻心入肺的芳香。
爹回来时满面春风地说,这蚯蚓真是管用,那个徐姨说她也要在阳台养蚯蚓,以后万一出事了好救急!然后又给我下了命令,运两袋泥土回来。我只得再次去找光头强要。本来执法者老去找执法对象办私事,对工作是大忌讳,但有什么办法呢,偌大一个城市,我到哪里去找泥土?
那天,我背着爹看了他的微信圈。那个“乡下徐娘”也发了图片,一张是在阳台花盆养蚯蚓的图,另一张是她脚上被开水烫伤已结痂的伤疤。点赞的人竟然超过了三十人,我替爹点了个赞。下面还有一大串评论:
——我也要养蚯蚓,但找泥土是个难题!
——自从来城里跟孩子一起住,都好几年没见过蚯蚓了!
——我以前就是用蚯蚓治好了褥疮,不打针不吃药,很神奇!
——城市那么大,蚯蚓哪去了?
——城市是蚯蚓的坟墓,很想念以前在农村老家的日子!
——老家的土地庙有副对联:人生土是根,命存地为本!
……
不出所料,爹在晚饭后又给我下了一道命令——运三十袋泥土回来,剑友们都想在阳台养蚯蚓!
爹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刚从音响器材店订购了一条桥线,一千多元。当送货员上门时,我才发现钱不够,只得硬着头皮跟唐小栩要。她一听便火冒三丈,你这狗改不了吃屎的,又去烧钱,你那破音响全是阴间里的鬼。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跟你耗不起,以后咱桥归桥,路归路,你跟破音响过日子去!啪一声,手里的萨米特陶瓷杯摔在地上,一地渍水和碎片,几片柠檬圈像车轮散落着。我的脑神经剧烈地一收一放,仿佛看到一起惨烈的车祸。
只得退了桥线,无比郁闷地开着车去找光头强。拧开车载音响,是陈超的《解药》——
……
你不是我想要的解药
不值得我对你那么好
我中的毒我自己解掉
再痛也不要假的拥抱
你不是我想要的解药
总会有谁对我比你对我好
你下的毒你自己喝掉
我刑满了不再坐你的牢
……
我一向不听流行歌曲,听多了那些经典音乐,总觉得流行歌太矫情、太轻浮。但不知怎的,这首歌却濡湿了我的眼。唐小栩说我中的毒太深,这一次竟闹到了分道扬镳的地步。我买音响前前后后花了五六十万,差不多能买一套房子了。离开了音响,我觉得日子是苍白的,生活总得还有比吃喝拉撒更纯粹的东西。以致有人想高价买整套音响,我一口回绝了。而现在这大环境下,单位没什么福利,完全靠工资吃饭,唐小栩怎么能不抱怨呢?所以,我一直在找解药,但越找却越是陷得深。
当光头强开着泥头车上路时,被我拦住了,叫他把车开到前面水泥地上,递给他几十个蛇皮袋。光头强搞不清楚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都来找他要过几次泥土了。而这一次,却要几十袋!
装了满满一后尾箱,还有十袋只能堆在车后座与前座之间的空位上。我感觉自己的车也变成了泥头车,正开往城市这个大填土坑。前面车灯闪烁,双眼迷离间,须臾出现了高耸的楼群,须臾又出现了宽广的沃野;须臾出现了奔涌的车流,须臾又出现了扑棱的飞鸟;须臾出现了黑黢黢的河涌,须臾又出现了清凌凌的溪涧……我的脑神经有点错乱,耳际又响起了唐小栩的臭骂声,他妈的像无比凌厉的蝉鸣。我只有想象着自己坐在家里的音响室,正播放着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舒缓恬静,自然灵动,婉约悠扬。
不经意看了一下后视镜,恍惚间出现了爹紧绷的脸。后面一辆亮着车灯的大货车突然偏离了原来的路线,啸叫着蹿上来。我的手离开了方向盘,身体失去了平衡,这个喧闹的世界一下子跌入静谧的深谷。
我是在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中醒来的,唐小栩紧紧地抱着我,一边摇着我的身体,一边竭力哭喊,王大宏,你醒醒,你醒醒,以后尽管玩你的发烧音响,我再也不骂你了。我说的是气话,我们怎么能离婚呢,儿子都长这么大了,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我并没惊动她,脑神经还在急剧地一收一放,一会儿缩成蒲公英飘向半空,一会儿张成大降落伞飘落城市。我看到一群穿清一色太极服的大爷大妈,还有爹,正在城市的夜色里脸呈笑意地舞剑。一个熟悉又遥远的声音响起,大宏,是这几十袋泥土救了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终于相信世上有一种叫灵魂的神秘东西,我刚才听到我的灵魂在说话,它在空中以祥云的姿势飘荡着,最后轻柔地回到了我的身体里。
我睁开眼。
爹说,大宏,你终于醒过来了,苍天有眼!
徐姨说,孩子,多亏这些泥土,像菩萨一样把你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爹和徐姨挎着太极剑,红缨飘飘,美极了。
唐小栩惊喜地抹干泪水,大喊道,王大宏,算你有良心,没有丢下我和儿子独自去逍遥!
我扯了扯嘴角,笑了,感觉有了力量,在家人的搀扶下站立起来,抖抖身上的土末,我闻到了那股清香的气味。我的车被撞得变了形,车尾箱凹陷进去,两扇车后门也歪挂着。一大堆泥土倾泻出来,挡住了那辆大货车蛮横的车头。大货车歪嘴裂鼻,危险灯一闪一烁,俨然一只被降服的魔兽。我一阵惊悚,要不是有车上的几十袋泥土,我早已成了大货车魔爪下的肉松。
这时,无意间瞥见一条蚯蚓从泥堆里探出头来,在路灯下扭动着腰身。
“嗞——”,以为是蚯蚓的鸣唱,却看到儿子手里拿着那只盒子,这声蝉鸣明显带着几分喜悦。儿子脆生生地说了声,爸,我们回家吧!
我摸了摸他的头,说了句——臭小子!
责任编辑/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