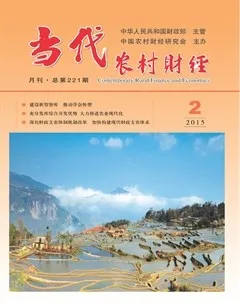农民市民化的路径探讨




农民市民化是我国下一阶段城镇化的核心内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指出,下一阶段的城镇化将“以人为本”,以加快农民市民化为目的,缩小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缺口为导向。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战略地位,决定了对市民化路径研究的必要性。本文通过对我国三大地带的9个主要代表城市、9个县域地区的市民化成本测算,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等理论,系统研究双路径市民化成本及其对农民市民化的影响。
一、农民市民化的基本路径
从有关文献看,目前农民市民化存在两种基本路径:一种是有迁移市民化,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最终穿越城乡之间有形和无形的“户籍墙”,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另一种是无迁移市民化,即人口并未迁移,但其居住位置在人口调查的城乡分类定义中由农村变为城市。
要大力促进农民市民化,政府就需要满足新增城镇人口对公共设施的需求,因而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同时农村人口需要足以维持在城镇生活的收入。这些投入就是市民化的成本。市民化的成本因两种不同市民化道路而有所不同。在大中城镇,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如何通过投资建设扩大城镇容纳新增人口的能力,满足新增人口的需求,将是政府的核心任务;而对于进入大中城镇的农村人口来说,想要成为市民前提条件是解决在城镇就业的问题。在县镇地区,由于各项基础建设的缺乏,加强基础建设、改造农村环境、提供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相同的条件,将是县镇政府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双路径农民市民化成本模型
对农民市民化成本的测算,主要出发点在于农民融入城市需要付出最低成本。其实农民进入城镇并不困难,难的是获得一份足以维生的工作支付其最低生活。基于前人对农村人口城镇化成本的分析,并综合有迁移市民化与无迁移市民化的区别,本文认为,农民市民化的社会化成本是指农村人口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活、生产方式等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转化并顺利融入城市社会所必须投入的最低资金量。生活成本中包括了水、电等家庭普通日常需求,以及为了获得与城镇人口相同的工作,必须达到的人力资本含量所需要付出的教育成本,为了获得城镇居民的各种养老福利而需要购买的各项社会保险金额等。同时,政府也需要投入一笔相应的费用,以支持土地城镇化过程中的资金需求。
本文根据农村人口迁入较为集中的城市,分东中西三大地带选取了9个城市、9个县域地区进行研究。本文的研究机M9MPlQQAimiHfs8nWi/jfA==制如图一所示。
(一)有迁移市民化路径
从现实角度出发,有迁移的农民市民化成本即为当前城镇居民基础的支出,包括人力资本获得成本、公共卫生、就业扶持、权益维护、社会保障、住房条件改善等公共服务中每个领域所需要的支出。其成本模型可表示为:
C = Cprivate + Cpublic (1)
Cprivate =C1 + C2 + C3 (2)
农民进入城镇,首先要适应城镇生活,就要考虑到城市生存的各个方面。C1是个人生活成本,它衡量的是农村人口在城市生活的日常开支,包括城镇生活的人均水、电、气、交通、通讯、事务开支等方面的支出,这其中扣除了城镇住房支出。这一指标衡量的是城镇人口为满足基本生存需求需要支付的成本。C2 是城镇居民教育成本,衡量的是农民工市民化后获得与城镇居民的平均劳动技能所产生的人均教育支出。C3是农民市民化后在城镇的居住成本,这其中包括了城镇居民为食品、衣着以及日常交通每年需要支付的成本,这一指标衡量的是各城市城镇居民平均交通和通信费用。在有迁移市民化路径中,各项指标均以城镇低收入标准来衡量。
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对于新增的城镇人口,政府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城镇公共基础设施。政府的成本模型如下:
Cpublic=S1 + S2 (3)
S1是政府在城市除房地产外固定资产的投入成本,S1=IN/Pc。IN是2011年各城市的城镇固定资产投入,Pc是2011年各城市的城镇人口数量,通过处理将得到2011年各城市政府人均投入固定资产量,乘以预计每年将增加的人口数量,将得出未来政府为应对新增人口需要支出的固定资产建设成本。H2是城市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支出,这一项衡量的是城镇在支持教育事业、发展教育事业方面支出的成本。
(二)无迁移市民化路径
无迁移情况下,农民的市民化是就地转移在附近的县镇与乡镇就业、居住。也就是说,政府为改造农村地区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以支付新建城镇的需求。因此,乡镇地区的城镇化,政府需要支出的费用将比有迁移情况下的城镇化要多,新建的道路、房屋、公共设施都需要乡镇政府的资金投入(见表二)。
无迁移路径下的公共成本为GOVC1=(TV / PG ),GOVC1为县镇与乡镇政府为建设完善交通系统,开辟新道路所需要投入的成本;TV为上一年政府为建设新道路所投入的资金;PG是上一年乡镇地区的人口,从而测算出为新增人口政府需要支出的道路基建费用。GOVC2=(IV / PG),GOVC2是除房地产之外的政府固定投资;IV为县镇与乡镇地区上一年除房地产的投资之外的固定投资;PG为上年乡镇地区的人口,从而测算出为满足新增人口对城镇环境的需求,政府需要支出的固定投入费用。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有迁移路径下市民化成本结果(见表三)
从有迁移路径下的市民化成本结果可以发现:
1.东部地区的城市个人成本偏高。
北京、上海、广州由于处于经济发展最先、最迅速的地区,城市各项设施的使用费用以及物价水平均比其他城市要高,由此造成了三个城市的个人成本偏高。
2.东部地区的城市社会成本低于其他两个地区。
东部地区各城市是中国城市发展情况中最快的,城市发展越是完善的地区,对于个人来说,进入城市生活的门槛往往较高,而由于前期的建设已经较为完善,则在城镇基础建设方面投入反而较少。东部地区的人口相较于其他两个地区的人口更多,这可能是造成社会成本低于其他两个地区的原因之一。
3.西部地区的市民化中成本最高。
主要是因为其社会成本相较于其他两个地区更高。为促使全国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国家应该加大对西部地区城市建设的投入力度。
(二)无迁移路径下市民化成本结果(见表四)
根据无迁移路径下的结果可以发现:
1.个人成本东部地区偏高。
个人成本与县域的物价紧密相关,从结果来看,同样是由于经济核心城市发展更好,导致了东部地区主要代表城市周边的县域地区的物价相较于中部、西部更高。
2.社会成本西部地区较高。
由于西部地区土地面积广,人口相较来说少,因此在相同的基础建设投资水平下,人均社会成本反而相较于东部与中部更高。同时,也反映了西部亟待开发的现状。
(三)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双路径市民化平均成本对比(见表五)
从平均成本的角度出发,有迁移市民化平均成本,东部、中部的都比无迁移市民化平均成本要高出很多,由此可以得出,对于想要进入东部大中城市的农民来说,先进入周边经济发达的县域地区积累资本、适应城市生活会更好;而西部地区的无迁移平均成本比有迁移平均成本要高的原因,是西部地区县域地区相较来说设施较为落后,需要更多的政府投入,导致了最终平均总成本更高。
四、实现农民市民化的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一)下一阶段,农民市民化要依靠政府的投资建设。
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容纳能力是农民市民化的关键。通过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道路、医疗等方面的投入,能够有效满足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新增市民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不会导致人均资源过于稀释。
(二)下一阶段,农村人口市民化可以通过两类型市民化并进的方式加快发展。
根据实证结果的对比可以发现,无迁移平均成本较有迁移平均成本更少,这意味着GV35nwLp4huC98HBe1Oz4Q==市民化道路不应该只限于有迁移路径,无迁移市民化同样适合现在的中国。我国的革命事业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而城镇化是再一次的“革命”,进入新时代,或许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径,会是减轻国家、农民负担的方式。
(三)下一阶段,农民市民化的个人成本需要通过普惠金融等方式减轻负担。
经过研究可以发现,农村人口要进入大中城市的成本远超过农村人口可以承受的范围,然而进入大中城市寻求发展又是农民现在的主要诉求,因此在有迁移路径下,将需要更多的普惠金融的支持。
根据三个结论,提出两条政策建议:
一是政府政策引导。在“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凸显的当代社会,需要的是社会的安定,双路径市民化提供了农村人口两条道路,政府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农民对市民化道路的选择,从而均衡各地市民化的进程。
二是民营资本进入金融市场,通过服务小微、区域差异来满足不同地区城镇化的需求。虽然普惠金融是双路径农民市民化的主要资金援助来源,但是国家对细分到县、镇地区的资金需求并不能做到尽善尽美,而民营资本则刚好可以通过区域差异化,来满足不同地区对于贷款、援助的不同需求,从而更好地促进市民化进程。
参考文献:
[1]李炳坤. 关于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几个问题[J]. 中国工业经济, 2002, 8: 003.
[2]王竹林. 农民工市民化的资本困境及其缓解出路[J]. 农业经济问题, 2010 (2): 28—32.
[3]刘传江, 程建林. 双重 “户籍墙” 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J]. 经济学家, 2009 (10): 66—72.
[4]张国胜, 陈瑛. 社会成本, 分摊机制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J]. 经济学家, 2013, 1: 011.
[5]张国胜. 基于社会成本考虑的农民工市民化: 一个转轨中发展大国的视角与政策选择[J]. 中国软科学, 2009, 4: 56—69.
[6]黄锟.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分析[D]. 武汉大学, 2009.
[7]唐根年, 徐维祥, 贾临宇 等. 中国农民市民化经济门槛与城市化关系研究: 理论与实证[J]. 经济地理, 2006, 26(1): 118—121.
[8]周小刚, 陈东有. 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理论阐释与政策选择, 农民工市民化 [J][J]. 江西社会科学, 2009, 12: 032.
[9]陶然, 徐志刚. 城市化, 农地制度与迁移人口社会保障[J]. 经济研究, 2005, 12: 45—56.
[10]蔡昉. 人口转变, 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 经济研究, 2010, 45(4): 4—13.
[11]约翰, 奈特, 邓曲恒等. 中国的民工荒与农村剩余劳动力[J]. 管理世界, 2011, 11: 003.
[12]蔡建明, 王国霞, 杨振山. 我国人口迁移趋势及空间格局演变[J]. 人口研究, 2007, 31(5):
[13]王春蕊. 禀赋, 有限理性与农村劳动力迁移行为研究[D].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14]陈广桂. 农民城镇迁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D]. 南京农业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2009.
[15]罗必良.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城镇化战略[J]. 农村经济, 2013, 1: 003.
(作者单位:湖南省湘潭大学商学院)
责任编辑:欣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