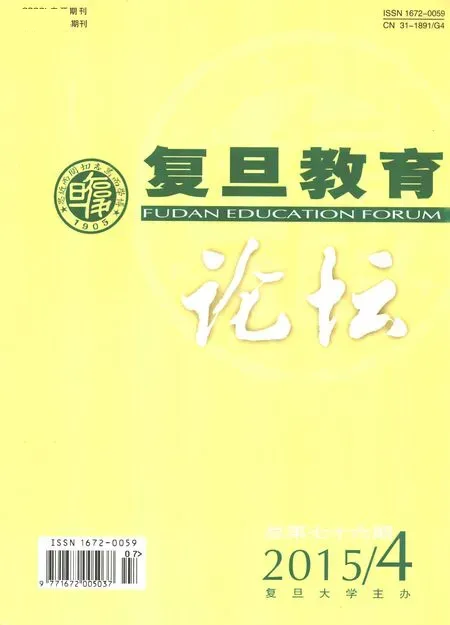中国民办高校董事会规范结构和行为结构偏差的实证分析
王一涛,刘继安
(1.浙江树人大学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研究院,浙江 杭州310015;2.上海交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上海200240)
大学的内部领导体制是内部治理的基础和核心,在大学的发展中扮演极其重要的作用。按照政策法规规定,我国公办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而民办高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民办高校的董事会并不是新鲜事物。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私立高校如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借鉴美国私立高校的大学治理制度,普遍将董事会作为其最重要的决策机构。[1]改革开放之后“美国取代苏联成了新的学习榜样”,[2]我国民办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再次借鉴董事会制度,成为我国民办高校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
我国民办高校的董事会制度有什么特点,实际运行的成效如何?很多学者曾经对民办高校的董事会进行过研究。[3-5]但是,因为数据获得难度比较大,学术界对民办高校董事会制度及其运作的实证研究非常匮乏,代表性和深入性都有待拓展。本文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探究我国民办高校董事会的组成和运行特点及其成因,为完善民办高校的董事会制度提供政策建议,促进我国民办高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理论框架和重要概念
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是本文分析的理论框架。[6]该学派认为,在开放的组织环境中,一个组织要生存就必须不断从外部环境中获得资源。这些资源主要有三大类:(1)实物、资金和人力资源;(2)信息;(3)社会和政治的合法性支持。这些资源往往不是组织能够自主生产的。为了获得资源,一个组织必须与控制资源的其他组织相互交往并进行交易,拥有资源控制权的其他组织对该组织有一定的控制权。一个组织对其他组织的依赖程度取决于三个因素:(1)资源的重要性和组织对该资源的依赖程度;(2)利益群体对这一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的控制力;(3)替代资源的存在情况。
Pfeffer和Salancik(1978)应用该理论解释董事会的组成时认为,董事会规模大小和成员结构是组织对外部环境的理性反应,组织从外部获得资源的情况和组织内部权力配置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同时,组织内部的个人或团体从外部组织争取到的资源越多,其在组织内部的影响力就越大。[7]
本文的分析还将用到以下两个重要概念。第一个是法律规范结构。虽然学者对法律规范结构的内涵理解不尽相同,但基本上认为包括以下要素:假定、处理和制裁。假定是指明规范生效条件的部分,处理是指明行为规范的内容(主体权利和义务)的部分,制裁是规定在不遵守规范时的制裁部分。[8]第二个是行为结构,指的是构成人的行动系统的要素和要素之间的关系,通常包括动机体系、行动体系和结果体系。动机体系包括致动因、动因、动机和目标等;行动体系是人的行为表现过程,包括计划、准备、实施等步骤,起决定作用的是行动的手段;结果体系是人的行为产生的后果,包括直接后果和间接影响。[9]规范结构对行为结构的行动体系直接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但对动机体系而言只是致动因之一。行为结构的结果体系为规范结构的制裁提供考量依据。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种方法来探索民办学校董事会的实际运作情况。第一,我们浏览了444所民办高校的官方网站,获得了212位举办者在学校中的任职信息。其中,我们重点分析了87所民办高校官方网站中关于董事会的相关信息,这87所民办高校分布在北京(10所)、福建(26所)、安徽(20所)、吉林(9所)、四川(20所)、宁夏(2所)等6省市自治区,包括了我国的东、中、西部。从办学层次来看,这些民办高校既包括本科高校,也包括高职(专科)学校。第二,我们搜集了37所民办高校的章程,章程对民办高校的治理体系和规则做了文本的说明。①第三,我们深度访谈了8位举办者或他们的接班人,9位校级管理者和9位中层行政管理人员,从而获得了对26所民办高校董事会相关信息的了解。第四,我们按照方便抽样的方法对河北、山东、河南、浙江4省内5所民办高校的158位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试图从教师的视角来反映董事会的特征和运作成效。
三、研究发现和分析讨论
(一)董事会的地位和职权
我国关于民办教育的一系列法律法规都赋予了董事会以重要的决策职权。2003年9月开始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九条规定:“民办学校应当设立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2004年4月开始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民办高校的董事会具有聘任校长、修改学校章程、审核预算和决算等重大事项。2012年出台的《教育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进一步强调要“规范民办学校董事会(理事会)成员构成”、“完善董事会议事规则和运行程序”。
我们的调查发现,几乎所有民办高校都声称该校赋予了董事会以决策职权。在87所民办高校中,有15所民办高校的官网上没有说明该校的治理方式。在其余72所民办高校中,有66所表示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91.7%),6所宣称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8.3%)。
官方网站只是学校对外传递信息的一个平台,而章程则具有法律地位。《实施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章程是民办学校内部治理应遵循的基本准则。②本研究发现,37所民办高校的章程无一例外都赋予了董事会决策权,其中32所民办高校的章程直接表述为“董事会(或理事会、董事局)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剩下的5所民办高校章程虽然没有如此表述,但是其要么有“院长对董事会负责”的表述,要么有“董事会是决策机构”的表述。据此可推断,董事会或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我国民办高校普遍采取的内部治理体制。董事会制度的建立可以看做是我国民办高校对社会合法性支持(法律规范)依赖的反应。
(二)董事会的人员组成和权力分配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民办高校董事会成员结构没有硬性规定。《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二十条规定:“民办高校的董事会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教职工代表等人员组成。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理事或者董事应当具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董事会由五人以上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董事会负责人应当品行良好,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同时指出要“规范民办学校董事会(理事会)成员构成,限定学校举办者代表的比例,校长及学校关键管理岗位实行亲属回避制度。”
国外有学者根据董事会的成员构成情况,将高校的董事会分为“专家型董事会”和“代表型董事会”两种类型。[10]专家型董事会即董事会的主要成员是由各类专家组成,比如财务、教学、管理、法律等方面的专家。代表型董事会是指董事会的成员结构能广泛代表学校内外的各类利益相关者,比如学生、教师、管理人员、校友、社区代表等。
我们的调查发现,我国部分民办高校的董事会成员包括教育、管理、财务等方面的专家,但是这些专家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很低。所以“专家型”不是我国民办高校董事会的主要特征。我国大部分民办高校的董事会有1-2名教职工代表,但是所谓的教职工代表往往是学校的中层干部,普通教师一般没有机会,学生、校友等利益群体一般也都没有进入董事会的机会。所以我国民办高校的董事会也很难称为代表型董事会。
根据212所民办高校的举办者在学校的任职情况(见表1),即83%的举办者担任董事长(理事长)或者同时身兼决策机构和行政管理的领导者,我们认为我国大部分民办高校的董事会可以概括为举办者控制型董事会。

表1 212所民办高校创办者在学校中的职务
进一步分析发现,举办者控制型董事会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举办者是董事会的核心人物,在董事会中处于控制地位。如果民办高校是个人创办的,则创办者处于董事会的核心;若民办高校是企业举办的,则该企业的董事长处于该校董事会的核心,他往往委派多名代表进入董事会从而获得对董事会的控制。第二,举办者往往安排家属成员进入董事会,从而使我国民办高校带有家族化的典型特征。我们调查的26所民办高校中,有12所民办高校董事会中有2人或多人是同一家族的成员。这一点使我国民办高校和家族企业非常类似。第三,“一元决策”。国外民办高校的董事会往往是由不同主体构成,且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决策的制定并实现相互监督和制约,但是我国民办高校中,举办者的个人意志基本上不受约束。
举办者控制型董事会还导致了我国民办高校董事会的另一个特征:隐蔽性。既然董事会是大多数民办高校的决策机构和权力机构,那么学校应该在各种场合广泛宣传和介绍董事会成员,学校的教职员工对董事成员也应该很熟悉。但是,调研发现,大部分民办高校不公开董事会的成员构成。87所民办高校的官网中都详细介绍了本校领导班子成员(包括正副校长和正副书记),但只有不到一成(8所)的民办高校在官网公开了董事会全部成员名单。我们在问卷中询问158位教师“是否清楚学校董事会的组成”,结果回答“非常清楚”、“ 比较清楚”、“ 知道一些”、“ 不太清楚”、“ 完全不清楚”的比例分别是1.9%、14.0%、41.4%、36.9%和5.7%。相比之下,当我们问教师“是否清楚学校领导班子的组成”时,相应的比例分别为36.3%、43.3%、15.9%、4.5%和0%。
民办高校的董事会成员构成也有例外情况。我国有少部分民办高校是纯粹公益性的民办高校,这些民办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得到了政府的较大扶持,比如浙江树人大学、南京三江学院、上海杉达学院等。这类民办高校占我国民办高校总数的10%左右。这些民办高校的董事会没有举办者控制的色彩,董事会中既有政府官员代表,也有教育、管理等各类专家,这类民办高校董事会和美国私立高校的董事会构成较为类似。
举办者控制型董事会的上述特征可以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行为结构与规范结构的偏差来解释。我国关于民办教育的法律法规都规定民办高等教育是公益性事业,属非营利组织。我国法律法规尽管允许民办高校投资者可以取得合理回报,但回报是作为对其办学的奖励,与按照投资比例取得经济回报有本质不同,而且获得合理回报要遵循严格的规定。虽然我国民办高校的举办者都希望通过办学来培养人才、奉献社会,但与此同时,大部分民办高校是投资办学而非捐资办学,举办者希望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法律法规可以规范行动体系,但却无法控制行为结构中的动机体系。动机体系与规范结构的偏差就会导致行动体系的“似是而非”:既然民办高校的资产无法直接取得回报,也不能像家族企业的资产一样继承给后人,举办者只能将控制权尤其是人事和财务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手中,才能实现包括获得经济回报在内的办学目标。由于董事会是法律所认可的决策机构和权力机构,控制了董事会就相当于控制了整个学校,所以举办者通过多种努力来加强对董事会的控制。
应该看到,举办者这样做具有现实合理性。与美国私立大学的资源来源多样化不同,我国的民办高校资源来源渠道单一:在初期基本上通过举办者的实物、资金以及人力资源投入,通过滚动发展达到一定规模后,则主要依赖学生学费以及学校自身的其他收入。这一特征决定了我国民办高校董事会不会像美国私立高校董事会那样由外部人控制。[11]我国民办高校学费依赖和董事会内部人控制的特点与日本的私立高校接近,但与日本私立高校董事会真正意义上的内部人控制不同的是,我国民办高校内部人的权力集中在举办者手里,而不是在所有内部的利益群体(创办人、行政管理人员、教职工和学生)代表手里。造成这一不同是因为日本私立高校在创办时得到了政府扶持和社会捐助,是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这与日本的政策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12]
(三)董事会的决策机制
我国相关法律对民办高校董事会的议事规则和程序没有做出详细规定。《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民办高校的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民办高校的董事会讨论诸如“聘任校长、修改学校章程、制定学校发展规划”等重要事项时应当经2/3以上组成人员同意方可通过。除此之外再无实质性要求。《实施意见》也只是笼统强调要“完善董事会议事规则和运行程序,董事会召开会议议决学校重大事项,应做会议记录并请全体董事会成员签字、存档备查。”
现实中,我们发现董事会的议事规则和程序比董事会的成员结构更不为人所知。对教师的问卷调查表明,87%的教师不清楚董事会的运行规则和运行程序。实际上,举办者控制型董事会的成员结构决定了董事会不是一个严谨的决策机构。而且,当举办者控制了董事会之后,即使建立了完备的程序和规则,其可信度也大打折扣。
我们对董事的访谈发现,大多数民办高校的董事会每年召开2-4次会议,但是也有民办高校的董事会几乎不开会议。一位在民办高校工作了3年的校领导说,“我校有董事会,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开过董事会会议”。这位受访者还表示,“我们省几十所民办高校中,董事会基本上都是一个摆设”。有一些民办高校是否召开董事会往往取决于举办者的意愿,如果举办者希望召开董事会就会立即召开,如果他不希望召开董事会,那么预定的董事会也会推迟。董事会的召开方式也非常多样。有一些民办高校采取会议的形式召开董事会,也有民办高校采取“董事长宴请董事”的方式召开董事会。
董圣足的研究发现,关于董事会重大决策的表决方式,采取“无记名投票、多数通过”的学校仅占4%,而采取“民主协商、董事长裁决”或者“董事长个人说了算”的学校高达60%。[13]我们的调查再次证实了董事会中各个成员的话语权极其不均衡的现象,董事长决定的事情其他董事一般没有办法改变。大多数民办高校的董事都默认了董事长权力过大这一事实。一所民办高校的董事认为,既然学校是举办者个人举办起来的,所以“我将自己的身份界定为学校决策的建议者而不是决策者,学校真正的决策者只有董事长一人”。这种观点代表了大多数民办高校董事会成员的观点。当然,也有民办高校的董事对举办者权力过大的现实表示不满,一位参与创办民办高校的董事无奈地表示,“顺他(指关键举办者)者昌,逆他者亡,不满意或无法忍受就只能离开”。
一些民办高校的举办者也不避讳董事会权力集中这一事实。他们认为这一制度安排适合现阶段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现状。一所民办高校的创办者明确表示,所有的决策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表决不利于学校的发展。“我看好的项目,即使董事会中的大部分都反对,我也要上。我相信我的直觉。”“一元决策”确保了民办高校的决策效率,使民办高校充分发挥了“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对社会需求的变动保持着灵敏的反应并能做出及时的回应,但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决策风险。
因此,举办者控制型董事会的议事规则和决策机制是以举办者为中心和主导的机制。举办者的个人决策很容易通过董事会决议的形式而变成学校的决策。比如,很多民办高校的创办者在退出学校领导岗位之前往往安排子女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在对外发布这些人事任命时,学校都会表示“这是董事会讨论的结果”。很明显,举办者通过对董事会的控制实现了对整个学校的控制。这里,规范结构中对处理的模糊表述或惩罚的缺失,为行动体系偏离规范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
当然,少数民办高校董事会是真正的集体决策机构,董事会的议事规则和程序较为健全。第一类是纯粹的公益性民办高校。这类民办高校没有明确的投资者,曾经或者正在接受政府的较多扶持,学校章程较为完备,校长任免、资金预算和决算、基础建设等重要决策都在董事会上民主讨论。第二类是企业投资型的民办高校。企业对民办高校的投资有账可查,所有权可以得到明确保护,投资方不担心失去对民办高校的控制权。此外,由于投资民办高校的企业往往有更为重要的经济业务,比如北京吉利大学的投资方吉利集团是我国最大的汽车企业之一,烟台南山学院的投资方南山集团拥有8大业务板块和2家上市公司,他们没有足够的精力和专业的知识来管理民办高校,所以他们往往吸收各类专家进入董事会。我们调查的浙江新和成股份公司投资的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以及宁夏宝塔石化集团投资的银川能源学院,其董事会运作都比较规范。
(四)董事会和校长的关系
在美国的大学治理机构中,聘任、评价和支持校长的工作是董事会的最重要职能,很多大学的校长拥有最大的决策权。[14]如前文所述,我国大部分民办高校都声称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负责”似乎表明校长在学校治理中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校长的实际职权如何?校长和董事会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需要注意到的是,创办者兼任校长的现象非常普遍。从表1可见,共有22.2%的创办者担任或兼任校(院)长。在举办者拥有对董事会的控制地位且担任或兼任校(院)长的情况下,所谓的“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仅仅是加强了举办者的权力而已。
若举办者自身不担任或兼任校(院)长,民办高校一般聘请从公办高校退休的校长担任校(院)长。我国公办高校的校长是具有行政级别的国家干部,所以,当他们到达退休年龄后就需要从管理岗位上退休,这为民办高校提供了充分的高层次人力资源。民办高校外聘的校长中,几乎都是退休的公办高校校长,比如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曾聘请原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张楚廷担任校长,文华学院聘请原华中科技大学副书记刘献君担任校长。
在国外大学中,董事会和校长往往通过相互支持但同时又相互制约和监督的方式提高决策的科学性。James Freedman认为董事会的职权范围是“治理”,而校长的职权范围是“管理”,这两者往往存在一定的交叉。[15]美国大学董事会联盟也指出,大学治理的“最终责任在于董事会”,但是董事会需要“依靠校长来实现对大学的领导,制定学校的愿景和战略规划”。[14]这进一步说明,董事会和校长之间蕴含着一定的冲突和张力,这种冲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决策效率,但是却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
我国民办高校中董事会和校长的关系和国外的情况不同。根据我们的调查,聘任的校长在民办高校中可能扮演下列角色中的一种或多种:荣誉性职务、公关者、咨询者或决策者。荣誉性职务的角色是指民办高校聘请一些校长仅仅为了提高学校知名度和社会声誉,这些校长一般曾经担任知名高校的校长,有的是中国科学院或者工程院院士,他们一年中只有几天的时间参加学校的活动,有的校长甚至一年只来学校一次。公关者的角色是指校长曾经在公办高校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资源,能够帮助民办高校处理和政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复杂关系。咨询者的角色是校长曾经作为公办高校的管理者,在教学、科研、学生事务管理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在董事会制定决策时发挥其智囊作用。当然,在部分民办高校中,校长也是重要的决策者,他们进入董事会参与董事会的决策,特别是在教学、科研等事务上拥有很大的决策权。
举办者和校长之间经常会出现一些意见分歧,因为校长强调如何提高教育质量,而举办者除了考虑教育质量之外还要考虑如何尽量节省经费以使自己以及其他的出资者获得合理的经济回报。当校长和举办者之间分歧比较严重时,举办者可能会随时辞退校长。由于校长大多是退休后的公办高校领导,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若他们的意见经常遭到否决,他们也会主动辞职。上述原因导致很多民办高校的校长任期很短。笔者访谈的一位校长表示,“校长就像是举办者的衣服,举办者想换就换”。
调查显示,在依靠滚动发展、产权不清晰的民办高校中,校长的角色一般是荣誉性职务、公关者和咨询者,举办者一般不赋予校长重要的职权,因为这类民办高校的举办者只有牢牢抓住学校的控制权,才能实现自己的各种办学目的。而在由大企业投资、产权相对明晰的民办高校中,董事会赋予校长的权力相对较大一些,因为这些企业需要依靠职业化的校长来管理民办高校。但是,即使在这类民办高校中,校长的权力也仅仅局限在教学和科研等事务中。比如:这类民办高校的财务负责人一般都是由举办方直接委派,重大的财务开支掌握在投资方而非校长手中;学校重要的人事聘任决定也是由投资方而非校长做出的。纯粹公益性民办高校的校长权力最大,校长一般是学校真正的一把手,在学校决策者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因此,可以说资源来源结构决定了内部治理结构的特征。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我们的调查发现,我国法律法规希望民办高校董事会能够担负集体领导的职能,但是在现实操作中,规范结构和行为结构有偏差。一些民办高校董事会沦为举办者控制学校和实现个人权力的工具。这些董事会内部对举办者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党委和教代会等制度安排也无法有效监督和制约举办者。举办者的办学动机、办学境界和管理能力成为影响我国民办高校发展的最重要的内部因素。当举办者具备卓越的管理能力和良好的办学意愿时,学校就会稳定快速发展;相反,当举办者管理能力不足或者办学动机以个人回报为目的时,学校就会存在风险。有的民办高校的举办者改变之后(比如举办者去世后由其子女接班),学校就会在短时期由盛至衰,甚至面临倒闭风险。根据我国民办高校董事会的现实情况,为了促进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我们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规范民办学校董事会(理事会)成员构成,限定学校举办者代表的比例。实际上,2012年开始实施的《实施意见》已经明确要求民办高校的董事会“限定学校举办者代表的比例,校长及学校关键管理岗位实行亲属回避制度。”但是由于缺乏对违反规范行为如何惩罚的规定,这一规定只在少数省区得到了贯彻,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落实该规定。很多民办高校的董事会中家族成员的比例较高,举办者兼任校长或者举办者的子女担任校长的现象也依然存在。我们认为,举办者及其代表的比例可以控制在1/3以内,同时要提高教育、财务、法律等各类专家在董事会中的比例。董事会成员结构的合理化是提高民办高校决策质量的基础,是民办高校由“个人治理”走向“制度治理”的必要条件,也是民办高校基业长青的根本保证。
第二,通过法规和政策形式增强其他利益群体(党委、校长、教代会等)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从而实现对举办者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从2007年起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开始向民办高校派驻督导专员,督导专员原则上担任党委书记并进入学校董事会,参与学校重大决策。这一规定在很多地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今后还需要继续加强。其次,要加强对民办高校校长任职资格的审核,同时保证校长在教学和科研事务中的独立决策权。再次,完善民办高校的教代会制度,每年至少召开一次教代会,重大决策应该让教职工代表审议,让教代会成为避免学校出现重大决策失误的制度屏障之一,同时通过完善的教代会制度提高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和工作积极性。
第三,加快民办高校信息公开步伐,要求民办高校主动向外界公布董事会成员构成以及董事会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2010年开始实施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要求高等学校主动向外界公布“内部管理体制、机构设置、学校领导等基本情况”,很显然,大部分民办高校没有根据该要求实行信息公开。民办高校是公益性组织而不是私营企业,董事会作为民办高校内部治理的核心机构,其成员结构和运行规则必须向外界公布并接受监督。董事会的透明化是民办高校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必要条件。
第四,推进民办高校分类管理。从长远来看,民办高校董事会问题的最根本解决之道是根据我国民办高校的实际情况,将其划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大类型。营利性民办高校可以模仿私营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但是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必须建立起与其非营利属性相对应的治理结构。董事会作为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关键,必须吸收各类利益相关者进入,限定举办者及其家属成员的比例,使董事会的决策公开、透明、科学,为我国民办高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注释
①福建省教育厅在2011年对外公开了福建省内当时所有民办高校(当时共17所)的章程,教育部在官方网站公布了2014年20所由独立学院转设为民办高校的章程。此外,作者还按照方便抽样的方法收集了另外5所民办高校的章程。
②需要指出的是,2011年出台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教育部31号令)仅仅适应于“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不适应于民办高校。
[1]宋秋蓉.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发展的政策环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 2) .
[2]COASE R H,WANG N.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18.
[3]阎凤桥,林静.商业性的市民社会:一种阐释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特征的视角[J].教育研究,2012( 4).
[4]张文国.中国民办学校法人制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63.
[5]黄志兵.民办高校三权合作式法人治理结构研究——基于宁波 A学院的个案研究[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1(4).
[6]HILLMAN A J, WITHERS M C, COLLINS B J.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A Review[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9(6).
[7]PFEFFER J,SALANCIK G R.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M].New York:Harper&Row,1978:245.
[8]罗玉中.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J].法学研究,1989(5).
[9]王加薇.行为科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27.
[10]BOERA H D, HUISMANB J, MEISTER-SCHEYTTC C.Supervision in'modern'university governance:boards under scrutiny[J].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2010(3).
[11]PFEFFER J.Size and composition of corporate boards of directors:The Organization and its Environment[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72,17( 2).
[12]阎凤桥.中国民办高校内部治理形式及国际比较[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7( 5).
[13]董圣足.民办院校良治之道——我国民办高校法人治理问题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232.
[14]Association of Governing Board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Association of governing board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statement on board responsibilities for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R].2010.
[15]FREEDMAN J O.Presidents and Trustees[G]//Ronald G.Ehrenberg(Ed.).Governing Academia.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