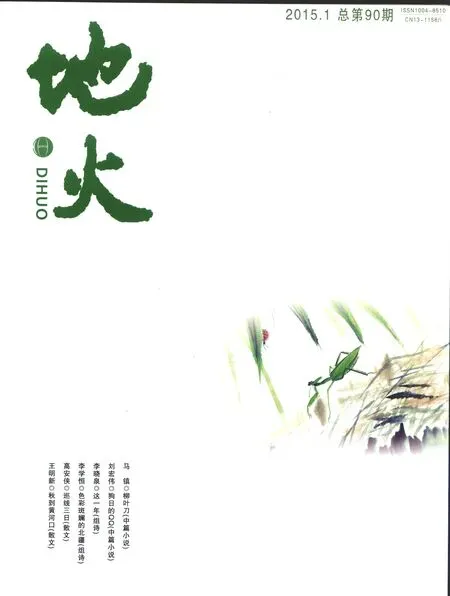桥上阳光
■曾羽
桥上阳光
■曾羽
薄雾刚刚散去,阳光随着泻落下来,闪烁着波光粼粼的河面,河面宽阔,河水混浊,左侧水流向上,右侧的水流向下,中间是一条白色的分水带蜿蜒其中,把顺流和逆流的河水表现得泾渭分明。这让站在大桥上的陶化雨一时有些诧异,随即他就释然了,这里离辽河入海口极近,河水流下和海潮上涨倒灌在这里交汇形成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河岸两边是绿到天际的芦苇荡,米八高,像剪子剪过,铺展开来。苇莺不知躲在哪株芦苇上不停地鸣叫着,“咂咂咂”“嘻嘻嘻”“咂咂嘻”“咂咂嘻”!远处的滩涂上,一大片碱蓬草红了,是那种醉红,红得养眼。
那个采油站还在,就在桥下边的那条砂石路旁,被芦苇的绿色包围着,粉白的围墙,粉白的房子,上端环绕着巴掌宽的橘红的带子,很醒目。门前两侧的小花圃充盈了绿色,初开的红的、黄的花朵点缀其中。一个穿着橘红工作服的采油工,将自行车推出站院大门,骑上巡井去了。
陶化雨举起相机,对准采油站按动着快门,不仅仅是采油站,还有大苇荡、辽河。他想起什么,在桥上回望,那片储苇场还在,几十座苇垛躺在那里,苇垛顶由黄色变得黯黑。不由得一声感叹,年年岁岁物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那时,陶化雨还是八九点钟太阳的年纪。那个秋天,他和一大批“八九点钟太阳”被送到河西岸修路,这里是油田新的上产区块。他们用铁锹、扁担把密匝匝苍黄的大苇荡剪开了,剪成一块一块的。他们住在绿帐篷里,寒风掀动着帐篷顶,呈现给他们几颗星星;烧原油的炉子又在倒烟,弄得满帐篷都是飘荡的大尾巴油灰;河水开始涨潮了,冰块挤压出吱吱喳喳的响声。
春节放假时,他被留下看连队的这片帐篷,谁让他是这青工里的最高职务排长呢。过了春节,陶化雨是跨过冰封的河面回家探亲的。前几天,河那边过来一拨人来这边苇塘拔纲草,从帐篷前经过。陶化雨闲得无聊就和人家搭讪,人家顺便也讨口水喝,话就多说了几句。他这时知道过冰河走十来里路就有个客运站,客运站到火车站的距离也不远,总之,比不过冰河回家要便捷许多。
陶化雨休完假,今天回来也是走的这条路。已是夕阳西下,灿烂的晚霞红透了天边。他拎着旅行袋走在苇塘的毛道上,远远地已经看到连队那片绿帐篷,再过一会儿他跨过冰河就可以回连队吃晚饭了。他的脚步轻快起来,大声唱着,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苇塘很宽阔,歌声传出很远。
站到河边时,陶化雨一下傻眼了,河里正在涨大潮,厚厚的冰层被割裂,冰排在潮水中飘浮着、走动着、碰撞着,有的还被推到岸上。他一屁股坐在旅行袋上,心里这个别扭,只剩一百多米就能归队了,可现在被阻隔了。
顶头那个绿帐篷里出来人了,他站起来,拼着嗓门吆喝着,那人听到了,向这边张望。
对面的河边上是十二班班长刘亚力。刘亚力大声喊道,陶排长,这大潮刚刚涨起,下半夜才会退下,你还是找个地方眯一宿吧,明天天亮过河稳妥!
他喊道,知道了!
晚霞玩了隐身,薄暮渐渐拉起,北风夹着刺脸的冰冷从河面蔓延过来,他不能在这里等待呀。陶化雨站起身,抓起旅行袋向河的上游走去,他期望上游某个地方有他过河的路……天上的星星开始眨动眼睛了,陶化雨的脚步变得沉重起来,期望在脚步的丈量中消失殆尽。他停下脚步,望着深邃的暗夜,看着还在上涨的灰白的河面。脚下是一条砂石路,有冻结的车辙印,他朝砂石路的黑暗里望了望,不远处有一处灯光,他决定走向那里,找个猫宿的地方。
灯光越来越亮,到了近前,是个采油站。水银灯照着红砖围墙红砖房,双扇铁大门紧闭着,值班室里亮着灯,一个背影坐在那里。陶化雨用力摇晃着铁大门,声音响亮。那个背影站了起来,是个男工,脸挤在窗玻璃上向外张望了好一会儿。陶化雨又摇了两下大门,男工才离开了窗户,开门走了出来。男工的个头不高,脸有些黝黑,三十岁的样子,头上戴了棉帽子,手里拎着一把大管钳子,冷着脸,横叨叨地说,你干什么呀?
陶化雨笑着说,不好意思,哥们,我想借个宿。
男工说,这是采油站,又不是旅社,借什么宿,走吧走吧。说着径直进了屋,啪的一声关上了门。
陶化雨有些眼直,想想,还是又摇了两下大门,男工好一会儿才懒洋洋出来,后面跟出一个女工来,脖子上系着一条粉围巾,明净的眼睛打量着他。男工这时说,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走吧!走吧!
陶化雨指指自己身上的黑色道道工作服,说,哥们,我也是油田的,就住在河对面,休探亲假回来,河里现在涨大潮,冰面都开了,过不去了,大冷的天,我就想在你们这里避避风寒,行个方便吧。
男工看了女工一眼,果断地说,不行,我们这里有规定,不许留人的,前面不远有村子,你去那里吧。陶化雨向黑暗里望了望,看不到一点光亮,就说,有多远呐?
男工说,十来里路吧。
陶化雨就皱了一下眉头,恳求说,我走了半天路了,实在是走不动了。
女工看着陶化雨,这时拉了男工衣袖一下,男工看了女工一眼,对陶化雨说,不是都和你说过了吗,走吧。说完,拉了女工一下,先进了屋。女工有些无奈地也走进门,进门时还回头看了陶化雨一眼。
陶化雨的肚子在咕咕叫着抗议着,他无奈地看了一眼紧闭的门,将旅行袋放在大门的墙垛边,靠墙坐在上面,拉紧了棉帽子,手插在袖筒里,闭上眼睛。他想,好歹这里有墙挡风,就在这里先眯着吧,半夜要是退了潮,也许就能早些过河去了……
哎,你醒醒啊!有人推了他几下,陶化雨睁开眼,是采油站的那个男工站在眼前。他揉揉眼睛,站起身,一只脚坐得有些麻木了。男工说,你没走哇,怎么在这儿睡上了,会睡出毛病的,快进屋吧。
陶化雨拖着一条有些麻木的脚进了屋,屋里真暖和,他坐在木条椅上,搓搓手。女工拿来一个印有红字的白搪瓷茶缸,倒好开水递给他,说,你喝点开水吧。
陶化雨说,谢谢。
男工这时说,哥们,刚才对不起了。
陶化雨说,没什么,谁让你们有规定啦。
男工脸上有些窘迫,女工微微地笑了一下。男工就说,主要还是不知道你的底细,虽然你穿的是油田的衣服,可是你这身衣服挺那个的,是吧?
陶化雨笑了,点点头,说,我明白。
陶化雨他们这批筑路工是油田新招的“大集体”工人,发的棉工作服挺另类,是黑色的“道道服”,走到哪里都知道他们的身份。这批筑路工是好几千人的队伍,大多都是下乡的知青抽调来的,最初打架斗殴、偷鸡摸狗是家常便饭,主要的个别人被专政机关收拾了。“大集体”在油田这里有些“臭名远播”或叫“谈虎色变”。
男工这时说,我叫王志鹏,她叫薛晓梅,你呢?
陶化雨说,我叫陶化雨。
王志鹏说,你休假怎么走到这边来啦?
陶化雨说,除了这条河,这边比那边好走多了。
王志鹏点点头,看了薛晓梅一眼,说,小陶,你先坐着,我得去巡井了。
陶化雨说,王师傅,你忙你的。
王志鹏出去了,薛晓梅说,陶化雨,你家是哪儿的呀?
陶化雨说,省城。
薛晓梅盯着陶化雨说,省城很大吧?
陶化雨说,没有北京、上海、天津大。
薛晓梅说,那也够大的啦,我就到过县城,吃一根冰棍就能走到头的那种。
陶化雨笑了,说,你说的县城也太小了点,和咱们现在的油田总部差不多少。
薛晓梅说,对,基本就是那样的,还是省城好玩吧?
陶化雨就开始说省城,说了故宫、说中街、说公园、说动物园、说电影院。陶化雨的嗓音很有磁性,能抓住人。
薛晓梅瞪着那双洁净的大眼睛饶有兴致地静静地听着,听得有些凝神。
夜半了,王志鹏巡井回来了,坐了一会儿就拿出饭盒,放在桌子上,里面是高粱米饭咸菜条,他看看陶化雨说,小陶,你也吃点吧?
陶化雨咽了一口吐沫,说,你吃吧,我正好眯一会儿。就脸冲墙趴在桌子上,闭上眼睛,他的胃有强烈的欲望,他忍住了。
薛晓梅掠了他一下,他转过头来。薛晓梅把一个铝饭盒盖放在他的眼前,里面有一块金黄的玉米面发糕,两匙清炒白菜片和一双新做的芦苇筷子,薛晓梅用清亮的声音说,你吃这个吧。
陶化雨看了薛晓梅一眼,说,谢谢你,不用,你吃吧。就把饭盒盖推了回去。
薛晓梅马上推了回来说,我这儿还有,你吃吧,多少垫补点。还把手里的饭盒让陶化雨看了一下,里面还有一块玉米面发糕,陶化雨还要推回去,薛晓梅的手已经挡在那里了,用恳求的目光看着他。他说,谢谢。
吃过发糕,又喝了些水,陶化雨的胃平静了许多,困意有些增长。王志鹏坐在对面,额头枕在胳膊上,有了些许的鼾声。薛晓梅粉白的瓜子脸架在胳膊上,静静地看着陶化雨,她想继续听陶化雨说省城的事。薛晓梅来自农村,她来油田上了二年技校就分配到这个采油站,她在这里已经两年了。过去小学课本上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她心里播下对城市那种生活的渴望,陶化雨的话深深吸引着她,让她着迷于那个世界。她只看过露天电影,没进过电影院。陶化雨对着那个渴望的眼神又讲了什么,困顿不知什么时候终结了他舌头的功能。
陶化雨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再次谢过王志鹏、薛晓梅离开了采油站,走在那条砂石路上时,他回了一下头,薛晓梅站在门口目送着他。他扬了扬手,大声说,我会来看你们的!
陶化雨跨过冰河时,刘亚力正站在帐篷头处张望着,看见他就走下来迎他,还说,排长,一看你晚上过得还不错。
陶化雨就把去采油站避风的事说了,当然也说到了薛晓梅。
刘亚力笑着说,排长,看来你命里有这一劫,就是让你走桃花运呢。
陶化雨笑了,说,你可别瞎掰扯了,说不定人家早就名花有主了。
刘亚力说,我听着不像,不信你去试试?
陶化雨说,但愿吧。
陶化雨的心中有了期待,并在心里拱出芽苞。那天他们修路的位置离来援建的大港油田前线基地很近,他在那里的小卖部买到了一盒午餐肉罐头。他把罐头藏好,这东西要是让刘亚力他们几个“狼”发现了,说什么都会成为他们口中餐的。
那天是薛晓梅上白班,陶化雨选择在家里出黑板报,他是团支部书记,他有这个特长和权力。时近中午,他从箱子里拿出装有三个馒头的饭盒和午餐肉罐头装进军挎,兴冲冲地过河了。阳光很好,很和他的心境,他哼着“咱们工人有力量”,来到了采油站。
薛晓梅看见他喜形于色,说,陶化雨,你怎么来了?
陶化雨看了一眼脸有些沉的王志鹏一眼,笑着说,上次谢谢你们收留了我,今天正好有时间,过来看看王师傅和你。王师傅,你挺好吧?
王志鹏的脸上有了些笑意,说,挺好,你们不忙吗?
陶化雨说,还好,我今天在队里出黑板报,抽些时间过来看你们。你们还没吃饭吧?
薛晓梅说,我们正要吃饭呢。
陶化雨说,太好了,咱们正好一起吃。说着,就打开军挎,拿出馒头和午餐肉罐头摆在桌子上。
王志鹏见了,拿起自己的饭盒就要去旁边的屋,还说,你们吃吧。
陶化雨见了,上前拦住王志鹏说,王师傅,你这样就不对了。就把他推坐在椅子上,拿给他一个馒头,挖了一大块午餐肉给他,说,王师傅,我就是来感谢你们的,没多有少,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吃吧。
吃过午饭,陶化雨坐了一会儿就要回去了,薛晓梅送出来挽留说,再待一会儿呗。陶化雨说,一会儿又要涨潮了,我别再被隔在这边。
薛晓梅笑着说,大不了还待在站里呗。
陶化雨说,我还是走吧,别影响你工作,我看王师傅见到我来有些不太高兴。
薛晓梅就抿着嘴笑。
陶化雨说,你笑什么呀?
薛晓梅有些羞涩地说,以后再告诉你。
陶化雨说,以后是什么时候哇?
薛晓梅笑着说,下次吧。
陶化雨说,这么说你是欢迎我来的啦?
薛晓梅笑着说,你自己想呗。
陶化雨过了冰河,向站在河边的薛晓梅挥挥手,他心里充盈着喜悦,脚步变得轻松快活。
虽然这里是“七九河开河不开,八九雁来雁不来”,可那中午的暖阳,有些蓝盈盈的冰面预告着冰河开始危险了,冰面已经开始变为竖茬。陶化雨第二次去看薛晓梅时,薛晓梅偷偷告诉他,王师傅前几天给她介绍了对象,是王师傅的内弟,她开始说考虑一下,现在给人家回绝了。陶化雨有些明知故问地说为什么?她笑着说不告诉你。今天,陶化雨过河来看薛晓梅,他知道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踩着冰面过河了,心里不由浮起一缕忧伤。薛晓梅高兴地送他到了河边,陶化雨迟疑着脚步,将一条新买的红纱巾系在她脖子上,拿起她的手,说,小梅,我恐怕不能过河来看你啦。
薛晓梅有些惊异地说,为什么呀?
陶化雨凝视着她说,冰河马上就化开了,这条近路断了。
薛晓梅眼里的泪一下盈满了,陶化雨轻轻地把她抱在怀里。薛晓梅扬起头说,这里要是能修座桥就好啦。
陶化雨安抚地说,小梅,桥就在我们心里。他激情迸发地吻着薛晓梅……
陶化雨再次站在河边时,冰排在河水的流动中消融着,一排又一排的雁阵鸣叫着变换着队形在空中掠过,两只仙鹤落在河边的苇地中悠闲地漫步。薛晓梅在河对岸挥动着那条红纱巾,像挥动着一团火,陶化雨挥动着手臂,大声呼喊,我爱你!薛晓梅在回应着。他们约定写信,每周寄一次,他们有时间就来到河边,碰面了就在河边呼喊、凝望。
赵指导员找陶化雨谈话,说,小陶,你最近好像有点变化呀。
陶化雨说,是吗,指导员?
赵指导员说,你没什么事吧?
陶化雨摇摇头说,没有哇。
赵指导员说,没有就好,你副队长的任命已经批复了,明天早会宣布,南皮岗有条新砂石路的任务,需要你带人驻点收砂石料,没问题吧?
陶化雨信心满满地说,保证完成任务。
陶化雨住到了更偏远的南皮岗。
薛晓梅来信说她母亲问她谈恋爱的事,她坦言告诉了母亲,母亲因为你是“大集体”,表示了极其强烈的反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啦。
陶化雨回信说,你先拖着吧,我的考验期是一年,到了十月份考验期满就好了,到时候我去拜见你的父母,我会说服他们的。另外,我刚刚报名电大历史系,按规定毕业后身份就会改变的,你放心吧。
薛晓梅说,我期待着。
芦苇已经长到肩头高了,薛晓梅有一个月没有来信了,陶化雨有些疑惑,他的去信如泥牛入海,这让他心里火烧火燎的。南皮岗的砂石路终于完工了,他回到驻地就奔了河边,对岸没有薛晓梅的身影,他挺沮丧的。一个采油工在砂石路上走过去,他高声呼喊着,薛晓梅!那个采油工似乎是听到了,回头看了他一眼,摆了摆手,走掉了。
陶化雨有些沮丧地回到队里,他急切地想知道薛晓梅到底怎么啦?接任他排长的刘亚力见到他说,怎么,没见到?
陶化雨点点头,说,薛晓梅到底怎么啦?真急死人了。
刘亚力说,不行你就请假过河去看看吧。
陶化雨说,这个假我怎么请,实话实说肯定不行,我又不想撒谎,还是算了吧。
刘亚力说,你这个样子我看着都闹心。
陶化雨想想说,亚力,明天中午你陪我去河边一趟吧。
刘亚力说,行。
陶化雨和刘亚力来到河边。是落大潮的时候,浑浊的河水在向下流淌着,正午的太阳暖暖的。陶化雨到了河边就脱下衣裤,从军挎拿出塑料袋装好。刘亚力说,你干什么呀?
陶化雨说,我要游过去。
刘亚力急了,说,你疯了!你可别胡来呀,这才六月天,河水还是挺凉的,手脚抽了筋,这要出点什么事,不值当啊。
陶化雨说,亚力,我就想知道薛晓梅到底怎么了?我让你来是给我加油打气的,你懂吗?
刘亚力看看陶化雨刚毅的神情,举起握紧的拳头,大声说,我懂了,你一定能行的,加油!
陶化雨在刘亚力高昂的加油声中游上了岸,尽管他这时嘴唇发紫,牙齿在不停地打战,他还是迫不及待地穿上衣服,匆匆奔向了采油站。
采油站是王志鹏的班,王志鹏看到陶化雨愣了一下,脸上的表情相当复杂。陶化雨急切地问,王师傅,薛晓梅呢?
王志鹏说,她没上班。
陶化雨说,为什么?
王志鹏说,她没写信告诉你吗?
陶化雨说,没有哇,王师傅,出什么事啦?
王志鹏蹙起眉头说,因为小梅和你的事,小梅她妈以自杀相逼。小梅是个孝顺的孩子,就答应她妈不和你来往了。
陶化雨的心被触痛了,说,她现在在哪儿?
王志鹏说,我不知道。
陶化雨恳求说,王师傅,求你了,她家在哪儿?我去她家找她。
王志鹏说,小陶,我真的没法告诉你。
陶化雨有些激烈地说,你不告诉我,我也会打听到的。
王志鹏说,小陶,如果你真的爱薛晓梅,你就应该尊重她,不要去找她啦,她够难受的啦,这也是她的意思。
陶化雨呆呆地看着王志鹏,他的心很痛,又茫然无助,他应该让薛晓梅轻松些。
三十年后,在一本新编的安全案例中,陶化雨看到一个工伤烧伤案例,其中提到薛xx。陶化雨有些疑惑,从时间、地点、姓氏看,这个因工烧伤的人就应该是薛晓梅,他这时有所悟。
前天,陶化雨的电脑上闪现一个新号码,他上线说,您好!怎么称呼?
对方说,薛晓梅。
陶化雨一时懵住了,三十年了,怎么会?就说,你在哪儿?
薛晓梅说,在上海女儿家里。
陶化雨说,你有女儿?
薛晓梅说,资助的。
陶化雨说,你好吗?
薛晓梅说,我很好。
陶化雨说,能发一张近照吗?
薛晓梅说,我还记得你的样子。
陶化雨明白了,说,我也是。
薛晓梅说,听说采油站门前的河上新建了一座大桥,你这个油田的摄影家能照些照片发给我吗?
陶化雨说,这个绝对没问题。
薛晓梅说,谢谢!就下线了。
陶化雨在桥上捕捉着美丽的瞬间,一对仙鹤在空中翱翔,隐入绿色苇海中;一行白鹭在蓝天滑翔,落入河滩红碱草边觅食;七八只水鸟贴着水面飞翔一段,落入水中逆流嬉戏;两只小渔船,一前一后“咔哒哒”地压开水面,拖着长长水花的尾巴向入海口驶去……
一辆轿车停在他旁边,下来一对年轻的红男绿女,勾肩搭背。男的说,这座桥建得真好,这里的景色也不错。女的笑着说,以后我们见面更方便了。说完,上车走了。
在薛晓梅原来站过的地方,现在沿河岸边铺了一段砌石,有好几个人支着遮阳伞在砌石上悠闲地垂钓着。陶化雨把镜头对准了那里,镜头里竟出现一个头上包着红纱巾的女人,在走向河边。他诧异了,马上按下快门,再定神看看,千真万确。他疑惑了一下,马上向那里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