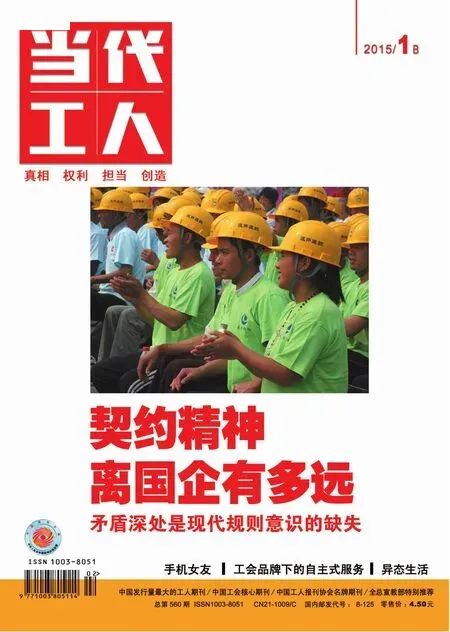没有重要的事情了
文/老 愚
没有重要的事情了
文/老 愚
黄叶纷飞,大雪将至,知天命之年行将过去。在马年之前,我心忐忑;甲午将尽,方知孔夫子所言不虚。至圣先师对人生贴过系统性标签: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在这些阶段来临之前,本人半信半疑——真的是那样的吗?心里极渴望得到确认,与先哲定论合辙的人生,才是踏实可靠的。
接近30岁时,最为惶恐。那时虽已成家,琴瑟和谐,却无立锥之地,借住于单位一间铁皮屋,白天猫一般蹑手蹑脚,夜晚娇妻归巢,更须屏息静气,怕惊扰了看门老头。一旦汇报上去,后勤就有了驱赶的口实。最可怕的是,突然失去了工作资格。那个喜欢画鹰的一把手,属于机敏的阶级斗争高手,不知是听了与我交恶的某官员的构陷之言,抑或凭嗅觉嗅到了本人身上的异端气味,对我痛下杀手,罗织罪名,剥夺了做编辑的权利。黯淡的岁月里,支撑我的唯有时间,我冀望时光待流逝,清明乾坤降临,一切美好的重又吐露芬芳。年轻人有的是时间,并不惧怕扼杀自己才华的势力。在夜里,我有时会喊出声来:所有的黑暗都来吧,拿出你们的杀手锏来对付我吧!
回想起来,彼时颇有几分负荷天下重任的自负,有一股燃烧的劲头。
“我们是同一棵树上的叶子,但绝不是同一片!”
不惧怕黑暗,也算是“立”起来了吧?
到40岁,怀揣新闻理想,远赴武汉办报。在新媒体崛起的情势下,挫败几乎是必然的。转投门户网站,学习做网络时代的编辑。那些趾高气扬的年轻人,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末路。焦虑和空虚,在人到中年的当儿来了。韶光盈盈,我看到的却是遍地落英……自己微胖的身躯躺在枯叶丛中,任由北风卷走。轻,生命如此轻佻,似乎都不值得留恋。44岁那一年,坐在北四环的理想大厦里,我时时惶恐。
身旁皆是成功的面影,但财富和权力,都掌握在那些人手里。身处似乎无限向上的社会,却有坠落之感。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明白生命正在拐头,自己的热度慢慢下降,已是斜阳光景。此时,方明白一个道理:太阳升起时慢,坠落时迅疾。感觉到生命的下坠,一切都在快速流逝,恰如圣人所言: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心理与生理皆有颓废之势,常常不自觉地怀疑自己的选择,从职业到婚姻……灰暗,绝望,甚至产生了某种幻觉,指望用一次恋爱拯救自己。有一段时间,笔下倾泻出诸多“春天”、“妩媚”之类的字眼,诗意的吟唱里,抒发的实为无力与迷茫。那或许是情感的最后一次挥霍。
若有《山海经》所言的“赤华黄实”之草可食,或许可达“不惑”之境界。
46岁以后,困惑才渐渐消退。我感觉,正在经历由外而内的蜕变,视线从远处收回,转而关注一己之心灵。年轻时的梦,实现与否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今是否还有新梦?这是一段惊涛骇浪的航程,躁动平息了,生成了更持久的动力。
50岁这一年,在4月和9月先后做了两次辟谷,身心为之一变。我用两个词来描述自己的状态:“神清气爽”,“身轻如燕”。从内到外,完成了人生的转变。健康的生活方式,身心和谐的日子,终于迎来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以前,不明白何谓生命的盛年,而今懂了。
不到这一天,你是不会明白的。眼前豁然开朗,迷雾散开,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了。可以做想做的任何事情,也可以随时中止;可以做成任何想做的事情,前提是需要确认那是从内心决定要做的。我不能说,一切都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但发自内心的比例越来越高。若有一天,行为皆发自内心,我也就接近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了。
时间的流逝不再让我恐惧。30岁时,感觉被时间拽着走,不免有几分慌张;40岁时,急速流逝的时间,令人沮丧;50岁以后,日子被一只大手翻开阖上,只觉得那是个诳人的假动作,它只是想让你感觉到他的存在。心在胸内,不为所动。你从容地度过每一个时日,平静又安详。
年轻时不相信自己会老,喜欢“青春不朽”之类的妙语。不知不觉却老了,对年轻和衰老自然有了心得。此刻,“老”并不是一个坏字眼,它带给我前所未有的镇静与从容:从云端徐徐落下,俯瞰自我及万物,经历过的人生画面一幅幅展开,那是另一个我。在某处应该拐弯,在某处当急刹车,在某处遇到的某人不应该疏忽……然而,一切都已定型,有各种遗憾,却并不后悔,好像在欣赏好友的人生,充满了会心。
一天天老了,但并不惧怕衰老。我渴望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刻。
更远的前方是什么?那是谁都知道的,终点站。都要下车,有人自觉,有人被赶下车而已。生不由己,但人生的体量和长度是由自己决定的。下车之前,创造更多属于生命的光华,观赏更多斑斓多姿的风景,如是而已。
短促而奇妙——人的一生本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