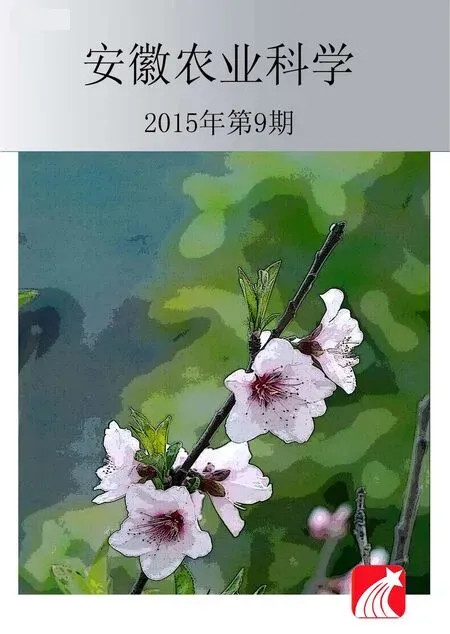水域生物监测研究进展
王美垚,管建洪
(镇江山水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江苏镇江 212125)
水域生物监测研究进展
王美垚,管建洪*
(镇江山水湾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江苏镇江 212125)
水域生物监测技术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日益广泛。综述了水域生物监测的概念与特征、常用指示生物、水域生物监测方法与应用、水域生物监测的发展前景。
生物监测;水环境;指示生物
水环境监测通常采用的传统方法是理化检测方法,通过测定水体中有害物质的浓度来评价水体水质情况。生物与其所处的周围环境是彼此相互作用的统一系统,其中一方例如水体环境中各种水质因子发生浓度等的变化都将会对生活在该水体环境中的各种生物产生直接作用。Wepener等研究发现,水体中有毒有害污染物将会对水体中的生物产生毒害作用,一方面,其会对生物体的组织产生损伤作用,进而也就影响了该生物正常存活、生长、甚至是繁殖。另一方面,各种有毒有害污染物还会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影响,严重影响到生态系统的平衡等[1]。20世纪初,Cairns和Schalie提出了“生物监测”这一概念。生物监测方法因其可以反映有毒有害污染物在生物体内的富集程度,可以直接反映环境质量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以综合反映环境质量状况而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现今已成为常用的水质监测方法[2-5]。笔者从生物监测的概念与特点、水生指示生物、水域生物监测方法和应用以及水域生物监测前景4个方面进行综述,旨在为今后更好地开展水域生物监测提供参考。
1 生物监测概念及特征
1.1 生物监测的概念生物监测指通过生物个体、种群或群落对环境质量及其变化所产生的反应和影响来阐明环境污染的性质、程度和范围,也就是通过生物体的各种反应来体现进而对环境质量水平进行评价[6]。环境与所处其中的生物彼此影响、彼此互作,是一个统一的系统。由于生物体生活在水环境中,其各种行为如正常的活动、摄食、生理代谢等会对水体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与此同时,环境也会对生活在其中的生物体产生反作用,存在于环境中的各种有毒有害物质会对生物体产生危害,会引起生物体行为的改变如正常的活动受到抑制等,甚至影响到生物体的正常的生长发育,严重者则会导致生物个体的死亡,进而导致种群结构发生变化,同时也会对整个生物群落甚至是生态系统造成毁坏性的影响。
1.2 生物监测的特征生物监测相比于理化监测,具有效率高、使用便捷等优点,具体特点如下:
1.2.1灵敏性好。 研究发现,采用理化检测方法以及精密度很好的理化检测仪器进行监测时,对于环境中存在的一些浓度极低的微量化学污染物都很难检测出,而此时采用生物监测方法,却可以很好地体现出[7]。
1.2.2连续监测性。 水体中有毒有害物质因其长期存在,因此会对相应的水体环境造成一种长期的、持续性的、累积性的影响,生活在水体中的生物也是长期受到此种污染的影响,会在其形态、活动状况甚至是繁殖等各种生理行为上有所体现,因此生物监测具有良好的连续性[8]。
1.2.3监测功能多样化。 生活在水体中的生物多种多样,不胜枚举,而其中的很多种生物对于水体中不同的有毒有害物质做出的反应或者是出现的不良症状等是不同的,因此生物监测具有十分突出的多样性。
1.2.4较强的污染物富集能力。生物体长期生活在水体中,因此对于水体中的有毒有害污染物具有长期、持续性累积作用。由于级级扩大的生物富集作用,最终水环境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将提高数十万倍,这样也就更突出地体现出了水体污染状况。
1.2.5监测成本低。 生物监测所需要的仪器相对简单,监测覆盖面积大,并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因此相对于理化检测所需的各种昂贵仪器来说,监测成本更低[9-10]。
1.2.6综合性高。水体环境中的有毒有害物质种类多样、彼此相互作用,对于水体造成的损害影响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一种综合性效应。理化检测通常所能体现的只是单一污染物的性质、浓度等,而水环境中的生物体则能更好地综合体现其对于生物体的损伤作用,因此生物监测对于水体污染状况的体现更具有综合性以及客观性[11]。
2 水生指示生物
水生态系统中包含有各种水生生物,如浮游生物、底栖动物、水生高等植物、鱼类等。当水环境遭受污染时,会对水体中各类生物个体、种群组成、结构等造成影响,因而水体中的各种生物对于水域污染具有很好的指示性作用,因此可以通过对水环境中生物种群的组成、结构、数量等进行监测,进而对水体质量作出评估。能够体现水质状况的这些水生生物又被称为指示生物[12]。
2.1 浮游生物浮游生物是水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是水环境质量的最直接体现者,其种群的组成、结构、生活状况等都会因水质状况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藻类是水体水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水环境内的有毒有害物质极容易对藻类造成损害,会对藻类的生理状况造成影响,对其正常代谢产生阻碍作用,同时还可能影响藻体的正常功能,如光合作用等,严重者则会导致藻体的生长停滞、大量死亡,影响了水生生物群落组成,严重破坏了水生态系统平衡。不同的藻类对于水体环境的要求是不相同的,例如,当水体质量较好时,水环境中的绿藻以及蓝藻数量就会较少,而当水体遭受到严重污染时,则会出现蓝藻以及绿藻数量较多的现象。因此,对水体质量进行监测时,可以通过监测是否出现了蓝藻以及绿藻来判断水体是否遭受到了较严重的污染。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监测水体中藻类生活状况、生长以及繁殖状况等来对水体质量进行评价。
2.2 高等水生植物在水域生态系统中,水生高等植物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维护水生态系统适宜的结构组成进而维护水体生态系统的健康良性循环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水环境中各种环境因子的含量等的变化会对高等水生植物的存活状况、生长、代谢以及繁殖情况等带来影响,反之水域生态系统中的高等水生植物的生命活动情况又会反作用于水体中各环境因子,进而影响水环境质量。在水体生态系统中,高等水生植物对于水体质量发挥调节作用,可以通过抑制有害藻类的生长或者是某些藻类的恶性生长以保证水体维持正常,同时有利于维持水体良好的透明度,进而维护水体质量。鉴于高等水生植物对于维护良好水质以及对于水体质量的良好体现性,其也成为水环境常用评价指标之一。
2.3 底栖动物底栖动物包括甲壳动物、软体双壳动物和水生昆虫等,由于该类生物具有加速有机质分解、蓄积有毒有害污染物促进水体净化等功能,因此底栖动物是体现以及维护水体生态系统健康的一种重要类群。由于底栖动物长期栖居于水体底部,因此水体底质状况则会对其生长以及繁殖状况等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底栖生物的独特特性,诸如生活史较长、种类繁多、活动区域较固定等,使其经常作为水环境污染的常用指示生物之一[13]。其中的软体双壳类对于水环境中尤其是底质中的有毒有害污染物具有较强的蓄积的能力,因此其经常用于水体水质状况监测[14-16]。一些生理指标例如生长因子等不仅可以体现生物体的营养状况,同时还可以反映水体环境对其造成的影响,因此其经常作为水质监测评价指标[17]。对于遭受严重污染的水体,指示生物所产生的病理学变化以及死亡率等指标也常作为评价水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18-19]。
2.4 鱼类水环境质量的改变会对鱼体的生理机能造成影响,尤其是水体中的一些有毒有害污染物会在鱼体内富集,对其机体造成损伤,因此鱼类常作为评价水体质量的指示生物之一。可以采用肉眼观察鱼类死亡率来进行判断。张云美等采用家用洗涤剂对食蚊鱼、孔雀鱼、红剑鱼等进行了急性毒性试验,研究结果表明,洗涤剂会对鱼类产生长期慢性毒性作用,进而推测出生活污水对于鱼体的毒害作用[20]。王丽萍等研究污水处理厂排出水对鱼类的影响,结果表明污水处理厂排出的废水对于鱼类具有很强的毒性作用[21]。
3 水域生物监测方法及应用
3.1 生物群落法1955年Beck首次提出采用生物指数来对水体水质状况进行评价。1960年Goodnight等提出了通过确定颤蚓类数量占全体底栖无脊椎动物数量的比例来确定水体污染程度,同时也提出以80%为参考标准,污染较严重的水体该污染指数>80%。1964年Bell等提出了判断有机污染以及有毒废水污染的方法,那就是以水生昆虫与寡毛类湿重的比例来作为评判标准。现如今,最常使用的是微型生物群落监测法(PFU法)。它是通过采集到的生物群落的结构与功能的各类参数指标来对水环境质量进行评价。使用该方法时,要根据待监测水域的特征来选择适宜的生物学指数[22-24]。PFU法准确、便捷,具有较好的重复性,可以在群落水平上体现环境因子对于生物的影响。现今已有许多学者采用PFU法对湖泊、水库等水体的生物种类、丰度等进行了监测,也应用于水体富营养化程度的评价中[25-27]。
3.2 生物蓄积监测水域环境中的双壳贝类、鱼类等对于水体中存在的有毒污染物如重金属离子、农药等具有较强的蓄积能力,在上述有害物质浓度较低时仍可以体现出其毒害性,因而常用作评价水环境质量的指示生物[28]。有学者开展了不同水质条件对于罗非鱼各组织细胞的生物毒性作用,试验结果表明对于鱼体组织细胞染毒培养时间仅为18 h[29]。也有学者开展了硫氰酸钠、二甲基甲酰胺等几种污染物对于常见淡水鱼类的急性毒性试验[30]。杨小玲等采用贻贝和牡蛎对水体进行监测,检测结果表明渤海近岸水体中生物体内丁基锡含量为23.4~162.4 ng/g[31]。
3.3 指示生物监测法水环境中指示生物的行为以及生理状态会伴随水体中各环境因子性质、含量等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可以据此变化来对水体水质状况进行判断。Wepener等采用鱼类作为指示生物来对水环境质量进行监测。研究结果表明,水环境中的污染物对鱼体生理机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有研究者将两栖动物、虾、蟹等投放到未达到致死剂量的毒性污染物的水环境中,研究结果表明,上述生物会选择主动游入清水区以防止污染物对机体造成损伤[32-33]。另外,生物的习性、摄食行为等也会因水体环境质量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3.4 生物毒性监测法由于面对水环境中的有害因子,水体中生物的行为、生理机能会作出相应反应,生物毒性监测法就是采用了该种原理而对水体质量进行监测的。通过生物毒性监测法,可以判断具有较强致毒作用的污染物为何物、其对于生物体的损伤程度如何、对于水体环境会造成何种影响等。另外,由于细菌、浮游生物、鱼类等生物的特性,因此其在水环境污染评价、有毒废水处理效果、制定污水排放标准等发挥着重要作用[34-35]。李丽娜等开展了Pb对泥螺的慢性毒性试验[36]。同时,发光细菌法[37]也是生物毒性监测的常用方法。该方法的原理是运用了某些微生物具有发光的特性,而水体中的有毒有害污染物质将对生物的发光特性产生抑制作用,抑制强度与污染物的毒性成正比。已有学者运用发光细菌法对污水毒性进行监测,证实该方法快速、简便,且具有较好的灵敏度和可靠性[38-39]。
3.5 其他方法除了上述生物监测方法外,人们还采用生物体内有害物质残留的测定、水生植物生产力的测定、以及幼虫变态试验等方法来对水域环境进行监测。水生植物生产力的测定是通过测定水生植物体的光合作用能力、固氮能力、其所含有的叶绿素含量等指标的变化来判断水域环境的污染水平。生物体内有害物质残留的测定则是根据水生生物对于有毒有害污染物具有蓄积作用的特性,采用理化检测方法来确定其体内毒物的分布以及含量,并据此来研究水域环境中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分布、含量以及转移规律[40]。变态期的幼虫相对于其生活史中的其他阶段来说,对于污染物的敏感性更高,污染物会阻碍幼虫完成变态发育,因此可通过观察其能否在附着基表面顺利变态来监测水体污染物的毒害性[41]。
4 展望
4.1 制定合理的环境质量标准,加强生物监测立法我国的生物监测起步较晚,至今还未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没有形成法定化的生物监测指标体系,这样也就大大阻碍了生物监测的发展。因此这也就需要相关部门制定统一的环境标准和生物监测指标体系,通过制定相关环境法律法规来将生物监测指标列入环境质量影响评价和水域污染源排放的监督管理工作之中。
4.2 监测方法的标准化相对于理化检测,生物监测具有更好的客观真实性,同时其也可以综合体现水域环境状况以及有毒有害污染物对于水生态系统的影响。随着水域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生物监测的重要性就越发地突显出来,其应用领域也越发广泛起来,与此同时,在理论研究上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由于技术等的限制性,例如群落监测的结果较难定量化等问题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也就使得对于生物监测方法来说,至今还未有较为系统统一的国家或是地方性环境质量标准来进行界定。所以,这也就更需要广大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要坚持不懈地致力于生物监测方法的标准化,不断开展相关性研究,以期早日确定生物监测的标准方法。
4.3 提高生物监测的技术水平生物体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分布特征,对于同一生态系统中的同种生物,如果其所居地不同,对于有毒有害污染物其会产生不同的耐受性。因此,在开展生物监测时,应充分考虑待监测生物的地域性特征来确定适宜的监测频率,这也就使得生物监测工作更具复杂性、艰巨性。在开展生物监测工作中,会遇到许多现实性问题,这也就需要我们更应在不断持续、深入开展生物监测工作的同时,努力提高生物监测技术的高效性、精准性以及灵敏性。
众所周知,理化监测具有即时性、具有相对统一的标准、较强的专一性、不受地域限制等优点。各种环境因子对于生物体的影响则具有长期性、持续性的特点,有毒有害污染物产生的不良结果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潜在性、综合性、持续性的,这些都是理化监测所无法实现的。另一方面,尽管生物监测不具有理化监测的上述优点,其是运用了生物对于有毒有害污染物所作出的相应反应,如生理行为及功能产生变化等来对水域环境质量进行评价,但是它所具有的高灵敏性、多功能性以及综合性等优点对于人们对水域环境质量作出合理的评价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今后开展水域环境质量评价工作时,要在运用生物监测的同时更好地与理化监测进行结合,以期对于水体环境质量作出更加客观、全面、精准、科学的评价。
[1] WEPENER V,VAN-VUREN JHJ,CHATIZAF FP,et al. Active biomonitoring in freshwater environments:early warning signals from biomarkers in assessing biological effects of diffuse sources of pollutants[J]. 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the Earth,2005,30(11/16):751-761.
[2] EVERAARTS JM,SLEIDERINK HM,DEN-BESTEN PJ,et al. Molecular responses as indicators of marine pollution:DNA damage and enzyme induction in Limanda limanda and Asterias rubens[J]. Environ Health Perspect,1994,102(12):37-43.
[3] CAJARAVILLEM P,BEBIANNO M J,BLASCO J,et al. The use of biomarkers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pollution in coastal environments of the Iberian Peninsula:a practical approach[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00,247(2/3):295-311.
[4] 孔繁翔.环境生物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38-140.
[5] 吴邦灿,费龙.现代环境监测技术[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239-240.
[6] 万本太.中国环境监测技术路线研究[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311-313.
[7] 李江平,李雯指示生物及其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J].云南环境科学,2001,20(1):51-54.
[8] 徐希莲.水生昆虫与水质的生物监测[J].莱阳农学院学报,2001,18(1):66-70.
[9] 张增光.水生生物在水质监测中的应用[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4,14(7): 150-151.
[10] 赵怡冰,许武德,郭宇欣.生物的指示作用与水环境[J].水资源保护,2002(2):11-14.
[11] 沈惠麒,顾祖维,吴宜群.生物监测理论基础及应用[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6:338-346.
[12] 董铭洪.环境污染与生态修复[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56-60.
[13] 刘建康.高级水生生物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241-259.
[14] GOLDBERG E D,BOWEN V T,FARRILNGTON JW,et al.The mussels watch[J].Enviromental Conservation,1978(5):101-125.
[15] GRANBY K,SPLIID N H.Hydrocarbons and organochlorines in common mussels from the Kattegat and the Belts and their relation to condition indices[J]. Mar Pollut Bull,1995,30:74-82.
[16] HENDRIK SA,J PIETERSH,DE-BOER J. Accumulation of metals,polycyclic(halogenated) aromatic hydrocarbons and biocides in zebra mussel and eel from the Rhine and Meuse River[J]. Environ Toxicol Chem,1998,17(10):1885-1898.
[17] NICHOLSON S. Cyt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biomarker responses from green mussels,Pernaviridis(L.)transplanted to contaminated sites in Hong Kong coastal waters[J]. Mar Pollut Bull,1999,39(1/12):261-268.
[18] NASCIC,DAROS L,CAMPESAN G,et al. Clam transplantation and stress-related biomarkers as useful tools for assessing water quality in coastal environments[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1999, 39(12):255 -260.
[19] SCHMIDT H,BERNET D,WAHLI T,et al. Active biomonitoring with brown trout and rainbow trout in diluted sewage plant effluents[J]. Journal of Fish Biology,1999,54(3):585-596.
[20] 张云美,潘永全,韩志刚,等.家用洗涤剂对红剑鱼、孔雀鱼和食蚊鱼的急性毒性实验观察[J].四川动物,2005,24(2):213-215.
[21] 王丽萍,张雁秋,徐正华.污水处理厂出水对鱼类的影响的实验研究[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2,31(3):311-314.
[22] 徐希莲.水生昆虫与水质的生物监测[J].莱阳农学院学报,2001,18(1):66-70.
[23] 程英,吕琳,雒彦军.应用水生生物监测水污染[J].黑龙江环境通报,2001,25(1):79-80.
[24] 郭沛涌,林育真.应用微型生物监测水质污染[J].山东环境,1998(1):19-20.
[25] ARHONDITSIS G,KARYDIS M,TSIRTSIS G. Analysis of phytoplankton community structure using similarity indices a new methodology for discriminating among eutrophication levels in coastal marine ecosystems[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3,31(5):619-632.
[26] 李凤超,沈韫芬,刘存歧,等.应用原生动物群落评价枯水期白洋淀的水质现状[J].生态学杂志,2005,24(7):785-789.
[27] 阮惠扳,赵汝浓,黎康汉.周丛原生动物群落监测水污染的研究[J].山大学学报论丛,1995(3):56-60.
[28] 沈治蕊,卞小红,赵燕,等.南京煦园太平湖富营养化及其防治[J].湖泊科学,1997,2(4):377-380.
[29] 李素文,任风玉,张鸿卿.罗非鱼肝细胞作为环境污染生物监测指标的初步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31(1):115-118.
[30] 张彤,金洪钧. 用八种淡水鱼类监测四种污染物的急性毒性[J]. 中国环境监测,1997,13(1):31-34.
[31] 杨小玲,杨瑞强,江桂斌. 用贻贝、牡蛎作为生物指示物监测渤海近岸水体中的丁基锡污染物[J].环境化学,2006,25(1):88-91.
[32] STANSLEY W,ROSCOE D E,WIDJESKOG L.Effects of lead-contaminated surface water from a trap and skeet rang on frog hatching and development[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1997,96(1):69-74.
[33] HOPKINS W A,ROE J H,CONGDON J D,et al. Nondestructive induces of trace element exposure in saquamata reptiles[J].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01,115:1-7.
[34] 张俊秀.环境监测[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28-31.
[35] 许敏.微囊藻水华毒素异构体的年度变化及其环境因子的分析[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2.
[36] 李丽娜,陈振楼,许世远,等.长江口滨岸潮滩底栖泥螺受铅污染的急性毒理试验[J].海洋湖沼通报,2005(2):88-92.
[37] THOMULKA KW,MCGEE DJ,LANGE JH. Use of bioluminescent bacterium photobacterium phosphorous to detect potentially biohazardous materials in water[J].Bull Environ Contam&Toxicol,1993,51(4):538-544.
[38] 张秀君,韩桂春.发光细菌法监测废水综合毒性[J].辽宁城乡环境科技,1998,18(6):19-21.
[39] 孙扬,李永峰,韩博.水污染生物监测现状[J].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8,22(2):152-155.
[40] 李慧蓉.生物监测技术及其研究进展[J].江苏石油化工学院学报,2002,14(2):57-60.
[41] DIAL N A,BAUER C A. Teratogenic and lethal effects of paraquat on developing frog embryos(Ranapipiens)[J]. Bull Environ Contam &Toxico1,1984,33(5):592-597.
Research Advance of Biological Monitoring on Water Environment
WANG Mei-yao, GUAN Jian-hong*
(Zhenjiang Shanshuiwan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Zhenjiang, Jiangsu 212125)
The application of biological monitoring on water environment is more and more widely. The article introduces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 of biological monitoring on water environment, biological indicators, method and application of biological monitoring on water environment and prospect of biological monitoring on water environment.
Biological monitoring; Water environment; Indicator organism
王美垚(1984-),女,天津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渔业生态环境与资源。*通讯作者,高级工程师,从事水产养殖与生态研究。
2015-02-06
S 181.3
A
0517-6611(2015)09-257-04